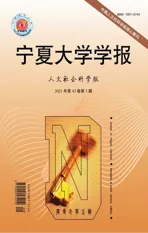道义相亲:苏颂与“三苏”关系考论
2021-12-25刘炳辉
刘炳辉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关于苏颂与“三苏”叙宗盟的时间,有学者将其定在嘉祐五年二月。清人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嘉祐五年庚子》即持此说:“(二月)十五日抵京师,寓于西冈,苏颂来叙宗盟。诰案:此文(指《荐苏子容功德疏》)作于建中靖国元年辛巳归常之时,计以四十余年,乃嘉祐庚子重入京师事也。苏颂年八十二卒,当生于真宗天禧庚申,时年已四十一,以《东都事略》考之,乃除馆阁校勘时也。”[1]今人颜中其先生《苏颂与苏轼》一文亦认为“从二月叙宗盟,到当年秋天,苏颂与三苏父子在西冈作为近邻相处,约有八个月的时间。”[2]在《苏颂年谱》中,颜先生又重申这一说法[3]。笔者认为,两个家族是否“叙宗盟”,以及时间和地点还有讨论的空间。基于此,本文将展开两家关系的探讨和论述。
一 两家叙宗亲始于何时
苏洵之兄苏涣,始字公群,晚字文父,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官至提点刑狱,是眉山苏氏政治上发迹的一个信号。然而苏洵屡屡不能中举,不能为苏氏家族崛起助力。至和二年(1055年),苏洵作《苏氏族谱》,追溯苏氏之先:“出自高阳,而蔓延于天下。唐神龙(705—707年)初,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是始。”[4]长史味道即苏味道,唐代赵州栾城人,与杜审言、崔融、李峤并称“文章四友”。神龙初,苏味道“以亲附张易之、昌宗,贬授眉州刺史。俄而复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未行而卒”[5]。苏洵不仅追索眉州苏氏之源,而且建立苏氏谱系,目的正是为普通的苏姓庶族地主家庭崛起造势。后来,苏辙将文集命名《栾城集》或许也与此有关。
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携苏轼、苏辙到成都拜谒张方平,张方平荐苏氏父子于欧阳修。次年,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到达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6]是年,欧阳修知贡举,痛击“太学体”,苏氏兄弟双双中举。苏洵虽未能中举,但是他的文章颇受韩琦、欧阳修的赏识,父子三人一时名动天下。本应在京城大放异彩的苏氏父子,却因苏洵之妻程氏去世而匆匆返回蜀中。嘉祐五年二月十五日,苏洵、苏轼和苏辙再次来到汴京,租住在西冈。苏轼《与杨济甫书》对此有明确记载:“前月半已至京,一行无恙……见在西冈赁一宅子居住,恐要知悉。”[7]这封信作于三月初,杨济甫是苏轼的同乡。苏氏父子再次来到汴京,嘉祐二年的轰动效应早已过时,为了尽快打开局面,在朝中已有些名气和地位的同姓苏颂自然成了苏氏父子刻意结交的对象。
与亟待崛起的眉州苏氏相比,同安苏氏可谓家世显耀。从唐末、五代到北宋,苏颂家世代都是仕宦之家,祖父苏仲昌,在仁宗时官任复州太守,父亲苏绅在仁宗时官至翰林侍读学士。皇祐五年(1053年),苏颂除馆阁校勘,至嘉祐五年(1060年),一直在京城,凡九年未迁,是年秋才差知颍州。
苏轼《感旧诗·并叙》云:“嘉祐中,予与子由同举制科,寓居怀远驿,时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8]王、颜二先生认为两家“叙宗盟”在嘉祐五年二月,然而刚刚抵达京城就与同安旺族苏颂家搭上关系似乎有些牵强。据孔凡礼先生考证,是年六月,苏轼他们已搬离西冈,“轼、辙寓居怀远驿”[9]。怀远驿是北宋接待番使的地方,“辛巳,置怀远驿于汴河北,以待诸番客使”[10],“掌南番交州,西番龟兹、大食、于阗、甘、沙、宗哥等国贡奉之事。”[11]苏轼、苏辙为应制科而寓居怀远驿,苏洵此时住在雍丘,三人都已远离西冈。如此一来,两家“叙宗盟”的时间应该提前,缩短在二月至六月,双方只有短暂的四个月的交往时间。在长诗《感事述怀》中,苏颂自注云:“予初置京师西冈宅,甚隘陋,罢相日,二府诸公见过,以为不称相第。”[12]其孙苏象先所撰《丞相魏公谭训》也有相关记载:“祖父待试时,曾祖居西冈,相远十余里”[13],“元祐丙寅,祖父为天官尚书,居西冈杨崇训之故第。”[14]按照苏颂自注和苏象先记载,苏绅曾经住过西冈,苏颂购置杨崇训西冈之宅在元祐元年(1086年)。因此,苏颂所谓“罢相日,二府诸公见过”,以及苏象先所说“二府诸公相过,苏黄门”[15]云云,应指苏颂罢相后苏轼、苏辙去他府上劝慰,事在元祐八年(1093年),非嘉祐五年事,也不是去“叙宗盟”。事实上,目前我们只能肯定庆历二年(1042年)前后,苏颂为科考曾寓居西冈,并未找到嘉祐五年初,他也居住在西冈的证据,也就是说“二月叙宗盟”的说法并不可靠。退一步来讲,即使嘉祐五年二月“三苏”租住在西冈的时候,苏颂也住在西冈,二月至六月,短短四个月的时间,让两个向无往来的家族见面即“叙宗盟”,显然也是过于仓促。
那么两家建交究竟始于何时?我们只能从双方文集中抽丝剥茧。元祐二年,苏颂作《次韵刘叔贡舍人从驾》诗云:“自叹荆枝半凋落,若论宗戚亦霑荣。”[16]苏子容无疑是比较注重宗族亲戚之间的联络往来,在自注中他回忆了两家“叙宗契”之事:“某早蒙子瞻昆仲叙宗契,贡父亦舅氏姻家,因尝通书。”此番话透露出两点重要信息:其一,两家只是“叙宗契”,也就是认过宗亲、连过家谱,并未“叙宗盟”。其二,强调此事由苏轼、苏辙二人倡导,说明当时苏洵并不在场,而且其《嘉祐集》也未提及此事,很可能根本不知此事。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苏颂双方早年曾“叙宗契”,并未明确具体时间。苏轼《荐苏子容功德疏》云:“伏以自昔先君以来,常讲宗盟之好。俯仰之间,四十余年。”[17]苏颂卒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五月,苏轼此文作于之后。前推四十年,苏轼所谓两家“常讲宗盟之好”当在嘉祐五年二月“三苏”到达汴京之后。然而,“早蒙”和“四十余年”都是非常模糊的时间,而且苏颂说“叙宗契”,苏轼讲“宗盟之好”,两人对叙宗亲的看法并不一致。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苏洵对此事的态度。其《族谱后录》云:“眉之苏,皆宗益州长史味道;赵郡之苏,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风之苏,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内之苏,皆宗司寇忿生”[18]。虽然几百年前是一家,但是苏洵强调渊源有自,眉州苏氏与同安苏氏所宗不同。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去世,苏颂作挽诗《苏明允宗丈》,其二云:“常论平陵系,吾宗代有人。源流知所自,道义更相亲。痛惜才高世,赍咨涕满巾。又知余庆远,二子志经纶。”[19]在挽诗中,苏颂称苏洵为“宗丈”,并赞扬苏轼、苏辙“志经论”,前途无量,说明此时他已认下了这门宗亲,并且对两家关系有“道义相亲”的准确定位。苏洵强调源自苏味道,苏颂坚持叙“平陵系”“宗契”,苏轼则强调“宗盟之好”,三人的说法并不一致,因此,所谓“二月苏颂来叙宗盟”,乃至两家“叙宗盟”的说法都不可靠。况且“宗盟”除了宗亲关系,还有攻守同盟的责任,远比“宗亲”牢靠。然而纵观苏颂与“三苏”之交往,双方并未表现出同盟关系,具体论述将在下文展开。
让我们回到之前讨论的叙宗亲话题。既然苏颂《次韵刘叔贡舍人从驾》诗和苏轼《荐苏子容功德疏》都未明确两家认宗亲的具体时间,那么两家叙宗亲有可能会发生在何时呢?我们不妨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首先,从时机来看,嘉祐五年二月,“三苏”租住在西冈。六月,苏轼、苏辙已经搬离西冈,寓居怀远驿,苏洵住在雍丘。九月,苏颂差知颍州。之后,双方各奔东西,一直没有合适的时间和机会。其次,在嘉祐五年至治平三年这七年时间,除了治平三年,苏洵去世,苏颂有挽词外,两个家族之间并无诗文往来。双方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文字往来,其实始于苏洵去世,苏颂的祭文。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苏洵去世,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在朝中力量尚显弱小,非常需要在京任职三司度支判官的苏颂施以援手。面对才华横溢的苏氏兄弟之邀,苏颂也是乐于接纳。于是,有着天然血缘关系的同安苏氏和眉山苏氏,认宗亲、连宗谱之事水到渠成。
二 循序渐进的关系
在苏颂《苏魏公文集》和现存苏洵《嘉祐集》中,我们找不到两人之间的诗文唱和往来,只能从苏颂与苏轼、苏辙的交往之中,逐步把握和定位两个家族之间的关系。
(一)欧阳修的纽带作用
我们梳理苏颂与苏轼、苏辙之间的关系,自然绕不开三人共同的恩师欧阳修。
苏颂之孙苏象先曾明确记载欧阳修为苏颂座师:“祖父别试南庙,欧公为考官。”[20]《欧阳文忠公二首》其二云:“早向春闱遇品题,继从留幕被恩知。何期濲水缄书日,正是椒陵梦奠时。感旧绪言犹在耳,怆怀双泪谩交颐。谁将姓字题延道,公立门生故吏碑。”[21]这首挽诗倾注了苏颂对座师欧阳修深切的哀悼之情,感人肺腑。先是“春闱”,继而欧阳修任南京留守,苏颂为推官,师生相处颇是融洽。长诗《元祐癸酉秋九月蒙恩补郡维扬》,再次重申了始终不渝的师生情:“予举进士日,欧阳公主文衡,误见赏拔。后留守宋都,予在幕府。自尔相知尤厚,始终不替。”[22]欧阳修对苏颂也是寄予厚望,赏识有加:“尝谓余曰:‘爱君至诚,喜得共事。故事事奉诿,必不惮烦也。’又尝亲书余考牒曰:‘才可适时,识能虑远。珪璋粹美,是为邦国之珍;文学纯深,当备朝廷之用’”[23]。
巧合的是,苏轼和苏辙也是欧阳修的学生。欧阳修不仅仅是借以罢黜华而不实的“太学体”,而是真正欣赏苏轼的才学和文章,有意培养苏轼为下一任文坛盟主,接过古文运动的大旗。《举苏轼应制科状》云:“新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其行业修饬,名声甚远。”[24]对苏轼评价如此之高,在欧阳修奖掖后进中独树一帜。其《与梅圣俞书》对苏轼的喜爱更是情不自禁:“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轼所言乐,乃某所得深者尔,不意后生达斯理也。”[25]面对欧阳修的倾力栽培,苏轼也是不负众望,终成宋学集大成者。他曾评价欧阳修之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26]其怀念欧阳修《西江月》(平山堂)词云:“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27]睹物思人,情真意切。苏辙《龙川别志序》称:“欧阳公永叔、张公安道皆一世伟人”[28]。“伟人”一词,足见心中欧阳修地位之高。正是通过同一恩师欧阳修这层关系,苏颂与苏轼、苏辙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固。
(二)缓慢发展的熙宁年间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作《荐苏子容功德疏》,简要回顾了两个家族的交往:“伏以自昔先君以来,常讲宗盟之好。俯仰之间,四十余年。在熙宁初,陪公文德殿下,已为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际,缀公迩英阁前,又为五学士之首。虽凌厉高躅,不敢言同;而出处大概,无甚相愧。敢缘薄物,以荐一哀。伏惟三宝证明云云。”[29]熙宁元年(1068年)苏颂任知制诰。十二月,苏轼、苏辙从蜀中返京。次年,苏颂拜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同知审刑院。直到熙宁四年(1071年),苏颂出知婺州(今浙江金华),苏轼通判杭州,这段同殿为官的交集才告一段落。
到达杭州后,苏轼游孤山而作《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苏辙有和诗《次韵子瞻游孤山访惠勤惠思》。离杭州不远、身在婺州的苏颂也有《次韵苏子瞻学士腊日游西湖》相和:“腊日不饮独游湖,如此清尚他人无。唱酬佳句如连珠,况复同好相应呼。君尝听事嗟罪孥,虽在乐国犹寡娱。是社稷臣鲁颛臾,直道自任心不纡。最爱灵山之僧庐,彼二惠者清名孤……君怀经济才有余,名声妖孽惩颜蘧。且来山林寻遁逋,更玩四营兼参摹。”[30]在诗中,苏颂称赞苏轼腊日游西湖的雅兴,对他怀才不遇颇为惋惜。苏轼随即《再和》:“君才敏赡兼百夫,朝作千篇日未晡。朅来湖上得佳句,从此不看营丘图。知君箧椟富有余,莫惜锦绣偿菅蘧。”[31]苏轼称苏颂“才敏赡兼百夫”,“箧椟富有余”,要苏颂莫要谦虚,常来唱和。苏颂之孙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还记载,两人曾在金华见过面:“祖父与东坡同在金华,因论作赋之方。”[32]虽然这段时间,苏颂依然称苏轼为“苏子瞻学士”,两人间的唱和也仅此两首,但是苏颂对苏轼无疑是颇为欣赏:“祖父尝云:‘苏子瞻有盛名而退无自矜之色,此为过人。’”[33]遗憾的是,这一时期苏颂与苏辙并无诗文唱和往来。正是靠着苏颂与苏轼之间的相互欣赏,两个家族的关系正在缓慢推进。
(三)急剧升温的元丰年间
元丰二年(1079年),苏颂赴御史台讯鞫:“壬子(七月),诏大理寺鞫吕氏为陈世儒请求事移御史台,内命官两问不承,即听追摄,两省以上取旨。中丞李定言,已遣王彭年就濠州劾苏颂,乞令彭年逮颂诣台对狱,余当追命官,除两省外,依勘大学公事已得指挥。”[34]在组诗《元丰己未三院东阁作》中,苏颂对此事有过详细描述:“言者以为推劾不尽,诏移大理。而理官推迹陈氏姻党干求府政,纵出重辟事,下御史推求。己未岁,予自濠梁赴台讯鞫,卒不涉干求之迹,而大理反有传致之状,虽蒙辩证,听命久之,不得出。邑邑不已,作诗十篇记一时事,非欲传之他人,但以示子侄辈,使知仕宦之艰耳。”[35]苏颂必须听命朝廷,无法自主的命运,郁闷却又不能说,只能诉诸笔端,感叹仕宦艰难。同年七月,著名的“乌台诗案”轰动朝野:“诏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时定乞选官参治,及罢轼湖州,差职员追摄。既而上批,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追摄,又责不管别致疏虞状,其罢湖州朝旨,令差去官赍往。”[36]黄庭坚所谓“苏子瞻文章好骂”,最终给苏轼带来了牢狱之灾。先是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言苏轼谤讪朝政,御史台又搜集到《钱唐集》作证。八月,中使皇甫遵从湖州拘捕苏轼回京。
《苏颂传》云:“意颂前次请求,移御史台逮颂对。御史曰:‘公速自言,毋重困辱。’颂曰:‘诬人死,不可为已,若自诬以获罪,何伤乎?’即手书数百言伏其咎。帝览奏牍,以为疑,反复究实,乃大理丞贾种民增减其文傅致也,由是事得白。”[37]代表公正谏言的御史台,竟然成了引诱冤假错案的温床,苏颂对此无能为力,只能予以揭露和批判:“却怜比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38]尽管自己的遭遇已是匪夷所思,但是一墙之隔的苏轼所受的折磨,更令苏颂担忧。其诗《己未九月予赴鞫御史闻子瞻先已被系予昼居三院东阁而子瞻在知杂南庑才隔一垣不得通音息因作诗四篇以为异日相遇一噱之资耳》,对于两个家族的情谊以及他和苏轼的共同遭遇,进行了深刻反思,感情真挚,动人心魄。其三云:“源流同是子卿孙,公自多才我寡闻。谬见推称丈人行,应缘旧熟秘书君。文章高绝诚难敌,声气相求久益勤。”其四云:“近年出处略相同,十载邅回我与公。杭婺邻封迁谪后,湖濠继踵絷维中。诗人嗫嗫常多难,儒者凄凄久讳穷。他日得归江海去,相期来访蒜山东。”[39]苏颂九月到达御史台,此时苏轼已因“谤讪朝政”先被拘系。“才隔一垣不得通音息”,同病相怜的处境和心境,一下子将他与苏轼的距离拉近,苏颂因作诗四篇,“以为异日相遇一噱之资耳”。诗人重申同宗同气连枝的愿望,既对“公自多才我寡闻,谬见推称丈人行”的过往进行回溯,也对两人连遭贬谪的境遇加以总结,最后约定“他日得归江海去,相期来访蒜山东”,两人的情谊得以升华。这四首诗,既是苏颂对苏轼的评价,也是他与苏轼、苏辙道义相亲、患难与共情谊的准确反映。
熙宁八年(1075年),滕元发牵涉赵世居谋反案;元丰二年,苏颂赴鞫御史台和苏轼“乌台诗案”的遭遇,现在来看,并非单个的意外事件,而是皇权日益加强的表现,面对渐变的复杂朝局,文人士大夫理应自觉反省。事实上,在《与滕达道六十八首》第八,苏轼曾敏锐感觉到时局的变化,也流露过反对“新法”的悔意,而滕达道是他的密友,内容应该可信:“盖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40]关于苏轼这封包含悔意的信究竟写于“元丰前,还是元丰后”,学界今无定论。朱刚师《苏轼与滕达道尺牍考辨》一文论断比较符合实情:按《苏轼外集》编次,将“忏悔书”系于熙宁十年至元丰元年徐州时期,不失合理性:“今日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可以理解为苏轼对“宋神宗改变年号,亲自秉政,带来政治环境显著变化”的明确意识[41]。
从御史台出来,苏颂和苏轼各奔东西。这一时期,苏轼有《与苏子容四首》,第一和第四写作时间不定,二和三大致可考。其二云:“适人见言,宗叔坠马,寻遣人候问门下,又知有稍损,不胜忧悬,又不敢便上谒。家传接骨丹,极有神验,若未欲饮食,且用外帖,立能止痛、生肌、正骨也。匆匆奉启,不宣。”[42]听闻“宗叔”苏颂坠马,苏轼当即差人问候,并送上家传接骨丹,十分忧心。信中提到“不敢便上谒”,行动受限,应作于元丰三年(1079年)至六年(1083年)苏轼贬谪黄州时期。这是两家叙宗谱后,苏轼唯一一次按辈分称呼苏颂为“宗叔”。其三云:“向来罪谴皆自取,今此量移之命,已出望外。重承示谕,感愧增剧。以久困累重,无由陆去,见作舟行,沂洛夏末可到也。公所苦,想亦不深,但庸医不识,故用药不应耳。蕲水人庞安时者,脉药皆精,博学多识,已试之验,不减古人。度其艺,未可邀致,然详录得疾之因,进退之候,见今形状,使之评论处方,亦十得五六。可遣人与书,庶几有益。此人操行高雅,不志于利,某颇与之熟,已与书令候公书至,即为详处也。更乞裁之,仍恕造次。”[43]元丰七年(1084年)正月,“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苏轼言,汝州无田产,乞居常州。从之。”[44]“量移之命”,即指此。“见作舟行,沂洛夏末可到”,当是作于赴常州的路上。“沂河,自山东沂州城西流,至下邳西南入泗达于淮。洛水自定远县西白望堆入寿州界,至新村南十五里入淮。”[45]又云“公所苦,想亦不深”,既安慰苏颂,又为他介绍医生庞安时,并“与书令候公书至,即为详处”,无微不至。
赴任常州,途经润州,苏轼作《苏子容母陈夫人挽词》,表达了对两家情谊的珍惜:“苏、陈甥舅真冰玉,正始风流起颓俗。夫人高节称其家,凛凛寒松映修竹。鸡鸣为善日日新,八十三年如一晨。岂惟家室宜寿母,实与朝廷生异人。忘躯徇国乃吾子,三仕何曾知愠喜。不须拥笏强垂鱼,我视去来皆梦尔。诵诗相挽真区区,墓碑千字多遗余。他年太史取家传,知有班昭续《汉书》。”[46]挽词情真意切,不仅对苏颂母亲“凛凛寒松映修竹”的高节予以歌颂,对不知喜愠的苏颂也是赞誉有加,推崇之至。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卷六记载:“祖父元丰六年自吏部侍郎丁曾祖母忧归润,象先侍行。”[47]宋人庞元英《文昌杂录》记载:“元丰甲子六月,吏部侍郎苏颂以忧去官”[48]。元丰甲子即元丰七年(1084年)。庞元英是欧阳修的次女婿,与苏轼同时代人,所记应该可靠。三者相考,则苏象先所记元丰六年“丁曾祖母忧”恐误。可见苏轼这首《陈夫人挽词》不仅对苏颂家族意义非凡,其史料价值也非常重要。苏轼又有《与苏子容二首》,其一写作时间不定,孔凡礼先生《苏轼文集》题注“离黄州”[49]。苏颂元丰二年知沧州,四年,召回京师权派吏部,至七年六月丁母忧去职。苏轼元丰二年底出狱,至元丰六年底,一直贬居黄州。两人不曾见面,系于离黄州恐不妥。其二云“某欲径往毗陵”,当作于元丰七年(1084年),赴常州途中。
正是元丰二年同拘御史台的生死经历,使苏颂与苏轼的关系急剧升温,两人诗文往来频繁。
(四)元祐年间
元祐元年(1086年)至元祐七年(1092年),苏颂一直在朝任职。七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宰相)。苏轼、苏辙先后在朝廷任翰林学士。元祐年间,朝堂有朔党、洛党和蜀党之争,苏轼的两次策题和扬州题诗之谤,即是表现之一。苏象先说“祖父在元祐间,不取诸公太纷纭,常云:‘君长,谁任其咎耶?’”[50]苏颂之所以能在元祐以后愈演愈烈的党争中独能保全,正是因为苏颂一生不立党援。因此,与苏轼、苏辙同朝为官,苏颂与苏氏兄弟继续保持道义上的援助,双方的诗文往来也归于平淡。三年,苏轼作《卧病逾月,请郡不许,复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锁院,是日苦寒,诏赐官烛法酒,书呈同院》,苏颂有诗《次韵子瞻锁院赐酒烛》相和。五年,苏轼在杭州作《送李陶通直赴清溪》,还曾提及苏颂,诗云:“忠文、文正二大老(司马温公、范蜀公,君之师友),苏、李、广平三舍人(苏子容、宋次道与先公才元,熙宁中封还李定词头,天下谓之三舍人)。”[51]八年,苏颂因论贾易复官事,遭杨畏和来之邵弹劾而罢相。《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李清臣与许将小简云:‘容、功之罢,虽言者乘之,殆别有谓,非面叙莫悉也。’当考。”[52]又:“邵伯温云:杨畏攻刘相,出(初)意谓必相苏辙,朝廷乃以苏颂为右仆射。畏又与来之卲言苏相留贾易诏命不下。苏相遂罢。不知清臣所称有为是何事,岂即邵伯温所记杨畏反复攻击,为苏辙地乎?当考。”[53]《福建通志稿·苏颂传》载:“侍御史杨畏欲引苏辙为相,遂与监察御史来之邵劾颂稽留诏命”[54]。时有传言说苏颂罢相与苏轼、苏辙兄弟有关。然据苏象《丞相魏公谭训》,苏颂罢相是对事不对人,与苏轼、苏辙无关,比较合理:“二府诸公相过,苏黄门云:‘莫须翼日见上,少叙陈然后求罢,贵全进退之礼。’国史《本传》言‘与同列议事不合,锐然求退’云云。然所言数人者皆名贤,观过知仁,可以无愧矣。泰陵既亲政,畏等首论二苏,不遗余力,相继南迁,权舆于杨氏也”[55]。
除了制诰公文,苏辙与苏颂几乎没有诗文唱和,两人的关系一直比较平淡。元祐二年,苏辙作《韩干三马》诗,苏轼有和诗《次韵子由书李伯时所藏韩干马》,苏颂也有诗《次韵苏子瞻题李公麟画马图》。是年,苏颂又有《重次前韵奉酬子由子开叔贡三舍人二首》,同时奉酬三舍人。两次和诗,苏辙均无回应。三年,苏颂“为廷试详定,得李注元发,欲以第一人,苏黄门诸公不悦”[56]。苏黄门即苏辙,可见他与苏颂的私交确实一般。其《龙川别志序》称“苏子容、刘贡父博学强识,亦可以名世,予幸获与之周旋”[57],算是他对苏颂的正面评价。
三 “道义相亲”“无甚相愧”的合作关系
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云:“祖父尝言:‘吾平生未尝以私事干人,至于陛立奏对,惟义理之言。故历事四朝,中间虽迁谪,不愧于观过矣。’”[58]正是“不以私事干人”的处世原则,决定了苏颂与苏轼、苏辙不会太亲密,也不会疏远。《苏明允宗丈》挽诗所谓:“源流知所自,道义更相亲”,宗亲和道义正是苏颂对他与三苏关系的界定。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贬谪惠州,路经扬州见了苏颂,这大概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建中靖国元年,苏颂去世,苏轼作《荐苏子容功德疏》云:“虽凌厉高躅,不敢言同,而出处大概,无甚相愧”[59],有共同的利益,也有分歧,两家四十余年的情谊至此画上了句号。回溯两个家族的交往,“三苏”这边,多以苏轼为代表。双方求同存异,互有主动,既有密切联系,也有平淡如水,远未达到攻守同盟的境界。两家之间的诗文往来,无疑是最好的证明。总而言之,“道义相亲”“无甚相愧”的合作关系,应该是苏颂与三苏关系最中肯、贴切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