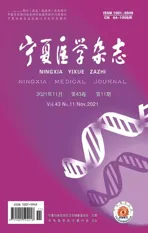骨性I类青少年患者拔牙与非拔牙矫治后上气道形态及舌骨位置的变化
2021-12-09樊永杰
赵 恬,白 晶,张 佐,樊永杰
上气道(upperairway)分为鼻咽、腭咽、舌咽、喉咽,其主要生理功能包括呼吸、发声以及吞咽[1]。咽气道是一个由肌肉组织构成的软性管道,本身具有较大的可塌陷性[2]。而不同治疗方案的设计,可能会引起患者面型的变化、口腔体积与牙弓长度的改变以及口周软硬组织的改建,从而引起上气道体积改变。

1 资料与方法

1.2 治疗方法:所有患者选用MBT直丝弓矫治技术进行矫治,拔牙组分为排齐整平牙列、关闭拔牙间隙、精细调整3个治疗阶段。第一阶段使用镍钛丝进行排齐整平牙列;第二阶段使用0.019×0.025 mm不锈钢丝滑动法关闭拔牙间隙,设计中度支抗;第三阶段根据个体问题针对性进行精细调整。非拔牙组病例分为排齐整平牙列、精细调整2个阶段。所有拔牙组病例选用高转矩托槽,非拔牙组病例选用标准转矩托槽。
1.3 数据获取:所有头颅(定位)侧位片均由同一位技师使用同一机器拍摄。拍摄要求:直立位,眶耳平面平行于地面,牙尖交错位,双唇放松,自然闭合,不吞咽,不咀嚼,呼气末时屏住呼吸拍摄。测量方法应用Uceph软件(Win标准版)进行定点及头影测量分析,选择自定义分析法,加入气道测量项目。所有测量项目均由同一医师在软件上进行定点测量,并由其他2 名研究人员复查2 次,每个项目重复测量3次,取其平均值。2 次测量误差超过1 mm 或1°时则重新测量与定点。
1.4 头影测量标志点及测量项目:根据曾祥龙、郭涛[3-4]等学者的研究,本研究的测量标志点及测量项目见表1-表2及图1(目录后)。

表1 测量标志点

2 结果
2.1 正畸治疗前垂直骨面型对上气道及舌骨的影响:骨面型垂直为均角的患者30例,高角21例,低9例。正畸治疗前均角、高角、低角的患者各项上气道及舌骨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2 气道(及舌骨)测量指标

表3 垂直骨面型为均角、高角、低角患者治疗前上气道及舌骨位置指标
2.2 拔牙组患者治疗前后比较:拔牙组矫治前后上气道形态及舌骨位置比较发现,所有指标在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拔牙组中PNS-R、SPP-SPPW、H-MP、H-FH、H-S项目略有增大,PNS-UPW、V-LPW、TB-TPPW、U-MPW项目略有减小,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非拔牙组矫治前后上气道形态及舌骨位置比较,所有指标在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非拔牙组中PNS-R、V-LPW、H-FH、H-S项目略有增大,H-MP 变化不明显,SPP-SPPW、PNS-UPW、TB-TPPW、U-MPW项目略有减小,见表4。
2.3 拔牙组与非拔牙组患者治疗前后及组间比较:拔牙组与非拔牙组患者矫治后上气道形态及舌骨位置比较发现,所有测量项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拔牙组与非拔牙组相比,在治疗后PNS-R、PNS-UPW、TB-TPPW、U-MPW、V-LPW、H-S项目略有减小,SPP-SPPW、H-MP、H-FH项目略有增大,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5。

表4 拔牙组与非拔牙组治疗前后上气道形态及舌骨位置的变化差异比较
2.4 不同垂直骨面型患者正畸治疗前后比较:垂直骨面型为均角、低角的患者正畸治疗前后比较,所有测量项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垂直骨面型为高角的患者正畸治疗前后比较 H-FH项目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测量项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6。

表5 拔牙组与非拔牙组治疗后上气道形态及舌骨位置的变化差异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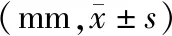
表6 垂直骨面型为均角、高角、低角患者正畸治疗前后上气道形态及舌骨位置的变化差异比较

测量项目治疗前治疗后t值P值U-MPW 均角10.96±2.6510.03±3.380.87>0.05 高角11.84±2.9910.03±4.540.9>0.05 低角11.97±3.3511.57±1.760.275>0.05V-LPW 均角15.39±3.7515.23±3.810.093>0.05 高角16.76±2.4816.60±4.220.092>0.05 低角16.97±3.4515.93±4.141.45>0.05H-MP 均角12.98±4.3411.91±4.570.508>0.05 高角8.61±3.538.73±2.86-0.061>0.05 低角8.20±6.088.13±6.810.013>0.05H-FH 均角82.03±8.0782.35±18.28-0.043>0.05 高角76.86±6.0188.07±8.17-5.59<0.05 低角76.73±5.5184.30±8.34-2.853>0.05H-S(Hor) 均角5.93±5.016.26±5.60-0.128>0.05 高角7.29±7.4313.23±8.76-1.481>0.05 低角11.83±5.696.57±3.782.502>0.05
3 讨论
本次研究了垂直骨面型为高角、均角和低角的青少年骨性I类患者。ZHONG等[5]指出,骨性Ⅰ类的低角、均角到高角儿童患者上气道中上部,也就是鼻咽、腭咽气道逐渐减小,舌咽部分没有明显差异。张明烨[6]等通过研究骨性I类不同垂直生长型的成人患者上气道显示,上气道上部即鼻咽部未见明显差异,而上气道中下部即腭咽、舌咽气道有明显差异,高角患者腭咽与舌咽部气道容积较小。与我们得出的结果略有差异。本研究显示,骨性I类青少年高角、均角和低角患者的初始上气道没有显著差异。得出结果的不同可能与样本量的差异、纳入研究对象年龄段或参考垂直骨面型分型的基准平面不同有关。
长期以来,正畸医生一直在关注拔牙矫治与非拔牙矫治对上气道的影响,以及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关系。通过头影测量对上气道进行分析发现,拔牙治疗与非拔牙治疗对骨性I类青少年上气道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青少年上气道周围的软硬组织的生长可能部分掩盖了治疗效果。有文献报道[7],上呼吸道的生长主要发生在乳牙列(0~5岁)和早期恒牙列(12~16岁)阶段,与生长期相对应。青少年患者正处于生长发育期,伴随着颌骨及上气道三维方向的生长,内收前牙后口腔容积并未减小甚至有少量增大,同时软组织的代偿适应能力也较强,因而出现了大部分指标的增长。青少年患者生长改建、肌肉及软组织的适应能力均较成人强,故青少年患者的大多数指标并未出现明显改变。青少年拔牙矫治前后上气道矢状径并不会发生明显的改变,这与斯蒂法诺维奇[8]的研究一致。结果提示,与成人相比,青少年患者处于生长发育的快速阶段,其自身的生长及适应性改建,能部分代偿拔牙后内收切牙对上气道矢状径的影响[9]。丁寅[10]等研究显示,从替牙期恒牙期少年的上气道结构在不断变化着,口咽段在整个观察期基本维持稳定,而鼻咽和喉咽段可能由于颅面硬组织的发育以及舌骨位置随年龄的改变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增大。目前,对于生长发育是如何影响上气道的,其机制与过程并不十分明确。
本研究结果显示,拔牙组和非拔牙组之间的气道没有显著变化,但气道容量的评估由于多因素而变得复杂。在大约2年的治疗期间,上气道的变化可能是由于呼吸方式、图像采集过程中舌头位置的变化、测量误差,或由肥胖和一般炎症引起的软组织变化。
在不同文献报道中[11],拔牙组的上气道显著差异可能是由于拔牙间隙关闭支抗设计的不同而结果不同。当关闭间隙时,拔牙组中前牙唇倾度虽发生了明显改变,但此改变量尚不足以引起舌骨、舌体以及下颌骨位置的改变,所以上气道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另一方面,轻度拥挤和严重拥挤患者拔牙矫治后上气道的体积变化有显著差异[12]。严重拥挤的患者在正畸治疗后气道有增加的趋势,相反,轻度拥挤的患者往往会看到气道容积的减少。当对轻度拥挤的患者进行拔牙矫治时,在牙列排齐后会出现更大的拔牙间隙,导致前牙更大的回收和牙弓的缩小。如果由于拥挤的原因拔牙矫治,气道可能不会减小。
骨性Ⅰ类高角患者正畸治疗后,舌骨有向下移动的趋势,舌骨向下移动,会使上气道减小。以往的研究表明[13-14],与均角和低角患者相比,成人高角患者气道更为狭窄。拔牙矫治可能会使后牙前移,但因为设计中度支抗,后牙前移量并不大,产生下颌平面角逆旋的概率微乎其微。再加之生长的作用,高角患者生长型为垂直生长型,生长的作用难以避免。因为病例样本量小,故没有把拔牙治疗与非拔牙治疗分开,所以也会对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拔牙矫治与非拔牙矫治不能改变骨性Ⅰ类青少年患者的上气道形态,但对上气道形态的长期影响,目前还没有肯定的答案。本研究采用X线头颅(定位)侧位片评价颅面结构,所得数据较为科学可靠。但因研究者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数年前正畸常规使用二维影像手段,无法反映宽度方面的情况。此项研究应继续扩大样本量,加入MRI、CBCT等三维影像手段,得到更丰富全面的信息。因为青少年患者存在上气道增龄性改建,所以有必要长期追踪正畸治疗结束的青少年患者气道变化情况。在后续的研究中,还会将样本限制在成人患者,以解决之前研究中生长的混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