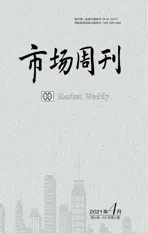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研究
2021-11-21陈宏睿
陈宏睿
(南京审计大学,江苏 南京211815)
全球价值链理论最初来源于价值链理论,沿着“价值链”“价值增值链”“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的演进顺序而来。 1985 年,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即每一个企业都在循环地进行着设计、生产、销售、配送等服务产品的活动过程,而这种全过程可用“价值链”来表示,这些活动为了价值创造而活动。 1985 年,Kogut提出了“价值增值链”,他认为产品生产的实质就是一条价值增加链,每个厂商可能只参加了增加链的某一个环节。 1999年,Gereffi 认为“全球商品链”是商品由于跨国生产分工所形成的分布在全球各地并且又相互联系的企业和相关的支持组织所形成的生产网络。 在此基础上,2001 年,Gereffi 在《价值链的价值》一书中,从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治理、升级、政策等问题出发,发展了全球价值链理论。 随后,UNCTAD 对全球价值链给出了一个较为官方的定义:“全球价值链(GVC,global value chain)是在世界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者服务的价值而进行生产、销售、回收等环节的全球性企业网络组织。”所以,可以看出,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演变到全球价值链理论时代的产业内分工,将产品的设计研发、加工生产、营销销售、售后服务等过程分割成不同的价值链环节,由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来完成,最终通过服务性活动实现产品的整体形式、所有功能和全部价值,从而提高交易效率、实现专业化经济的增长。
但是,每个国家由于要素禀赋和生产能力的不同,会参与不同的价值链环节,获取不同的价值增值,因此不同国家的GVC 地位也就不同。 在当前的国际贸易格局中,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博弈游戏中最大的玩家之一,如何实现争夺有利地位,发展壮大自身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成为当前最为核心的命题。 而制造业,作为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重要抓手,使得中国一方面紧紧抓住了产业转移浪潮和高效利用国内闲置生产要素的历史性机遇,获取了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巨大红利而实现了飞跃发展,另一方面它也继续决定了接下来几十年里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态势和全球地位(制造业增加值的GDP 占比,从2004 年以来所有年份均超过27%①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可以说是中国崛起宏伟蓝图上极其重要的一块关键拼图,因此,抢占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高端地位,高质量发展中国制造业,获取、创造并分享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红利,便成为中国复兴之路上的关键一步,因此接下来论文将沿着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度、影响因素和提升逐渐展开,探索跃向高端之路。
一、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度方法
关于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测度方法,不同学者有不同的选择指标与测量方法,因此也可以根据不同的特征和角度进行系统分类和框架打造。 但实际上,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主体是产品,其目的和结果是为了增值,因此论文据此对其地位指标的测量进行如下分类:
(一)最终产品角度
从最终产品角度入手研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是从出口产品的一些基本性质出发,如出口产品的价格、出口产品的质量、出口产品复杂度等。
施炳展(2010)构造了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和世界出口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差异度指标,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价格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因此得出了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结论。 胡昭玲和宋佳(2013)通过研究中国产品出口价格的变化来分析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发现中国制造业的地位比较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地位才有所提升。
Hallak 等(2009)根据其所提出的产品质量指数模型,测算了中国等10 个国家在1990~2006 年期间内出口产品的质量指数,发现中国的电子、通信等产品的质量存在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因此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所提高。
出口产品复杂度,是一种反映一国整体、产业以及产品技术含量的指标。 Lall 等(2006)认为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其能够出口的产品品种越多样,复杂度越高,在指标的构建中,将一国产品出口额占世界该产品出口总额的比值与一国人均GDP 进行加权平均从而获得技术复杂度。 Hausmann(2007)提出了EXPY 指标,即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该指标的测度分为部门层面和国家层面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EXPY 指标以RCA 指数作为权重来与各国人均收入进行加权平均,从而得到部门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Rodrik(2006)利用出口复杂度指数在测算中国的出口技术水平时,发现中国的出口技术水平与人均GDP 为中国3 倍的国家的出口技术水平大体相当,即“Rodrik 悖论”。 邱斌等(2012)利用复杂度指标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在2001 ~2009 年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发现期间大部分行业都处于总体上升的趋势。
(二)增加值角度
从贸易增加值角度入手,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法也略有不同。 Hummels 等(2001)最先提出了HIY 分析法,他认为在出口产品中内含的进口投入品的价值即为垂直专业化,出口中的进口投入品价值与出口值的比值即为垂直专业化指标,代表了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垂直专业化程度。 相关学者也在这个指标的基础上对一国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进行了测量,如文东伟等(2010)以此为基础,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发现其虽然较低但增长迅速。
由于HIY 方法的两个关键性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因此Koopman 等(2008、2010、2014)对其进行了修正,提出了KWW 法和KPWW 法,把总出口分解为国外附加值和国内附加值两部分,而国内附加值分为国内直接附加值出口、国内中间附加值间接出口、国内复进口附加值出口三部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由于该指标测算科学并且应用性极强,使其成为当今比较主流的GVC 地位测量方法。 周升起(2014)采用GVC地位指数,基于TiVA 数据测量了1995 ~2009 年中国制造业的GVC 地位,发现中国制造业整体以及细分部门的GVC 地位较低,呈“L”型演变特征,其中劳动密集型部门的GVC 地位相对较高。
二、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因素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决定,其实质仍然是如何取得竞争优势,因此其根本的决定可从比较优势理论中窥知一二。
比较优势理论从古典经济学开始,首先由亚当·斯密(1776)提出的“绝对优势”,然后到大卫李嘉图(1817)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然后到新古典阶段由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H-O 理论,以上的理论可以称之为“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 在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可以发现“要素禀赋”处在一个核心的位置,要素禀赋主要是指劳动力和资本,因此很多学者都将劳动力和资本引入决定国际分工地位的模型中。胡昭玲等(2007)认为低劳动力成本是我国一个很大的比较优势,是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 陆甦颖等(2010)实证检验发现,制造业的国际分工程度与劳动力成本呈负相关,与劳动生产率呈正相关。 郑江淮(2013)实证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制度环境等对我国制造业GVC 地位攀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随后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其主要包括弗农(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林毅夫(2013)的《新结构经济学》、Krugman 的“干中学”效应等。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中,核心关键体现为技术进步,学者们也围绕其展开了大量研究。 Humphrey(2004)认为,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对应了不同的技术层级,技术能力的提升是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关键因素之一。 张奎亮(2011)运用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研发投入是中国制造业提升GVC 地位的基础性因素,技术因素对其起到了正向作用。
事实上,如何对比较优势进行强化,政商学界都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其中通过FDI 与制度来强化比较优势是两种最常见的表现形式。
首先是FDI。 FDI 目的有很多,如为了减少劳动力成本而转移工厂、为了获取关键技术而进行并购投资、为了打开消费者市场、夺取市场地位等,其或多或少都实际地参与了比较优势的强化,所以FDI 是一个影响制造业GVC 地位的重要因素。 文东伟等(2010)计算了中国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中来自国外增加值的贡献达29%,而国外增加值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FDI。 Wang(2007)、Xu(2009)、祝树金等(2010)都认为FDI 对一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为正。 但是也有学者通过实证发现FDI 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总是正向的,如李强等(2013)实证发现FDI 虽然能够提高劳动密集型行业的GVC地位,但是对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却不显著。 FDI对制造业GVC 地位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的分析与验证。
其次是制度。 制度是一个国家进行政府干预最常规的手段,制度和政策对比较优势的强化起到了强烈的催化剂作用,林毅夫(2013)在《新结构经济学中》也大大肯定了制度和基础设施对一国比较优势的基础性支持作用。 祝树金等(2010)采用法律规则指标来代替制度质量,实证发现制度质量和自然资源的交叉项对出口复杂度和GVC 地位的影响显著为正。 李强等(2013)实证发现,以政府经费为代表的制度环境等对我国制造业的GVC 地位攀升具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戴翔和金碚(2014)分别采用经济风险指数、金融风险指数、政治风险指数来衡量制度质量,发现制度质量的完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和GVC 地位能够起到非常显著的作用。
综上,要素禀赋、技术进步、FDI 与制度都或多或少地对一国制造业的GVC 地位有着较为明显的促进影响。
三、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思考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从表现形式来看,其特征主要体现为从技术含量较低的环节向更高的环节演进,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更多的附加值(Kaplinsky,2000)。 而要实现这种提升,Gerriff(1999)、Humphrey 等(2002)提出了一种以企业为中心,包括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以及链条升级的四种升级方法分类。 而这四种分类方法都暗含了企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来实现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价值链升级的本质可以理解为是企业竞争优势的实现,从而实现更大的价值。
把视角再向前推进一步,企业若需要实现竞争优势,需要实现更大的价值,其根本上依旧可以考虑从要素禀赋、技术进步、FDI 和制度入手。 对应地,可以考虑更好地去调配利用好闲置生产要素,注重高级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累积与集聚,注重发挥好竞争与创新这两个要素兴奋剂的作用推动技术进步,以及发挥FDI 和制度的辅助促进作用。 事实上以上几种路径,不仅仅是企业竞争优势的实现,更是一国生产产出增加的实现,都可以归结对应到增加生产要素、使用更高级的生产要素以及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这些最根本的提高产出的经典路径中去。
综上,可以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继续贯彻执行好供给侧改革的国家战略,将广大的资金和劳动力从过剩产能和产业里解放出来,利用自由市场引导进入需要它们的行业中去。 二是注重高级生产要素的累积,要悉心培养适宜的高质量要素的经济社会生长环境,如更自由公正的营商制度、更有利的人才激励制度、更宽松的FDI 投资环境、更适合吸引高质量FDI 的投资制度等来吸收国内外高级生产要素,提高国内的高级生产要素集聚水平和密集度,从而逐步改善升级国内的要素结构。 三是注重打造国内价值链,向全球创新链逐步转型(刘志彪,2015)。 国内价值链是指以本土企业为核心,以国内市场为基础,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到消费售后的整个价值链大部分环节都由国内完成。 由于国外的竞争常常不能体现为有效竞争,并且国外的技术溢出存在很大的壁垒损失,使得本土企业必须要依靠自己的研发创新,在国内强大的市场基础上,与众多国内企业形成有效竞争和产业集聚,最大效率地实现国内产业间技术溢出,进一步实现技术领域的创新和突破。
希望且相信依据以上几点,能够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和价值实现及增值能力,从而能够提高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助力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