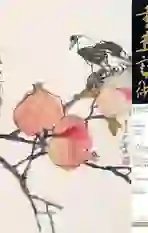公学与私学、成人与成己:康有为书学中的儒教理想及其现代意义
2021-08-25张兴成
张兴成
关键词:书学;康有为;儒家政教;古今之變
康有为在《春秋》“三世说”基础上,结合严复译介的“天演论”,形成了一种带有进化论色彩的历史哲学和社会演变模式。在政治制度上,由君主制到民主制,由小康到大同,康有为给历史的演进确立了一个终极的理想。[1]早于这套社会进化理想的设计,就民众与个体的成长而言,康氏亦基于儒家政教传统,形成了一套“教学”理论与教化学说。这套学说在其《教学通义》《广艺舟双楫》等著作中,借书学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故书学是理解康有为儒教思想不可或缺的视角。
一
《广艺舟双楫》“学叙第二十二”和“述学第二十三”分别讨论了书学如何“成人”和“成己”的问题。“学叙”言学书的一般秩序和进境,针对所有的学书者;“述学”言康氏自己的学书历程和体会。若对应康氏《教学通义》(1885年)中的说法,前者重“教”,后者重“学”,前者意在“成人”,后者意在“成己”;前者言学书之普遍规律与规范,后者言学书的个人师承与追求;前者为“公学”,后者为“私学”;前者为“古学”,后者为“今学”,以此而观,书学第一次古今之变在晚周至秦汉,由古之公学转向今之私学,公学为全民之教,私学为专业之学。从形式上看,这两章有模仿包世臣《艺舟双楫》的痕迹,《艺舟双楫》中“述书”(上中下)和“答三子问”等章节都涉及包世臣对自己学书进程和学书的一般理路的讨论,其中不少内容和观点为康有为承继。不同的是,康有为更着意于自己的政教理想与自我宣传。
“述学”从康氏自己的家学开始,由祖父康赞修发蒙,成人后师承朱九江先生,通过朱九江而溯得粤海诸家(谢兰生、黎简等)笔法,经陈兰甫先生而重小欧《道因碑》。在此期间,康有为的书学还是一个建立在帖学传统和“干禄”需求基础上的路子,以唐楷、刻帖和二王行草为主。关键点在,经张延秋,由帖转向碑;由朱九江,知邓石如篆书;壬午进京,大购汉、魏、六朝碑版,遂由传统帖学观转向碑学一派。因见碑版益多,遂“知隶楷变化之由,派别分合之故,世代迁流之异”;[2]174又经朋友指授,于沈曾植明方笔之要,从张裕钊法书中悟方圆互用之法,从邓石如楷书知古法气息之难。故康有为总结自己的师承,执笔得自朱九江,临碑用包世臣法,笔法悟自张裕钊,而气息胎格本自邓石如。康氏自述的书学规模与其《与沈刑部子培书》(1889年)、《与朱一新论学书》(1891年)等自述的学术规模一样,博取而约观,审时而通变,由此可以看到康氏撰述《广艺舟双楫》之学术与思想基础,亦能明了康氏何以能将其书学与经学等相贯通。
相对而言,“学叙”一章更为重要,因为在此更为明确地寄托了康有为的儒家政教理想。此章虽名为叙“学”,实为言“教”,开篇就言“学之难成”在“教之无其序”,一切政教首当明“序”。康氏说,学大学先事小学,言性理先明训诂,为八股先学文史,写卷折先临碑刻。行有轻重缓急,学有先后本末,不得其序,难以精进。[2]169康氏在此对当时的人才培养与科举取法方式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学大学而不事小学,言性理而不明训诂,意在批评晚清教学中缺乏人人必会之“公学”“实学”,多为无用之虚理,导致整个社会缺乏真正可用之人才;为八股不学文史,言士人流于应试套路,钻研形式,不明文史掌故,何以经世济时?写卷折先临碑刻,言楷法无气骨,无根底,精致整洁的卷折耗万千学子精气神于表面之光鲜,书学无益于士人德行之培养。总之,士人所学皆循个人利禄之道,于国家、民族而言实为无用之学。康氏借此表达了对晚清政教的强烈不满。这些观点与康氏《教学通义》等早期著作多有呼应,亦承袭了晚清改革派人士龚自珍、魏源等人的主张。[3]
于具体的学书秩序,康有为提出了诸多的建议。先学执笔,从结构入,分行布白求章法,至骨肉气血精神皆备,然后成体求意态。作书先学大字,行草从方笔始,临摹用九宫格,学碑刻要长肥加倍,等等。最关键的是择碑和临摹,康氏极力推荐《张猛龙碑》和《龙门造像》等,意在通过方厚雄强之北碑培养学者的笔力与气骨,矫南帖“靡弱之病”。[2]169-170书学如同经学,是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学习、临摹基础之上的。临摹过程既是一个体认经典文化内涵,攀缘经典高度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反观自己、认识自己、提升自己的过程。因此,康有为说临仿就是通过古人外在的“形质”去认识古人内在的“性情”,每一件作品都代表一种文化人格,通过书学之路,学者得以认识无数鲜活的人格、心性,与各种“形质”“性情”打交道,熔铸成自己的血脉、气质,形成自己的体格意态。基于此,康有为构建了一个融书学与文教为一体的学习理路:
能作《龙门造像》矣,然后学《李仲璇》,以活其气;旁及《始兴王碑》《温泉颂》以成其形;进为《皇甫驎》《李超》《司马元兴》《张黑女》以博其趣;《六十人造像》《杨翚》以隽其体;书骎骎乎有所入矣。于是专学《张猛龙》《贾思伯》以致其精,得其绵密奇变之意。……然后纵之《猛龙碑阴》《曹子建》以肆其力;竦之《吊比干文》以肃其骨;疏之《石门铭》《郑文公》以逸其神;润之《梁石阙》《瘗鹤铭》《敬显俊》以丰其肉;沉之《朱君山》《龙藏寺》《吕望碑》以华其血;古之《嵩高》《鞠彦云》以致其朴;杂学诸造像以尽其态;然后举以《枳阳府君》《爨龙颜》《灵庙阴》《晖福寺》以造其极。[2]171
康有为在此描述的是一个“理想的”书法家学习的过程,更是一个中国人如何在文化经典中塑造完善的文化人格的过程。他要求学习书法的人不能追求片面的“个性”与“新奇”,“凡所立之宗,奇古者不录,靡弱者不录,怪异者不录。立其所谓备众美,通古今,极正变,足为书家极则者耳。”[2]136“备众美,通古今,极正变”,这既是对所学法书的要求,也是对学书者的要求,“书若人然,须备筋骨血肉。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加之姿态奇逸,可谓美矣。”[2]146完美的书法和完善的人格一样,要求平衡、健康、圆融,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4]所以,活其气一成其形一博其趣一隽其体一致其精一变其意一肆其力一肃其骨一逸其神一丰其肉一华其血一致其朴一尽其态一造其极,这是书学之路,更是“文而化之”“人文化成”之道:单薄进于丰厚,靡弱进于雄强,朴野进于文明,夷狄进于中国,据乱进于太平,小康进于大同,人世进于天道。这与其说是在言书学,不如说是在宣扬儒家政教之理想。
康氏的这种思想在前辈包世臣那里已有先声,包氏自述求学过程:“仆以奔走风尘,弱冠废学,常叹生秉殊分,使不迫于饥寒,以三年余暇,沉浸遗编,源于《风》《骚》,以端其旨,以息其气;播于子史,以广其趣,以饬其势;通于小学,以状其情;汇于古集,以炼其神,以达其变,则虽不能追踪汉魏,力崇淳质,悱恻雅密,接武鲍庾,其庶几矣。”[5]包世臣说的不是书法,而是更为深广的经、史、子、集,但其中的道理却是一样的,以文化人,通过古代典籍,端其旨,息其气,广其趣,饬其势,状其情,炼其神,达其变……包世臣以自己的体会和人生历程,演示了文化是如何使自己原本弱小的心灵不断强壮,偏狭的心智变得充盈,从一个迫于饥寒的底层书生最终炼成济世利民的经世学人的过程。
人问学书之序与方,包世臣答:“始如选药立方,终如集腋成裘。”先学唐人,然后进求北碑,“以博其体势,闲其变态”,再由真入行草,学褚临《兰亭》,学《阁帖》《争座位》,等等,至“诸家之形质、性情,无不奔会腕下。虽曰与古为徒,实则自怀杼轴矣”。[6]所以包世臣言,“万古名家,无不由积学酝酿而得”。所谓“积学酝酿”“与古为徒”等,即教以成人;所谓“自怀杼轴”,即学以成己。
二
儒家重视文教,以为人皆须教化而成,正如《周易》“贲卦彖辞”所言:“观乎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干宝曰:“四时之变,悬乎日月。圣人之化,成乎文章。观日月而要其会通,观文明而化成天下。”[7]广义的“文”包含了“天文”与“人文”,亦即包含了自然天地运行之道(天文)和圣人效法自然天地运行之道而创造的人伦之道(人文),狭义的“文”则可专指人文,即圣人所创造的文字、制度、器物、艺术等等。以圣人所创的人文施诸民众,使之明理知性,动静合乎自然,行为合乎礼节,人与天,人与物,和谐有序,便是理想的“化成”世界。所以,中国人很早就重视“教化”的重要性,“化”在甲骨文中是两个相对而行的“人”字会意而成,一个人向上行,一个人向下行,意者“化”就是人的分化,向上的成了贵族,向下的成为奴隶,向上的尊贵,向下的卑贱。而在儒家看来,更重要的是德行和精神层面的区分,所谓“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君子下学人事而上达天道(“下学上达”),行健向上,追求精神的自由与德行的完善,内以化己,外以化人,“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小人则向下沉沦,为器物所役,陷入低俗的生活世界。一个化成的世界就是一个社会地位和精神品格上尊卑有序的世界。故“文化”意味著对人性的改造,使之在社会地位和精神品质上皆往高处走,即荀子所谓“化性起伪”,庄子所说的“鲲化为鹏”,宋儒常讲的“变化气质”等等。“文”即文饰、打磨,“文化”即“文而化之”,“人文化成”,指通过文饰与打磨使人性变得更加美善,因此,一个人要“化成”,离不开“文”,不“文”则不足以使社会秩序和谐化,不“文”则不足以使心灵世界合理化,不“文”则不足以使人格境界高贵化。所以,真正的“文人”乃是“人文化成”之人,而非后世以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为装点之人。如何通过“文”以化成世界和人心,便是圣人立法创教的根本。
书法作为儒家文教的构成,至少可以追溯到《周礼》“六艺”之教,“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8]周代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故康有为在《教学通义》中将之皆归诸“公学”范畴,意即“自庶民至与世子莫不学也”,尤其书、数之学,“识字持筹,尤应尽人共解。今人欲习工商,必先识书算。若不解作字,不解持筹,便为弃物。……故书、数为天下古今通行之公学,未有能外之者。”[9]23康氏认为人道立于礼教伦理与事物制作,礼教伦理关乎德行,事物制作见诸道艺,此圣人所以重“教”与“学”。作为六艺之一的“书”属于道艺之门。因为德行、道艺为立人之本,自卿、大夫、士至民莫不学之,故书与数等六艺当为“凡人之通学”,“天下通行之公学”。因此,书是圣人政教与王制之重要构成。此为黄帝创制(舟车、文字等)以“敷教在宽”之通变宜民思想,后世教学日趋偏狭,越来越专属化,六艺渐为少数特权阶层所习,而为“官守”。而官守之学经春秋战国之乱而“失官”,康氏以此“为学术之大变,后世人民不被先王之泽者在此”,学术、道艺教民化民之功不显,书学变成了“小艺”,为“幼童之学,师儒闲习之而不道,故《论语》未尝一言及书、数”。至汉代,先王所传“书学实亡”,书学变成了专门之学,或称“私学”(如汉代以通小学文字学者为“令史”,后世以善书者为“中书舍人”“侍书学士”“书学博士”等),再后来,变成了文人之“游艺”,演化为士人业余“小道”“末技”,成为“无用”之学,或者变成了科举干禄的工具,成为耗费、禁锢读书人心力之利器。[9]20-35
在此,康有为借《周礼》所记以言儒家“敷教在宽”之理,并以之以论证其所申“教学”之民主意义本诸古礼与古法,以复古为变法之根据。故敷教在宽,通变宜民,源于康氏的民本思想。康氏此论未必皆符合史实,其目的也未必是为了证史,而是指向变革,于今其意义将越来越凸显。今天,书特别是数等的确已成为人人皆习之“公学”,但人们更愿意视书为工具或“艺术”,罕有人重视其与“立人”“化人”之关系,只因他们对书学与圣道、王制之关系不明。因此,发明康氏此论,当有切中时弊之效。
《周礼》六艺之“书”当然非作为艺术之“书法”,其含义要广,包含了字学与书学两端,故儒家“书教”(非《尚书》意义上的“书教”)首在识字,亦重书写。至汉代,书学已成“专学”“私学”,《汉书·艺文志》:“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10]91按汉初律法,书学已成选取官吏之重要科目,要求应试者在识字(讽)和书写(书)两方面皆达到相应的程度(九千字、六体),特别是在文字的统一和书写的规范上更是要求严格,不得写错(不正),否则依律法办,足见汉初对文字及其写法在国家大一统政教中的重要性的强调。字学与书学在此并重,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和虫书等六体,既要求认识,还要求能书写,“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对文吏的这种要求无疑有助于推动汉初的文化及文教。尤其是汉代经历了文字的“古今之变”,古文(篆书)与今文(隶书)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分乃至断裂,此亦中国书学史上的另一次巨变,要求“通知古今文字”亦是应对这一断裂与巨变之现实要求。“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10]94许慎《说文解字序》中亦记,“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庭中,以礼为小学元士。”[11]至西汉末期,识古文者益少,而古文经学兴起,正欲与今文经学争立博士学官,小学与训诂乃是古文经学之长,所以《汉书·艺文志》列小学字书于“六艺略”,小学取士在此时兴盛,亦与此背景有关,客观上也促进了书学在儒家文教中的地位。
至清代,阮元、包世臣和康有为等所谓的“碑学家”或碑派书法倡导者都有“返于汉”或“本汉”之论,他们欲打破所谓“帖学”的统治的背后,有着更深远的文化与政治理想。宋以来的帖学将书法不断往越来越偏狭的“艺术”“私学”方向引导,使书法成为专属于文人的装饰,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书”作为儒生“公学”之性质。所以,清人由宋学而返汉学,康有为等又欲由乾嘉学者所崇尚的东汉许郑之学返西汉今文经学,由此而直溯孔子,上追三代,直探华夏礼乐文明之本与源。此乃清人“复古以更新”之路,亦华夏文明复兴之道。以此返本溯源之理路观之,书学亦当从帖学而返碑学,由碑学而明书学非只有“私学”,还当重视其“公学”价值。但碑学帖学之分已属流而非源,从本源上说,书法之所以在古代中国不是专属于少数人的艺术,而是所有读书人(“士”)的“本能”,亦非仅仅因为其无所不在的实用性,在儒家那里,还因为它是士人塑造自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人磨墨墨亦磨人,我写字字亦写我,书法像所有的高级文化一样,其意义都在于塑造理想的“人”(君子),形成卓越的“民族性格”乃至“文明精神”。
因此,书学在儒家传统中一直是教化(成人成己)之重要方式,是礼乐文明的载体。书法的美体现在用笔、结字、章法的形式秩序之中,更展现在与书写者内在的心性、德行之精神秩序共节奏的和谐里,同时也可视为时代、社会和家国秩序之象征。所以,在康有为那里,“书教”(此非儒家《尚书》之“书教”)与“乐教”是一体的。康有为说,三代先圣教人,最重乐教,《尚书·尧典》夔教胄子,《皋陶》之“九德”,《洪范》之“三德”,《大学》正心、诚意,《中庸》之教,等等,皆在“变化气质”,皆可归诸乐教传统。[12]康有为受乃师朱次琦影响,一生教学皆遵循师法,“以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为学规”,从早年的长兴万木草堂到晚年上海的天游学院,一以贯之。(1)康氏认为,“教”以“变化气质”为上,不以博通礼文度数为尚,亦不以践履敦笃为难,因为变化气质而“德成”,“德成为上,行成次之,威仪为下”。[13]97在康有为看来,人皆有所偏,即便性行高美之贤,亦不能免。朱子看人,全是“气质”,祛除气质之害,是理学家修身之首要。尤其是针对那些国政民命所托之貴胄、政治人与士子,如何变其矫急傲慢之偏,素为先圣所患。康氏指出,纠偏矫患,无过于声乐:
安之弦缦,作之金石,动之羽旄,以和其气血,动其筋骸,固其肌肤,肃其容节。使其血气不和,弦缦见之,容节不和,羽旄见之,肌肤不和,金石见之。动志而有,发言而有,律焉,谐焉,举足而有节焉;漫之濡之,涵之润之,待其涣然释,怡然顺,体与乐和,志与气平,蔼然而中和,琅然而清明,刚柔缓急,悉剂其称,则学之成也。[13]98-99
乐教、诗教目的在“变化气质”,使人心性臻于中和,理智保持清明,养成“盎润和乐之气”,这对于那些从事政治的贵胄和贤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一般士子和民众亦不可废弃。气质可化者,惟“中人”,惟大众,康氏欲承三代“敷教在宽”之传统,重视“公学”,亦有此因。(2)然周衰乐亡,汉以后乐学渐没,夷乐西来,易我和声,梨园百戏,淫艳歌舞,俳优捐伎通行,遂致雅乐难闻。康氏慨叹,承四千年之文教,而乐学中绝,致贤才难教,风俗难美。(3)乐教实关乎儒家三代政教之承传与推行,然乐学中绝难道也意味着乐教所守之“中和”理想之消逝?后来宗白华说,“中国音乐衰落,而书法却代替了它成为一种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三代以来,每一个朝代有它的‘书体,表现那时代的生命情调与文化精神。”[14]这一判断与康有为的看法是一致的。康有为在书法中寄托了乐学的“中和”之教,“上通篆分而知其源,中用隶意以厚其气,旁涉行草以得其变,下观诸碑以备其法,流观汉瓦晋砖而得其奇,浸而淫之,酿而酝之,神而明之。”[2]171-172书法之教的目的亦在“变化气质”,使学书者的人格心性趋于盎润和乐,臻达清明美善。
三
康有为诉诸三代和《周礼》的所谓“公学”“私学”之分属于典型的“托古改制”,其目的不在“发现”古史,而意在通过“发明”传统以改造现实。其目的是指向当世与未来的,于今亦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书学在今天经历了新的古今之变,作为实际而普遍功用意义上的“公学”和少数人从事的专业化的“私学”在当代有了更明确化的区分,前者可谓一般意义上的“写字”,后者则是艺术创作层面的“书法”。二者在古代社会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古代士人的日常的实用性书写和有意识追求的超功利的审美化、个性化创作界限有时并不清晰,但现代书家则非常强调书法作为艺术创造的审美性、个性和主体性,一者因为现代社会中(毛笔)书法的实际功用即作为“公学”的性质在不断弱化,二者因为中国传统知识和文化系统在以西学为参照的重构过程中,书法的“艺术”“美术”学科身份和专业化发展需要,在不断强化书法作为“现代艺术”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定位。于是形成了一个古今错位、标准不定的现象,有的人更乐于讨论古典书法的“文化”,而强调当代书法的“艺术”;也有的人用古典书法的标准去衡量当代书法,或者以当代艺术的尺度去批评古人;这些都是未能理性地辨析“古今之变”的结果,但也客观地折射出书法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学科与身份危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我们还希望书法是一种延续了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士人艺术,而非符合现代美学标准的“造型艺术”“视觉艺术”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强调,书法的专业化过程就不是一个与其古典价值基础和文化结构“脱钩”的过程,恰恰相反,是如何重新夯实其古典文化基础,并以此与现代艺术精神对话,不断创新的过程。因此,当代书学不得不向两个方向努力,一是向传统的回归,避免文化断裂,重新深入地去研究古典书法及其背后的思想基础和文化结构;一是向现代世界敞开,积极探索各种新的创造性道路,在现代文化语境中打造书法的文化品质与艺术精神。否则,书法要么只是一种“摹古”的复制行为,虽然在传承文化上尚有一定意义,但终归会因缺乏创造性而失去普遍的吸引力,成为历史陈迹或古董;要么变成了另起炉灶的现代艺术,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无关。
对此,重提康有为的“公学”“私学”之论或许不乏现实针对性。书法在今天需要从不同层面来加以理解,作为大众喜爱的一种文化活动和中国人日常的实用性书写,书法的“公学”功能并未完全丧失,相反,就传承、守护汉字文化而言,这一功能我们还要强化,要求每一个中国人写对、写好汉字,要求在大中小学推广书法教育,其首要目的在此。当然“公学”意义上的书法并非只就实用性而言,同时还应兼顾审美性和道德教化功能,通过书法这样的实用性文化更有利于实施普遍的全民性的“人文化成”目的,这也是康有为强调“公学”之意图,借古之“敷教在宽”理想以推行现代之民主启蒙与大众教化。“公学”意义上的书法教育目的不在培养艺术家,而在塑造良好的公民德行和健康的现代人格,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儒教的许多思想和做法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而作为“私学”层面的书法,则应是在“公学”教养的基础之上,探寻个性化、专业化发展之路,以审美创造力和艺术想象力为训练基础,以自由表现力和思想探索力为培养方向,通过书法去推动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去创造中国文化的新高度,去实现自我文化人格的完善与卓越。因此,“公学”意义上的书法的主要目的在“成人”,实施普泛的人文教化,培养健康的公民德行和文化人格;而“私学”意义上的书法的主要目的在“成己”,构建自我的独立气质和艺术个性,最大程度上去实现自我。或许,我们今天的书法教育离这个理想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强调这种儒教理想和意识是必要的,尤其是对那些在从事书法普及教育的工作者和有志于成为书法家的专业人士来说,首先应明了的就是这“成人”“成己”之道。
古希腊哲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谈到通过诗来“净化灵魂”,改造城邦的政治担纲者、立法者的德行,政治秩序是建立在灵魂秩序基础之上的,什么样的灵魂决定什么样的政制。因此,诗教从来就是关乎城邦乃至文明根基的大事。同样,三代以至朱子所强调的“变化气质”亦是儒家政教之要义,选择什么样的“气质”来作为华夏文明的根基,也会决定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竞争中的位置和未来。中国艺术变化气质的方式在“移人之情”。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说:“是故艺之至者,必移人情,然非其人之情先能自移,则艺固不至矣。夫以伯牙之学,成连之教,而移情必以海上为期,情固必移于海上乎?(4)古人闻涛声、见剑舞而悟草法,览山川雄奇,诗文为之增气,是岂有迹象可拟,理趣可寻者乎?”[15]能移人之情故能移人之艺,反之,能移情之艺方能移人、化人。艺与人以及由此系联之历史文脉、天地宇宙等,虽无迹可寻,无象可拟,却无时无处不在移人之情,化人气质。这种天与人、艺与情的互动构成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宗白华以唐代诗人常建之《江上琴兴》一诗为例,言琴声“一弦清一心”,“万木澄幽阴”,“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琴声安能有此力?实则琴声通过移人之情,使得人之心境、心性改变,遂觉万木澄阴,江月既白,江水更深。因此,宗白华说,“艺术的境界,既使心灵和宇宙净化,又使心灵和宇宙深化,使人在超脱的胸襟里体味到宇宙的深境”。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肃剧净化的是城邦的政治灵魂,那么,中国艺术所移(净化)的乃是人的宇宙意识与生命情调;前者意在促进城邦特定群体的德化,祛除灵魂中的劣性而葆有灵魂的德行,[16]后者意在培育人本于天地而又被各种社会轨辙禁锢的“活跃的、至动而有韵律的心灵”。[17]
对于康有为这样的政治家、思想家来说,之所以会对书法这样的“末技”“小道”加以持续的关注,视为终身之爱好,除了因为书法是士人修习之传统之外,更重要的是书法所承载的儒家教化精神和修己成人之道,康氏在儒家思想遭遇前所未有之挑戰之衰世,赋予书法以深情,寄予书学以深意,正与此有关。在这物质和技术日新月异,价值与观念不断更新的时代,康有为通过书学表达的政教思想依然有着深切的现实关怀。于个体而言,提供了一条如何将我们从“单面人”和“世界黑夜的贫困”中拯救出来的必由之路。通过那些伟大的艺术经典和古典智慧,不断打磨我们,雕饰我们,充盈我们,润泽我们,让我们从偏狭、平面、拘陋、庸常的异化人格和物化世界里解放出来,变得健全、丰满而冲和。于文明而言,这个日益走向歧路而变得越来越物质化、技术化和同质化的现代世界,个体消失在他的功能和角色里,文明迷失在它的竞争和冲突中,“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18]当以信仰为支撑的时代在理性化的“解魅”中一去不复返,当知识人不再禀有“立法者”的地位,我们所应当做的或者说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保持“头脑的清明”并努力传播这种清明。站在古今之变的交汇点,康有为等智者不断地提醒我们,现代文明离不开古典文明的启迪。“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起飞”,当西方人返回古希腊去召唤他们的智慧女神时,我们同样需要重返汉唐,追溯先秦,倾听远古的“大和之乐”。
(本文系西南大学博士启动项目“清代经学对书学的影响”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