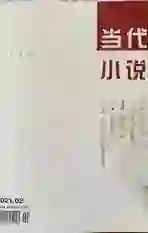台阶(短篇小说)
2021-03-26龚继岳
龚继岳
周一
喵呜——喵呜——
一大早,楼道里传来猫叫春的声音。丫丫把大脸猫放进来,在它身上来回捋了几下,就去了洗手间。
陈泗撂下碗筷,往后一扬,背靠在沙发上浏览微信,余光却四下踅摸。
大脸猫两眼直勾勾地满屋子踅摸了一遭,扭动着身子翻了几个滚,起来,蹭完茶几腿,再蹭陈泗的裤脚,接着叫一声,喵呜——
碗筷收拾利索,走出厨房,邬青提起丫丫的书包,站在洗手间对面等丫丫,好送她去上学。
乜斜着大脸猫蹭来蹭去,陈泗鄙夷地在心里哧了一声后,下定决心,不能再拖了,得提出来了。甩出三个字:离婚吧。
三个字随着猫叫飘过来,过了一会儿,邬青才歪一下头,瞅着他的花格上衣,还回两个字,随你。
陈泗一下子从沙发上弹起来,对着屁股口袋,插了两插,才插好手机,走到门口,边开门边说,那咱去民政……
不就去办个手续吗?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邬青这次连头都没歪,接过话茬,去民政局前,我提个条件。
陈泗关上开了一半的门——这是要狮子大张口啊!张吧,张吧,反正没车没存款,房子是公家的;要女儿,巴不得,省得带个拖油瓶。
你说吧,什么条件?
婚后你把我抱上楼,既然不过了,你要再把我抱下去。
喵呜——大脸猫见男主人不理它,女主人也装作没看见,只好对着房顶继续叫。
没问题。陈泗轻飘飘地回答。
这一周,你要一直抱我下楼。邬青紧跟着补充,今儿周一,5月9号,到周五13号,下楼,直接去办手续。
一个月也不是个事儿,只要答应办手续。陈泗心里话。说出口的还是那仨字,没问题。
条件谈妥,丫丫也从洗手间出来了。
妈妈脚不得劲儿,让爸爸抱着下楼,丫丫自个儿下楼。邬青边说边把书包背在女儿身后。书包里也就几本画书,一只铅笔盒,不到一公斤。
丫丫小嘴噘得老高。等爸爸像抱自己那样,真把妈妈抱起来时,又稀奇又兴奋,爸爸抱妈妈喽,爸爸抱妈妈喽。
多年前邬青下岗后,在陈泗的引荐下,在他的单位做临时工。不到半年工夫,单位里就疯传两人有一腿。那时一个已为人父,一个已为人母。
出门。邬青伸手锁好门,任陈泗抱着下楼。
喵呜——
门一开,大脸猫吱溜蹿出去,叫着奔向楼上。
他们家住中单元202室,从门口到二楼与一楼的转角处,九级台阶。俩人下台阶时,丫丫已在转角处等着了,看景似的看着爸爸抱妈妈下楼。
咕咚——咕咚——
喵呜——喵呜——
左边是墙壁,右侧是楼梯扶手。下到第三级台阶,陈泗转脸向左,毫不犹豫地。脸对着脸,彼此喘气声都清晰听见,却相对无言,不如面向墙壁。大脸猫却非常配合,差不多每下一级台阶,就恣意地和着脚步声可劲地叫。
出门前,陈泗随手抱起邬青——要散伙的买卖了,还抱什么抱?好在天儿不算热,充其量应付一下,抱出门而已。
泰安四季分明,谷雨过后,满大街还都长袖紧束,立夏当天,就遍地短袖。
然而,出门后,陈泗把邬青放下来已不可能。邬青锁好门,实实在在地顺势搂住了他的脖子。面向墙壁的同时,陈泗不得不向上托一托邬青,为的是把她抱牢稳,后面毕竟还有二十多级台阶。
咕咚——咕咚——
一双脚承担着两个人的重量,脚步声除了沉稳之外,还多了一些凝重。从二楼到一楼底,一共三十级台阶,到101室门口是十八级。
走下第一个九级台阶的最后一级,便是转角处了。顺着墙面,陈泗发现了转角处的蜘蛛网,那种车轮式的,小半圈小半圈地织在一起,像极了半个树墩的年轮。网中间两只蜘蛛摞在一起,正忘情交欢。
风柔柔地吹过纱窗,一股浓浓的大蒜味迅速弥漫开来。陈泗再次扭脸面向墙壁——他厌恶邬青满嘴的大蒜味。
邋遢女人。猫一聲迭一声地叫,角角落落里都散发着骚情,让他无所适从,陡增抱怨,莫非婚后女人都这德行?
婚礼那天,陈泗抱着邬青上楼,像眼下的大脸猫一样,轻巧地蹿上楼来,直到看见那个大大的3F时,才知道已来到三楼。不是后面同学跟着,他真想抱上九楼,站到楼顶,大喊一声:我,陈泗,跟邬青结婚了。重温在大学里抱邬青时的感觉,简直是妙不可言。所以,上楼时一步一个台级,嫌太慢,多数是一步两级,甚至是三级。尤其在邬青发式的牵引下——仕女一样的发髻,前边高绾成扇形,后面一丝不乱地拢在一起。伴着阵阵脂粉香,陈泗由扇形旁若无人地向脸蛋亲吻着、吸吮着……哪管后面跟着起哄的同学,从一楼一直吻进屋。可眼眉前儿,唉——出门前,图省事,邬青随手一挽,拿发卡直接将长发别在头上,宛如一个粗大的问号。
只睃了一眼,陈泗便发出了感叹。一声叹息,替换了对女人的埋怨,连同猫叫,继而琢磨有意思的蜘蛛。
雌蜘蛛的生殖器是俩并排的小孔。交配时,雄蜘蛛通过两根铅笔状的器官完事后,狡猾地留了一手,将其中一根铅笔舍在对方体内,堵死小孔,以防同性与配偶交配。剩下的一根,却不耽误再与别的异性交配。但夫妻蜘蛛不轻易交配第二次,另一根铅笔是留给情人的……想起从网上看到的这些,陈泗蓦地觉得,有意思是有意思,自己咋有点像蜘蛛?这念头一闪而过后,又觉得不是——跟邬青重组家庭,原本就是个错误。得离,必须离。
陈泗的怨叹,邬青能不察觉?其实,察觉男人有异样,远的不说,比如上周六晚上,差不多快零点了他才回家。周日,邬青洗他的花格衬衣,都隔了一宿,杏仁蜜味还那么冲,浓得熏人。
上大学前,邬青虽然也用过杏仁蜜;花格衬衣也是她替陈泗选的,但现在她厌恶杏仁蜜,更讨厌花格衬衣。
我最闻不得那种叫杏仁蜜的破化妆品,真受不了啦。两人在开房时,陈泗告诉她,黄脸婆非说从小用惯了,搽其它的过敏。
抓起花格上衣,邬青闻了闻,是那味儿无疑。当时陈泗还说粉质的味道忒刺激,一闻就膈应。生完孩子,那事儿少了,他非要,睡前人家就搽这个……有一次,逼着人家洗干净,人家也不伺候,他居然打了人家。当夜,人家冒雨回了娘家。一周后,岳父找上门,逼他道歉后才让女儿回来。
陈泗与邬青的绯闻三传两传,传得跟真事儿一样。后来,直至两人在宾馆开了房。究竟开房是跟绯闻赌气,是谁主动的,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接下来,各自离婚后,俩人领了证,重组。
爸……见爸爸抱着妈妈出了单元门,丫丫觉得挺好玩,想问,爸爸,明天还抱妈妈吗?可陈泗放下邬青,第二个爸字丫丫还没脱口,他便骑上电动车扬长而去,直到背影变成黑点了,也没回头看一眼丫丫。
妈妈,味……丫丫抬脚刚要上踏板,小手捂住邬青的嘴。
女儿一说大蒜味,邬青本能地一歪头,赶紧起身,向陈泗远去的方向茫然地看了一眼,便泪湿眼底……直到站上踏板的丫丫喊饿了,拿钥匙往电动车上插了两插,才插准,且拧了两下才把钥匙拧到底。
喵呜——
妈妈,猫——载着丫丫直奔小区前的合欢饭店。走出不远,丫丫看到大脸猫从楼道里叫着蹿了出来。
周二
要是还抱妈妈,爸爸得先抱下我去。等陈泗抱丫丫返回来,邬青已等在门口。
喵呜——喵呜——
等在门口的还有叫春的大脸猫。
转角处的窗户仍然重叠着。抱起邬青,还没来得及下台阶,清风送来一阵绿箭清香,陈泗一下记起,今儿早餐少了邬青心仪的腌大蒜。
泰安大蒜有名。邬青找一山泉水桶,将事先搁盐水里泡好的大蒜填进去,撒上糖,倒上山口陈醋,第二天早餐就能吃。
绿箭清香,那是久违的味道——上班后,只要陈泗不喝茶,邬青猜他一准儿没吃早餐,不仅为他买来胡萝卜肉丁蒸包,一定还有一条5只装的绿箭口香糖。
邬青头上的“问号”换成类似仕女的发髻——前半部分盘成一个扇形,后半部分扎成若干小辫子,绾成一朵花,最少用50多个卡子固定住,宛若含苞的花蕾。跟前夫的婚礼上盘过后,直到与陈泗再婚的婚礼上,又盘过一回,再没盘过。用邬青的话说,一周最少要鼓捣一次,每次拆、洗、编、盘,没有俩小时,捯饬不完。忒麻烦。都姑娘她妈了,再捯饬,给谁看?
咕咚——咕咚——
来到转角处,两只蜘蛛紧挨着伏在网上,像在说悄悄话。偏有一只苍蝇,从纱窗破损处钻进来,粘在蜘蛛网上,愈挣扎愈结实,眨眼之间,动弹不得。
往下,开始走第二层台阶,陈泗诅咒着那只苍蝇,顺墙面撒目。昨天的小广告又覆盖上新的。粉红色的广告纸上,特号黑体字十分醒目:为彻底改变全国离婚率连续7年递增的现实,请你试试XXXX……床上和谐了,离婚率就会直线下降。广告纸贴在厚薄不一的灰尘中间,格外刺眼。陈泗感觉很滑稽,不,是扯淡。不扯淡的是,打扫卫生的老太太忒应付公事,再交物业费,一定参她一本。
苍蝇找死,墙上是扯淡的“牛皮癣”,楼道里充斥着猫的叫春声。陈泗百无聊赖,此刻的他也是一脸的问号,他不明白,当初抱她上楼时咋没觉出什么分量,轻而易举就抱上了楼。可眼下觉得邬青铅球一样下坠。这种感觉来自邬青小肚子上的那堆赘肉,每下一级,赘肉一晃动,连带他全身都在晃动。最明显的是小腿肚子,一哆嗦,全身紧跟着颤抖。上山容易下山难,爬过泰山的人都知道,即使拿支烟袋,也不如空手下山轻松。每下一级台阶,颤抖一下,他就朝下看一眼,看一眼就多一层愁。愁台阶与台阶之间距离太大,愁台阶忒多。十八级后面还有十二级,设计者也是多余,都他娘设计成九级一拐弯,不就省出六级吗?还节约了成本!这哪是三十级台阶,简直是三百级。咕咚咕咚地一级一级往下下,跟蜗牛爬没什么两样,一步走完,多好。还有大脸猫,你早不叫晚不叫,偏偏这个节骨眼上喵呜、喵呜地叫不停,好像是在慢哟、慢哟地耻笑他……这样寻思着,他下意识地一步下了两级台阶,重心一下子失去平衡,险些把邬青扔出去,幸亏靠在了右边扶手上,才稳住脚步。万般无奈,陈泗只得再次向上托一托,实打实抱住,接着下台阶,皱皱眉,硬着头皮。
咕咚——咕咚——
心里再别扭,也不能真把人家扔了,毕竟答应人家了。不止是践行承诺,陈泗疑惑的是邬青肚脐眼以下,咋就多出了一堆赘肉——在大学里抱她上楼时,上衣一抻,衣角刚好露出肚脐眼。由于裤腰太短,肚脐眼以下暴露无遗,光滑细腻、性感洁白,让他的目光即刻变成欲望……可眼前就是一堆实实在在的赘肉,就像一堆和好的面坨,平摊在案板上。赘肉不赘肉的,周五以后就从自己的视野里永远消失了。迁就邬青在美人痣处挠痒痒,他将目光移了过去。
美人痣在左眼角略靠上一点,跟某主持人的位置正好相反。有这颗美人痣,主持人更显大气端庄,可邬青好像忌惮得很。邬青上班后,跟陈泗对办公桌。手头的活儿一干完,就对着手机收拾美人痣,恨不得一下揪掉。还兀自念叨,咋不跟某某一个位置呢?有人碰上了,奉承两句,自是飘飘然。倘听谁说她臭美,馬上一脸乌云,连摔加砸,丢三落四。为这,陈泗没少提醒她。提醒,也是白费口舌,用他们重组后陈泗的话说,邬青属鼠的,落爪就忘。有时正拾掇着,电话铃响了,要记通知,桌上找不到笔,手一伸,把对面陈泗的拿过来。记完,你再放回去啊!她不,随手一撂。下次再用,又大年三十买不到锅似的,再一通乱忙活。俩人成家后,陈泗直接说她脸上,期待她改掉乱拿乱放的恶习,不料她生就的胳膊长就的肉——到睡觉了,才记起手机还没充电。隔几天,又充电了,却到处找不到充电器,最后才在床底下找到……
从大学相识,到在一个锅里摸勺,陈泗不否认,自己“皮袍下面”着实藏着个“小”字。
大一时,邬青崴了脚,陈泗抱着她进教室,回宿舍,上楼下楼。一周后,自己能上下楼了,又追加了一周。陈泗问,明明你自己能走了,咋还让我抱?
恢复得忒快。邬青说。
让人抱还上瘾了?
算是吧。邬青一点也不掩饰,从小,父亲就喜欢抱我,抱起来不是塞给我块水晶糖,就是亲我的脸蛋儿。边亲边说,俺青儿真俊,不搽杏仁蜜,一样招人疼。都上初中了,还嚷着让父亲抱,父亲瞅一眼母亲,象征性地抱我一下……
还没听完,陈泗就憋不住了——好家伙,敢情把我当成你老子了!等着,我早晚把你弄到手。陈泗瞄一眼她的腰际,心里话。可大学四年下来,邬青总对他若即若离的。哪个美女后面不是一拨一拨的?不是当年的夙愿犹在,陈泗显然也不施以援手,介绍到自己单位来。但天理良心,在稀里糊涂地走进宾馆之前,两人是清白的,绝对。
当啷——哗啦——
喵呜——喵呜——
走完第二个九级台阶,来到101室门口时,大脸猫也蹿了下来。室内像是一只水杯砸向防盗门。惊得陈泗一哆嗦,稳定之后,才转身走剩下的十二级台阶。大脸猫吓得辨不清方向,惶恐之中又蹿上楼去。整个中单元都知道,101室男主人很牛逼,平均两三个月换一个女主人。只要听到三天一哭,五天一闹,保准,这是又要换了。
邬青乱拿乱放的毛病,也许是被陈泗说疲沓了,别说哭闹了,连犟嘴挑理她都免了,也从不往心里搁。一日三餐,照样热汤热饭。
他俩开房的事传开后,邬青的临时工被辞,先在超市当服务员,后干保洁,因她乱拿乱放的毛病,被先后辞退。眼下所在的绣品厂,工作台上明明有自己的小剪子、尺子、绣花线,上午还在,下午,基本就一样不剩了。一旦要用,随手再取附近姐妹工作台上的。时间一长,老板耳朵里灌得满满的,但老板听惯了邬青一口一个伯父伯父地叫着,并不辞她,安排她专门剪线毛。剪线毛不用到处乱动,你老么实地坐那儿,一片一片地,把边角线毛剪干净就万事大吉。一坐一天,低着头,不停地剪呀剪。回家后,急三火四地做好饭,再不停地揉搓脖子,晃脑袋。陈泗由办公室主任贬成调度科的小职员,调度数据,填填表格,眯着眼也能完成。晚上回家,精力倒是充沛,却心里窝火。男人一不顺溜了,自然想那事。邬青呢,一坐一天,颈椎疼得要命,床上自然大打折扣。没办法,陈泗只好到女儿床上将就。女儿却死活不让,最后,沦落到睡沙发……
走过一楼转角处,开始下最后的十二级台阶。
兴许是101室摔水杯的响声忒大了,走到第二级台阶时,陈泗还回头张望了一下,收回来,正好遇上邬青的目光。相对,也只是一霎霎儿,陈泗再次移到美人痣上。
咕咚——咕咚——
新婚之夜,陈泗盯着怀里的邬青,轻轻地抚摸着美人痣。
你稀罕?邬青问。
嗯。
该让你第一个摸。
我何尝不想,现在也不晚。不过,我摸着摸着就想起了蜘蛛。
蜘蛛咋了?
雄蜘蛛一旦交配……陈泗描述了一遍网上看到的内容。
吃着碗里,瞭着锅里。你们男人净是馋猫儿,光兴自个儿放火,不兴旁人点灯?
你终于归我了,当然不许。
咕咚——咕咚——
喵呜——喵呜——
大脸猫可劲地叫着,从楼上蹿下来。一直找不到发泄对象,蹿出楼道后,失落地奔向东单元,很快又蹿回来,蹿进楼道。
爸爸这会儿怎么笑了?大脸猫蹿上去,爸爸抱着妈妈下来,爸爸竟还露出了喜欢脸。丫丫疑惑地打量着陈泗,额头紧蹙:从昨儿个下楼,爸爸的脸,跟幼儿园好凶人的老师一样,谁都躲着,今儿咋了?妈妈听话了?
周三
疙疙瘩瘩了两天,担心让丫丫看出来。昨天下午从幼儿园接出来,邬青送到娘家去了。
咕咚——咕咚——
喵呜——喵呜——
吃完早饭,邬青像前两天一样,站在门口等着。陈泗出门后,弯腰欲抱她。蹿上来的大脸猫围着陈泗蹭,转身看猫时才发现没换衬衣。掏钥匙,准备回屋换。邬青说,花格衬衣不在衣橱左边,就还在阳台上挂着,我记不清了。
睡沙发一个月左右,陈泗酒后嘟囔,这家到底是谁的?我连个睡觉的地儿也没有。当天晚上,邬青主动睡沙发,让出大床。只可惜一张空床盛不下他胀满的欲望,合上眼,眼前一会儿是杏仁蜜,一会儿是邬青,两个女人的腰际交替飘荡着。飘得时间最长的还是杏仁蜜,因为她少了那堆赘肉。没有赘肉,再不搽膈应人的破杏仁蜜,就更好了……这不是陈泗的空想,在他一次又一次睡沙发后,去杏仁蜜那儿给儿子过生日时,梦想终于照进现实。回家后,身上带着杏仁蜜的味道,邬青认为正常。可不过生日时,再闻到他花格衬衣上还散发出的这味,她心里就一哆嗦。
每次回来晚的理由都是加班。加班,若干次之后,邬青再没心没肺,也不会不明白,他俩出事后,陈泗由一个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降为一般人员,很少加班。乱拿乱放的毛病改不了,邬青就在床上补。歇班了,顾不得颈椎疼不疼,咬着牙能坚持几次算几次。
咕咚——咕咚——
喵呜——喵呜——
这时,两人来到第一个转角处。花格衬衣右边的领子窝在里面,邬青替他展开后,目光向上一挪,正好碰上陳泗的目光。邬青以为他又在看美人痣。光注意他的衬衣了,邬青忽略了自己的衬衣,胸前的第二个扣子没有扣上,抑或说她有意没有扣上。确实,陈泗由美人痣,穿过脸蛋,游弋到脖子以下,定格在扣子两边的点上。
那是两个让陈泗梦牵魂绕的点。从大学里邬青崴脚之后,多少回在梦里甜蜜地飘来荡去,终于等到在宾馆开房后如愿以偿。第二天上班后,趁旁人不注意,陈泗递给她一张字条:你今天怎么老是捂胸?她在字条反面写好答案,再还回去:问你自己!陈泗与杏仁蜜离婚前,儿子每次吃奶,他老是盯着,直到杏仁蜜提醒他了,他才醒过神来。当年抱着邬青上下楼两周,总感觉有两只小鸽子,扑扑楞楞地要从她怀里飞出来。儿子每次吃奶,都像是衔住的鸽子。在宾馆里,他终于像儿子一样衔住了。生怕鸽子干渴,不停地喂鸽子唾液。更担心鸽子一翅子飞走,死死地衔住,直到邬青喊疼……
喵呜——喵呜——
来到第二个转角处时,陈泗被猫叫春声拽了回来,再瞅一眼邬青的两个点,俨然秋后熟透的柿子,压平之后软塌塌地摊在席子上。鸽子则若隐若现地飞走了。楼道太窄,飞不起来,在墙壁上碰了一下,落在地上,被猫叼走了。
贪嘴猫,给我还回来。陈泗在心里骂,你叼走了鸽子,就是叼走了老子的魂儿——抱着邬青睡一宿,起床后,陈泗在洗手间看着邬青洗刷。邬青说你不洗刷,看我干什么。他并不急于回答,绕到她身后,两只手穿过腋下,逮住两只鸽子……
你怎么小孩子一样,邬青娇嗔地说,馋猫!
不馋,我的魂儿就丢了。
这当然是在生丫丫以前。自从有了丫丫,邬青的小肚子一天比一天肥沃,肥成这堆赘肉。陈泗每每伏在邬青身上,只觉得肚脐眼以下在顶着他,好在黑灯瞎火的,当成杏仁蜜的一样找回魂儿。可一触摸到她双手垫在颈椎下,紧闭双嘴,他不得不偃旗息鼓——颈椎疼得她呲牙咧嘴时,赶紧闭上嘴。
丢了魂儿,就得找魂儿。在还没有动提那仨字的念头之前,陈泗的信念很决绝,没了魂儿,咋活?
丫丫一点也不随邬青,从小就不粘陈泗,尤其是上幼儿园以来。邬青问,丫丫,你是爸爸的小棉袄哩,咋不让爸爸跟你睡?
爸爸不光打呼噜,丫丫小嘴一撇,一脸不屑地说,还跟老师凶小朋友一样,老凶你,烦人。
洗完澡,邬青老是忘记拔下热水器的插头,一通电一宿。翌日一早,少不了陈泗的数落。有错在先,邬青也不还嘴。有一回周末,都吃过早饭了,丫丫在画光头强。听爸爸还不住声,先用手捂住耳朵,继而停下画笔,悄悄拽拽陈泗的衣角,妈妈不关,爸爸也没关啊。还问邬青,妈妈妈妈,你怎么不凶爸爸呢?
咕咚——咕咚——
一开始挨凶,邬青还纳闷儿——当初对办公桌时,陈泗不是不知道自己丢三落四的毛病啊!咋一个锅里摸勺了却容不下自己呢?
大脑里的内存显示过后,凝重了邬青的表情。走出单元门口,邬青已做好把自己放下的准备了,陈泗却不由自主地使劲抱了她一下,才放下。还说,你脸色不好,要不,在家歇歇?
邬青顺口应着,背对陈泗,尽量不让泪水溢出。等陈泗走远了,她才转过身来,去推电动车,恍恍惚惚地。电动车报警了,这才记起还没插钥匙。
掏钥匙,打开,邬青刚要推,西单元那位老人听着收音机,正从楼前经过,用手一指,意思是前轮还锁着呢。
喵呜——邬青说声谢谢,弯腰打开那把U形锁,一抬头,大脸猫正在前轮前冲她叫……
周四
喵呜——喵呜——
大脸猫叫春到今天,声音明显降低,也许是叫累了,却多了一些茫然与惶恐,虽然还在蹿上蹿下。
咕咚——咕咚——
三天来,陈泗的每一脚,脚脚踩在邬青的心口上。为躲避陈泗的目光,邬青时而闭上眼睛时而睁开,与其说一直在琢磨,不如说在纠结,纠结他脚步的快慢。慢了,充其量多挣扎一会儿;快了,不是挣扎成功,就是失败。快点好,还是慢点好,邬青吃不准。
邬青嵌进了陈泗的身体里,重新回了一下炉,重生后回到了她大学时代。陈泗天天抱著她上楼,整宿整宿在床上折腾,直至陈泗成为面条一样,风一吹就倒,她心疼地把他拉起来,说你找到了魂儿,却掏空了身子,多不值当……陈泗强撑着身子又要去抱她,她却四处躲藏……
昨天出单元门时,陈泗也明情,自己使劲抱了一下邬青,晚上,躺在床上反思自己为什么有这一举动,三琢磨两琢磨,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怀里抱着邬青,重温着昨夜的梦境,陈泗淡淡地一笑,继续下台阶。
咕咚——咕咚——
笑自己痴人说梦,还是舍不得邬青?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可不是舍不得,干嘛深情一抱,是考虑到明天就是周五了,使劲抱一下,彻底放手?陈泗说不好,心里疙疙瘩瘩的,只好接着昨天夜里继续反思:你把人家抱上楼,眼下凭什么又推出去?是要找第三个女人,还是跟杏仁蜜复合,就能找到魂儿?陈泗真有些吃不准。可以肯定的是,昨天下台阶,他确实注意到邬青脸色凝重,眼睛时开时闭,昏睡一般。几次张了张口,欲问邬青为什么,最终还是作罢,但脚步明显放慢。这一慢,感觉怀里的邬青比前几天轻松多了,一如第一次抱她上楼时那样轻松。手上轻快了,心里也跟着轻松。这可是三天来从未有过的难得心境。哪里来的好心情呢?——墙上的“牛皮癣”不见了,墙面刷洗一新,换上了新纱窗,楼梯扶手露出了本来面目草绿色,总之,楼道里清亮了许多。看来,老太太觉悟了,没等参她,自觉把楼道收拾干净了,包括墙角的蜘蛛网。事实上,泰城争创全国卫生城市开始了。
清亮的楼道似有一束光亮,穿透了陈泗的胸膛,但白净的墙面,亮得有点让他刺眼,以至于眼睛灼痛,在四下里睃巡了一圈之后,回到邬青脸上,短暂停留后又扭向墙壁,因为他看到了一张模糊的脸,与他记忆中无法重叠——这还是那张熟悉的脸吗?
咕咚——咕咚——
迷迷瞪瞪中,陈泗忆起了邬青第一天报到时的情景——我毕业后一直在企业,机关工作包括人情世故啥都不懂,没心没肺的,老同学得多照顾。坐在陈泗对面的邬青,笑着说。
慢慢适应,没问题。那是他第一次对邬青说没问题。
后来,俩人真出问题后,陈泗很认真地端详了一下办公桌对面的邬青。造化可真会耍弄人,一个缺心少肺的女人,偏偏生得如此标致——丰腴红润的脸蛋,凹凸有致的身材。大学期间如果是花骨朵,而今已盛开绽放。一笑俩酒窝,加上那颗美人痣,再盘好头,杏仁蜜给她提鞋的资格都不配。可眼下面对的是,邬青脸蛋干瘪,酒窝显浅了;美人痣虽在,少了丰腴的衬托,倒像是随便洒落的黑芝麻;如果削去小肚子上的赘肉,整个人就是拉长的水桶。
离婚时,俩人都是净身出户,除了工资,几乎上无片瓦。登记后,好在申请了一套40多平方米的廉租房。婚礼那天,亲戚朋友都敬而远之。说是婚礼,实际上也就几个同学前来捧场,才不至于太冷清。喜宴后,进屋站了一站,同学们就都走了。被辞退后,邬青干服务员,干保洁,直至进绣品厂,目的是不让自己闲着,多挣一分是一分。生丫丫的头一天,上班走到半路,疼得实在受不了了,才给陈泗打电话。生下丫丫,邬青无法上班,只好在家加工手串。白天,迁就丫丫睡着了,她连饭也来不及吃,为的是多串一串,多挣个仨核桃俩枣。舍不得买洗衣机,葱白一样的手指,洗衣服洗得早已关节分明,糙如树皮。陈泗下班回家后,饭做不中,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玩手机等着,也从没搭把手。尽管这样,陈泗还整天数落邬青丢三落四,连丫丫都看不惯他……
咕咚——咕咚——
喵呜——喵呜——
哪里来的野猫,叫得烦人。邻居203室的女主人从外边回来,在一楼转角处,见到大脸猫,话说出来了,也看到了他俩下楼来,眼神顿时由埋怨换成羡慕,满眼放光地接着说,哟,你俩还这么浪漫啊!
这也是个张开嘴就能看到肠子的女人,男人在外有了相好,生了孩子都上一年级了,把房子都过到相好的名下,离了婚,女人才明白真相。没地儿去了,申请了廉租房。既然是一墙之隔的邻居,就经常过来串门。每当邬青劝她再走出一步时,她总是瞅一眼陈泗,叹口气说,我哪有你的命好,摊上个心疼你的男人。
陈泗跟人家点头微笑后,溜墙边往里一靠,让过去,扭回头,刚好撞上邬青的目光。他还保持着笑容,邬青局促地动了动嘴唇,似乎是在配合自己,等又合上了,他才跟着合上。
要是邬青不上班,也当全职太太,头发盘成仕女的样子,也涂脂也抹粉,天天打扮得顺条顺绺,能不红润丰腴、凹凸有致?美人痣能会像散落的黑芝麻?邬青是邋遢,哪个女人愿意邋遢?可为了多串一串手串,连饭都顾不上吃,更不要说打扮得顺条顺绺了。还有她的颈椎疼……
钻杏仁蜜那儿找到魂儿吗?一个声音打断了他。
喵呜——谁稀罕你的破魂儿,还你。那个声音好像是大脸猫的。
魂儿落我这里了。又好像是蜘蛛的声音,赶紧拿走吧。
颈椎——找魂儿——陈泗眼前一亮,彻底照亮了他的胸膛,居然还出了一头汗。
走出单元门口,陈泗小心翼翼地放下邬青,又一把拉进怀里,像当年在宾馆里打开房间后,深情一抱。这才去推电动车,汗,也顾不上擦。
邬青愣在了门口,如坠云里雾里。大脸猫今天也很反常,一直跟在他俩后面直到出单元门,见男的放下女的,再次抱了一下,大脸猫跟邬青一样纳闷儿,扭动了几下尾巴,喵呜——喵呜——
他咋还出汗了呢?邬青不明白。今儿虽说立夏,也不至于吧?雾里看花一样,望一眼陈泗远去的背影,邬青轻巧地将钥匙一下插进电动车。
周五
一立夏就热乎辣的,甭费事了,咱出去吃。从周二开始,邬青要比平时提前早起两个小时,盘好头,再准备早饭。正打算开火下面條,陈泗制止了她。
锁好门,一抽出钥匙,邬青就被陈泗抱起来。
咕咚——咕咚——
喵呜——喵呜——
不知道什么原因,大脸猫今天不见了,但它的叫声依然还萦绕在楼道里,一如既往地配合着陈泗的脚步。
早饭没吃,我自己下吧!迈下两级台阶,邬青说着还要挣脱下来。别动。陈泗不但没有松开,反而像第一天那样向上托了一托,生怕邬青掉下来似的,稳稳抱住,几乎是脸贴着脸地提醒着,且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轻轻松松地下楼,骑上电动车,两人直奔合欢饭店。
肉丝面,两碗。落座后,陈泗招呼服务员。
肉丝面端了上来,热气腾腾。
这时,邬青的手机响了。屏幕显示,丫丫姥姥打来的,起身接电话。
早在他们入住小区时,饭店还只是一个小吃店。申请到廉租房后,俩人打扫完卫生,又累又饿,就在这里吃面。鉴于是婚后第一顿饭,陈泗提议,一人再来瓶泰山啤酒,庆贺一下。
邬青端起碗,与他的碰了一下,算了,一样干杯。说着,泪水洒落在饭桌上。
不是净身出户,俩人肯定不会住这儿——廉租房作为政府的福利,是给下岗职工和特困职工等弱势群体建设的。泰安出租房子的遍地都是,依陈泗的意思,宁肯租赁个人的,也不申请廉租房。邬青说,一个月租金还不到一百元,先住着吧。
两碗面一碰,碰落了邬青的泪水。邬青一掉泪,陈泗的鼻子也跟着发酸。小两口倘若对着两碗面簌簌落泪,无疑要吸引其他顾客的眼球。以洗把脸为名,陈泗躲开了。回来后,邬青还在等他。面,早就坨了。可陈泗感觉,那是天底下最可口的美味。
光知道蜘蛛有同类相残的习性,陈泗不知道具体原因。就在昨天晚上,终于在网上查到,雄蜘蛛不是不愿意与配偶交配第二次,一旦有第二次,就意味着精尽体亡,心甘情愿被配偶吃掉。
丫丫闹着要回来。邬青收起手机,重新落座,说,她姥姥让去接。
吃面吧,别再坨了。说着,陈泗还替邬青把面挑了几下,吃完,咱赶紧走。
饭后去干什么,陈泗没有说清楚,邬青也没有问。
饭后,陈泗说忘了拿钥匙。两人返回家。来到单元门口,邬青第一个扎稳电动车,意思是陈泗不用上楼了,自己上去,谁知他一把抱起邬青,旋风一般,径直上楼……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