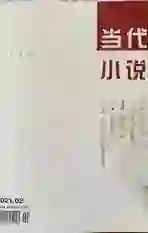他不是我二叔(短篇小说)
2021-03-26杨雅星
杨雅星
二叔没了,他膝下无子,父母让我以儿子的身份给他送葬。
我并不愿意领这差事,这种事情无论放在谁身上都是难为情的。何况我才十六岁,正是傲骄的年龄,同学要是知道了,肯定会笑话我的,尤其是飞燕。最近她看我的眼神有点崇拜的意思,若是让我扮演那个人的儿子,她是不是就要收回那点崇拜了。但是,父母说,你也就这么一个二叔。他生前也算是疼过你,还给你做过一把木手枪呢。
我嗤之以鼻,这把手枪的命运很模糊,也许还放在家里不知道哪个箱子里,也许是哪一年大扫除时早就被扔掉了吧。父亲看我不屑的样子,有些许焦躁,他下了命令,你二叔才四十多岁就没了,你奶奶伤心得晕过去好几次。平时她最疼你,如今你不送送他,你奶奶不是又要哭晕了吗?在孙辈里,奶奶最疼我,我最不能看见奶奶的眼泪。于是心里万般不乐意,但是身体也由着他们驱使到了二叔的灵柩前。
我们这里没了人,要在棺材里放三天。第三天的时候,才会在众亲戚不舍的哭泣声中盖上棺盖。二叔没有子嗣,并不会像别人家那样,有声势浩大、哭喊声此起彼伏的悲痛场面,也不会有人嘴里念念有词,犹如一群老和尚在唱经一般的肃穆场面。
我们守在灵柩前,村里管这种事的大爷们把虚掩的棺材盖移开。我并不想刻意去看里面的二叔,但是我长得高,体育课上站队跑步,我总是在最后一排。教室里上课一般也在最后一排,除非有段时间总是捣乱,老师就会让我坐在第一排靠墙或靠窗的位置。
此刻棺盖打开,我的眼睛顿时落在了棺材里的人身上。乍一看,并不是人,而是缩成一团的不明物,也许是一只被拔掉浑身毛刺的刺猬,也许仅仅是一团破败脏乱的棉絮。棉絮外面的一张脸,是一张枯黄的皮裹着两块颧骨,这张皮上有个黑洞,那是嘴巴。我不由得一哆嗦,觉得自己要被这张无底洞把魂儿给吸走了。幸好,那张嘴巴里放着一枚亮闪闪的硬币,挡住了入口。
我赶紧收回眼神,这时大爷却又吩咐,各自往棺材里放点钱,或者什么能寄托感情的小物。父母,还有姑姑,以及我堂姐——姑姑家的大女儿,都往里面放了点钱。我手里什么也没有,寻思正好不用放了。谁知,母亲却给我几张钱让我放进去,我战战兢兢,手臂抬在棺材的上空,手就一哆嗦,钱顺势掉进了里面,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终于要盖棺了,这次是要用钉子把棺材牢牢地钉住。大爷们拿着家伙什开始钉棺,父母就开始喊,笙,笙,你别怕,我给你盖房子挖厦。笙,笙,你别怕,我给你盖房子挖厦。
你们两个也跟着喊,你,父亲指着我,你喊的时候要记得叫“爸”。
我指指棺材,指指我自己,满腔不满,嘴里但也跟着喊,你别怕,我给你盖房子挖厦。以前,别人家没了人,小孩子都会看热闹的。只觉得他们念念有词的样子很诡异,只是无端地生出敬意,并不知道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今天终于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就是给死了的人盖房子,让他们在地底下有地方住。
“当当”的钉棺声,听起来那么刺耳,每“当”一下,我就心惊肉跳一下,好在大爷们效率颇高,钉棺仪式终于在我们若有似无的哭泣和念念有词中结束了。
那夜,我们要祭灵,在灵前哭逝去的人,并绕着祭桌哭三圈,当然是由管事的大娘、奶奶们搀着哭。祭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祭品,有各种各样的点心和水果。桌子正前方,摆着一个经过化妆的彩色猪头,这个猪头和飞燕小时候的毛茸茸的猪猪差远了。飞燕挂着鼻涕的童年时候总是爱抱着它。
那时候村里但凡有葬礼,我们必定看热闹。那些老的少的,披麻戴孝,拖着一根光秃秃的玉米秸秆,弓着身子,绕着灵堂一把鼻涕一把泪。哭诉着他的娘,他的爹,他的七大姑八大姨,为啥就狠心地去了,再也不管他了。
我们幼小的心偶尔会随着哭声升起一股莫名的忧伤,但我们更在乎的是桌上的点心和水果。祭礼一过,这些点心水果必定被我们抢食一空,除了那个长得像小丑般滑稽却又无比威严的猪头。那时候的葬礼,是我们平淡生活里神圣又有趣的事。
对二叔的祭奠仪式很快结束,之后,我们就在灵堂守灵。说是灵堂,只是用一张勉强能遮风挡雨的帐篷搭建而成,地上铺着足够厚的麦秸,因为在里面跪着的时间可不短。
唉,才四十多就没了,真恓惶……我听帐篷外面的大爷大娘唏嘘不已。
二叔恓惶吗?我好像需要重新审视一下二叔了。在我眼里,他一直是我们家族一个代表羞耻的符号。小时候同学提起他,我还和同学打了一架,说不认识这个人,他不是我二叔。
待在这个隔绝外人的灵堂,这漫长的时间里,足够我回想一下恓惶的二叔。
二叔一直是个光棍,但他曾经有个老婆,也曾经有个孩子。
据说他二十岁左右时,瘦瘦高高的,总爱穿着一身浅色的西装,总爱把头发梳得层次分明。他初中毕业,在村里也算有点小文化,甚至在哪年桃花红杏花白的季节里还做出了几句诗。村里有好几个暗恋他的姑娘,都暗示家人说媒。但是,他很快就迎来了人生的一个很大转折。
那個年代,村里人结婚早,20岁是正常的结婚年龄,二叔的伙伴们陆陆续续娶了自己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新娘子。那天是飞燕她三爷家的小儿子结婚,新郎官一直闹着不肯娶,说是嫌新媳妇长得不好看,嘴巴太大,还是个地包天。
飞燕她三爷硬是把儿子塞进了借来的桑塔纳轿车里,把他赶进迎亲的队伍里去。后来人们闹起笑话来总是说,她三爷是“赶鸭子上架”。
因为二叔长得白白净净,还有点帅气,迎亲的队伍里自然是有他,他一度是我们村的门面。女方家有钱,自然也有好酒,不免三杯两盏地喝多了。没人具体记得二叔那天究竟喝了多少酒,反正没有到了趴下的程度。
媳妇接回来后,当然要闹洞房。小伙子们把客厅的门用身体堵得严严实实,里三层外三层。新郎抱着新娘往里挤,挡着门的小伙子“哟哟”地喊着号子,新郎一使劲,他们就发出一片欢呼声,假情假意地挪腾一下身子。看似这堵人做成的门终于松动了,新郎就会乘胜追击再次冲上去,却仍然是密不透风的墙。
如是几次,新郎就会疲累,终于抱着新娘要做最后的冲刺了,人做成的门却赶在他们冲刺之前,像大坝开了闸。二叔作为大坝的一员却反应晚了,这不能怨他,怨他身后的人反应晚了,新郎抱着新娘径直冲到了二叔身上,然后三个人又一齐压在了后面那个人身上。后面那人正是村长家的老三。
“妈的,眼瞎了吗?”村长家的儿子拳头眼看就要抡上二叔的头,一场争斗在即,但是眼明手快的伙计们早就把我二叔架出去喝酒了。
新娘进了婚房后还需煞费苦心找她的红鞋子,不过这份热闹都是女孩儿们的事了,男人们都在外面喝上了酒。
这本是一场村里再正常不过的婚礼,这场婚礼也许并没被几个人记得。但是这场婚礼过后,二叔却让很多人无法忘记了。
新婚的第一天,新娘的一声尖叫划破了村庄的黎明破晓,也揭开了二叔人生崭新的一页。新娘一大早起来扫满地的瓜子皮,当她掀起床单扫床下的瓜子皮时,赫然看见一个男人正在酣睡,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吓得尖叫。
也许她不叫就好了,后来人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总是这么感叹,然后就有人适时地插话,感叹着这个女人的无奈,唉,她要是不叫,人们会觉得她和老二的确有一腿。
是的,床底下那个人就是我的二叔。二叔被新娘的尖叫吓醒了,新郎把二叔拽出来时,二叔不知道是睡得迷迷瞪瞪,还是被吓得迷迷瞪瞪。总之,从那之后,二叔经常是这样迷迷瞪瞪的。他可能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在别人家的床底下。
新郎一家把二叔绑到村委会,村长给二叔上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教育课。教育课非常有效果,二叔从此再没有参加任何一个人的婚礼,再也没做过任何人的伴郎,甚至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做过新郎。
二叔长得帅,有点文化,不适合在村里种地,于是进城去打工。刚进城后,他好像是在一个印刷厂里打工,干了不到两个月;后来又在一个理发店里做学徒;然后还在一个饭店里当过跑堂的。再后来听说,村长家的老三,头被人打破了,住院缝了好几针,听说出院后,这个纨绔子弟变得有点呆傻。然后我二叔从此就消失了。
爷爷奶奶日渐苍老,尤其是在二叔消失的这几年里,爷爷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扛着锄头,走在田间小路上,爷爷的脸上挂满了心事。
在一个秋风扫过落叶的季节,二叔回来了,还带着一个模样很是端庄的女子。大家都凑在一起议论纷纷,老二在外面骗了一个女子。这个女子是云南人,还有人说这个女子是马来西亚人。总之一定离我们这里很远,不然凭二叔那样的名声,哪里能讨得下媳妇。
二叔这一年二十五岁,风华正茂,正是婚嫁年龄。病恹恹的爷爷也好像一下子健康了起来,似乎从前并没有生过什么病,他和本家和村里的乡亲们一起张罗着儿子的婚事。
婚礼那天,秋日的艳阳高照,二叔和新娘子穿上一身红衣拜堂。隔壁家的土坯墙上却跃下来几个人影,那是几个穿着便衣的警察,讯问几句后,二叔就被戴上手铐带走了。
眼明手快的老人赶紧张罗了一只公鸡,脖子上,鸡爪上系上红布条,塞给新娘,新娘被推着搡着拜堂成亲,和一只肥硕的大红公鸡度过了漫长的洞房花烛之夜。
第二天一大早,爷爷出来扫院子,看见自家的木头院门敞开着,新娘在凉风习习的早晨跑了。爷爷晃了晃就倒在地上再也没站起来,爷爷突发脑溢血。出院后,他整日躺在床上,吃喝要人喂,屎尿要人倒。
六个月后,那个新娘偷偷溜回村里。趁着大家都在地里,家里没人时,她给炕上放了一个襁褓,又不见了。众人知道了都纷纷跑来看,一会儿说,和老二的嘴巴有点像呢。一会儿又说,这老二又不在家,这娃来历不明,不能留。
奶奶把襁褓中的娃娃抱在怀里,端详了一会儿,终于放心地哭了,这眉眼,这嘴巴,连这小鸡儿,都和二娃小时候是一样一样的。她趴在爷爷耳朵边,说,这是你家的种呢,是你笙儿的娃。爷爷嗯嗯啊啊了几声,流了几滴浑浊的老泪。没几天爷爷就去世了。
三年之后,二叔服刑结束,像迟到的学生走进教室,众目睽睽之下,故作淡定地回了村里。他再也不复以前帅气的模样。吃了几天牢饭的人,变得更加白皙,就像村里的女子坐月子似的那种白,是那种因为不见阳光,缺少身体锻炼的白。他越发不爱开口,只有在谁家红白喜事的酒桌上,二两酒灌进肚子里,才能看出他不是一个哑巴。
也只有在酒后,他才会想起那个娃娃。娃娃已经三四岁,整天就知道吊着鼻涕,光着腚在乡村飞着蜻蜓的小路上捉蚂蚱,或者和一群小朋友往一堆土上撒上尿,美滋滋地和泥巴。
那天二叔把那个娃娃抱在怀里,亲了又亲。一定是酒气熏人,胡子拉碴扎得那个孩子疼,孩子就踢他,在他怀里哭闹不止。红着眼的二叔把孩子放下来,孩子撒腿要跑,二叔拎了孩子的一只胳膊,把娃娃的整个身子提起来,抡在半空里,画着圈圈。
夕阳的火光里,那个孩子就像一簇挥动着的小火苗的影子。路人把孩子从二叔的手里抢下来,给了奶奶,奶奶紧紧抱着孩子,骂二叔是个六亲不认的魔鬼。二叔拿着酒瓶子,腿软软地站不稳,嘴里含糊不清,我有亲人吗?孩子在他手里終究是活不下去的,二叔又在一次酒后,把娃娃扔进了水缸。
我长大后,问过奶奶那个娃娃最后的结局,奶奶说送人了。我却坚持说,肯定是被淹死了。善良的奶奶不忍心说出“死”这样的字眼。她骂二叔时,骂得狠,但总是流着泪。
二叔从牢里出来,什么活儿都不干。日上三竿,村里老人都去地里干活儿了,二叔仍旧在床上睡得昏天暗地。家里水缸没水了,奶奶说,去挑桶水回来,二叔就说,你不会去挑吗?该收麦子了,奶奶说,去把地里割好的麦子拉回来,二叔蒙着头说,不去,要那些东西干啥?奶奶气急了,就会拿笤帚打二叔,二叔把头往奶奶手底下钻,你打呀,打死我吧。
姑姑在市里有点小脸面,托人给二叔找了个活儿,在一个旅游景点当管理员,干了两年,竟然混成了合同工。他具体干些什么活儿,我没大听他们详细说,反正每月按时领钱,糊口绰绰有余。
二叔自此迷上抽烟喝酒,也更加不听奶奶的话。
奶奶说,你都三十多了,娶个媳妇儿吧。
二叔却顶撞,要娶你娶,我不要。
眼看都要35岁了,在村里,男的35岁还娶不到媳妇,意味着这辈子就要打光棍了。奶奶着了慌,一直央求着爸爸和姑姑,你们的亲弟弟,你们能眼看着他打光棍。
于是爸爸和姑姑四处托人给他找媳妇儿。邻村有个女的,36岁,带着个十岁的男娃,人长得不赖,也勤快。前面那个男的出车祸死了,一年多的时间里,她没心思再找。如今听说这个男的有份还算靠谱的工作,每个月有点固定收入,也有点文化,她觉得她和儿子以后的生活能有保障。
于是两家约好见见面,见了一面双方觉得行,二叔也不抗拒。正好赶上秋收季节,女方娘家有三亩玉米要收。
爸爸和姑姑说,她家就这一个女儿,你要是觉得人家行,就去她家里帮忙收玉米。去了勤快点,多干点活儿。二叔倒也听话,在某一个早晨,踩着中秋的露水,拎了二斤猪头肉,屁颠屁颠上门了。
在地里掰了一天玉米,晚上女方她妈妈把那二斤猪头肉切了,还做了些其他的菜,她爸把家里存了几年的好酒也拿出来了,爷俩喝了个饱。二叔喝多了,倒头就睡。
第二天,老爷子早早起来要上工,二叔还在睡。老爷子觉得自己挺有本事,把未来女婿都给喝趴下了。等中午他回来时,看到未来女婿还在睡,于是打发女儿叫醒他吃饭。
吃完饭,老爷子说,不休息了,直接去地里。
二叔却说,不去了,玉米叶子太扎人。
老爷子也就作罢,别把未来女婿扎出个好歹来,就让他在家里晒玉米。
二叔把屋檐下面的带皮的玉米棒子都摊在院子里,又去睡觉了。
没想到那天下了阵雨,他们从地里匆匆跑回来,浑身上下湿漉漉淌着水。院子里的出水口被玉米堵上了,水都堵在院子里,一地玉米棒子在水里打着旋儿。
他们进去,看到二叔四仰八叉躺在床上,鼾声如雷。老爷子气愤之极,拿起擀面杖退后二尺,就要打上去。
她妈挡住说,别打出个好歹。问问闺女,这样的人,她要不要跟,毕竟能吃公家饭。
闺女已经不是二十多岁的物质女孩,她说以后过起日子来,难免不合。
于是他们把二叔叫醒,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好吃好喝伺候着。到晚上又给他割了二斤猪头肉,打发他回家了。
我听一个远房亲戚说起这事时,远房亲戚摇着头一个劲地感叹,怎么能有这么懒的人呢。这桩婚事要是成了的话,多好的光景啊。
奶奶气得不轻,用院里的扫帚把二叔好一顿打。二叔冤枉地喊着,这有什么,我又没吃亏。爸爸和姑姑后来再也不敢给他牵线了,奶奶也慢慢放弃了给小儿子娶媳妇的念头。
二叔在村里本来是有些朋友的,但是自从那次婚宴上被人家新娘子从床底下打出来之后,他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大家都结婚了,这样的人尽量避开吧,就算从小玩到大的朋友还想玩耍,但是新娘子都在有意無意地扇着枕边风。
除了永康。永康是他们这伙人里最穷的一个,即便如此,穷苦又老实巴交的永康也娶到了媳妇,是同村的一个同学。媳妇左手有点缺陷,小时候被开水烫过,食指和大拇指粘连在一起。只有去永康家,他们两口子不但不嫌弃二叔,还把家里最好的茶拿出来招待。二叔对他们也很大方,有时候去他家吃饭,也会带着几个小菜。
有一天,二叔突然失踪了,一起失踪的还有永康的媳妇儿。
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电话打到爸爸这里,爸爸一脸呆愣。那时候,我们在市里卖肉,属于村里最早进城致富的那一批,我们在市里租着一个小院。一天早上,我妈一打开门,就看见二叔领着一个女人,站在我家门外,那女人就是永康的媳妇。
我爸和我妈吓了一跳,赶紧把他们迎进来,看着这对私奔的鸳鸯,很有些不知所措。我爸想马上给村里联系,被我妈挡住了,她说这是你情我愿的事,又不是拐卖妇女,你先别声张,看看情况。
他们两个就很踏实地住下了,他们总是半卧在沙发上看电视,二叔的右手从女人的背后穿过去,轻轻搭在她的右肩上。她的左手缩在二叔的左手里,二叔摩挲着她的粘连在一起的大拇指和食指。
他们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还会偷偷亲一下。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自从他们来了,我的余光就一直在偷偷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那个女人的头发很长,很飘逸,总是散落在二叔的身上。眼睛不大,像两颗小小的花生粒,虽然熟了,但是营养不够。他们什么活儿也不干,那时候的卫生间还在院子里,他们都是跟着一起去的。就像我平时玩的橡皮泥,两种颜色的橡皮泥混在一起,真不好分开。
我妈给他们煎了我爱吃的南瓜饼,煮了紫菜蛋花汤。年底,猪肉市场大好,我们还要去市场上。我爸本来要把我留在家里,我妈却示意把我带走。
我们到天黑才回来,他们已经睡下了,冰箱里所有的熟食一扫而光,幸亏我在夜市上吃了肉夹馍,要不就得饿一整夜。
第二天我妈一大早起来蒸了包子,他们还在睡。晚上回到家,包子也都吃光了。后来几天我妈就不再做饭了。临近年关,市场上确实很忙,再说就算做了,也吃不到我们嘴里。
用我妈的话说,这对祖宗待了有一个礼拜左右吧,说要走了。临走时,二叔给我留了一把木制的枪。那时候,我的玩具并不多,这把枪我着实稀罕了一阵子。
除夕,我们回老家看奶奶。奶奶老了很多,灰褐色的头发稀稀拉拉,脸也比以前消瘦了。奶奶一只手拉着我的手,另一只摸着我的脸,我靠在奶奶的怀里像个小猫,我们还像小时候。只是奶奶的手不再像以前那么温暖了,手上的肉少了,那些老茧就像树上长出了刺。
奶奶哭着问我姑姑,笙可怎么办?
姑姑摇头叹息着。
就在这晚,大年三十,二叔回来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二叔推门进来了,却是一个人。爸爸问,你领的人呢。
回她家去了。
回娘家了还是永康家。
过年呢,当然是和她孩子男人一起过啊。二叔似乎很明白事理呢。
你还知道人家有男人有孩子。拐人家做什么?你拐就拐了吧,这又各回各家是什么意思?
身上没钱了。过年呢,外面的饭店也不开,没地方吃饭。
我们都以为,二叔这一次又得吃官司。姑姑头疼地说,又得丢这张老脸了。我们都等着永康找上门来讨伐,没想到永康却说,媳妇回来了就行,她说以后再也不这样了。笙也是我唯一的好哥们,就这样吧。
我们家过意不去,给了永康家一千块钱,说是给孩子当学费。
村里的人又戳了我们家一阵子脊梁骨,“朋友妻,不可欺”,这话我以为就长在书上,没想到也能发生在我们家里。
二叔也不再去永康家了,他和永康媳妇之间有没有爱情,我们真的不知道。有时候我希望他们之间爱过,只是迫于道德伦理,他们不能在一起。我希望二叔贫瘠得荒漠一样的感情世界里,也曾长出过一只嫩芽,我希望他有过爱情。
二叔不再去永康家之后,却串起了别人家的门。别人也开始不再像以前一样防着二叔了。慢慢地我也听说了,村里流传着一个新鲜事儿,二叔那方面不行。
在村里,一个男人,如果那方面不行,别人看你的眼光就怜悯了很多。所以二叔曾经做过的龌龊事,好像一下子就被人原谅了。他去任何一个朋友家的时候,别人也就不好意思表现出闭门谢客的意思了。但是二叔也不白坐着,临走,他刚刚打开的那盒烟,一定放在朋友家的桌子上。
有几次,有人家办红白喜事,爸爸和妈妈带着我去。我在他们家里会看到二叔,二叔坐在客厅的木凳子上,和众多人一起喝着茶,抽着烟,我倒觉得他真正常,终于和别人一样了。他聊着天,经常会聊着聊着就咳嗽起来。咳完了就端起茶喝,放下茶杯也就不聊了。
后来我还见过他几次,他的食指和中指夹着烟,烟一直在燃烧,很久他才吸一口,这一口却几乎把整支烟吸完。
他最常做的就是一边聊着天,一边不停地做着弯腰的动作。他总是跷着二郎腿,腰像虾米一样弓着,两只胳膊肘支在大腿根部。这个姿势本身就是一个蜷曲的样子,但是他还是把腰更深地弯下去,又直起来,弯下去,又直起来。当然这个直,不是我们平时那样的直。他手里的烟,也跟着晃来晃去。根据我仅有的生理知识,我觉得他一定是得了前列腺炎。
有时候,我们会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他问我学习怎么样,身体怎么样,我都含糊着,不和他交流。他总是给自己添一杯酒,一口喝完,咂吧着嘴,说,这小子,长大了。
匆匆吃完饭,我就跑了。和他同在一个空间里,我都觉得不愿呼吸。
后来我上学,看见他的机会越来越少。我几乎忘掉自己还有这样一个二叔。我甚至希望飞燕,希望我的同学们都忘记我有这样的二叔。
时光就像阳光,会照耀你,让你在某个阶段顺风顺水,自带光环。就像我和飞燕在初中最后的时光,我们被圈在幸福的光环里,转晕了也不自知。
它也会溜,会躲,对你全然不顾。你的人生從此蒙上阴翳,你一直躲在下雨天的树底下,湿哒哒的雨滴从沉沉的绿叶子上掉下来,随着“啪”“啪”的声音,你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湿,越来越沉。你倾倒在地上,蜷缩在雨水和泥土里,渐渐地和那些掉落的叶子一起腐烂。
我们都需要长时间的阳光照耀,照遍身体的每个角落。它随着时间,流经我们岁月的每一条河流。这样,每次回想往事,记忆里都会有阳光。我觉得我是被阳光照耀的,无比温暖。
忽然有一天,爸爸说,回老家吧,你二叔没了。这是个插曲,是晴天里偶然一次调皮的阵雨。不过有时候,阵雨也是能把人浇透的,因为我们可能对阵雨没有任何防备。
祭完灵,我一直待在二叔的灵堂里,没人需要我这个假儿子做什么,也许大人们忙得忘了我吧。我渐渐地困了,躺在玉米秸秆铺就的地铺上,我琢磨着九月份就可以上高中了,我还能不能和飞燕在一个班。
灵堂外面传来阵阵低语声。
笙命苦呀,身体有了问题,咱就治,治不好再说。我看他从来没有治过。
咋治呀,治了是一时的。还会再犯。
本来得病死了也不为过。可是你看他弄的,死了还让人说闲话。
也不能都怪他吧,当初在飞燕妈床底下,要是飞燕妈不叫,也就私下了了,谁也不知道这回事。
肯定是村长家那个做的孽,笙心里有了梗,死也要死在那个床底下。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偷偷进去的,听说好几天都看不见他人了。谁发现的,还是飞燕妈吗?
不是,这次是飞燕,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硬邦邦的。
唉,瘆得慌。听说,笙他儿子,和飞燕正处得好着呢。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