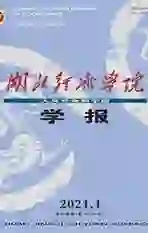交付视域下偷换二维码收取钱款的犯罪厘定
2021-01-25王风瑞
王风瑞
摘 要:二维码支付的大行其道,使得偷换商家二维码而收取商家钱款的犯罪行为逐渐出现。在新型支付方式的影响下,由于财产转移的方式不同于传统方式,对于该犯罪行为也出现了盗窃罪、诈骗罪,甚至是侵占罪的不同认识。但是,在当前的犯罪解释之下,盗窃罪无法解释商家成为犯罪的被害人但是在犯罪过程中并未占有钱款的问题,诈骗罪无法解释顾客并没有将钱款处分与行为人的意思的问题。二维码作为一种支付方式,其改变的是货币交付的过程,因此对于偷换二维码的犯罪定性也只有在准确把握交付过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通过对货币交付过程的各方關系、财产转移的时间等进行解构,将犯罪行为准确地嵌入到交付过程之中,行为人是在顾客完成支付行为之后、在商家对财产产生社会观念上占有的前提下以秘密方式实现了财产占有的转移,故应构成盗窃罪。
关键词:二维码;盗窃罪;诈骗罪;交付
一、问题的提出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电子支付取代货币支付,成为主流的支付方式。在财产的储存、支付方式更新的过程中,财产性犯罪的手段也在不断地更新。二维码在成为支付手段之下,也逐渐变成犯罪嫌疑人犯罪的手段,通过偷换商家二维码来收取商家钱款的犯罪在实践中亦有发生。2017年11月至12月期间,倪某将事先准备的微信二维码偷贴于商家用于收款的微信二维码上,从而获取顾客通过微信扫描支付给商家的钱款,共计985元,被上海金山区人民法院判处盗窃罪①。2017年2月至3月间,邹某将郑某、王某等人店里的微信二维码调换为自己的微信二维码,从而获取顾客通过微信扫描支付给商家的钱款,共计人民币6983.03元。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向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但是最后法院认定被告人行为构成盗窃罪,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检察院指控邹某构成诈骗罪定罪不当②。偷换他人二维码收取钱款的行为究竟构成盗窃罪抑或诈骗罪,不仅涉及当事人的定罪量刑问题,而且涉及被害人的确定和追缴犯罪所得后的赔偿问题,因此对于该行为的犯罪定性问题殊值研究。
二、传统犯罪构成基础上的犯罪定性
由于偷换二维码收取钱款的行为渗入了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的领域,犯罪手段的先进性使得该犯罪行为呈现出与传统犯罪行为不同的样态。该犯罪行为中既包含了盗窃罪的秘密转移行为,又出现了诈骗罪中虚构事实、认识错误等犯罪事实,因此对于偷换二维码收取钱款的行为究竟属盗窃罪还是诈骗罪存在着争议。
(一)偷换二维码收取钱款的犯罪定性之争
在偷换二维码收取钱款的案件中,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认为其构成盗窃罪或诈骗罪呈现对立的态势。
坚持“盗窃罪”论者内部存在着二元分化。一者认为在行为人偷换二维码收取钱款的过程中,顾客系行为人用以犯罪之工具,其通过利用顾客的付款行为窃取了商家的财物,属于盗窃的间接正犯[1]18。行为人与商家、顾客之间并不具有沟通交往,行为人只是通过操纵二维码抽象地使商家、顾客等人陷入行为错误之中;二维码为商家所出示,顾客并无核查之义务,故无所谓陷入认识错误。顾客的扫码行为,充其量只是“转移错误”。因此,行为人正是利用“缄默形式的财产转移”,占有了本应由商家收取的钱款[2]41,属于典型的盗窃犯罪行为。
二者认为,在行为人偷换二维码收取钱款的过程中,行为人与顾客、商家不存在任何的沟通,顾客也并没有将财物交付于行为人的意思,仅有将财物处分与商家之意思。偷换二维码的行为相当于将商家的二维码的钱包挖破了一个洞,客户的钱款穿过商家的二维码账户而进入到行为人的钱包之中[3]61-62。因此,属于行为人以秘密的方式转移财物的占有,构成盗窃罪。亦有学者认为行为人盗窃的并不是钱款本身,而是商家的价款支付请求权[4]105,行为人偷换二维码,意味着窃得商家的债权人地位,法律后果是将商家针对顾客的债权转移给自己享有,构成盗窃罪[5]106。在此种情况之下,交易过程已经结束,客户已经退出该过程之中,仅是行为人与商家发生了相互关系,因此被害人是商家,客户与该犯罪行为不产生任何关系。
坚持诈骗罪不以处分意思为必要的学者认为,诈骗罪作为一种交往沟通型犯罪,被害人的处分意思仅具有同意的表象,并非真实意思表示,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对于“财产决策事项”的意思互动才是成立诈骗罪的必要条件[6]170。商家由于行为人偷换二维码的行为而受到欺骗,误以为钱款进入自己账户;当商家同意顾客离开时,即意味着做出了免除债务的意思表示,商家虽没有处分的意思,但是实际上处分了债权,在诈骗罪的成立不以处分意思为构成要件的前提下,行为人即构成了诈骗罪[7]33。该种犯罪认定认为受欺骗者非顾客而是商家,顾客并未进入到犯罪的相互关系之中,商家是单一的被害人。
而坚持诈骗罪以处分意思为必要的学者认为,诈骗罪与盗窃罪区分的关键在于被害人意志具有瑕疵,该种瑕疵系被害人基于行为人诈骗的事实而产生了处分意思,被害人因自身处分意思而受损,属于自损型犯罪,而盗窃属于他损型犯罪[8]698。基于处分意思的必要,顾客因为受到行为人的欺骗而限于错误认识,处分了自己的财产,顾客在处分了自己的财产之后,被害人究竟为顾客抑或商家,在诈骗罪的基础上却也产生了不同的认知,形成了“三角诈骗”“普通诈骗”“双向诈骗”的不同认识。
坚持“三角诈骗论”者认为,在偷换二维码收取钱款的过程中,顾客被冒用的二维码所骗,顾客陷于认识错误并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自己的财产,进而使商家遭受损失。这属于一种新型的三角诈骗,其构造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受骗人产生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受骗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自己的财产——被告人获得或者使第三者获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9]24在新型的三角诈骗中,受骗人与被害人相分离,顾客基于错误认识按照被害人的指示处分了自己的财产,虽然顾客存在认识错误,但是其行为是按照被害人指示进行,因此不具有民法上的过错,所以商家丧失了再次要求顾客转移自己财产的权利,因此商家成为被害人。但是,亦有学者认为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系指能够引起被害人财产减损可能性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为受骗者的财产抑或是他人的财产并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9]58。因此,偷换二维码收取他人钱款的行为与传统“三角诈骗”无异,并非新型“三角诈骗”。
坚持“普通诈骗论”者认为,行为人用偷换的二维码实施了诈骗的行为包括先偷换二维码的行为和利用二维码取财的行为,行为人偷换二维码的行为不具有直接取财的性质,属于虚构事实的行为[11]126。顾客在扫码付款时,基于对于商家的信任而产生了对于二维码的错误认识,并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转移财产所有权,具有错误认识和处分意识,该犯罪事实已经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但是,顾客处分的是自己的财产而非他人财产,被害人与被骗人是同一人,因此不具备成立三角诈骗的空间。顾客的交付行为并没有实际完成买卖合同的履行,因此就是一种损害,就属于刑事法律关系中的被害人;商家的损失是由于买卖合同的履行瑕疵而产生的,可以通过民事买卖合同关系来解决,并不应当纳入诈骗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范畴[12]14-15。在偷换二维码收取钱款的犯罪行为中,被害人应当是顾客而非商家。
坚持“普通诈骗论”者亦有人认为商家只不过是行为人进行诈骗的工具,行为人是诈骗的间接正犯。当商家要求顾客扫码付款时,商家并不知道二维码被偷换的事实,因此没有诈骗的故意;但是商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得顾客陷于错误认识,错误地处分了自己的财产,在此意义上,偷换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对客观事实情状的操控,而并非一种意思联络[13]42。行为人通过偷换二维码的行为将没有欺诈故意的商家作为自己实施诈骗的工具,以间接正犯的身份实施了诈骗行为。
坚持“双向诈骗论”者认为行为人实施了偷换二维码的诈骗行为,同时使得商家与顾客陷于错误认识,顾客认为二维码为商家二维码而处分了自己的财产,而店家误认为顾客已经完成付款而处分了自己的商品,最终商家损失了商品,遭受财产损失[11]124。“双向诈骗”论显然是建立在整体财产犯罪的基础之上,对于财产的损失与获得进行整体的考量以确定是否发生了财产损失,商家由于处分了商品而未获得价款而遭受损失,成为本案的受害人。
最近,亦有学者打破原来盗窃罪与诈骗罪二元对立局面,认为偷换二维码收取钱款的行为构成侵占罪。由于顾客只知道商家的存在而不知二维码被偷换的事实,顾客仅有将财产处分与商家的意思,而不具有处分与行为人的意思,因此不具有诈骗罪所要求的处分意思;顾客通过扫码的方式支付钱款,该钱款直接进入了行为人的账户,商家未建立占有,行为人也未曾侵害过商家对于钱款的占有,也不具备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人自身的行为导致商户没有获得应得的债权利益,非法取得了被害人的财产,属于恶意占有,因此负有返还义务;尽管行为人直接取得商户收款的行为(前行为)难以被评价为类型化的财产罪名,但是一旦取得,拒不返还,那么,继续非法占有商户财产的行为(后行为)就是侵占行为[14]118。因此,偷换二维码收取钱款的行为构成侵占罪。
(二)偷换二维码收取钱款犯罪定性的症结
当前无论是“盗窃罪论”还是“诈骗罪论”,无论是普通诈骗论还是三角诈骗论,都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症结。
坚持“盗窃罪论”者,无论认为盗窃的客体为财产还是价款支付请求权,都无法解释商家在该支付过程中从未实现对于财产的占有,钱款通过二维码直接进入了行为人的账户。在商家未实现财产占有和支配的前提下,行为人偷换二维码的行为并没有侵害商家对于财产的占有,不符合盗窃罪的本质特征[14]116——通过秘密的方式或者以和平的方式转移财物的占有[15]727。
在“诈骗罪论”中,如果认为处分意识并非诈骗罪所必要,将难以划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界限,在盗窃罪中,被间接正犯所利用者往往是不知情者,如果处分意识不为诈骗罪所必要,众多的盗窃罪的间接正犯将被认定为诈骗罪[16]161。此外,仅以客观行为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将会无限扩大处分行为的范围[5]98。例如,甲在试衣服时,谎称型号不对,趁店员查找衣服之际穿衣服逃走,在处分意识不要说的背景之下,这种典型的盗窃罪也将被列入诈骗罪的范畴。坚持处分意识不为诈骗的必要,基于沟通交流而产生处分财产效果就可认定为诈骗罪,完全是为将偷换二维码收取钱款行为认定为诈骗罪而进行地曲意迎合,这将造成诈骗罪的体系混乱,不合刑法体系逻辑。
在坚持处分意识必要的前提下,“普通诈骗论”“双向诈骗论”“三角诈骗论”均无法解释一个问题——顾客仅有将财产处分与商家的意思,而未有将财产处分与行为人的意思,顾客将财产交付于行为人属于“无意识交付”,难以具有诈骗罪所要求的处分意识。处分意识是处分行为的核心内容,如果占有转移并非基于受害人的处分意识,该财产移转不能视为诈骗罪的“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17]121。顾客将财产交付于行为人,并非是基于“将财产交付于行为人”的错误认识,而是基于“将财产交付于商家”的认识,财产占有转移的行为与效果均不是建立在顾客的处分意识之上,因此难以符合诈骗罪中“错误认识”“处分意识”“处分行为”的构成要件要求。
此外,“三角诈骗论”者主张顾客处分了自己的财产而使得商家遭受损失,该种损失的转移系基于顾客不具有民法上的过错。顾客在未具有处分权限的前提下,自己处分自己财产的行为,损害结果却落于他人头上,行为与结果难以架构因果关系的桥梁。不具有民法上过错应当通过民法救济途径加以解决,因为不具有民法过错而使得犯罪构成认定的损害主体发生法律拟制转移,使得民法与刑法的结构功能错位,该案件中被害人的确定难以具有说服力。
对于侵占罪,更难有解释基础的存在。从对象上讲,侵占罪的对象限于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行为人既未获得顾客或者商家的授权,代为保管财物;该钱款亦不属于商家或顾客的遗忘物。侵占罪肆意扩大了侵占罪成立的犯罪对象,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三)小结
偷换二维码收取钱款的行为之所以在犯罪認定上存在如此多的症结,乃在于当前对于偷换二维码收取钱款的行为解构不够彻底。二维码收款行为属于交付行为,该种交付属于何种交付,顾客何时完成交付,行为人取得钱款之时顾客是否完成了交付都是在犯罪认定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偷换二维码犯罪中,二维码本身不具有财产性,犯罪行为在于取得财产的行为而不在于偷换二维码的行为。行为人在取得财产时,若顾客已经完成交付,则就不存在顾客处分财产的行为,那么就不存在构成诈骗罪的基础;若顾客尚未完成交付,则属于顾客将财产处分与行为人,则存在构成诈骗罪的可能。
三、二维码支付中交付过程的解构
交付是占有的转移,即某人将某物的占有转移于他人,包括了现实交付与观念交付[18]56。传统民法之中,交付行为一直与公示公信原则相联系,交付系通过占有的转移以对外展示物权的转移或使物权转移具有公之于众的可识别性[19]56。但是,在电子支付的过程中,货币转移的过程系在电子平台完成,不再具有标的物占有转移的外观与公示性。通过二维码进行支付是否属于货币交付以及属于交付的何种形态,需要通过对于交付进行信息时代的概念解构进行明确。
(一)交付的构成要件
传统民法将占有的概念界定为“占有转移”,但是“占有转移”属于对“交付”概念的一种过程性界定,在过程性界定的过程中,无论是从物权法视角还是从债权法视角,都会出现标的物法律状态不明的空白状态。从债权法角度讲,占有转移并非一瞬完成的事项,在占有转移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交付方放弃占有而受让方尚未取得占有的可能,此时,标的物将处于无人占有的状态,货物毁损、灭失风险将无人承担;从物权法角度讲,此时第三人非基于受领之意思取得占有,将构成物权法上之先占,当事人均无占有回复的权源。显然,过程性的交付界定仅是对于交付进行的行为抽象,这种界定方式使得交付过程中产生的法律关系无法明确,且观念交付在过程性界定中难以契合“占有转移”的现实要素,无法明确交付的构成要件。
由于交付是受让方继受取得标的物的占有,因此交付方放弃对于标的物的占有,是受让方取得占有的前提,该种放弃是双方当事人合意的结果,必须基于交付方的意思自治。一般意义上讲,占有是指对于标的物具有事实的支配力,这种事实的支配力包括了物理上的支配、第三人的戒除以及占有人控制的意图[20]52-60。因此,交付过程中交付方对于标的物占有的放弃意味着其不仅要失去对于标的物物理上的支配,也要放弃对于标的物控制的意图以及第三人对于标的物的占有不得进行干预的尊重,使得受让方能够基于控制的意图取得对于标的物的继受占有,同时受让方的继受占有能够获得排他性的支配力。
当交付的过程性要素被弱化,状态性要素势必凸显出来。当交付方基于丧失控制的意思放弃管领,那么受让方就实现了对于标的物的事实管领。由于交付过程中的受让方是基于交付方放弃的意思而取得标的物,“交付意义上的受让方取得显然应归入占有继受取得的范畴,但是,由于法律将占有界定为对物的实际管领力,所以即使是在继受取得中仍需考察取得人是否取得了对物的实际管领力。”[21]44这种管领并不以实际控制为必要,只要交付双方当事人具有转移标的物占有的合意,受让方基于转移的合意随时具有实际控制的可能即可。德国民法典第854条第2款规定:“取得人能够对物行使管领的,原占有人与取得人的合意,足以取得占有。”因此,在交付过程中受领方取得对物的管领,必须承载对物进行管领的意思,但存在一般性的而非指向一个特定物的意思,即为足以[22]696。
通过对于交付状态要素的拆解,交付的完成需要以下几个要素的完成:交付方对占有的放弃、受让方取得占有、受让方取得占有系由交付方的意愿促成[21]43-46。在对交付强调状态要素而忽略其过程要素的背景下,交付的当事人视角凸显,交付在“实际控制可能性”的情境之下无法确保自身的公示公信效力,第三人也无法从交付的占有状态转移之中推定权源状态如何。交付的取得功能被置于重要的地位,更加强调对于标的物的自主占有,即占有的自主意思性。
(二)第三方支付下的交付关系解构
在第三方支付中,金钱的交付并不直接发生在具有交付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而需要经过第三方交易平台。在这种情况之下,传统现实交付中直接在当事人之间实现的占有转移被打破。在现代交易活动中,交付经由他人之手实现亦属常态,包括了经由占有辅助人交付、经由占有媒介关系交付、经由所谓被指令人交付[23]96。不同的是,在第三方交易平台作为被指令人的情况之下,法律关系呈现多样化,形成了交付方与受领方、交付方与被指令人、受领方与被指令人之间三重法律关系③。
在第三方平台参与的支付关系中,由于交付方在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之前,就已经同意第三方支付平台所提供的服务协议,因此支付方与第三方服务平台就服务协议意思表示一致,双方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在交付过程中,交付方通过指定受领人同时向第三方平台发出支付指令而完成资金的交付。《支付宝服务协议》第3条第3款规定:“通过代为支付款项服务,您可以支付款项给您指定的第三方。具体是指自款项从您指定账户(非支付宝账户)出账之时起,至我们根据您或有权方给出的指令将上述款项的全部或部分入账到第三方的银行账户或支付宝账户之时止的整个过程;或自您根据本协议委托我们将您银行卡的资金划转到您或他人的支付宝账户或自您因委托我们代为收取相关款项并入账到您的支付宝账户之时起,至委托我们根据您或有权方给出的指令将上述款项的全部或部分入账到第三方的银行账户或支付宝账户之时止的整个过程。”④《微信支付用户服务协议》第3条第2款规定:“你可以使用本服务向你指定的收款人转账,本公司将根据你或你指定的收款人的支付指令,从你的‘零钱或你关联的银行账户扣划相应资金至收款人的微信支付账户或银行账户。”⑤
“在支付委托合同下,付款指令属于《合同法》第399条第1句的‘指示,是单方的、须受领的意思表示。指令內容包括付款人、付款账号、收款人姓名、收款账号、付款金额、甚至款项用途等。”[24]55需要注意的是,在第三方平台支付过程中,交付方基于服务协议负有审慎使用的不真正义务,特点在于违反该义务“并不发生损害赔偿责任,仅使负担此项义务者遭受权利减损或者承受不利益而已。”[25]88具体而言,系指付款人发出指令的过程中,指令的收款人、收款账号、付款金额等于发生错误,付款人不得撤销,亦不得向第三方支付平台要求损害赔偿,仅得自己承担因错误支付遭受的损失。
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服务协议内容中既包括了支付服务,也包括了收款服务。当当事人同意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服务协议,与第三方平台成立委托合同的之时,该委托合同即包括了两项内容——支付委托合同和托收委托合同。《支付宝服务协议》第3条第2款规定:“通过代为收取款项服务,您可以收到他人向您支付的款项。具体是指自您委托我们将您银行卡内的资金充值到您的支付宝账户或委托我们代為收取第三方向您支付的款项之时起,至根据您的指令将该等款项的全部或部分实际入账到您的银行账户或支付宝账户之时止(含提现)的整个过程。”⑥《微信支付用户服务协议》第3条第2款规定:“收款:你也可以通过微信支付服务收取他人的转账资金,本公司可将该笔资金转至你的‘零钱。你也可以将零钱余额限度内的资金转移至你关联的银行账户,本公司也可按照法律规定或本协议约定直接将‘零钱余额资金转移至你关联的银行账户。”⑦在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支付的过程中,第三方平台既作为支付受托人,又作为托收受托人,具有了双重身份。在当前各种支付平台对于二维码限制的情况下,支付所委托的第三方平台与收款所委托的第三方平台必须是同一平台,但是并不能排除未来各方平台可以互用的局面,在此情况下就可以实现支付委托与托收委托的分离。
在第三方平台支付的情况下,最重要的问题在于第三方支付的性质。在第三方平台支付中,当事人对于第三方平台或者对于银行享有的仅为债权,如果认为交付方所转让的是自己对于第三方平台或者对于银行的债权,那么交付方的支付行为即成为以债权为担保的债务允诺,属于代物清偿[26]98。但是,在现今时代,电子支付的盛行使得货币由纸币符号向电子符号转化,虽然理论上当事人对于支付平台或者银行享有的是债权,但是这种债权已经无需转化即可作为支付手段实现流通。账面货币与现金货币已经同时具有一般等价物的本质,账面货币支付的法律效果已经与现金支付无异。通过第三方平台使用账面货币支付已经不属于用他种给付代替交付,而属于债务的履行[21]58。
四、基于交付过程的犯罪性质厘定
在商家与顾客使用二维码交付货币的过程中,顾客与商家合意通过二维码进行支付,顾客具有放弃占有支付平台中特定数量货币的意思,顾客在扫码支付的过程中亦实际放弃了对于账户中特定货币的占有;一旦该货币进入商家的支付平台账户内,商家即基于“自主占有”的意思实现了对于货币的占有,此时,满足了交付中“交付方对占有的放弃、受让方取得占有、受让方取得占有系由交付方的意愿促成”的构成要件,交付过程完成。从《支付宝服务协议》和《微信支付用户服务协议》的内容来看,第三方服务平台服务的过程为“从账户出账之时起,至根据指令将特定款项的全部或部分入账到第三方的银行账户或支付宝账户之时止”,因此第三方平台服务的过程即为交付的整个过程。
(一)交付视域下顾客的被害人身份判定
在交付制度的视域之下,判断偷换二维码收取钱款行为属于何种犯罪首先在于被害人的确定,而确定被害人的首要任务在于顾客交付是否已经完成。若顾客已经完成交付,则其在已经履行完毕货币支付义务的情况之下理应获得商品,就不可能成为本案的被害人;若其未完成交付,则属于顾客将财产处分与行为人,则顾客将是直接的被害人。有的学者仅从最后结果来确定被害人,认为顾客虽然错误处分了自己的银行债权,但是顾客获得了商品,实现了自己的交易目的,没有受到财产损害[9]22。该理论显然是脱离合同履行义务的判断而得出的结论,若顾客未完成交付,则属于为履行合同义务,商家既可以基于债权要求顾客再次履行付款义务,也可以基于不当得利要求顾客返还商品。若认为商家的债权消失,必须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在判断顾客是否完成交付的过程中,首先要断定顾客是否违反了审慎使用的不真正义务。审慎使用义务不同于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时的注意义务,法律上要求每个人对他人的合法权益有注意义务,但并无对自己利益的注意义务[27]29,如果顾客的过错致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那么顾客应当忍受这种损害而无法请求赔偿。审慎使用义务的违反在于顾客因过错错误使用支付平台“作为原因之一促使损害的发生,从而使行为人所为之行为与损害之间无因果关系或者仅有部分因果关系”。[27]30就效果论而言,顾客扫描了错误的二维码从而使得资金未能进入商家的账户,顾客的行为使得行为人偷换二维码与损害结果仅有部分因果关系。但是,审慎使用义务的违反要求顾客具有“非固有意义上的过错”或者“对自己的过错”,即顾客没有采取合理的注意或者可以获得的预防措施[28]88。在偷换二维码案件中,顾客系按照商家的指示扫描二维码,且不同二维码之间不具有肉眼的可识别性,即使顾客付款之间进行辨别,也无法防止损害结果的发生。因此,虽然顾客错误支付了价款,但是顾客并不具有过错,因此,并未违反审慎使用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第138条、第141条的规定,顾客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全面履行付款义务。顾客与商家约定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并且向顾客提供了二维码,顾客按照约定,向第三方支付平台履行了付款义务,交付了价款。债务人向第三人做出给付,原则上不发生履行的效果,但是经债权人允许或者事后追认的除外。[29]599由于商家通过与第三方支付平台订立服务协议,第三方支付平台基于委托合同已经取得代为收款的代理权,商家向顾客提供二维码,表明其已经同意顾客向第三方支付平台履行,因此顾客的履行发生效力。第三方平台作为商家的受领代理人,代为受领顾客的支付。当顾客支付的价款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特定账户出账,进入商家制定的特定账户之时,该交付过程也已经完毕,顾客已经全面适当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因此,顾客取得商品有法律依据。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能够发生清偿的法律效果,即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债的关系消灭。换言之,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使得债权人丧失对债务人的债权。[30]57顾客基于买卖合同全面、适当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取得了购买商品,属于正常买卖合同的交易者,不具有任何的财产损害,不可能成为被害人。
(二)基于被害人的犯罪性质认定
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有财产价值,因此偷换二维码的行为不具有盗窃罪的性质。犯罪性质的判定在于取得财产的手段,因此判断偷换二维码收取钱款的行为属盗窃罪还是诈骗罪关键在于判断当事人取得财产的手段为何。该取得手段系财产从被害人转移至行为人过程中的手段,对于财产取得手段的判断核心在于财产转移过程的界定。
在行为人更换二维码之时,在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任何的财产转移,财产的移转肇始于顾客付款的过程中。在付款过程中,商家委托第三方支付平台代为收款,第三方支付平台作为受领人代为受领顾客的支付。当账面货币从顾客的账户内流出,进入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过程中,财产转移未发生任何的错误。但是,当财产进入第三方支付平台之后,该账面货币本应进入商家的账户,但是基于二维码的错误,该账面货币进入了行为人的账户。因此,行为人取得财产的过程不在于通过二维码直接使得顾客将财产处分与行为人,而在于顾客与商家约定通过第三方支付的情况下,顾客向第三方支付平台交付了账面货币;第三方平台在受领货币之后,本应进入商家的账户,而基于行为人偷换二维码的行为,二维码识别错误而进入了行为人的账户。顾客并没有将财产处分与行为人的意思,而仅有将财产处分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意思,并意图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使得处分的账面货币进入商家的账户;顾客基于将账面货币交付于第三方平台的意思表示,完成交付行为,第三方支付平台代为受领了给付;而行为人通过偷换二维码的手段使得本应进入商家账户的账面货币进入了自己的账户,这是行为人取得财产的直接手段。“这种在不知情状况下的财物转移,不是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因此,不应当构成诈骗罪,应当构成盗窃罪。”[31]171
行为人取得财产的方式系通过秘密转移行为,而并非基于顾客或者商家的错误认识而进行财产处分的行为,该取得财产的方式符合盗窃罪的特征。问题是,商家在行为人取得财物时并未占有该财产,那么该财产能否属于行为人盗窃商户的财产呢?盗窃的对象虽然必须是他人占有的财物,但是占有所要求的支配不仅包括物理支配范围内的支配,而且包括社会观念上可以推知财产的支配人的状态,即使应占有者未占有该财产,但当财产为第三者占有时,也应认定为他人占有的财物[32]875。根据一般社会观念,顾客在扫描商家的二维码对商家进行付款时,在顾客完成付款行为之后,该钱款应为商家所占有⑧。虽然顾客并未对财产形成物理性的支配,但是“无论他人占有、行为人占有抑或无人占有的财物,只要被害人没有放弃财产权,无疑均属于财产犯罪的保护对象”,[33]119行为人通过偷换二维码而转移了该财产的占有,属盗窃了商家之财产。
当顾客按照商家的要求进行扫码支付时,顾客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价款,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商家交付商品亦是履行合同义务的必要内容。当顾客完成付款行为,该账面货币从顾客账户流出时,就已经进入商家的财产控制领域之内[3]61,只不过该控制未达到物理控制的强度。行为人通过二维码秘密转移处于商家财产控制领域内的财产,是对商家财产占有的侵犯,商家基于行为人对于自己占有的侵犯而成为直接的被害人,商家的损害并非由于顾客的处分行为导致,而是直接归因于行为人的财产转移行为。
五、结语
一直以来对于偷换二维码收取钱款的犯罪界定,是对扫码付款行为进行普通观念上认定之后得出的结论。但是,通过二维码付款是一种在第三方参与下的支付行为,其交付的实现过程并不同于现实的交付行为,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财产转移的时间、节点、方式也不同于我们的一般认知。通过对第三方支付参与的框架下所形成的法律关系进行解构,实现了对于二维码支付下交付行为的解剖,准确认识了在偷换二维码收取钱款的过程中行为人在何时取得财产,通过何种方式取得财产,财产经由何种路径进入到行为人的账户之中,从而对于犯罪的性质做出了更为清晰的认定。在交付的视域之下,对于盗窃罪的认定更新了信息时代盗窃的概念认知,对于时代发展之下犯罪的定性做出了转型预设。
注 释:
① 参见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6刑初357号刑事判决书。
② 参见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2017)闽0581刑初1070号刑事判决书。
③ 在實际金钱支付的过程中,由于当事人资金有可能储存于银行账户之中,还可能产生被指令人与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由于本文重点在于对交付过程进行分析,侧重于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参与下当事人之间交付的完成情况,因此对于第三方支付平台与银行之间的关系不再进行讨论。
④ 参见《支付宝服务协议》,网址https://render.alipay.com/p/f/fd-iztow1fi/index.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1月7日。
⑤ 参见《微信支付服务协议》,网址https://weixin.qq.com/cgibin/readtemplate?uin=&stype=&promote=&fr=&lang=zh_CN&ADTAG=&check=false&nav=faq&t=weixin_agreement&s=pay,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1月7日。
⑥ 参见《支付宝服务协议》,网址https://render.alipay.com/p/f/fd-iztow1fi/index.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1月7日。
⑦ 参见《微信支付服务协议》,网址https://weixin.qq.com/cgibin/readtemplate?uin=&stype=&promote=&fr=&lang=zh_CN&ADTAG=&check=false&nav=faq&t=weixin_agreement&s=pay,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1月7日。
⑧ 根据德国学者的观点,盗窃罪中的他人占有,包括两个要素:实施上的支配以及社会上对于该支配的承认。二者属于负相关关系,事实上的承认越有力,社会上的承认就可以越薄弱;反之,社会承认越有力,事实支配就可以越薄弱。
参考文献:
[1] 许浩.偷换商家收款二维码的行为定性[J].人民司法,2018,(35):18-19.
[2] 蔡桂生.缄默形式诈骗罪的表现及其本质[J].政治与法律,2018,(2):38-49.
[3] 杨兴培.“三角诈骗”的法理质疑与实践批判[J].东方法学,2019,(4):51-69.
[4] 叶良芳,马路瑶.第三方支付环境下非法占有他人財物行为的定性[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3):103-109.
[5] 柏浪涛.论诈骗罪中的“处分意识”[J].东方法学,2017,(2):97-107.
[6] 蔡桂生.新型支付方式下诈骗与盗窃的界限[J].法学,2018,(1):169-181.
[7] 张忆然.诈骗罪的“处分意思不要说”之提倡——“处分意思”与“直接性要件”的功能厘定[J].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19,(3):29-38.
[8] 姜涛.网络型诈骗罪的拟制处分行为[J].中外法学,2019,(3):692-712.
[9] 张明楷.三角诈骗的类型[J].法学评论,2017,(1):9-26.
[10] 马寅翔.限缩与扩张:财产性利益盗窃与诈骗的界分之道[J]. 法学,2018,(3):46-59.
[11] 张庆立.偷换二维码取财的行为宜认定为诈骗罪[J].东方法学,2017,(2):123-131.
[12] 刘梦雅,张爱艳.偷换商家支付二维码案的刑法认定[J].中国检察官,2018,(1):12-15.
[13] 徐凌波.置换二维码行为与财产犯罪的成立[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2):34-47.
[14] 张开骏.偷换商户支付二维码侵犯商户应收款的犯罪定性[J].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8,(2):107-119.
[15] 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6] 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17] 王立志.认定诈骗罪必需“处分意识”——以“不知情交付”类型的欺诈性取财案件为例[J].政法论坛,2015,(1):119-131.
[18] 郭明瑞.物权法通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19] 李宗录,栾玥婷.交付原则下交付的功能重释[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56-65.
[20] [意]鲁道夫·萨科,拉法埃莱·卡泰丽娜.贾婉婷,译.占有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21] 刘家安.论动产所有权移转中的交付——若干重要概念及观念的澄清与重构[J].法学,2019,(1):37-52.
[22] 杜景林,卢谌.德国民法典——全条文注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23] 王泽鉴.民法物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4] 李建星,施越.电子支付中的四方关系及其规范架构[J].浙江社会科学,2017,(11):52-60.
[25] 王泽鉴.债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6] 王洪亮.债法总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7] 尹志强.论与有过失的属性及适用范围[J].政法论坛,2019,(5):26-37.
[28] 程啸.损害赔偿法中受害人共同责任的规范模式[J].政治与法律,2017,(5):81-91.
[29] [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M].郑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30] 高磊.论清偿效果之于三角诈骗的认定[J].政治与法律,2018,(5):52-61.
[31] 黎宏.电信诈骗中的若干难点问题解析[J].法学,2017,(5):166-180.
[32] 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33] 胡东飞.盗窃及其在侵犯财产罪中的体系地位[J].法学家, 2019,(5):113-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