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合影
2021-01-03但及
但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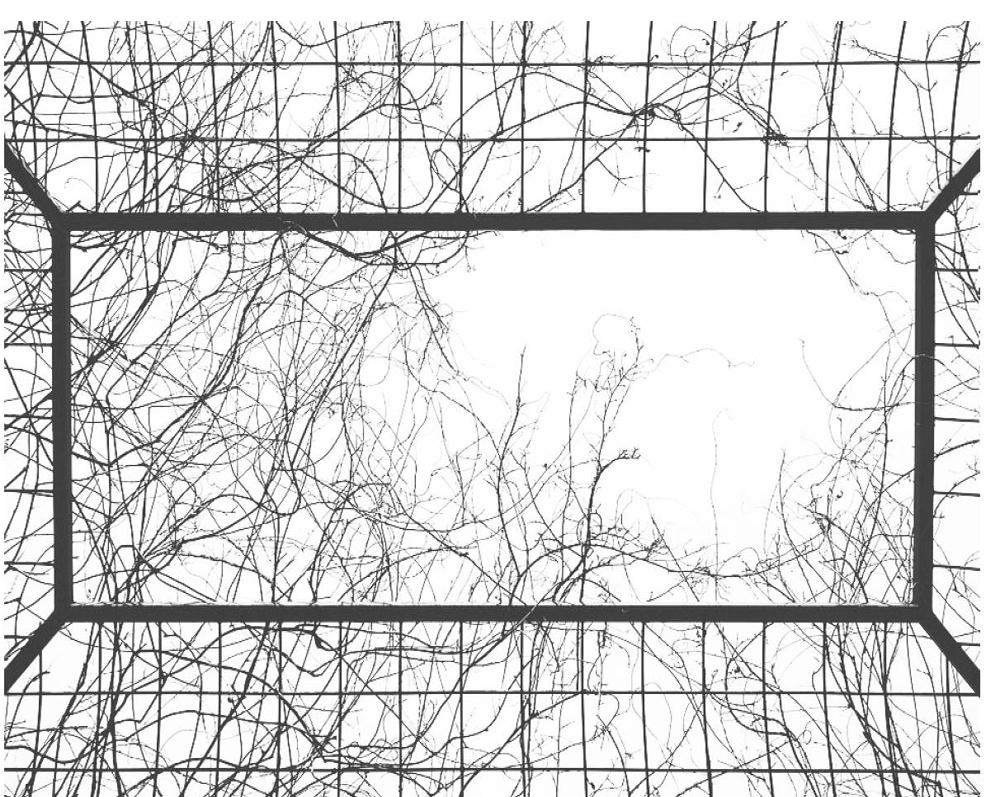

1
电话通了,里面没声音。我喂了一会儿,还是没声音。想挂时,却听到了哭声。
声音凄婉,带着某种怪异与变腔。“啊……啊……”我耐心地等待着。“是吴律师吗……我……我是有坤老婆……”
就在这个电话里,我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有坤死了。
有坤死在医院里,是在输液的时候突然死去的。“你能来一趟吗?帮我们一把。有坤经常提起你,你们小时候很要好。”
我握着手机,紧捏着。已经多年没见有坤了,他这几年做小老板,做起了混凝土搅拌生意。就在顺风顺水时,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眼前浮现出不同时期的他,儿童时的,年轻时的,以及人到中年发福的样子,这些像资料片一样快速流过。事到如今,人已撒手而去,我怎么能拒绝这份要求呢?
把事务所的事安顿好,我就立刻开车前往。从市里到五泾需要四十分钟,那里也是我的故乡,我童年、青年都在那里成长。一路上,熟悉的乡村道和河流不时闪现,路边的树摇晃着,让我的眼睛生疼。以前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有坤装在玻璃罩子里。一进他家门,就看到了。花圈不多,三三两两,散落在白墙两边。原先我以为有许多人,但没有,屋里稀稀拉拉,出人意料地冷清。有坤躺着,与我们隔着罩子,头向上,眼睛紧闭,两侧的肉有些下坠。看上去,有点不像他,连头发也少了许多。
“是律师,律师来了。”有人这样说。
在有坤面前鞠了三个躬后,他老婆出现了。以前我见过她,但不熟。有坤很早结婚,结婚时还给我发过请帖,但我没出席。现在一张苍白的女人的脸正在向我靠近,她头发蓬乱,黑衣,头上插了朵白花。白花怪怪的,好像撒了一团鸟粪。“吴律师,终于把你盼来了……他只能靠你了。”她身子摇晃,好像要散架,随时会倒下来。
“不急,不急,慢慢说。”我说。
女人的眼圈是红的,潮的,眼神也是麻木的。她没有看我,而是盯着地皮。
“都是我不好,我不好啊。是我推他去医院的。是我啊。”她喃喃地说。
“他得了什么病?”我问。
“他心痛,一直胸闷胸痛,走路也两样。我就让他去,他不肯,我一定让他去。他就去了……这样永远去了。”她呆如木鸡。
“输了什么东西?”我又问。
“银杏液什么的,我叫不全……好像是银杏什么的……是我害了他。”女人捂住脸,脸上的肌肉在抽搐。
我们谈话时,有坤像个怪物装在里面,在偷听我们的谈话。这楼应该是近几年盖的,三层,地上铺大理石,装修也不错。客厅里有大屏电视,还有一圏沙发,上方还挂了幅牡丹图。有坤现在就躺在中央,身影挡去了牡丹图的一个角。一阵风吹来,花圈倒下了几个,飘带哗哗作响,还缠绕到一起。
有人来扶花圈,还叫我乳名小小吴。这里的人都叫我小小吴,我在这里长大,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现在我难得回来,逢年过节,走个亲戚之类的。可以说,这里我既熟悉,也陌生。对人也如此,有些我叫得出名,有些则根本不熟,但他们好像都认识我,都叫我小小吴。于是,我只能不停地点头,递上微笑。
“现在人也没了,还是节哀吧。我想办法,争取给个说法,还要赔偿。”听我这样说后,她木讷地点了点头。她请我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吧。但说心里话,我没把握,医疗纠纷牵涉到许多部门和人,我以前也打过这样的官司,最后不了了之。
不久,我走到了户外。
大片的田野映入眼帘,现在是秋末,田里金黄纷呈。稻子沉沉地挂在梢头,风一来,它們就在上面摇晃。清新的空气里不时夹杂些鸡粪味。
2
边上有间破败的屋子。墙面斑驳,长满青苔。屋檐好似断了,塌了半个,又勉强支撑着。
印象中,这应该是小法家。我已经有十多年没见小法了,没想到房子成了这样,难道他已搬家?沿着屋舍走了一圈,门虚掩着,屋内长草,墙面松动。显然没有住人。
不远处有片菜地,有个妇女在锄草。我上去询问。
“小法,他早去见阎王了。这个可怜鬼,没有比他更可怜的了。”她挺直腰,拖着锄头说。
“见阎王?”我不解。
“跟有坤一样。那是去年的事,他生病,病死了。”
我的心一紧。小法比我小,中年,正值当年,怎么会得病呢?连着两个儿时的同伴去世,我内心很不是滋味。“不知道什么病,谁也不知道。你看这屋也要塌了,没人了,家里一个人也没了。”妇女一声叹息。
我内心恍惚,直直地看着这灰屋。眼前晃动着过去,我与有坤和小法在游戏。我们从弄堂里窜出窜进,躲进芦苇丛。我们还在水里沉浮,迎着湍急的水流劈波斩浪……眼前这每一寸土地上,都留有我们的足迹。当年的气息似乎还在。然而现在,我们竟阴阳两隔,再也不能相会。
小法的死,我一点也不知情,没人通知我。但我知道,他生活在穷困里,自从他妈改嫁,他爸病故后,他就一个人生活在这世界上。单身,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嫁他。他也渐渐脱群,谁在不知他在忙什么,独来独往,像孤魂一样东游西荡。我偶尔会从别人的谈话里,得到他消息的片言只语。直到现在,这个妇女告诉我,他已离世,且一年有余。
故乡于我是既近又远,上大学后,我就离开了这里。我在市里做律师,每天忙忙碌碌,对这里似乎出不了多少的力,更没有多少热情来关注这片封闭的土地。小法啊,小法,我心里这样念叨着。在我眼里,他就是个老实人,有时也耍点小滑头,但那点伎俩总会被人戳穿。
我去推门。刚一推,一块砖就掉了下来,差点砸在我脑门上。我打消了进去的念头。
“可怜的人啊,死了一个月才发现,身子都臭了。”妇女这样说。
我站在那,身子好似僵住了。
这时,有坤那边有亲戚进来。花圈抬着,脚步迟缓,我看到了一张张麻木的脸。哭声随风而来,呈波浪形,回荡到了外面的田野里。一只灰鹭拍着翅膀,从眼前掠过,停在一棵树上,仿佛在张耳倾听。
回到车里,我从公文包里找到一张白纸,包了两千元。我想给了钱以后迅速离开。
有坤老婆在楼上,坐着,面对窗户,一片阴影长长地投在她身上。这个背影让我惊觉,我犹豫着是否靠近她。她像石头一样坚硬、沉默。我的脚步声她没听见,这时,一只猫从床上跳下,惊动了她。她惊恐起身,看到了我,像做错了事。
当我把素包递给她时,她瞪大了眼,再快速地往回推。“不行,不行,怎么行呢?我……我是叫你帮忙的。”她的手冰凉且粗糙。一缕头发挂下来,挡住了她一只红肿的眼。
“一定得收。这是规矩。”我又推了回去。
“……你能来,我很感恩。”说完,她竟“扑通”一声跪到我面前。我拉她,竟拉不动。“你要帮这个忙,他是冤死的。”
“我明白。我会尽全力的,会的。”
她沉得很,我甚至触到了她手臂上的鸡皮疙瘩。上面还有一道道手抓的痕迹,痕迹里带着几缕血丝。这双手臂让我不舒服,我甚至想放开了。
终于,她抬了抬身子,我借势把她塞到一把椅子里。她的眼怪模怪样的,像是涂了一层胶。
“心在绞……好像榨油机在榨……”她捂着胸。
“人已死,也叫不回来了,你还得照顾好自己和孩子。”他们的儿子已经读高中了。尽管这话起不了作用,但我还得说,否则我就没话可说了。
“……他的老爹老妈,在养老院里……我不知道该不该通知……人都老了……本身就在拖日子,弄不好又出人命……”
我又是一惊。
的确,没看见两个老人,如果让老人知道的话,可能又是一场灾难。她的判断应该对的。“要瞒着他们,一定要瞒着。”我这样说。
“我……我就怕他们出事。”
“跟所有的亲戚都说一下,不要传出去。不能再让他们知道。赶快通知。”我说。
就在那一刻,我决定留下来,想帮助做点事。我打消了马上回市里的念头。
3
丧事办得简单。有坤父母不在,许多亲戚无从知晓,也无法通知。
丧事后,我就调查这件事的起因及原委。医院对我的出现很不满,几次干扰我的调查与收集证据。医院说,你找医务科好了,由他们统一处理。医务科说,你找卫生局好了,那里有专家,会鉴定。事情就是这样扯皮。
半个月后,我起草了一则起诉书,上诉到了法院。当我把起诉书递上时,我给有坤的老婆打了电话。“谢谢你啦,有坤在天之灵会感谢你的。”电话里,她还说了有坤父母的情况。“我都不想去,看到他们就像刀……刀在割。”
“他们还不知道吧?”我探问。
对方没声音。我喂了几句,还是没声。我一阵紧张。
还好,过了一会儿,我听到粗重的喘息声。
“对不起……一直瞒着,不晓得能瞒到什么时候,总有戳穿的时候。就怕这一天。”
“先瞒了再说。否则,不可想象。”我说。
“每天夜里衣服都湿透的。我总在想,是我害死了有坤。”
“别这样想,这事不能怪你。”
“我不催,他就不会去挂这个断命的水,也不会死……死了。是我害的。”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折磨人。我除了规劝几声,还能做什么呢?有些伤痛需要时间来愈合。她处在水深火热中,日日在煎熬,但现在我更担心的还是有坤的父母。他们老了,朽了,就像小法家的那个屋脊,随时可能塌下来。这一塌,那么全家就都塌了。
我决定去探望一下他的父母。小时候,一直跑他家,有时还蹭饭吃。我记得上大学时,他妈送了我两罐麦乳精,加外一个脸盆和一把雨伞。我一直记着这份情。周末,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买了盒装牛奶、蜂王浆胶囊和两个新疆哈密瓜,驾车开了过去。
养老院在五泾边上,离集镇大约五里地。房子是新造的,老远就看到高高的红瓦屋顶,像是覆盖了一层红叶。秋日的大地正在收尾,金黄的树叶在风中翻飞,然后四处撒落。稻田已收割,只剩下稻茬子留在田里。车子刚停在养老院宽敞的大门口,就听到了狗叫声,一条狗不知从哪里窜出,瞅着我。
有坤父母住在底楼,工作人员把我引过去。门一推,就看到了有坤妈,正拿着抹布在擦锅子。抹布黑不拉叽的。看到我,愣了下,那张皱巴巴的脸上绽放出了笑容。“你怎么来了?真是你啊,太好了。”然后,她大声地叫躺在床上的有坤的爸。叫不醒,她就去推了把。他从被窝里探出头来,一脸茫然。他既不欢迎,也不排斥。
“他糊涂了,不认得你了。”她说。
“糊个屁啊,醒着呢,是小小吴。那个结巴的小小吴。”说完,又把头缩回了被子。的确,我小时候结巴,说话拖泥带水。老人清醒着呢,他这么一说,我倒反而笑了。
“这个糊涂虫还叫对了,不理他。”她让我坐下,一双油腻腻的手一把握住我,并抚摩着我的手背,那模样就像我小时候那样。我有些尴尬,又不能拒绝。“你能来看我们真是太好了,还拿礼物来。空手来就行,何必拎东西呢?”嘴上这样说,但我看出她很高兴。一笑,皱纹更多了,整张脸就像个大麻花。
我坐在那,浑身不自在。屋里,弥漫着一股怪怪的老人味。
“小小吴,你聪明啊,不像我们有坤。他人笨,只会点笨活。你看你多好,我听有坤说你做律师啊,这是个好饭碗,挣大钱呢。”她不停地搓我的手,搓得我也变油腻了。我抽了抽,没抽出来。
“只是个工作罢了。”我答。
“噢,不,现在打官司的人多。你看你穿得多挺括,有模有样,不像我们有坤。他已经好久没来了,说忙。忙个屁呢,大伙都懂,他嫌我们老了。他嫌脏。”
“有坤不是这样的人。”终于,我抽出了手,呼吸也顺暢不少。
她叹了口气。“不过,他还是孝的,给起钱来不吝啬。”
她转过身,去拉抽屉,掏啊掏,掏出一包云片糕来。“吃点,吃点吧,乌镇特产,好吃。”她把糕塞到我手里。她又去泡茶,水不开,茶叶末子还浮在上面。
男人开始咳嗽,被子起伏着,一股尿臊味随咳嗽传来。“他浑身是病,老了。我们都老了,不顶用了。我也有关节炎,天不好就发。”她的牙齿上黏了片菜叶,那片青叶不时会从嘴里冒一下。她当年可是知青,长得秀气,在我们这一带也算个人物。
“你碰到有坤了吗?一个多月没来了,瞎忙!要说忙吧,也不至于这样,连个电话也没有。良心给狗吃了。”她说。
“有坤挺好。”我开始撒谎。说这话的时候,我的脸都红了。
“他好是好,就是没脑子。人家说大头的人聪明,可他的脑子没你好使,你聪明,小小吴小时候就比别人聪明。”说着,她又去翻纸箱。翻了一会儿,拿出一本相册来。“你看看,这里面有你小时候的样子,你机灵,点子多。”
相册推到了我面前。
我开始翻相册,里面有黑白照,也有彩照。大部分人我认识,也有不认识的。泛黄的照片仿佛时光穿梭机,我顺着这些照片,让记忆重返童年。
“有你,里面有你。你快看。”她在一旁催促。
顺着她的手指,我把目光停留到其中一张上。黑白照,三人合影。三个人靠在桥栏上。我瘦得像根甘蔗,站在中间,两边各有一人,一个是有坤,另一个则是小法。
我弱不禁风。有坤则不同,他大头,头发像鸡窝一样顶着。小法突着眼,穿的衣服半吊着,膝盖处还打了块大补丁。三个人目光向前,背景是河,河里还有条木船。那是在南双桥上拍的。
恍惚感更重了。现在,另外两人在另一个世界,他们仿佛在瞅我,用目光紧紧地抓着我。我赶紧把目光移开,不忍心再看。
“你们是好朋友,整天窜进窜出。可惜小法运气不好,小小年纪就死掉了。”她的手伸过来,指甲里藏着污垢。她把指头按在小法的头上,我只能看到小法剩下的半截身子,还有那块显眼的补丁。
我把相册合上了。
“怎么不看了呢?还有呢,还有好多照片。”她道。
4
坐了半小时,我提出要走。她有些依依不舍,好像我的屁股还没坐热。
“再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嘛。”这样子让我想起以前,她便是这样,动不动还会塞颗糖果。
“有坤来就好了,我让他到外面请你吃饭。这小子就是不来。”
我避开她的眼神,不敢直视。我还凑到床前与男人告别。他撑起半个身子,招了招手,身上那件棉衫上有个洞,很显现。
“真是丢脸,让他换一件,就是不肯。”她有点嫌弃地说。
她拉着我的手,不肯放。现在我也适应了,不介意。她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那里停着我的车。当我用遥控打开门车时,她挡在了车子前。“有个事,想跟你说,一直闷在心里,难受死了。不说快要憋死了。”
我有些惊愕。难道她知道有坤的事了?想想应该不可能。
“是小法,小法的事。”她呜咽一声,低下了头。
“小法怎么啦?”我问。
她突然哭了。哭声凄凉,像一只猫在叫,我毛骨悚然。小法,她与小法有什么事呢?他们两家是邻居,比邻而居,难道会有误会?
“我对不住他啊,越想越对不住啊。”她用手背擦着泪。传达室的人像是嗅到了什么,把头探出门厅。我把身子转过来,挡住那人的目光。
“慢慢说,有事你慢慢说。”我劝慰着。
“我跟有坤也不说,有坤这人嘴太快……我受不了……可你不一样,你有知识,你今天来了我很高兴……我忍不住想说。不说的话,我会得病的,我像在火里烤啊……”她的唠叨令我心急,我急于知道发生了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你跟有坤、小法都是好朋友,我要跟你说,我说了,真的说了……不说受不了,我一直在做噩梦。”她那失态的表情令我陷入尴尬。
“这孩子太可怜,从小他妈就走了……我看着他长大,一点点变成个小伙子。”
关于小法,我当然知道。他就像只孤鸟,一个人生活。除了家里的二亩地,谁也不知他在忙什么。这就是我对他的了解。
“我看他可怜,就给他点东西,几个南瓜,一袋米什么的……我们家造了新房子,贴了大理石,大家都夸……这孩子一直住在他那间破房子里,有时还漏水,高低不平的。这些年他就是这么过的。他人好,对我也客气,一直阿姨长阿姨短的……”我不明白她跟我说这些是为何。再说,人死了一年多了,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她,怕她知道有坤的事。这才是最要命的。
太阳耀眼,挂在天上,不远处公路上不时有车扬起尘土。前方正在修桥,一面小红旗醒目地插在桥墩上。
“他死了,死了就回不来。你不要想了。”我打断她的话,拉开车门。就在这时,她猛地攥住我,手指甲也嵌到了我肉里。“我怕啊,怕他来找我呢。我对不住他!”那眼神里满是惊恐。
“怎么会呢?”我越来越糊涂了。
“有天,我去他那屋……门开着,就进去了。他在生病,一直在生病,病十几天了……里面臭烘烘的,菜摊在桌上,都馊了……我看到他,他整个人被鬼缠住一样,眼里也有鬼火。真的有鬼火,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他说我要死了,说这句话也是有气无力的。我看到一个鬼就在他身边,还在缠他……”
我瞪大眼,想,她在说胡话了。
“我是逃出来的……我没有告诉别的人,连有坤也没有告诉……我怕一说,就要送医院,弄不好还要有坤掏钱。我,我……我不舍得那几个钱啊……可是,可是他就这样死了……他是有机会的,只要我说出来,总会有人去帮他……我就这样,什么人也没说……”
原来如此啊。
“他是不该死的,我只要……只要说,只要一个电话,医生就会来……我怕掏钱,我……舍不得那几个钱……钱……我难受呢……”
她变成了一个我陌生的人,神態凄凉,失魂落魄。一时间,我也不知怎么表态。“到养老院就为了这……我怕看到他那间屋,我难受啊……为什么会这样?小小吴,你帮帮我,你有知识有文化……有坤只知道混凝土搅啊拌啊,其他什么也不懂……小小吴,你看我生不如死呢……”
说完,用力一甩,她把一条长长的鼻涕扔到了地上。
5
返程时,我把车开得很慢。
刚才出现的一幕令我不安。我怀揣秘密,没想到人家也藏着更深的秘密,我像出逃一般离开那里。生活的真相有时让人恐惧。
我开了另一条路。这是条小路,车少,人少,车在缓缓滑动,我想让脑子清静些。秋日的柏油路上落叶凋落,一层层地铺着,车子碾过会有沙沙的战栗声。老路弯道多,路面也时有坑洼,两旁房屋稀少,偶尔有鸡鸭在池塘边散步。天阴了,太阳逃走了,空气里有烟火味,像是有人在烧田里的稻草。
一块石牌坊从眼前划过,那里有成片的树林,显得茂密与幽深。小河从中穿过,此时正是芦花开放的时刻,芦花昂着头,在远处看着我。我突然反应过来,这里是墓地。有坤和小法应该就葬在这里。
墓地没有门牌,大门是敞开的。
车缓缓地靠在路边,停了下来。我看到通往墓地的那条悠长的路。路笔直,延伸着,通往更深的地方。两旁长满了芦苇,风拂来,芦花就像秋千一样荡着。
车头旁也有几枝芦花,它探着头,似在望着我。我掏出烟来,点上,开始朝空中喷烟。
这时,一个身影从石牌坊那里冒了出来。那是个老年妇女,佝着背,穿一件灰色的秋装,手提塑料袋。我觉得眼熟,但又想不起来。她没有朝四周看,径直地往那条笔直的墓道走去。背影融到了芦花丛中。
记忆里应该有这样一个人,她是谁呢?我想不起来。
天越发阴沉了。远处云在跑,风也劲,芦花更晃荡了。当我把烟蒂扔到地上时,突然想起来了。是她!肯定是她!就是那个早已改嫁的女人。
我为自己寻到记忆而喜悦。她应该是为小法而来的。我决定跟进去,尾随她,我想看看一个远道而来的母亲,当然也想看看有坤和小法现今居住的环境。
走过牌坊,一股阴惨惨的风迎面而来。我追随着那团背影。
她走了约五十米后,拐到了另一条小路。我听到自己沉重的脚步声。风掀起树浪声,边上是一个个密不透气的墓碑。它们都藏在松林背后,风一吹,都无言地站了出来,像在注视着我。
女人在走,背弓得厉害,快成九十度了。与我记忆中她的模样相比,已老得不成样子。天空发黑,好像被幕布挡着了。有乌鸦在树丛里鸣叫,看到人,拍动翅膀成群地惊起。她在一处墓碑前停下,芦花和松树挡去了部分身影。
她是教训过我的,我记得,是在从前。
她找上门来的情形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次,我与小法打架,我们为了水渠里的几条鱼打了一架。结果,我把小法摔倒在地,骑在他身上,狂抽了几个耳光。就在当天下午,这个女人气势汹汹找上门来。她一进门就一把拖住我的衣领,不停地摇晃着。“你打小法,你这个混账……”她声音响亮,气势如山,连邻居们都听到了。她就这样拖着我往外走,我就胡乱地挥动着两手。拳头挥出去,我击到了那个胸口,击到了那团软绵绵的肉上。直到现在,我仿佛还记得那团肉带给我的那份战栗……的确,我当时欺侮了小法。
我在离女人后面五六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女人跪在一个墓碑前,她在磕着头。风声在墓碑丛中穿越和兜转。芦花在激烈摇动,身子柔软地倾斜,但依然支撑着。乌云变浓了,在头顶翻卷,好像随时会洒下雨来。耳朵最深处,我仿佛听到了闷雷声,沉沉的,不真实,像有东西从墓地上碾过。
这是她改嫁后,我第一次见她。她俯卧在地上,身子在起伏。我想,她是不是要请求儿子的原谅?如果她当年带着小法走,命运会不会又是另一番景象?我的脑海在翻涌,里面盘旋着这些古怪的念头。
继续走近,我看到了放在墓前的几个苹果和一些糕点。地上刚烧的一堆纸灰,被风吹起,卷到了空中。墓碑矗立着,是简陋的水泥板,上面写着五个字:许小法之墓。
她花白的头发如一个鸟巢,胡乱地扎在头顶上。很快,她发现了我,朝我投来警觉的一瞥。她的眼睛像两块核桃干。
“阿姨好!”我靠近,对她这样说。
“小法,小法,你没有死?”她瞪着眼,看着我。我奇怪极了,背上甚至泛起一片冷汗。
“小法,你真的没有死?你还活着?”她朝我靠近,一双浑浊的眼睛紧紧地锁着我,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是小小吴,我不是小法。”我道。
“真是太好了。你来看妈了,真的吗?让我来摸摸你。”
她那雙手就伸了出来,展在空中。然后,她脚步踉跄,朝我扑来,我想躲开,但又怕她摔倒。她一把抱住了我,浑浊的气味也一齐抵达。我被她紧紧地拥着,就像当年被她拖着时一样。
“小法啊,妈想你啊……”说完,她就笑了。她一笑,我更难受了。
我拼命挣脱,但她抱得紧,一推,她跌跌撞撞起来。于是,又重新去扶她。
“阿姨,不是,你弄错了。我不是。”
第二轮的拥抱再次发起,她把双手撑开,像只大鸟一样。我一个转身,开始奔跑,除了逃跑,我没有别的法子。“别走,小法,别走。”她在后面,边追边喊。
我惊慌失措,甚至不敢回头。我知道她就在后面,在不远的地方。她还在跑,我能听到脚步声、喊声,间隙里还有她的几声放浪笑声。
我加快步伐,在芦苇丛里乱窜,还折倒了几根芦苇。
天色越发阴沉,雨就徘徊在头顶,但没落下来。我拉开车门,气喘吁吁,快速发动。我朝后方快速张望了一眼,那里什么人也没有,只见芦花在风中零乱地舞动。
现在,风把芦花压得更低了。
责任编辑杨静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