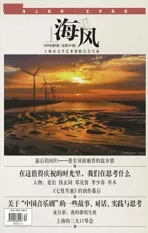“入坑”与“出圈”关于“中国音乐剧”的一些故事、对话、实践与思考
2020-12-16
■ 本刊记者 秦 岭

“入坑”,网络流行词,指陷入某一件事中不能自拔。“出圈”,网络流行词,“饭圈”常用语,意思是某个明星、某个事件十分走红,其热度不仅在他们固定粉丝圈中传播,而被圈子之外的更多“路人”所知晓——在《北京日报》的年末盘点文章里,这两个词,被列为2019年中国音乐剧的年度关键词。
确实如此。随着原创新形态声乐演唱节目《声入人心》在全国范围内的热播,原本寂寞的“中国音乐剧”圈,忽然涌入了大量“垂直入坑”的新鲜观众与热情粉丝;诸多相关热门事件及备受关注的当红人物,也使得音乐剧、特别是“中国音乐剧”这一地位尴尬的“小众艺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出圈”爆红,成为中国文娱的“热门产业”,一片充满无限可能的“蓝海”。
而这片“蓝海”的中心,应该就在上海。
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统计数据则显示,2019年上半年,上海全市专业剧院共举办音乐剧演出292场,吸引观众28.7万人次,剧场票房收入6152.63万元(人民币),在11个剧种中排名首位,音乐剧已然成为上海文化演出中重要的细分市场。2019年11月,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与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宣布共建中国音乐剧产业基地。12月,“演艺大世界——2020上海国际音乐剧节”高调官宣,这个项目由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与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主办,试图打造“立足上海、辐射全国的音乐剧名片”。如果不是后来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彻底打乱了节奏,2020年的上海音乐剧演出市场势必热闹非凡。
经历了戛然而止的2020年第一季度,捱过了艰难挣扎的第二季度,然后撑起了努力暖场的第三季度,半年多的被动静默后,上海音乐剧市场终于迎来了一段“报复性”反弹——即便依然有着上座率的限制,即便海外引进剧目始终归期难定,可第四季度上海的音乐剧演出日历照样被填得满满当当。
而其中,有一个重点不知你是否察觉:在这样的背景下,即将产生的那些统计数据——举办音乐剧演出多少多少场,吸引观众多少多少人次,剧场票房收入多少多少万元(人民币),它的归属都将是“中国音乐剧”,这些剧目的创作主体也都是“中国音乐剧人”。当一整个音乐剧市场都(哪怕是被动地)敞开给“中国音乐剧”的时候,谁说这不是另一种殊胜的机遇(挑战)呢?
以上全部,构成了我们这篇文章的背景与初衷。中国音乐剧曾经怎样走来?其问题何有,症结何在,前路何如?站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我们和几位沪上音乐剧“圈内人”,认真地聊了聊。从他们各自的行业经历与艺术实践中,或许可以映射出中国音乐剧的一些面向,并提供一些可以进一步思索的方向。
一个音乐剧演员职业样本里的中国音乐剧之路
见到朱梓溶的时候,她正在为《暖场》的演出做着积极的准备。
《暖场》是中国音乐剧产业基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事业部与新浪微博在疫情期间联合发起的一系列线上音乐剧演唱会的共同名字。沪上十数家音乐剧制作公司,利用各自手上的剧目和演员资源,通过互联网直播平台聚合在一起,以线上音乐剧音乐会的形式与观众“保持联系”,在剧院无法正常开启的这段“真空时期”,积极维持“音乐剧”的热度和曝光率——颇有点“抱团取暖”的意思,有情怀,有创意,事实证明,也很有效果。
“音乐剧演员是需要舞台的,你一旦脱离舞台了,就什么都不是了。”朱梓溶说,“所以我觉得《暖场》这个项目特别好。通过一系列活动,一方面我们的戏能让更多观众看到,另一方面也是在告诉观众,有这么多中国音乐剧人一直在为华语音乐剧的发展不断努力,这一切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停止。”
朱梓溶进入音乐剧这个行业非常早。2003年,她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系。对于中国音乐剧来说,这是一个颇有意义的时间点。就在这之前的2002年,百老汇英文原版《悲惨世界》登陆上海大剧院,作为舶来品的“音乐剧”正式叩开了上海演出市场的大门;同一年,上海音乐学院成立了音乐戏剧系,紧随其后的2003年,上海戏剧学院也招收了她的第一个以音乐剧表演为方向的本科班——某种意义上,朱梓溶音乐剧生涯的展开与上海音乐剧发展的脚步几乎同步。
而当时的情况确实称得上是“鸿蒙初开”。进校之初,朱梓溶坦言自己对“音乐剧”这个戏剧样式毫无概念,“学校、老师,包括专业课程设置,也都在摸索当中,可以说大家都在一起同步成长”。她最大的感受,是“音乐剧太有魅力了”,她几乎一经接触,就被迅速俘获,“音乐剧能让一个原本与它毫不沾边的人,一下子燃起这么大的热情,当时的我就在想,这个舞台表演形式太好了,我对音乐剧的未来充满信心。”
然而跳出艺术的象牙塔,当时的演出市场上,就连“音乐剧”这个细分项目本身都还没真正形成,让业内充满期待的“音乐剧”依然是个“小冷圈”。5年学成毕业,朱梓溶并没有成为想象中的“音乐剧演员”,她进入上海轻音乐团,成为一名独唱歌手。她觉得自己很幸运,比起那些去文化馆工作的同学,她还有音乐,还有舞台。但和许多热爱音乐剧的伙伴一样,她始终等待着一个让自己可以“学以致用”的时机。

光阴匆匆似水,中国音乐剧的春天却总是似近实远。
“我们算是最早一波从音乐剧专业毕业的人。但真正进入音乐剧这个行业,却是跟后面比我们晚了五六七八届的小朋友们同步。”朱梓溶终于在2013年等到了自己商业音乐剧演出的“处女秀”——由宁财神总策划,何念任总导演的《女人一定要有钱》于2012年底首演,2013年开启二轮演出。对于这部剧,制作方打出的宣传语是“千万级打造的上海首部原创音乐剧”,导演何念则在首演谢幕时雄心壮志地表示,“希望这部作品能成为真正属于上海的原创作品”。
无论何念的愿望究竟实现与否,毋庸讳言,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朱梓溶开始真切地看到了中国音乐剧不断向暖的曙光。“我觉得到了2015年大概可以算是一个转折吧。随着引进到国内的音乐剧剧目越来越多,观众群也被慢慢培养起来了,海外原版音乐剧、海外版权剧中文版和中国原创音乐剧这几个不同的类别被明晰地划分了出来。”
新绎剧社的《摇滚·西厢》、三宝操刀的《聂小倩与宁采臣》、李盾制作的《啊!鼓岭》、徐俊导演的《犹太人在上海》……这些音乐剧迷们多少叫得出名字的中国原创音乐剧也都诞生在2015年。“原创热了”,有媒体在报道中这样写道。

这一年,上海国际音乐剧论坛也举行到了第四届。过去的三届里,中国的音乐剧市场经历过原版音乐剧引进的热潮,感受过音乐剧市场的兴起,整理过本土化英美音乐剧的经验,也畅想过原创音乐剧的爆发。但在“原创热了”的2015年,中国音乐剧的圈内人却显得更加审慎,他们不断批评与反省:我们缺乏好故事,演员表演还相对薄弱,制作产业化程度也不够……“我们中国音乐剧发展毫无疑问跟西方不一样,甚至跟日本、韩国也都有很大的差距。”时任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总裁的张哲做过这样一个比喻,“现在中国音乐剧的发展就如同我们把生长在野外的这么一棵植物,要让它放到室内去生长,过去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认为选好一棵树木,放到室内种下去就可以养活了,但是没有那么简单。把一个树木放到室内栽植可能有很多过程,是一个反复的过程,放过来以后可能不适应气候、温度、湿度,然后看它不行了,拿到外面去适应一下,然后再搬到室内,这样慢慢野外植物适应了室内的环境。我想中国的音乐剧发展恐怕就处于这么一个阶段。”
“差距依然在。”时间拉到五年后的现在,坐在我对面的朱梓溶仍旧抱持着差不多的想法。从2015年到2020年的五年时光里,中国音乐剧毫无疑问在不断奔袭、前进,戏确实慢慢变多了,制作公司也慢慢变多了,与之相应的,愿意为中国音乐剧走进剧院的观众越来越多了,电视里有了中国音乐剧相关的节目,甚至也有了足够“出圈”、可以带动流量的明星,一切都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着——这些都好,但是“还不够”。
“从综合能力来讲,中国演员整体上的确没有国外演员强,因为音乐剧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不单单是唱。”朱梓溶说。相比国外已然十分成熟的音乐剧市场,我们的“音乐剧文化”还在形成的过程中。“欧美国家的小朋友从小就有音乐剧的课程、戏剧兴趣班,乃至少儿剧团,他们的音乐剧推广是成体系的。而我们这一代演员,普遍要到考大学了才开始接触、学习,这里就是时间差。现在我们也慢慢开始了对年轻观众的培养,00后这批孩子出来肯定会好很多。”
“时间差”所指向的问题,不仅仅针对演员,更在于创作。“这十几年也培养了不少音乐剧人才,大家也看过的《声入人心》,知道其实我们有很多好演员。但演员只是其中的一环,而音乐剧是一个集体的创作,我们创作团队还没有跟上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现在不少艺术院校都开设有音乐剧表演专业,可是关于音乐剧创作的专业呢,几乎没有。
“现在有挺多年轻人开始发挥他们的能量,开始写一些作品,我真的觉得,哪怕是小小的戏,能不能给他们一些扶持,给他们时间和空间成长,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和扶持。同时,在遭遇困难的时候,是否也能提供一些基础的帮助。”朱梓溶说,“我其实特别希望中国音乐剧能有自己的工会。我是比较幸运的,我有我的单位,但更多音乐剧演员是自由职业者,他们是单打独斗的,而音乐剧行业的普遍薪酬是很低的,当问题出现的时候,他们缺乏基本的保障。比如因为今年的疫情,我身边就有不少人被迫转行了。这是很让人心痛的事情。”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朱梓溶很看重这次的《暖场》——这个中国音乐剧人“民间自发”的携手团结的努力,让她真实地感觉到了来自行业内部的暖意。
就在我们的采访结束后不久的8月2日,作为《暖场》系列线上音乐剧演唱会的后续,“2020华语音乐剧大赏”在上音歌剧厅举行。12家音乐剧公司,19部华语音乐剧目,100位中国音乐剧演员,除了剧院现场,还有长达4小时的线上马拉松式直播。一周内,微博话题阅读量便突破1.5亿,讨论量、互动量超16万。这样的数据与曝光量,对于力量单薄的民营制作公司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这场疫情之下“应激”而来“暖场”演出,其本身或许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尚有不少改进与上升的空间,但无可否认的是,它也确实暗示着上海音乐剧产业未来发展道路上某种可能的方向。
另一个例子和另一番对话:我们究竟为什么而做戏
周可人也许就是朱梓溶在采访中提到的,那些小她个五六七八届,却几乎与她同步进入音乐剧行业的“小朋友”。与大学时代才开始了解音乐剧的朱梓溶不同,“95后”的周可人可以说是听着韦伯和桑德海姆长大的,他对音乐剧的感知同他自己的成长是同步的。

周可人的母亲何莹曾经是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的表导演老师,演员胡歌是她的学生,经常来家里做客、学习。“看妈妈给哥哥姐姐们上课”是周可人小时候的“日常”,相比其他孩子,他也有着更多接触舞台和戏剧的机会,而音乐剧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之所属”。人生第一次走进剧院看的音乐剧,就是2002年和母亲一起在上海大剧院看的那场百老汇英文原版《悲惨世界》。在上海戏剧舞台与家门口音像店的双重“加持”下,周可人在少年时代就“阅读”了大量西方音乐剧剧目——他就是朱梓溶所乐见的,在音乐剧语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音乐剧人。
2016年,当时还是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三年级学生的周可人,第一次登上音乐剧舞台。剧目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排演的音乐剧《两个人的谋杀》。舞台上,演员不仅要多角色迅速切换,还有大段难度极高的钢琴演奏,演员需要边弹边唱、边弹边念台词。与周可人在同一剧组搭档排练的刘令飞对周可人的钢琴功底与音乐能力印象深刻,他邀请周可人加入自己担纲制作人的百老汇音乐剧《摇滚年代》中文版制作团队,跟着资深音乐总监姜清华做执行音乐总监。
就这样,在“音乐剧演员”之外,“音乐总监”成了周可人的主业。音乐总监是音乐剧的制作过程中责任最重要的职位之一,工作包括协助找到最适合的歌手,和导演一起诠释剧本及歌曲,甚至要在每一场演出的时候负责引领歌手及乐手。年纪很小,资历不浅,这是音乐剧圈内对他的评价。从《月亮和六便士》《拉赫玛尼诺夫》《信》《我的遗愿清单》《蛋壳里的心跳》到正在上演的《阿波罗尼亚》和即将上演的《贝多芬》……周可人的音乐剧从业履历十分“丰满”。
“我正好赶上了音乐剧开始要发展的时刻。”周可人坦言自己对于这个行业曾经的“冷遇”没有切身的感受,他也很少对“艺术情怀”夸夸其谈,他更关心的,是眼下最切实的事:在音乐剧开始“破圈”,“入坑”观众越来越多的当下,这个行业要怎样才能好上加好。
“我觉得我们的专业性还是有待提高,我们的科学化的概念还不够强。”他说。科学性,这是周可人在谈及中国音乐剧发展时最多提到的一个词。“当然这两年已经好很多了,因为我们的音乐剧创作,已经从过去的导演中心制改成了现在制作人中心制,创作中的系统化问题已经得到很好的改善。像上海文化广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这样的大制作方,在运作上是非常科学的,但外面也有一些制作公司,可能就不是特别科学,很多时候一个剧组一个模式,工作的方式不是很系统。”
剧目创作的科学性,制作体系的科学性,人才培养的科学性……这些都是中国音乐剧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回答,那就是“你究竟为什么而做戏”,目的决定了道路和手段。
我们做音乐剧,就是要赢得市场。周可人的结论斩钉截铁。“音乐剧本身是属于大众。它不算高雅艺术,它就是个娱乐,是一种文化产品,所以不要把它想得太高,市场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要带着这个市场走。这当然不是说,我们要一味迎合市场,但如果你做了一个所谓的艺术品,观众却不喜欢或者看不懂,结果没人看,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说到这里,自然绕不过眼下大热的百老汇音乐剧《汉密尔顿》。这部音乐剧的故事改编自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本人的经历。这样一个乍看之下“又红又专”的题材,却扎扎实实地戳中了当下美国民众的内心,既炸裂了口碑又炸裂了票房。巨大成功背后的机制与符码,也确实值得中国音乐剧人解读与思索。
“在纽约大学的音乐剧教材里,就有很大一个章节是教你写词的,他们的课程还会涉及诸如:当你接触了制作人以后,怎样用10分钟去介绍你作品。他们的课程目的非常明确,设置也非常精密,他们很重视推向市场。”。
作品与市场,这其实是另一个意义上的鸡生蛋与蛋生鸡的问题。“美国有行业工会,他们工会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很支持孵化,很支持原创作品。所以美国一年能有五六百个音乐剧原创作品,然后从这五六百个里面挑出一百个进入外百老汇,再从这一百个里面挑个七八个进入百老汇——这样的创作量是能够产生质变的。近两年百老汇也井喷了一些音乐剧,比如《汉密尔顿》和《来自远方》,这两部在市场上取得巨大成功的音乐剧,之前都经过了很多年的筹备,期间,就有工会在背后支持你。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系统了。”
令人兴奋的是,像这样的事情,中国音乐剧圈也已经有人开始尝试着去做。针对目前国内音乐剧原创力短板的现状,上海文化广场联手海笑文化,连续推出了“2019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2020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力图集平台与模式之力,促进音乐剧行业共同成长。
关于这个实践,我们会在下一个故事里揭晓。值得一提的是,在“2019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最后成功孵化的作品名单里,就有周可人和母亲何莹的名字。这部名叫《生死签》的作品,由何莹担纲编剧、陈祺丰作曲、周可人任音乐总监,按照孵化计划,将在明年正式破壳而出,直面观众,接受来自市场的考验。
“我觉得明年会是原创戏的一个大年。因为疫情,国外的戏都进不来,就看你能不能把戏做出来。这是‘真金白银’的考验。”周可人说。作为一个音乐剧主创,他十分感激孵化计划给予他的帮助,认为像这样“科学的”“成系统的”“以市场为目标的”孵化正是眼下中国音乐剧所需要的。
“如果这样的孵化被系统地坚持下去,那再过个五六年,我们就能发现市场上有很多实打实的原创戏了。我想,这个才是中国音乐剧真正想要的方向。汉化引进的西方剧目再好,毕竟不是自己的东西。”
一次从“蛋壳里”出发的实践:不仅孵化作品,更孵化人

孵化,指动物在一定条件下在壳内发育,最后破壳来到外界,开始其自由生活的过程。每一部成功的音乐剧作品,在其诞生之初,都只是“蛋壳里”的那一个小小的胚胎,尚不成型,但又生机盎然,一旦给予它良好的环境、充足的养分,这些“蛋壳里的心跳”就有可能“破壳”而出,成长为独立而美好的生命个体。
这是“华语音乐剧原创孵化计划”的初衷。
“什么是中国式音乐剧?每个人都没有正确答案,但音乐剧的成功,必须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最大限度服务本土观众。”孵化统筹、制作人王海笑说。“做这个项目,不是为了眼前,急着打造一台音乐剧,我们希望做一片土壤,让更多的种子在这里生长。”孵化计划主办方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说。

有这样一组数据。道略演艺产业研究院2019年发布的音乐剧市场年报显示,2018年中国音乐剧票房增速达到92.8%,共收入4.28亿元。其中,引进音乐剧演出584场,票房达2.68亿元。中文版音乐剧演出900场,票房达1.03亿元。原创音乐剧演出979场,票房为0.55亿元。演出场次与票房收入的双重对比,说明了很多问题。
“从2002年《悲惨世界》进入上海,一路走到现在,大家其实都慢慢看到了音乐剧这种演出样式的好。在上海,我们能看到西方最好的音乐剧,一批忠实的音乐剧粉丝正在形成;另一方面,我们的原创音乐剧却完全无法与之抗衡。”费元洪说。中国原创音乐剧似乎陷入了一种东不成西不就的尴尬。“观众确实看过了好东西,审美眼界提高了,但平心而论,这其实也是广大人群中很少的一部分。可即便是没看过好东西的人,他来看中国原创音乐剧,一下子也不是很适应——因为我们也还没找到符合中国式审美的音乐创作方式。”
从2012年起,每年春天上海文化广场都会举行“原创华语音乐剧展演季”,几年原创做下来,费元洪发现“原创越来越难”——这个难指的是,难以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我认为,原创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就是商业化成功,老百姓真的是用票钱来养你这个剧组。如果还是靠基金或者政府补贴去做,不能算是成功。”而在他的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中国原创音乐剧大戏赢得口碑者固然有之,可在商业上能够完全实现自负盈亏的,“几乎没有”。相较之下,反而是一些小戏,比如《隐婚男女》《快把我哥带走》,市场反馈“还不错”。
“所以我的想法是,一、我们先做小,二、还是得调动年轻人的积极性。”
在费元洪看来,年轻人有强烈的创作愿意,也有活力,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能直接接上当下年轻人的地气,“他们的音乐语言是不一样的,就像文风一样,音乐剧的文风必须是现在流行的文风,老文风写得再好,毕竟“老”了,音乐剧要的是“新”。”孵化计划要做的,就是让这些有创意、有灵感、充满潜力的年轻人能够得到适当的引导,最后走向市场。“通过我们的孵化,希望能带给中国音乐剧一个新的动作,然后也解决一些原创音乐剧现在面临的问题。”

首届孵化计划作品《生死签》工作坊
这是一个参考国外创作经验而制作出的、有着严格时间表与创作步骤的严密计划。
第一步,先从投稿作品中海选出5部作品进入孵化程序,为他们选定合适的创作“导师”,同时给予主创3万元作品扶植基金。导师帮助主创为入选作品匹配所需的创作者,协助进行一期开发与修改。第二步,将进入剧本朗读与音乐工作坊。此时,再从5部作品中选出2~3部最具开发价值和市场潜力的作品,每部入选作品追加5万元现金奖励,并根据导师和评审给出的意见进行二期开发。第三步,对最终入选的这2~3部作品进行工作坊版本制作和市场化对接。最终,实现作品的商业化制作对接。
“有一句话说,‘Musical is Re-created’(音乐剧是在创作中不断磨合细化)。我们也做好了准备,有些戏可能就适合一年孵化,有些戏可能因为各种各样原因一年不行,会用两到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没关系的,不行就再来。做音乐剧是要金钱投入的,但我们先把花大钱的时机放在后面,前期更多的是对胚胎的呵护,就像人妊娠一样,前三个月是最重要的,这时候什么都看不到,但其实是最重要的,好的胚胎决定了他今后能否成长为健康的肌体。通过不断磨合,可以大幅提高原创音乐剧的成活率和成材率,激发青年创作者的创作能力和信心。”
2019年第一届“孵化计划”收到了77部原创音乐剧的作品,第二届激增到了147部,“如果把这些作品的创作者加在一起,可以达到三四百位这样一个体量,这是一个巨大的青年创作群体。”
现在,2019“孵化计划”的三部孵化作品《生死签》《对不起,我忘了》《南唐后主》最终都实现了商业化认标,计划在2021年正式推向市场。2020年“孵化计划”也已完成了“中期考核”,《南墙计划》《无法访问》《你在哪里》以及疫情特别征集剧目《两个人的城》等4部作品进入了下一阶段的孵化。而这长达两年的音乐剧孵化历程本身,也以“剧”的形式被记录了下来。这部名为《蛋壳里的心跳》的音乐剧,所有的音乐都来自“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的投稿。主创团队既在戏里,也在戏外。
“我们也没想到一部关于孵化的音乐剧,其面世竟然早于了其他的孵化音乐剧。”费元洪半开玩笑地说。很多人以为孵化计划孵的是“作品”,是“音乐”,实际上孵化的是“人”,孵的是一群热爱舞台又颇有才华的创作者,他们的每一次发声,每一步成长,都是蛋壳里传来的心跳声。
一些接踵而来的思考:在“入坑”和“出圈”的中间,我们还能做点什么?
从2002年到2020年,这18年间发生的种种与音乐剧有关的故事里,期盼有之、困惑有之、反思有之、尝试亦有之——或许就像有句话里说的那样: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会有希望。
回到话题的开头。而今,《声入人心》等综艺节目让中国音乐剧明星成功“出圈”,带动了音乐剧热度和观众数量,民营公司音乐剧制作数量的增多,带动了市场演出体量,两者叠加所造成的音乐剧热度,确实是圈内从业者、圈外媒体人以及音乐剧的剧迷们长久以来所期望看到的。
“现在肯定是中国音乐剧经历过的最好的时光。”音乐剧制作人俞惠嫣说。从《犹太人在上海》到《白蛇惊变》,再到眼下正在创排中的《赵氏孤儿》,她深耕中国原创音乐剧制作多年,为市场带去不少口碑之作。当下中文音乐剧演出市场传来的种种利好,让她感到振奋。而此前与音乐剧演员郑云龙在话剧作品上的一次合作,也让她切实看到了优秀音乐剧演员“出圈”后带来的巨大票房号召力和市场价值。
“演员‘出圈’带来的那些新‘入坑’的粉丝,原先或许并不了解音乐剧,但现在,他们选择走进剧场,他们愿意为音乐剧演出买票,这对于以产业化为目标的中国音乐剧来说,肯定是一件好事。观众可以为了任何理由走进剧场,对于我们制作方来说,要做的则是尽可能回应观众的期待,用优秀的作品、精良的制作,把已经走进来的那些观众留在剧场里,让他们从某位演员的粉丝进一步转化为音乐剧的粉丝。处理得当,这就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事实上,这也是中国音乐剧行业的共同心声,之前对话中,从业者们谈到的种种思考与实践也都无一例外地奔着这个目标而去。
与此同时,俞惠嫣也并不讳言,对于这股由明星效应带动起来的音乐剧消费热潮,音乐剧圈内外也确实存在着一些批评和警惕的声音。


2019年7月,《文汇报》就曾发表过一篇题为《音乐剧演出市场终于火了,但别乱了》的批评文章,列举出时下的种种行业乱象:演出票超售,演出商单方面取消消费者订单,并拒绝赔偿;音乐剧演唱会演出时长无故“缩水”四分之一;演出商挟“明星”推出“霸王”条款,预先充值的款项在观众订票未成功后拒绝退还;“鲜肉”演员演出失误严重,乐队总监质疑其专业水准遭粉丝围攻而被开除,巡演后半程质量接连滑坡……文章指出,“国内音乐剧产业要良性增长,就不能竭泽而渔”,要加强契约意识和专业精神,减少而不是过于依赖明星的个人影响力,投入更多精力打磨演出品质,才能保证剧目的长久运营和未来市场整体稳步增长。
俞惠嫣十分赞同加强行业规范约束的意见。“这其实是每一个行业到了它的快速发展期都会碰到的问题。中国音乐剧的职业化进程和国外成熟的体系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行业内部的监管机制也还没有形成。一些短视的制作方选择用割韭菜的方式挣一笔快钱,这样的行为对行业发展的伤害是毋庸置疑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相信,我们绝大多数的音乐剧制作方都是有信念有情怀的,我们的音乐剧粉丝们也是有辨别力的,他们知道如何用脚投票。”
不过,她并不认为明星带动市场本身是一个问题。“韩国音乐剧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就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他们走的就是明星带动市场的路数。”俞惠嫣说。一个成熟的制作人自然知道如何处理好其中的关系,“当然,当粉丝蜂拥而至的时候,确实也会暴露出我们行业内部的一些问题,这时候我们要做的,是厘清关键点的所在,哪些问题是固有的,哪些问题是新出现的,哪些问题亟须解决,哪些问题需要我们的耐心和决心,然后想方设法利用好这样一个契机,去真正做成一些事情。”
那么,在“入坑”和“出圈”的中间,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呢?
俞惠嫣的答案是,团结并规范行业,服务并引导观众。
“音乐剧从业者绝大多数都属于体制外文艺工作者。而在我们音乐剧行业内部,也确实还没有一个权威组织能够把这一大批人团聚起来,大家都各自为政。我们可能确实需要有这样一个组织,为行业建立一定的约束机制,提供一定的帮助与服务,引导这个行业往更合理有序的方向上走。”
她也同样举了美国演员工会的例子。首先,工会有一定的入会门槛,需要你有一定量的实际演出经验,这是一种专业性的证明。其次,在入会之后,工会也会给你提供一定的基础保障,但同时你也必须承担一定的创作义务。重要的是,工会辐射的是行业内的全部工种,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信息资源库,为音乐剧创作者之间的交流合作构筑了有效且便利的平台。“既保障了人才,又服务了创作。这些做法,都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在服务与引导观众这一边,俞惠嫣则感到,现在似乎还缺乏一个权威且公正的剧评平台,来有效帮助观众找到真正心仪的剧目,同时,也帮助创作者更好地对作品进行提升与打磨。“现在推送的很多音乐剧相关内容,都还是以商业宣传为主要方向的。一些客观真实的评价与建设性的肯定或是批评的意见,并没能被很好地汇集起来。这其实是很可惜的。而且就像我们业内常说的,音乐剧是靠一遍一遍磨出来的,打磨的过程中,观众们的意见本身也非常重要。”
创作的人多了,欣赏的人多了,产生优秀作品的可能自然也就更大了。中国音乐剧产业的振兴,不是某一个音乐剧从业者,某一个制作方,或者某一类观众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做到的,它需要所有人团结一心的共同努力。
春天来了,但道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