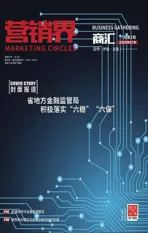晋商商业模式与金融创新的时代价值
2020-12-04山西工商学院李志锋
山西工商学院 李志锋
“十四五”即将开启,我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打造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成为“十四五”时期国家重要的任务。因此,商业模式和金融创新仍然是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推进我国新兴产业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温故而知新,晋商作为中国历史上十大商帮之首,其“货通天下”的跨区域贸易和“汇通天下”的金融创新,不仅在中国近代经济金融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而且形成了中国商业创新实践的经典历史范例。本文拟通过对晋商商业模式和金融创新演进的较为系统的探究,以揭示商业模式、金融创新与晋商发展的互动共生关系,为我国新时代企业商业模式变革和金融创新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适应性选择:地理环境与山西商人商业模式的形成
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晋商作为一个商业集团或群体能够在明清时期纵横捭阖500 多年,深刻影响和推进了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是一个偶然突发的商业现象,而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等因素相互联系,并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进过程。在没有其他更突出的因素介入晋商的研究分析以前,地理环境就可能构成研究晋商演化变迁的基本维度。被称为表里山河的山西,位于太行山以西,黄河吕梁山以东,北有长城,南有黄河,是一个地理边界较为清晰的封闭的地理环境。山西境内多起伏山川,北部土地贫瘠,中部和南部汾河流域土地稍沃,“八分山丘二分田”的地狭人稠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的自然条件,为满足养家糊口之需,外出谋生或经商就成为山西人适应环境的一种选择。
明清以前山西商人的商业模式,随着山西历史的演进、商业文化的启蒙和城镇的出现逐渐形成。山西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据历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山西。商代以来,山西不少封国和封地中心成为商业城市,并产生商人阶层。春秋战国时期,晋文公推行“工商食官”政策,百工和有名商贾纳入政府管理,“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汾河与黄河水上交通得到治理与畅通,上党等地城邑出现,太原以北戎狄与晋国商人贸易频繁,盐铁商人产生,并出现青铜铸币。猗顿问富于陶朱公,于晋南大畜牛羊,十年后富甲天下,称为晋商之祖。汉朝建立后,为了抵御匈奴南下,汉高祖不断加强太原的军事位置,太原也成为当时商业中心城市,山西商人与北部游牧民族和驻军贸易进一步发展。东汉初年,灵石成为山西古代三大都会之一,北越长城、途径蒙古、到西伯利亚转欧洲的东西方贸易另一条“丝绸之路”形成。北魏建都平城(398 年)后,商品交换随着社会稳定、经济恢复更趋于活跃,佛教交流活动促进了频繁的商业往来。618 年李渊父子灭隋建立唐朝,太原作为唐王朝发兵之地,军事储备和城市设施进一步增强,因而成为当时长安之外最大的城市,商业发达,并出现了办理借贷的信用机构。宋元时代,山西商人已经能与与徽州商人分庭抗礼、南北呼应。元代疆域横跨亚欧,塞北通往欧洲的商路得以拓展,在喀喇和林(今外蒙古哈儿和林)形成了很大的国际交易市场。
明朝以前,山西商人适应地理环境、城镇的出现和商文化的影响,在商业模式上经历了“本区域城镇贸易——跨区域民族贸易——多元化经营”模式的演进过程。经营的产品由本地的牲畜、手工艺品和中草药材等,进一步扩展贩卖包括茶叶、丝绸等南方的商品;经营的客户突破本地的居民而服务北方游牧民族和境外商户,客户关系和商业模式日益复杂,山西商人的活动领域更加广阔,遍及山西境内外,通过日益复杂的商业活动积累了一定的商业经营资本。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适应性效率(诺斯,2008),山西商人明清前期的贩运贸易商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山西商人适应环境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首先立足山西境内进行小范围的“上至绸缎,下至葱蒜”贩运贸易,解决自身生存、商业经验摸索和资本积累的问题;同时又展示出山西商人敢于突破山西封闭地理环境局限的束缚,跋山涉水、筚路蓝缕进行跨区域贸易的艰苦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使山西商人不断开辟商路和客户,不断扩展商业模式,不断积累商业资本,为晋商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山西商人适应环境,依靠本地资源禀赋进行贩运贸易起步的自立自强精神,为众多小微企业和创业者脚踏实地、艰苦创业树立了榜样;敢于突破山西封闭环境限制进行跨区域贸易的开放精神,对新时代企业家开拓奋进仍具有深刻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二、应势而变:明代“开中制”与晋商商业模式变革
山西地理位置上相对于历史上中原统治中心,是通往北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必经通道和军事要冲,历代朝廷在此多设重镇,重兵把守。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军需消费,为山西商人的聚集及商业模式的变革创造了较有利的独特外部条件。
在经济系统的演进中,制度是一个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制度变迁理论代表人物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绩效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及其质量具有决定性作用。任何一种商业模式的形成和演进都不可避免受外部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包括制度变革的影响。明初朝廷实行的“开中制”作为一项重大的制度变革,成为推动山西商人商业模式变革商帮崛起的重要因素。
明朝初年,为巩固政权和抵御元朝鞑靼残余势力的南下侵袭,朱元璋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设立9 大军事重镇,并派驻80 万军队驻守。为了解决驻军的军事给养问题,1370年(洪武三年)明政府实行食盐“开中法”,召集商人往北部边境运送交纳粮食、马匹等商品,换取定额盐引,凭盐引到盐产地领盐销往指定地点。因此山西商人从开始运送朝廷于陵县、长芦征收积储的“官米”,到后期自行采购贩运,甚至在边塞周边组织农民种粮缴纳置换盐引。
“开中制”推动了山西商人商业模式的变革和晋商的崛起。山西南部运城解州盐池是当时北部最大的盐场之一,山西北部长城外屯有80 万军队的大规模军需产品需求,再加上临近的蒙古游牧民族和民族贸易的相对集中在山西形成了区域化的特殊市场。山西商人敏锐地锁定了边塞军队和游牧民族的特殊客户群体,充分发挥山西位于中原与北部蒙古族地区连接地带的区位优势,积极利用“开中制”的政策建立了稳定而排他性的营销渠道,凭借粮食等商品的边贸获得“盐引”的特许权再高价贩卖盐品,迅速建立了较高的商业壁垒,获得了超额利润,实现了商业资本的迅速积累。此时,作为山西商人群体的晋商的商业模式不再是简单的异地贩运贸易,而是在山西北部边镇以粮食等军需补给换取盐引,以盐引的特许权贩运食盐,获利进一步采购粮食或茶叶等大宗物品贩运到山西北部边塞,从客户、商品、渠道等方面进一步聚焦和清晰,客户聚焦于边塞军队和游牧民族;商品锁定在粮食、盐、茶这些大宗的商品,品类减少,销量增大;营销渠道是由“开中制”政策保护的边塞贸易渠道,稳定而有壁垒;积累资本后部分晋商因此而由种植养殖业到酿酒业,商号遍及关内外,产业链进一步延长。晋商的商业模式演变为聚焦边塞军队和游牧民族的巨量客户需求,打通政府盐引特许权保护的营销渠道——组织粮食、茶叶等数量巨大的大宗的商品,以此进一步延长商业价值链,赚取盐引和便利的地理位置带来的低成本和超额利润。在商业模式上利用特殊客户群体整合商品链、物流链、产业链和资金链无疑是一种变革和创新。
晋商商业模式的变革和金融创新,推动了一批盐业巨子和巨商大贾的产生,晋商作为一个商帮在明末得以崛起,在经营盐业的同时,开辟了从武夷山到俄罗斯恰克图的万里茶路,商号逐步遍及国内商业中心城市和境外蒙古、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实现了“货通天下”。晋商的开拓进取的精神,为我国借势“一带一路”发展的企业家提供了很好的历史范例。
三、汇通天下:晋商山西票号”与金融创新
通过明代“开中制”制度变革带来的边塞贸易的战略性商业机遇,山西商人积极介入盐业经营,部分商人因此积累了巨额的商业资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人群体——晋商。随着商品贸易规模的越来越大,埠际间货币流通量大增,在明清以银钱流通为主的货币制度下,晋商遍及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商号运送现银的巨大成本和风险,对资金的异地汇兑产生了巨大需求,晋商基于商品经营的商业模式进行了进一步的创新,在明末清初探索并创立了经营货币专业汇兑的机构——山西票号。
1824 年创立的山西首家票号——“日升昌”,原来是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开设分号,经理雷履泰在“西玉成”北京分号经常为在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天津、四川之间的现款兑拨,后来要求兑拨的客户越来越多,就采取收费的方式进行兑付,改设“日升昌”由兼营汇兑到专营汇兑,票号由于解决了众多商户异地资金汇兑和风险规避的刚性需求而生意兴隆,“日升昌”于是彻底放弃颜料生意,由商品经营升级为资本经营,由一般商品贸易升级为经营汇兑的金融业。在票号发展之前或同期,晋商还创立了当铺、钱庄、印局、账局等相关的金融服务机构。山西票号创立后,乔家等山西富商纷纷转型介入,从山西平遥开始发展遍及全国各地,并扩展至香港、朝鲜仁川,日本大阪、大阪、神户等地,多达500 多处。1906 年,票号年汇兑公款达2257 万两,与政府的财政关系也日益密切,在19 世纪末代理政府饷银汇兑甚至垫付,几乎成为清政府的财政支柱。晋商商业金融与政府金融实现融合。从1824 年建立平遥日升昌第一家票号开始,晋商经营的产品由一般的商品变为特殊商品——货币,将商品贸易经营升级为资本经营,晋商遍布全国的商号纷纷成立或转型为票号,在清朝中期几乎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业,成为近代金融业的鼻祖。
关于创新与金融创新理论,1912 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革命性地提出的“创新理论”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把一种从来没有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其最终观点认为创新是资本主义增长和发展的动力。在金融创新理论方面,索兰斯(Eugenio Domingo Solans 2003)认为金融创新是指那些便利获得信息、交易和支付方式的技术进步,以及新的金融工具、金融服务、金融组织和更发达完善的金融市场的出现(王华庆,2011)。实践总是领先于理论发展的,尽管在明清时期中国只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包括山西票号在内的晋商的金融创新,已经走在了熊彼特等经济学家创新理论的前面。晋商创立的当铺、钱庄、印局、账局和票号等金融服务机构,使晋商的商业模式由商品经营升级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发展”的模式。晋商的票号与当铺、钱庄、印局、账局等金融机构为明清时期的国内外商品流通提供了便利的异地结算、支付和融资的工具,是一种新的金融组织的创新;包括基于应用数学技术的珠算、推进复式记账的“龙门账”记账法、作为货币记账单位的“本平制度”、最早使用的商业票据和银行票据、最早的转账结算和银行密押制度等,都是金融工具的创新,在百余年的金融业务运作中,晋商依靠这些创新与制度经营稳健,很少出现金融风险,其金融工具的创新性和领先性可见一斑。
晋商商业模式与金融的创新,不仅使晋商商业发展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山西票号的创立便利了商户之间的异地汇兑和资金融通,加速了商品流通速度,有效促进了明清时期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发展。在“货通天下”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汇通天下”,在近代中国金融业乃至世界金融创新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堪称中国和世界金融史上金融创新的重要里程碑。
四、基本结论与展望:晋商创新的时代意义
纵观晋商的崛起与发展过程,在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山西商人因势而变、勇于吃苦、敢于突破、不断创新,在商业模式方面持续变革,经历了由一般贩运贸易到跨区域贸易,由商品经营到资本经营的创新。在创造的客户价值、经营的产品服务类型、开辟的商路渠道、构建的“身股、银股”制度及其相与关系和政商关系方面,都在经历着推动商品经济发展和晋商自身发展的互动演进。独特的地理位置、边塞军事贸易、“开中制”是显性的制度与外部因素,晋商行走天下、艰苦奋斗、敢于开拓、以义制利、勇于创新的商业理念和变革精神,以及在商业模式上锲而不舍、不断创新的践行才是晋商在贫困落后的自然环境中努力奋起,成为中国商帮巨擘的内在动力和根本原因。晋商在明清时期商业模式与金融领域的一系列创新,创造了“货通天下”和“汇通天下”历时五百年的商业传奇。其形成的晋商精神与创新实践在创新驱动的新时代仍具有历久弥新的历史光辉和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