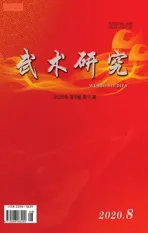辰溪龙头庵“掐龙舟”的文化生态变迁及传承逻辑
2020-11-24周兰江
周兰江 钟 曼
吉首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1 “掐龙舟”运动简介
龙头庵的龙舟当地人称为“燕尾龙舟”。龙舟都没有龙头,龙舟尾部向燕子尾巴高高翘起,龙头蜷卧着的三个大汉。龙头庵的龙舟都按宗族姓氏的不同,龙舟头尾分别涂上不同的颜色,为了区分同一姓氏中不同自然村的龙舟,所使用的旗帜的颜色又不同。每年的农历5月13是龙头庵龙舟最为浓重的时刻,辰溪龙头庵附近村寨的龙舟人员在头人的带领下陆陆续续下水。10点左右,四五十条左右的龙舟在龙头庵3000米长、400米宽的水面上进行顺时针划行,宗族力量越大,宗族的龙舟数量就越多。在龙舟独自划行过程中,如果不同颜色、姓氏的龙舟要进行龙舟比赛,则靠旗语,甲船碰到乙船,甲船的头旗手打出向乙船靠拢的旗语,乙船若划开,表明不愿比赛,则作罢;若向甲船靠拢,表明两船自愿比赛,两船蜷猪嘴的将两船头并齐、头旗手指挥打鼓靠拢后,活龙头互相进行拉、扯、箍等技巧阻止对方的龙船前进,龙头上蜷卧的大汉就开始进行掐架时,围观的村民开始为自己的宗族龙舟加油呐喊,小孩子坐在大人头上瞪大眼睛观看,生怕错过这激烈的时刻。“掐龙舟”活动是宗族展示彪悍、智慧、勇猛的一种方式,也是为宗族赢得荣耀的一种重要途径,同时也缓和了当地的族群关系,是族群认同和互动的文化象征。
2 “掐龙舟”运动形成的文化生态
2.1 辰溪龙头庵的地理位置及历史
龙头庵位于辰溪东南部,据县城41公里,东经110.34°,西经27.66°。沅水纵贯南北,其中瑶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0%。龙头庵是出入西南各地的关口重镇,形成了“骚人墨客,工农商贾,莫不以时云集于此”的画面,并形成了独特的七姓瑶文化,包括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据史料记载,龙头庵乡历史悠久,古为楚国属地,有瑶族先民在此居住。三国时期,诸葛亮曾驻守于此。唐朝贞观年间,因龙头庵的高地犹如龙头昂起,唐代的佛教信徒于此地建龙头庵寺庙于龙头之上。宋朝时,因大宋王朝镇压当地的猺寇叛乱,派将军来镇压此地的瑶人,瑶人被迫往崇山峻岭中迁,分布在此地高山里的各个区域。如今,龙头庵还有四神庙、宗祠以及瑶人坟的遗址。新中国成立后,龙头庵附近的瑶族文化逐渐被发掘和保护。
2.2 辰溪龙头庵的生态环境
征溪口遗址出土的一件褐色陶钵上发现有龙舟的图案。在这里也发现了龙的原型——南蛇,说明这里有适宜的温度、丰厚的深林以及濒临水面的洞穴群。当时沅水一带居住的居民,他们享有很丰富的资源。首先,地理环境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讲是非常有优势,他们靠近沅水促使当地的渔业资源很丰富,为龙舟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全国人民普遍面临大饥荒的年代中,生活在这里的许多家庭是靠沅江的自然资源来养活他们,如沅江里的渔和螺蛳成了他们的主要充饥食粮。其次,这里的气候比较湿润,属于中亚热带的湿润气候,全年平均气温在 16 度左右,而且这里的无霜期长,年平均日照时间在 1500 左右小时,其中,七、八月的日照时间为最多。雨水的处均降雨量在 1400mm,春季和夏季的降雨比较集中,因此这里的夏季和秋季干旱较少,这样的气候是非常适应水稻的生长。
2.3 辰溪龙头庵的社会制度环境
道格拉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1]传统乡村的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禁忌、族规乡约、文化传统)组成的。聚族而居就必须要有社会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仪式可以整合社会力量,创造一种看不见的神圣情境,通过仪式活动,确定社会秩序和社会等级。本研究着重分析“掐龙舟”仪式性活动运行的制度环境,田野调查发现,这些活动主要靠每个宗族的头人为基础的组织权力机构,以宗族血缘文化为保障。头人制定村规民约、祭祀活动等。在掐龙舟期间,村里每个人都有出槽子钱的义务、成年人都有回家划龙舟的责任、姑妈们都有为宗族龙舟上红的义务,如果做不到,红白喜事族人就可以不去帮忙,个体就会失去宗族的庇护,无法在村里立足。通过龙舟的头人组织制度,不仅强化了族群精英的权力关系,维持了乡村的秩序,重塑了乡村人们的行为规范,强化了本族的亲疏长幼关系规范着人们的,整合集体的力量,促进宗族文化的传承。
3 “掐龙舟”运动的变迁之路
3.1 五帝至战国时期—祖先祭祀的工具
据《元和郡县志》记载:“辰,蛮夷所居也,皆盘瓠子孙”。[2]盘瓠是辰溪瑶族人民的祖先和英雄人物。当时帝喾和犬戎氏发生战争,盘瓠为帝喾的战争取得了显赫的战绩,便得以和帝喾之女结为夫妻,婚后,迁入沅水一带,以狩猎和山耕为主,不断繁衍生息。但是晚年去看望儿子的时候,因为误会被杀死抛入沅江,得知真相后他的儿子们划着龙舟在沅江中寻找他们父亲的尸体,最后盘瓠在江里化身白龙升天而去,演变成瑶族先民对祖先、龙图腾的崇拜。盘瓠部落不得不通过原始的宗教祭祀仪式和划龙舟活动,这也解释了辰溪龙神寺庙、龙地名众多的原因,将具有血缘关系、亲缘关系的族群集中在一起,进行祭祀盘瓠的仪式和活动,祈求得到祖先神力的庇佑,从而在传统渔猎和耕作中获得丰收和生产,保佑族群无灾无难,五谷丰登。多次迁徙和生存区域不断扩大的盘瓠部落定期(祭祀、节日等)举行祭祀盘瓠图腾崇拜宗教仪式,运用龙舟祭祀和竞渡作为族群联系的工具,整合族群力量,有利于族群更好的生存和发展。距今1300多年的上辰溪罗子山瑶族乡的盘王殿就是反映和再现祭祀盘王的场景,龙舟作为祭祀的重要工具,祭祀盘王的同时整合族群力量。
3.2 汉唐时期—族群分化中的联系手段
中央王朝为了控制少数民族,对其进行隔离和分化政策,如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讨五溪蛮,导致五溪蛮的瑶族先民不断向深山里迁徙,从事“刀耕火种型”生产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为了生存和发展,瑶族先民开始分裂成一个个亚姓族群进行独立的生存和发展,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冲突。民间社会组织以“石碑制”为主,地域冲突得以缓解,地缘关系得到强化。瑶族遵循“石碑头人(寨老)”的管理模式,龙舟活动由寨老组织。据《旧唐书·杜亚传》记载:“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方舟前进,以趋疾者为胜”。[3]此时龙舟比赛的决胜办法主要靠速度为获胜的手段。而唐朝僧人见当地人民对龙舟的敬畏和痴迷,便在此修建了寺庙—龙头庵,达到传播信仰和教化的效果。活动期间,头人集合在龙头庵祭祀、参拜,白天进行龙舟竞渡,晚上同村、同宗一起用餐,开展篝火晚会活动,有利于加强族群支系地域的血缘和亲缘关系,商议划定有限生存空间,形成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生产资料的有效分配,并共同处理一些瑶族内部重大事宜。
3.3 宋元明清时期—族群矛盾中的润滑剂
辰溪的瑶族先民为了免瑶役,为朝廷提供大量的兵力,以夷治夷,嘉定七年 (1214 年), 臣僚复上言:“ 辰、沅、 靖三州之地, 多接溪峒, 其居内地者谓之省民,熟户、山瑶、峒丁乃居外为捍蔽 ……故皆乐为之用,边陲有警,众庶云集,争负弓弩矢前驱,出万死不顾。[4]在这期间,由于交通不便,龙舟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龙舟很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军事工具,然而在这一时期对龙舟的构造制造技术也发生大的变化,同时也锤炼了瑶族人民的体力、耐力、意志力、合作力等。据《米氏族谱》中的《四神庙考》记载:米氏先祖维雅公四兄弟是宋宣和二年 (1120 年)为镇压“瑶寇” 而来的军人。维雅公后来生有三子,罗子山一带的米姓家族就是维雅公的次子米柏公。米柏公长大后娶当地元朝土官郑万户之女为妻。 郑万户死后,米氏先祖米柏公袭其爵,成为当地土官,并替代郑万户统治管理七姓瑶。米氏家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把龙舟作为训练士兵的一种手段,并对龙舟的竞渡方式进行了创造性的改变。明代以后,瑶汉通婚、融合,龙舟在多种文化形态的融合中得以不断发展,在瑶汉之间缓解着族群冲突等功能。
3.4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末—民族识别下的族群文化危机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各地的瑶人族群统称为瑶族,瑶族又细分为布奴瑶、盘瑶、花脚瑶、过山瑶等。上辰溪的七姓瑶作为盘瑶的支系,有其独特的文化习俗。文革期间,龙舟被划为“破四旧”和“牛鬼蛇神”之列,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的代表,是封建社会残余。很多地方的龙舟都被劈坏焚烧,划龙舟则被认为是封建势力的复辟。虽然龙舟被禁,辰水流域人们对水的情怀很深。由于这期间的龙舟赛事遭到了扼制,所以导致了龙舟赛事发展不容乐观,甚至有倒退现象。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快速地发展,随之群众的生活程度也慢慢提高。此外,作为我国传统体育项目的龙舟竞赛也得到了恢复与调整。1978年5月,长冲口村青年人顶着各方压力,把龙船划到了龙头庵。此后各村龙船又重新做齐,连原来没有龙船的小村,也合伙做了龙船。但是,龙头庵在1986年,因掐龙舟引发了大规模的宗族械斗,造成人员的大量伤亡,政府销毁了所有的龙舟,禁划了20多年。1995年,辰溪曾家坪的龙舟前往岳阳参加了国际性民间龙舟大赛,展示了辰溪瑶族的民族文化。这期间,错误的政治政策和宗族之间的械斗扭曲了族群之间的关系。
3.5 21世纪至乡村振兴—族群文化展演的符号媒介
全球化导致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产生激烈的碰撞和交融,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入侵和渗透,必然会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认同带来严峻的挑战,这就需要在文化交往过程中的任何一方,都要保持对民族文化的自信。龙头庵及其周边地区的掐龙舟:一方面,在科学文化和工业文化的狂潮,以传统龙舟活动的仪式传统维持着乡土社会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以身体运动的方式进行文化展演。在文化展演中汇聚起的集体氛围能更好的传承族群文化。另一方面,以独特的文化符号在文化交流中展现着民族文化的自信,收获多元文化交互过程中的归属与自豪。如当地群众编排的排舞《七姓瑶俏龙舟》先后在辰溪县、怀化市作专场演出,同时,吸引了大量的群众、游客、记者以及学者的关注,七姓瑶的族群文化开始被深入挖掘和保护,当地政府也成立了以瑶族为核心的“七姓瑶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4 城镇化进程中“掐龙舟”的传承逻辑
4.1 集体记忆中的族群认同
通过身体实践的方式对族群过去的形象、历史、文化以及精神的重构。在瑶族“掐龙舟”运动中,仪式过程的精神文化、龙舟样式的物质文化以及头人组织的制度文化,是祖先适应生活、环境的行为的再现。在年复一年的周期性体育活动中,族群记忆得以强化,“掐龙舟”传统体育文化蕴含着族群历史、文化、精神信仰、价值观念等知识,个体在集体欢腾的场域中感受族群文化的规训与重复,集体欢腾的神圣空间使个体在无意识中习得和浸染族群文化、传统以及规则等,从而实现身体实践的记忆,使个体在集体行为的濡化中完成由生物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使个体的行为符合乡村生活的社会规范。重复性和周期性的集体活动有助于传递族群的历史记忆,在以身体为记忆的仪式活动中,他们将族群现存的文化和习俗融合到自身的生活,保持了族群文化的延续性。
4.2 宗族文化中的祖先崇拜
当地的彪悍民风与崇武尚勇的宗族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主要有若干机制起作用:一是当地部族的族长的积极提倡,族长为了生存发展,扩大自己的生存范围,提倡尚武精神,并通过宗族文化整合宗族的力量,将这种精神传递下去。二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关系甚密,对于住在山河之间的瑶族先民来说,除了稻田耕作之外,还要进行集体的狩猎活动。因此,在劳作之余,利用龙舟在江上锻炼自己的体力、耐力以及合作能力。三是军事斗争的需要,不仅要抵抗中央王朝的压迫,也有地方异族之间的兼并,一旦发生战争,龙舟就是运送战争人才和战争的工具,尚武之人才能在战争了保己、保家、保族。四是价值观的认同,在野蛮的文明中,武力是族群发展的手段,宗族对彪悍、勇猛之人给予了最高的荣誉,形成一种内在的价值观,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内化为个体自身的信念和行为准则。崇武尚勇的宗族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经过特定的空间、结构、场所对个体意识、观念不断渗透、熔铸而成的。“掐龙舟”运动延续了当地的崇武尚勇之风,崇武尚勇的宗族文化传承了“掐龙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