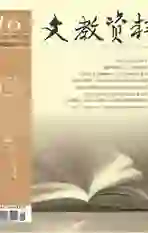魏晋家书与士人精神世界
2020-08-20田宇
田宇
摘 要: 魏晋两百年的分裂动荡使士人的精神世界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家书作为窥探士人内心世界的一面窗户,向我们诉说着那个时代的悲欢离合、千情万象。
关键词: 魏晋 家书 士人 精神世界
中国古代宗法制社会重家族、重伦理,以告诫道理、表达情感为主题的家书创作源远流长。以诫子书为例,可追溯至西周时期周文王的《遗戒》,此后有尹逸《遗言》、季孙行父《戒子》、田常《遗令》、孙叔敖《将死戒其子》等[1]。至魏晋时期,时代的巨变促使士人将关注重点从外在世界转移至内在精神世界,旨在抒发自身情感的家书得到繁荣发展,书写着这一时代士人的所思所感。
一、时代背景
魏晋两百年,时代动荡,国家分裂。目睹乱世中人们辗转流亡、朝不保夕的命运,士人的精神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摧残,内心充满痛苦,这一时期儒家经学已不能成为士子们的精神寄托,儒家学说的衰落破除了思想上的束缚,再加上乱离现实的刺痛,人们更多关注内在精神,抒发真情实感。有一定私密性的家书便为倾诉情感的需求提供了绝佳的载体,于是,这一时期家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数量上都体现出前所未有的进步。汉末群雄并起,干戈不息,三国间攻伐不止,政斗不休,西晋虽短暂统一中国,但“八王之乱”使国家分崩离析,士人朝不保夕,随之而来的是匈奴铁骑踏破中原,北方陷入战场,晋室南迁。身逢乱世,大一统时代“修齐治平”的机会不复存在,面对惨痛的现实,士人们选择各异,或坚守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以乐观的心态参与世务,或疏远儒家理想,消极处世以避祸患。东晋百年,政局相对稳定,士人的心态趋于平和,魏晋时流行的玄学逐渐繁荣,启发人们从山水自然中体悟玄理,再加上佛教的流行和玄佛合一的趋势,这时期的家书多日常生活、山水自然的描绘及文学的探讨,反映出文人雅趣。
魏晋时书信体散文发展到成熟阶段,在《典论·论文》中曹丕将书论、铭诔等纳入了文的范围之内,并进一步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2]。该论述对明确书这一文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任昉的《文章缘起序》细分文体为八十四种,其中又将书分为七种[2]。梁萧统编选的《文选》分类收录文章时专列出“书”类收录书牍作品,不仅保留了从两汉到齐梁的众多重要书信,更向我们展示了书信体的发展流变情况。刘勰的《文心雕龙》也对“书信”的基本内涵进行了阐释,他说:“盖圣贤言辞,总为之书,书之为体,主言者也。”[2]书信体题材多样、结构灵活、便于抒情的特点吸引了众多士子进行写作,促进了家书的繁荣。在汉代家书主要作为教子的工具,到了魏晋时期,家书的题材明显扩大,参与人数明显增多,折射出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
魏晋家书中展现的精神世界具有书真情、道真言的特点,无论是谆谆教诲还是娓娓道来,情感真挚朴实,贴近日常生活,贴近人物内心,我们从中可以读出作者最真切的想法。魏晋诗赋受流行的玄学思想影响,表现出“辞旨渊远”“寄托遥深”的特点,而魏晋士人家书则基本没有玄学思想,多抒发真情实感。这可能和家书本身的功用有关。家书是面向家庭成员而书写的文体,必然要求书写者将内心的真实想法交代清楚,如果在家书中大段论及“自然”“真”等较难理解的玄学思想,就势必会影响书写者思想情感的表达,也超出了家书文体的表达范围。魏晋家书展现出的士人精神世界,不同于主流明面上充满玄学追求的“魏晋风流”,而有其私密性、真实性。
二、魏晋家书中的出入世精神
魏晋时期,外部环境动荡不安,充满不确定因素,人们无法自主命运,只能被裹挟于时代洪流,辗转奔波。面对这样的时代,士人常常会产生命运无常之感,采取出世的态度,审慎为人,明哲保身。但也有人选择坚守儒家入世的精神,以积极的心态参与国家事务,展现出向上的风貌。兩种不同的态度既矛盾又统一,展现那个时代士人复杂的精神世界。
出世态度中最典型的是嵇康的《家诫》。嵇康为人“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3],这样的性格让他选择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招来了杀身之祸。在死前所写的《家诫》中,嵇康用大段篇幅告诫儿子为人谨慎,避免灾祸,不希望他重蹈自己失败的生活道路。面对“长吏”,他告诫儿子:“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4]而在做人的不同方面,“立身”应“当清远,若有烦辱,欲人之尽命,托人之请求,当谦言辞谢:‘某素不预此辈事。”[4]“行事”则“先自审其可……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守人,虽复云云,当坚执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4]。“言语”上“机动物应,则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4]。详尽为人之理。与嵇康同时的李秉在《家诫》中以当时名人的事例教育后代:“上曰:‘然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为明诫。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4]从中可以看到司马氏当政时期士人避祸保身的风尚。羊祜身为西晋大将、伐吴功臣,但在其《诫子书》《与从弟琇书》中却看不到身处高位的责任感、使命感,反而能感受到“惧盈满以受责”[4]的胆小谨慎、“恭为德首,慎为行基”[4]的处事态度,这可能和他经历过魏晋易代有关。曹魏后期,司马氏独揽朝纲,诛杀异己,以铁血手段夺取政权,这就造成由魏入晋的臣子惧怕皇帝猜忌,选择审慎的态度保身避祸。虞预在《与从叔父书》中表达对黑暗官场的担忧:“邪党互瞻,异同蜂至,一旦差跌,众鼓交鸣……此古人之炯戒,而预所大恐也。”[4]这也是一种出世精神。
在此之外,许多士人表达了积极入世的态度。诸葛恪在《与弟公安督融书》中表达了自己身为宰辅的责任感:“念出万死,无顾一生,以报朝廷,无忝尔先。”[4]张就在《被拘执私与父恭疏》中以“愿不以下流之爱,使就有恨于黄壤也”[4]表达自己以身许国、无心男女之爱的高尚情操,展现出一位武将的光辉形象。一代名相诸葛亮在《诫外生》中说道:“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4]这样的精神激励他一生尽职尽忠辅佐蜀国两代君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东晋名臣王导的家书透露着他捍卫儒家伦理、积极入世的精神。他在《与从子允之书》中劝诫王允为了振兴家族出仕为官,在《遗王含书》中批评王含身为逆臣“负先人平素之志”[4]“既没之日,何颜见诸父于黄泉,谒先帝于地下邪”[4]?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自觉捍卫儒家君臣伦理。
三、魏晋家书中的为人处世之道
魏晋家书中有许多以告诫子女道理为主题的诫子书,这类家书向子女阐述道理时或依据书者人生经验,或依据儒家伦理,或依据榜样人物。在劝诫之言中,流露出的是士人充满个性的为人处世之道。
曹衮身为魏国宗室,他在《令世子》中依据儒家礼乐伦理,告诫世子要有身为宗室之后的自觉。“接大臣,务以礼。虽非大臣,老者犹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奉圣朝以忠贞,事太妃以孝敬”[4]。一言一语之间是对礼乐伦理秩序的自觉维护。蜀国向朗曾为丞相长史并随诸葛亮北伐,深得诸葛亮的信任。他在《遗言戒子》中引用《传》中的话论证“和”的重要性,以此向儿子传达自己“唯和为贵”的处世之道。向朗认为“《传》称师克在和不在众”[4],表明“天地和则万物生,君臣和则国家平,九族和则动得所求,静得所安,是以圣人守和,以存以亡也”[4]的道理,因此“贫非人患,唯和为贵”[4]。诸葛亮在《诫子》中阐明“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4]的道理,其中“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作为家庭教育思想被后世推崇。此外,书中还提出了“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4]的道理,也是家庭教育思想的典范。西凉王李玄盛就对诸葛亮推崇备至,他告诫诸子:“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师,何必远也。览诸葛亮训励,应璩奏谏,寻其终始,周孔之教尽在中矣。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质略易通,寓目则了,虽言发往人,道师于此。”[4]李玄盛将诸葛亮看成儒家圣人,认为学习他可以给个人和国家带来巨大成功。其师法诸葛亮的为人之道的用意鲜明地显现出来。曹操的《戒子植》以自己做顿丘令时“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4]勉励曹植做事多思考,不要留下后悔。体现曹操善于反思自我的为人处事原则;曹丕的《诫子》告诫子女不知悔改坏事早晚会暴露出来,反映他反思自我、诚信做人的处事方法。
魏晋时的女性劝诫家书虽然不多,但也能以其细腻的情感展现女性独特的风格。郭照《敕外亲刘斐》中的“诸亲戚嫁娶,自当与乡里门户匹敌者,不得因势强与他方人婚也”[4]及《敕诸家》中所写“今世妇女少,当配将士,不得因缘取以为妾也。宜各自慎,无为罚首”[4],都能展现一位母仪天下的贤后形象。陶侃母亲湛氏劝诫儿子守廉:“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也。”[4]从中可以看出湛氏是一位深明大理、教子有方的贤母。孙琼在《与从弟孝徵书》中以周懿公和周文王做对比,教育从弟“而此圣以兴,彼愚以灭,盖置之失所”[4]的道理,是一位明理善教的贤姊。
四、魏晋家书中的亲情和爱情
亲情和爱情是魏晋家书中另一个重要的精神世界,保护着士人心中最柔软的角落,代表着士人心中最温暖的归处,承载着士人心中最质朴的情感。走进亲情家书和爱情家书,我们不仅能体会到动乱中思念家人的痛苦,感受到安定时分享生活的快乐,更能领会到离合时传达情意的真挚。其中女性的声音是时代的亮光。
表达对家人的牵挂、关心家人的情况是魏晋亲情家书中的重要内容,虞翻在《与弟书》中关心儿子的婚嫁问题,言道:“长子容当为求妇,其父如此,谁肯嫁之者?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旧族。”[4]当时虞翻遭人构陷,被贬远郡,他害怕儿子被自己牵连找不到媳妇,便写了这封家书。从中可以看到虞翻对儿子的深切关怀。不管自己身在何地,处于何境,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孩子,这便是父母之爱的伟大无私之处。陆景的《与兄书》写道:“自寻外役,出入三年,缘兄之笃睦,必时存之。宝录兄书,积之盈笥……有信忘数字,每见手迹,如复暂会。”[4]从抄录兄长的书信可以看出陆景的思念之深切及兄弟亲情之和睦。李衡在《临死敕其子》中告诉儿子自己为他留了“木奴千头”[4],临死仍要安排好儿子将来的生活;王修在《诫子书》中以“自汝行之后,悢悢不乐。何者?我实老矣,所恃汝等也,皆不在目前,意遑遑也”[4]表达对儿子的思念,从这两封家书能看出父母对孩子质朴且充满深情的爱。与家人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是魏晋亲情家书中另一个重要内容,这样的家书多出现于西晋“八王之乱”前及东晋时期,与当时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有着密切联系。谢万的《与子朗等疏》告诉儿子自己“便流火感伤,兼切不自胜”[4]的身体状况。谢玄《与姊书》写游园所见,《与兄书》写自己“垂纶”“钓鲈”的活动。陆机《与弟书》写自己游览洛阳“夏门”“仁寿殿”“监徒武库”“天渊池”等地的所见。从中可见国内环境稳定时士人的精神世界是平和、闲适的。
爱情家书反映魏晋士人的爱情心理,是魏晋家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廞在《与静媛等疏》中将三位妻子静媛、静仪、静婔当作能理解自己的知音,向她们诉说母亲去世的痛苦:“告诱静媛、静仪、静婔:此晦便当假葬,永痛抽剥,心情分割,不自胜。念汝等追痛摧恸,缠绵断绝,何可堪任,痛當奈何,当复奈何!”[4]从家书中的抒情可以看出王廞对女性的态度是充满尊敬的。王献之《如省》中写道:“相过终无服日,凄切在心,未尝暂掇。一日临坐,目想胜风,但有感恸,当复如何?常谓人之相得,古今洞尽此处,殆无恨于怀,但痛神理与此而穷耳。”[4]这是他离婚后向郗道茂表达自己思念之情的文字。王郗二人因为皇帝下召被迫分开,所以王献之在怀念前妻的文字中充满款款深情。《世说新语·德行》提到:“王子敬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5]可见王献之对前妻的深情。魏晋爱情家书中有着时代的光亮,那就是女性话语权的上升。黄门郎秦嘉的妻子徐淑曾写《答夫秦嘉书》《又报嘉书》,文辞优美,情感真挚,动人心魄。“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岩岩,而君是越,斯亦难矣。长路悠悠,而君是践,冰霜惨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动而辄俱?体非比目,何得同而不离”[4]?“镜有文彩之丽,钗有殊异之观,芳香既珍,素琴益好”[4]。这些句子正体现徐淑对丈夫热烈而真挚的爱情。而窦玄妻《与窦玄书》则是斥责丈夫喜新厌旧,表达诀别之情。书中写道:“弃妻斥女敬白窦生:卑贱鄙陋,不如贵人。妾日已远,彼日已亲。何所告诉?仰呼苍天。悲哉窦生!衣不厌新,人不厌故。悲不可忍,怨不自去。彼独何人,而居我处!”[4]都能看出魏晋时女性的个性得到张扬,女性的自立意识得到发展,女性的独立性得到增强。
五、魏晋家书中的士人风尚
在魏晋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士人的生活中形成了一些具有时代特点的风俗。这些风俗在家书中也有体现。当时盗掘墓冢现象严重,不仅是草莽流民,连一些军队将领也因为打仗需要而发掘墓葬。郭照《止孟武厚葬其母》中“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4]表明当时盗墓现象严重,郝昭《遗令戒子凯》中更有“吾为将,知将不可为也。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4]这样的描述。因此时人中厚葬的风气逐渐消退,代之以薄葬的要求。郝昭曾告诉儿子:“汝必敛以时服。且人生有处所,死复何在耶?今去本墓远,东西南北,在汝而已。”[4]魏晋皇室也多兴薄葬,对民间丧葬风气转变发挥了表率作用。郭照《止孟武厚葬其母》提到“首阳陵可以为法”[4]。首阳陵即魏文帝曹丕的陵墓,他遵从父亲曹操的意志选择薄葬,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由于时代原因、上层人物的提倡及魏晋玄学、佛学的影响,薄葬遂成为士人中的新风尚。如庾峻在《遗敕子珉》中说道:“朝卒暮殡,幅巾布衣,葬不择日。”[4]与动荡的时代环境相伴产生的另一种风尚是饮酒。酒可以帮人忘却现实的苦恼,所以乱世饮酒之风便盛行。士人在家书中多有对饮酒之行的劝诫,基本是站在“礼”的角度劝家人饮酒适度。王肃在《家诫》中说道:“夫酒,所以行礼、养性命欢乐也。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是故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备酒祸也。”[4]当作为主人招待客人饮酒时,需要“使有酒色而已,无使至醉”[4]。如果遇到被人强性劝酒,则“必退席长跪,称父戒以辞之”[4]。作为下属向上司敬酒时,可以“随其多少”[4],而玩游戏被罚酒时,则应该“示有酒而已,无使多也”[4]。王肃从生活细节出发告诫家人饮酒的规范。诸葛亮也写过同样的家书,他的《诫子》中是这样说的:“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致醉,无致迷乱。”[4]这些家书都反映了当时士人饮酒的风尚。
六、魏晋家书中的文人雅兴
魏晋士人家书中还有一类主要表现士人雅兴。这类家书和分享生活的家书多出现于国家形势较为安定的时候。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陆云《与兄平原书》(三十五首)及姚兴《答安成侯嵩难述佛义书》。陆运《与兄平原书》三十五首中和其兄陆机探讨文章、文学的家书占绝大多数。例如“云再拜:省诸赋,皆有高言绝典,不可复言。顷有事,复不大快,凡得再三视耳。其未精,仓卒未能为之次第。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恐故复未得为兄赋之最。兄文自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4]。姚兴的家书则反映了佛学对魏晋士人的影响。例如“卿若以众生为疑者,百亿菩萨,岂非众生之谓邪?然经复云,普明之诣释迦,皆与善男子善女人,持诸华香,来供养释迦,及致供养之徒,自应普蒙其润也。但光明之作,本不为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余波者,其犹蝇附骥尾,得至千里之举耳”[4]。分享生活的家書中徜徉山水的内容也能看出玄学影响的痕迹。
魏晋时代士人精神世界的森罗万象,都可以在这个时期的家书中窥见一斑。我们读家书,便可以走进士人的精神世界,品味那个时代的悲与欢、离与合、衰与兴。
参考文献:
[1]刘晓千.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D].泉州:华侨大学,2008.
[2]马臻.三国两晋家书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3.
[3]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02.
[4][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03.
[5][南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