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岛崎藤村的《千曲川风情》看日本自然主义文学风格
2020-08-04郑一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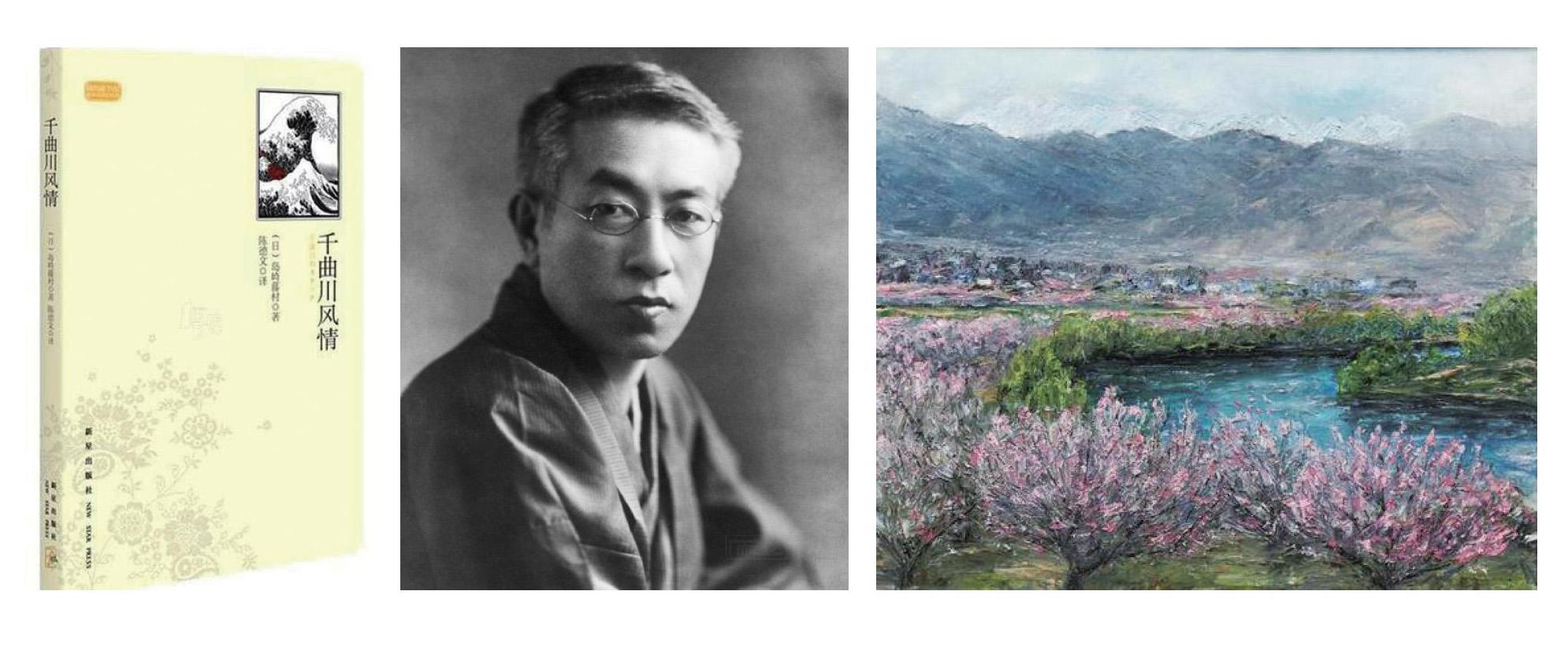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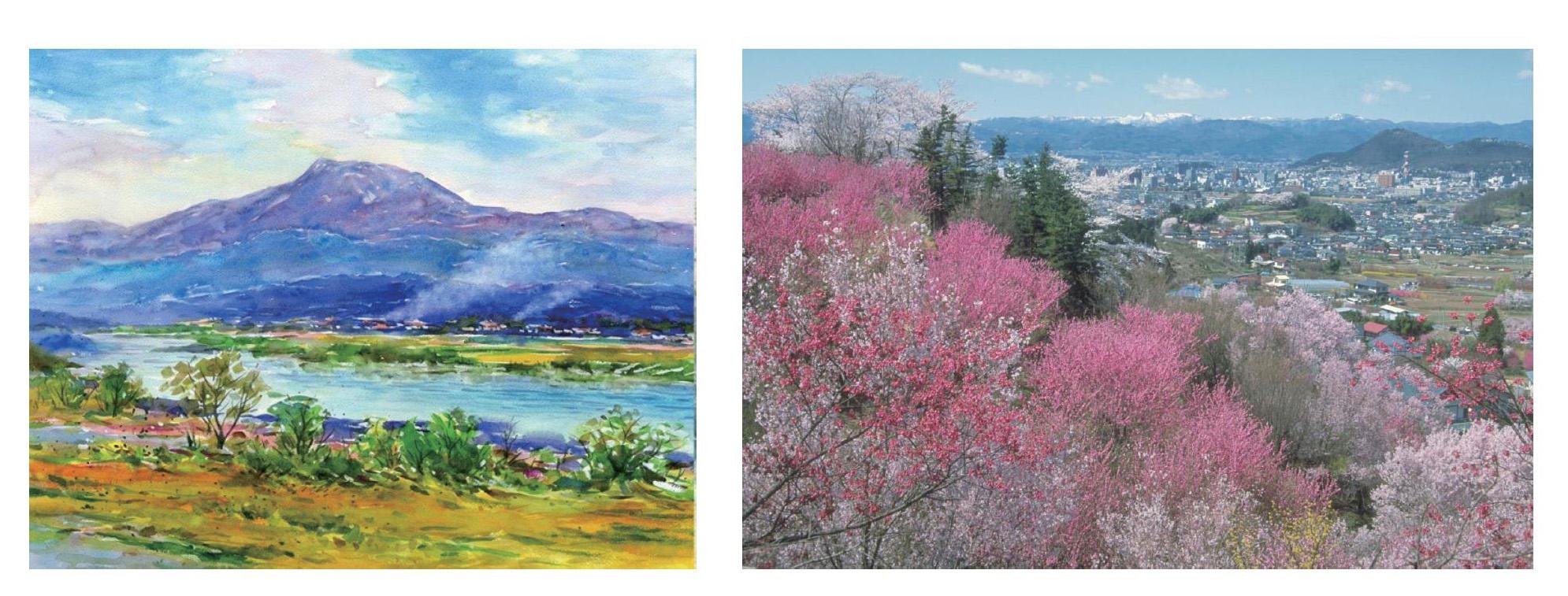
摘 要:以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岛崎藤村的《千曲川风情》为例,从创作视角和创作伦理的角度结合文本进行分析。揭示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对“自然本身”追求的僵硬和片面,“绝对客观”的创作观念混淆了客观和真实两种不同的属性,使自然主义实际上成为了“客观主义”;而作为创作手段的“绝对客观”的文字,恰恰呈现了最“不自然”的自然。
关键词:岛崎藤村;千曲川风情;日本;自然主义文学
一、自然主义的风格
——客观性抑或真实性?
自然主义创作方法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抒情等主观因素,轻视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崇尚单纯地描摹自然,着重对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做记录式的写照。
岛崎藤村的《千曲川风情》是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典型,作者贯彻“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的创作理念,努力试图回避主观视角和想象,用大面积篇幅对人物、场景进行了“一五一十”的描述,整个作品呈现出一幅全息风景画的样貌。作品的叙述风格也接近平直,作者几乎“不露声色”地陈述着环境和事件,甚至在罕见表达心情之处也只拣选“平静的文字”,对自然主义风格的追求在作品中贯彻始终。
正像作者在给吉村君的信(即《千曲川风情》序言)中提到这本书时所说的,是向吉村君介绍“我”在千曲川生活的“写生集”。作者的创作态度一目了然,即追求一种写生般再现的效果,书里的每一篇短文都透露出作者那副冷酷的观察者的态度——千曲川是作者想要原封不动“搬”到纸上的风景。而作者似乎没有注意到:风景画也有画者观察风景的观察角度,那么作者想要“搬”到纸上的“事物本来的样子”出自谁的视角呢?
还是出自“我”(即作者)看事物的视角。比如,在《少年群》中“我站在那里瞧着他们”[1]15,这个“瞧”就是“看”,就是作者的视野。这是叙述中的“看”,所以叙述本身就带着“看”的角度,也就是说,这个“瞧”,乃是作者“看”中的、作者自己的“瞧”。“我”“看”自己,自己也成为了自身视野的对象,在作者“看”事物(对象)的过程中,作者同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怎样建立的?作者到达事物之间的媒介又是什么?不妨设想,在“作者—事物”(即“主体—对象”)这一组关联式中,作者“看”事物的背景是否能够被彻底剥离?这种剥离的意图和操作是否带有主观性?不难发现,所谓“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本身就是一种不意识的观察角度,而“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本身就是带着一种不意识的主观视野去摹仿事物的方法。
再比如在《中棚》中“随着向千曲川方向沉落,山谷也越来越深了”[1]40,“沉落”“深”都是相对于作者的主观视角而言的,因为没有参照,就没有“沉落”和“深”的体现。后文“跟隅田川相比”,则是一种视角中的视角,在叙述视角中,作者主动提供了一种主观判断的视角——“跟……相比”。此外,“倾听”“感觉”“想象”等也都是一种“看”,是个人的感官或经验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这些便是作者同事物相联系的环节,是使自身的观察切入自然的角度,这种角度把自然分割开来,并进行选取,作者忠实描述的,是融入了自身视角的、主体所经验的自然。
自然主义对绝对客观的追求,背后的逻辑是人同自然作为主—客体的二元对立,越是强调客观,就越是要把主观显现出来,因为主观和客观本就是在以对方为界限的对立关系中互相映衬的。所以,将“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作为创作的出发点,这种“出发点”本身就是一种主观因素。因为自然是没有某个单一的出发点的,而出发点只能是意识的规定。换言之,这种“出发点”作为创作的基本原则,其实构成了一种采用客观主义的主观视角。
任何一种视角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存在本身是合法的,但当其作为一种绝对原则并追求极致表现的时候,就难免落于空乏的审美主义而丧失“真实性”。须知客观性和真实性乃是两种不同的意涵。因此,在创作实践中,作为一种“出发点”对真实性的近乎极致的追求,可能恰恰在不意识中既遮蔽了真实性,也同自然主义所追求的所谓客观性背道而驰。
二、“感官感知的自然”
——自然主义还是经验主义?
自然主义对绝对客观性的追求其实恰恰强调了主观的参与,上文已举例论证。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自然主义倾向也存在着诸多不可化约的主體的彰显,其中包括:作者对观察素材的取舍选择、作者的感官感知、作者个人情感不意识的投入,作者的语言(即思维与视角)等因素。
在《山庄》中:“乡下人的神经质都在这些地方表现出来了”“小诸就是这样……”[1]27,都是作者的主观判断;在《九月的田埂》中:“昨天看到的山和今天看到的山都不一样,几乎每天都发生变化”[1]53,则是作者的主观感受。在《落叶》中更体现得更为明显:
我真想到厨房里暖一暖冻僵的双手。穿着布袜子的脚趾也感到冷冰冰的。看样子,可怕的冬天就要临近了。[1]72
作者的手冻僵了,作者的脚趾感到冷冰冰的,这是他感觉到冬天就要临近了。自然的变化会引起主观感觉的变化,这些都是主体同自然之间相互渗透的部分,两者是无法彻底剥离开来的。
作者的感受、情绪、判断、常识等,甚至回忆、想象,其实都是作者作为主体视角的一种表现。在创作实践中,这些因素是不可排除的,因为一旦排除,就不可能再生成表达。而这些因素往往是作者主观不意识的,因而这些因素所形成的表达是不意识地被带到作品中来的。这些因素在作品中构成了对自然主义风格的先天破坏,成为自然主义白璧上“不自然”的瑕疵。
构成这种破坏的,是主体性的存在。主体性是自然主义作品中无法化约的“质数”,根本导致这不可化约的“质数”对自然主义孜孜不倦的追求的,是概念的混淆:在自然主义作家对“自然”的理解中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即“感官感知的自然”同“自在自然”的区别,在创作实践中,常误将两者混为一谈了。
“自在自然”可否被感知,换言之,可被感知的自然是否是“自在自然”,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感官感知的自然”与“自在自然”之间的“误差”则是无从判断、也不可敉平的。因而,自然主义所能达到的,并非像其宣称的那样,“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即按照“自在自然”的样子去摹仿,“自在自然”事实上是根本无法被统一到人的感官及意识中来的。
所以,自然主义叙事风格中,作者视角的相对弱化并不意味作者视角的消失,因而自然主义对绝对客观叙事的追求,本质上只是绝对主观叙事所呈现出的一种状态或一个角度。这种作者视角弱化的一个恶果,是在自然主义作品中充满了不意识的经验之流。“感官感知的自然”同“自在自然”处在不意识的混淆中,直接导致了作者对主观经验到的一切,做出所谓“忠实”的描述同对“自在自然”的再现之间也同样处在不意识的混淆中。因而自然主义文学归根结底其实是以主体经验为本体的一种经验主义的创作方式,在主题—客体的结构中,主体经验像一个无法化约的硬结,阻住自然主义作家通往“自在自然”的去路。
三、“自然”还是冷漠?
——自然主义作家同自然的关系
如果自然主义作家一心想要剥离自身作为主体的视角,一味“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根本不需要那么费尽心思,而只要架设一台摄影机,放置足够长度的卡带就可以忠实地记录一切了。但是,即便如此,摄影机也有其摆放的位置,也有镜头投射的方向,甚至还有摄影机的机械原理与底片冲洗时的操作手法等,通通都构成摄影机的视角——一切想要摆脱视角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或许有人会认为,摄影机的视角是没有情感色彩的,因而至少在此意义上,摄影机对事物的记录是客观公正、不带偏狭的。自然主义作家们是否正是抱此想法呢?——人要客观公正、不带偏狭地去摹仿事物,而把自身的眼光变成一台摄影机的镜头。那么,人能够超越摄影机吗?
问题在于:人出生成长,换言之,生存在大地上、社会中的过程,是生动的,不是摄影机能够模仿得了的。那么,生动地成长起来的个人,在观察事物的时候如何过滤得了自身的生存背景、社会身份、甚至是语言习惯?!个体在面对自然、面对他人的时候,会产生自身的态度——喜爱、厌恶、难过、同情等。这是个体同自然、同他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也是伦理关系,这便是主体“看”世界,即主体到达自然的过程或媒介。这里重要的是:人同自然、同环境、同社会,总是处在一种互生的关系中。
自然主义创作方法谋求在叙述中摒除个人情感,相当于强行割断人同自然之间的联系,即人是人,自然是自然。在这种叙述形态中,读者可以看到作者的“一视同仁”,却看不出作者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生动的事件所持有的态度和内心真实的情感。即便这种情感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也是极尽克制、压抑而显得十分不“自然”的。
在《护山人》中:“主人还谈起山火的可怖,谈起有的人被山火追逐着烧死了”[1]59,在这种叙述中,作者对于人的苦难所持的态度,是“自然”,还是冷漠?从文字中,读者几乎无从感知。自然主義确会导致这种模棱两可。质朴的文字风格中透射出带着古典气息的严肃格调,不卑不亢的情感态度中可以令人感到深沉的敬畏力量;然而,这一切也可能翻转为另一面,毫无生气的文字背后,或许隐藏着同样毫无生气的灵魂。文字是冷漠的,语气是冷漠的,作者对自己观察到的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的态度,是否也是冷漠的?这便造成了这样一种讽刺:唯一让自然主义作家们关心的,只是竭力隐藏起“我”的视角;而更加讽刺的是,正是这种隐藏的努力,才使自然主义作家的文字追求,更加不“自然”。
四、结语
自然主义的创作风格混淆了客观性和真实性,这种混淆造成了自然主义的实际创作陷于自身的反面——即不意识的经验主义,而背离了自然的经验。此外,在语言伦理层面,自然主义对自然模棱两可的态度与贯彻自然主义文风的刻意而为,恰恰造成了一种非自然主义效果。因为作家从与自然的关系中抽离自身,采取“旁观者”的态度,所谓的客观记录恰恰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参考文献:
[1]岛崎藤村.千曲川风情[M].陈德文,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郑一萌,同济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