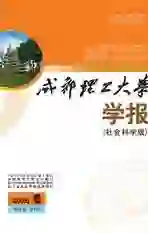积用成体:欧阳予倩对现代戏剧本质的诠释探赜
2020-04-18唐振
唐振
摘要:欧阳予倩的戏剧理论发生,经历了写社会人生之真、求现实与浪漫双美之合和援西体以合中用的过程化进路。他对戏剧本质的理解也在此进路中不断丰富:戏剧主题内容的现实性作为戏剧的主导性质,推动着创作手段的多元化和审美追求的多样性。同时,事实与价值视域下对艺术与思想关系的探微,亦能重新审视欧阳氏戏剧理论中唯美与写实、艺术与政治之关系。
关键词:欧阳予倩;戏剧理论;戏剧本质;理解;诠释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0)06-0086-06
现代诠释学的观点认为,理解是理解主体在不问断地与历史对话中完成的,由此而不断形成的包容历史与现代的整体视域形成了我们于对象身上所获得的理解。就此理论,我们就不难知晓为什么王国维那个历来为大多学人奉为圭臬的著名论断“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近百年后的京剧人却又再度对此质之以疑了,并以今日之经典曲目的叙事功能早已淡出为由,认为应将其改作“以故事演歌舞”。
贵为中国传统艺术的戏曲尚且这般,作为“舶来品”的现代戏剧尤为如此,特别是在中国现代戏剧早期滋生萌芽之际,有关戏剧内容、形式之探索一直都是有关戏剧讨论的主题。作为艺术的戏剧,其主题与内容决定了这一艺术样式的功能,形式与表现手段则影响着功能实现的程度。因此,就根本而言,有关现代戏剧的理论思索,实质上都是对戏剧的功能乃至本质的探赜,而这样的思索本身就在不断地丰厚着戏剧作为艺术的本质内涵。其中,欧阳予倩作为中国现代戏剧创始人和开拓者之一,他的戏剧理论发生过程实在可谓是戏剧本质的丰赡经过,他的戏剧创作与理论创作史也实在可称得上是关于戏剧本质的诠释史。
一、戏剧理论的过程化总结
欧阳予倩是“中国剧坛‘学贯新旧的唯一学人”,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的“两栖兼通”使得他能够放开眼光,始终“以世界性的眼光来探讨戏剧舞台艺术的现代性问题,努力汲取当时世界舞台艺术的新成果”,一生都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架设中国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之间的“金桥”。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中国与西方的交互激荡,催生了欧阳予倩自己有关现代戏剧的理论。然但凡一种理论发生,必然是受到彼时思想气候之影响,在此种外缘影响之下,理论的催生过程必有其实际生成的思想过程和内在发生理路,换言之,欧阳予倩的戏剧理论在被摆到“展览橱窗”之前,必然经历有“思想车间”中的理论耕耘。只有通过对其戏剧理论发生的过程化研究,才能使我们窥得其戏剧理论的自我修缮之过程和对戏剧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刻之经过。
依循欧阳予倩的人生遭际和戏剧与戏剧理论创作为线,可将其戏剧理论主张理出如下三个发展的阶段:
(一)写社会之真
虽然1910年代欧阳予倩便已投身戏剧创作,但1929年广东戏剧研究所建立后,才是欧阳予倩系统进行戏剧理论创作的一个高峰期,因此,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才算得上他戏剧理论思索的第一个阶段。欧阳予倩赴日留学期问,接受了小山内薰等人“戏剧是描写人生的高尚艺术,而不是低俗的娱乐”的观点,“戏剧是艺术”“为人生”也成为他毕生笃固的信仰。五四以来他积极投身于戏剧改革之中,认为“艺术的标准就是要把握住人生的真实,社会的真实。失了这真实性,作品便不能成立”。大革命失败后,他的剧作更加注重“站在社会前面”,戏剧思想中的写实主义凸显得也愈加明显。这一阶段,他的主要戏剧主张为“写社会之真”,戏剧的写实使其为戏剧,“有什么社会,便有什么戏剧”。“九·一八”事变后,欧阳予倩所创作的《李团长死后》《上海之战》等大量抗日题材写实主义剧作,进一步彰显戏剧当“写社会之真”的理论主张。但需要注意的是,“写社会之真”并不是将戏剧当作宣传的“工具”和“武器”,戏剧的写实并不代表戏剧应当成为政治的传声筒,“用戏剧来宣传,必须先有健全的戏剧”,戏剧的写实是建立在戏剧首先必须是健全的戏剧艺术这一前提之上的,這同时也是欧阳予倩一直以来的戏剧观点。
(二)求写实与浪漫的双美之合
欧阳予倩虽在其戏剧理论中表现出了较强的写实主义倾向,然而写实主义的戏剧并不是欧阳予倩的最终艺术追求,他虽一直主张艺术的写实,但同时也认为,通过戏剧传达人生社会之真,并不是非要借助写实主义不可。在1942年欧阳予倩寓居广西改革桂剧时,他便提出,“有些主张写实主义的人,绝对不理浪漫派的戏;唯美派系统的导演们,又对着写实主义以为不值一盼。不过我认为,如果不是很机械地存着偏见去看,各种表现的手法都有可取之处。”。此时欧阳予倩的戏剧理念进一步开阔,对写实主义的理解也走进了一个更深的层次,认为只要能够把握要点,能够把戏剧的内容完全无缺地表现,用哪一种手法都可以,倡导建立一个“新写实主义的体系”。他对戏剧表现手法应当多元化的认识,初步显现出一种求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双美之合”的戏剧创作观念。欧阳予倩在寓居桂林的六年问,主持了对传统桂剧的改革,并导演创作了一系列抗战剧作。同时,他和田汉等人一起策划举办的西南剧展,对聚集抗战文艺队伍、展示抗战文化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辗转广西进行桂剧改革的这一时期,欧阳予倩所进行的戏剧活动既是以文艺家的身份投身抗日救国的大潮当中,同时亦可算是欧阳予倩进行戏剧理论系统总结的第二个重要阶段。
(三)援西体以合中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欧阳予倩的研究更多集中在中国传统戏曲之上,其有关现代戏剧理论的重心也转至现代戏剧对传统戏曲营养的吸收中来。他通过对此前创作剧本的重新整理和对现代戏剧的艺术本质再思索,试图在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戏曲精髓的基础上,融合西方现代戏剧,从而形成中国自己的现代戏剧,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我们的话剧应当在中国传统艺术的传统基础上创造出更新的表现形式”。这是为欧阳予倩戏剧理论的第三次总结,主要表现为用西方的戏剧结构和戏剧思维结合中国传统戏曲的艺术元素与表现手法之“西体中用”的戏剧改革理念。
值得一提的是,欧阳予倩此三阶段戏剧理论并非冲突抑或割裂的,乃是在结合时代历史语境与自己戏剧创作中不断摸索并反思而得出的。写社会人生之真是戏剧能够“为人生”之根本,求写实与浪漫的双美之合是戏剧表现增强之手段,而援西体以合中用则是旧剧改革推行之方略。此三者共同表现出欧阳予倩对建构中国现代戏剧“新写实主义体系”的构想。
二、戏剧本质的过程化诠释
关于对象的诠释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在人文领域的研究对象表现尤甚,由循环诠释而得来的理解总在不断地丰富着理解本身。因此,任何一个无论从事实还是价值的层面对概念所下的判断,因为概念自身的历史性与生成性,致使我们都永远无法穷尽对概念本身的认识和理解。于是,才有了所谓“对于人造物,我们要历史地理解其性质并毕其功地彰显之”(即在关于对象功能的不断反思总结中逐步形成有关对象性质的认识)这一观念。就此看来,在对戏剧这一艺术形式的性质认识中采用以功能主导的“积用成体”之诠释方法是有理可循的。
返观欧阳予倩的戏剧理论,无论是“写社会之真”的写实主义抑或“求双美之合”的两种艺术手段并举,还是“西体中用”的旧剧改革之方略,都是在戏剧改革的浪潮中摸索戏剧艺术表现的方法,而无论何种方法之目的都在于实现戏剧“反映社会”“为人生”之功能。就此看来,欧阳予倩的三次戏剧理论总结表面上看是对戏剧表现方法的探索,实则是为实现戏剧功能之追寻,且对戏剧本质的理解恰就在戏剧功能的不断实现中被一步步加深。
从欧阳予倩的戏剧思想来看,无论是他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登高疾呼的写实主义,还是后期孜孜以求的新写实主义,都没有脱离戏剧必须以写实来进行艺术创作的理念,这一理念也体现在他毕生的戏剧创作之中。从他1913的处女作《运动力》到1958年的最后一部话剧作品《黑奴恨》,无一不以反映社会、揭示矛盾为主题进行创作。穷尽一生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都始终直面戏剧的写实,从这样一个层面看来,在欧阳予倩的戏剧理论中,戏剧的写实性乃是戏剧实现其“反映社会”“为人生”之功能对戏剧性质上的客观诉求,并且至少也应该被视作戏剧艺术的主导性质。
谈到写实主义,艺术的真实与世界的真实之关系则是挥之不去的一对概念,在如实直书与艺术的想象创造之间如何调和,成了戏剧创作中的一个紧要问题,这在欧阳予倩的剧论中则直接表现为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选择问题。
曾有学者对欧阳予倩的著名历史剧作《忠王李秀成》作出了这样的评论:
作者为了突出历史剧的现实意义,而忽略了最大限度地揭示历史的真实。太平天国本身是一次农民的“造反”,其内部存在的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但作者多少把这些问题简化了。……更值得商榷的是,剧中所描写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在不少方面与历史事实尚有较大的距离。但同时他又提出:
四十年代的读者和观众首先要从剧中得到的不是历史知识,而是现实斗争的鼓舞。剧本脱古喻今,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它的历史作用是肯定的。
此种既批评又肯定的态度,是史论中常见的表达,但在这种模糊处理的方式背后,那个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却始终念兹在兹。
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在分析历史、哲学、诗(艺术)与行动和思想之关系时,有这样一个观点,他认为:历史和哲学是对行动和思想的第一位模仿,构成特殊的历史论证或具体的逻辑论断;而诗(艺术)则是对行动和思想的第二位模仿,构成对历史的普遍性论证和对思想的普遍性表达,这种普遍性有着对真实的诉求,但却并不受制于真实。将此观点引入关于戏剧作品中世界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二者关系问题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见解:
世界的真实是一种历史的真实,而艺术的真实是一种诉求的真实,戏剧艺术在体认写实性的主导性质前提之下,应该允许艺术的合理想象创造。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二者在欧阳予倩的戏剧创作理论主张中,从来不是对立的二元,借助合理的艺术想象而造就的艺术真实,反而能收世界真实有时所不能达的反映社会之功。试想,如若在《忠王李秀成》此类历史剧中,一味地追求世界(历史)的真实,那么本应借助戏剧来传达的写实性岂不是又被如实直书的知识般的真实性所遮蔽?此种戏剧艺术创作手段(也即戏剧功能达成方法)多元化的观点是欧阳予倩对戏剧性质的又一次理解。
至于援西体以合中用,則是欧阳予倩在此前对戏剧性质理解基础之上的再一次有关戏剧性质之诠释活动。西方戏剧以写实为戏剧之主导性质,中国传统戏曲则以写意为艺术表现追求。以西方戏剧结构思维为体,中国传统戏曲表现元素为用,从体用关系上的中西戏剧之结合实际上便是戏剧审美追求中的写实与写意关系之融通。欧阳予倩力图在西方戏剧与中国传统戏曲的互相照明中建构一种民族的现代戏剧“新写实主义体系”,以更好达成戏剧的“反映社会”“为人生”之功能。同时,此种旧剧改革中以西方形式结合中国质料的做法,也体现了戏剧艺术作为综合艺术的本质属性。
纵观以上,结合以功能建主体的诠释思路,我们可以发现欧阳予倩从实现戏剧功能角度所进行的戏剧性质之理解,始终都围绕戏剧主题内容的现实性这一主导性质而展开,然后再往戏剧创作手段的多元化、审美追求的多样性逐层蔓延开去。他对戏剧理论的过程化总结,实在是对戏剧艺术本质的过程化诠释。
三、戏剧中艺术与思想关系之再思考
虽然欧阳予倩一再地强调“写实派与唯美派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但他仍不可避免地被左派戏剧家们批评为“与其注意内容的积极性宁可注意技术的完整”。“写实派”与“唯美派”的问题,“内容”与“技术”的问题,说到底,实则是戏剧中艺术与思想的关系问题。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政治格局的变动导致“将文艺作品当成某种‘工具以动员最广大的底层民众参与抗战,成为这一时期文艺界的共识”,因此如何处理戏剧作品中艺术性与思想性关系的问题成为特定的历史时代给当时戏剧家们提出的时代问题,他们彼时的参与回答构成了我们当下关于戏剧的认识。然而,理解本就是不断丰赡的经过,在我们当代的视界与经验下,过往的历史参与着我们当代的形成,我们唯有将我们的理解参与到影响我们的历史中,才能在理解中不断重塑历史,丰富我们的理解。因此,对戏剧中艺术与思想关系的再度思考将具有重大意义。
对这一问题,欧阳予倩曾用一个巧妙的比喻试图阐明此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说:“艺术服从政治,艺术为宣传政治,是颠扑不破的原则。艺术性与思想性相结合,要像盐在水里,看不见,喝着有味。”然而盐要充分溶于水中且看不见,必须经过充分的搅拌或是长时的溶解,戏剧艺术因其主导性质上的现实性则又不容许我们经历这漫长的时间的积淀,那么,在此艺术性与思想性和谐相溶的过程中,什么又能充当我们搅拌的那根“玻璃棒”?对此,欧阳予倩本人也提出了他的看法:
思想性通过人物形象表现出来就是艺术。要使观众所看到的是生动的人在行动、在说话,不是剧作者提着线的傀儡在说教。戏剧是诉诸观众的感性的,是让人用心来接受的。正因为这样,容易起宣传作用,也容易收潜移默化之功。
在他看来,这种盐与水的结合是借助戏剧中的人物形象而完成的,戏剧艺术传达其思想性的方式是借助演员的表演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艺术宣传思想的媒介。
戏剧中的人物形象是艺术形象,因此,这一思想宣传的媒介仍是戏剧体认其艺术性的产物,就此,我们进一步发现欧阳予倩确是将戏剧的艺术性置于思想性之上的,而之所以这样做,却是因为艺术诉诸人的感性,能更好地传达思想。正如有学者为他辩护的那样:他之所以坚持要在技术上“磨光”,是因为他注意到了戏剧艺术的本质与特性,目的是以“技术的完整”去更充分地发挥“内容的积极性”。
同时,宋宝珍对欧阳予倩的这一段评述又为我们对戏剧的艺术与思想之关系辩证提供了一条从事实与价值二分角度进行考量的新思路:
欧阳予倩对早期中国话劇的考评,是同时运用着两个基本的尺度的:一是以现代戏剧的基本概念衡量这一新兴的艺术门类的基本形态,从中发现它与传统戏曲的根本性区别和自身的生长潜力;二是以戏剧的社会作用来衡量这一新的戏剧所具有的现实效力,从中强调戏剧应当具有社会思想性。
她所提到的两个尺度,其实对应着戏剧这一概念的两个层面:戏剧作为艺术是一个“它是”的事实层面的问题,戏剧要宣传思想是一个“它应当”的价值层面的问题。就此说来,戏剧首先应该是艺术,这是它的艺术性本质所决定的,同时我们还希望戏剧这一艺术形式能够发挥一定的“反映社会”“为人生”的功用,这是我们对戏剧的一个“更高要求”。质言之,思想性是在艺术性这一事实层面基础之上给戏剧提出的一个更高价值追求。在处理戏剧的艺术与思想关系时,我们既不能因为艺术性的事实而去放弃思想性的价值,同时也不能因思想性的价值而去无视艺术性的事实。思想性是建立在艺术性基础之上的艺术追求,艺术性是思想性能够更好实现的基础保障。
关于戏剧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二元取舍问题,在另一位早期戏剧人田汉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田汉早期的戏剧观是源自新浪漫主义的,致力于在戏剧作品中追求超人生的美的境界,然而,在1930年田汉所发表的《我们的自己批判》中,他对此前所秉持的艺术至上观点又进行彻底检讨,自此,其剧作中“政治范畴的时代感和阶级意识正逐渐增强,对于艺术之宣传效用的认识正逐步加深”。在20世纪50年代后,他又在戏剧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二元取舍之间找到了他全新的戏剧艺术主张——“诗化现实主义”,深受欧阳予倩好评的剧作《关汉卿》便是该理论主张下的杰出作品。从早期的各倾一侧,到后期的求艺术与思想的融通,田汉对现代戏剧的理论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寻经过。无论是欧阳予倩的“新写实主义体系”,还是田汉的“诗化现实主义”,其实都是中国早期现代戏剧家在处理戏剧中艺术性与思想性二元关系的理论尝试,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此二人的理论主张在最终旨归上是若合一契的,因为在一个成熟的戏剧作品中,艺术性和思想性从不是对立的二元,而是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艺术形式整体。
总之,尽管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戏剧中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会产生一定的二元倾斜,但是此二者完全可以在一个成熟的艺术有机体中共存的。在我们看来,唯美与写实也好,艺术与政治也罢,无论是在艺术的功能与方法的论域,还是哲学的事实与价值的视角,它们都彼此相安于戏剧作为艺术的本质之下。
四、结语
“以歌舞演故事”还是“以故事演歌舞”,这不仅是一个戏曲理论的问题,还是一个诠释学领域的循环诠释问题;对戏剧理论的思考总结,同样不仅是一个戏剧表现方法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戏剧所承载的功能问题,和一个戏剧本质的诠释问题。人文领域诠释对象的历史性与生成性特质,使得我们只能在“积用成体”的方式中对对象性质进行逐层的理解。欧阳予倩的戏剧理论绝不是简单的由唯美主义到写实主义的转变,他的三次戏剧理论总结实则暗含了他对戏剧本质的一次次愈加深刻理解,由功能决定的戏剧性质在理解中变得越来越丰富,而中国现代戏剧的身影也在他们这一批老戏剧家们的一次次探赜索隐中被描摹得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