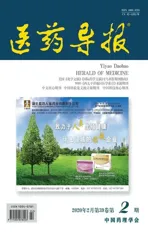临床药师参与不明原因发热会诊典型案例分析
2020-02-15白慧王小萍张鹏王煜
白慧,王小萍,张鹏,王煜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1.药剂科;2.感染疾病科,银川 750004)
不明原因发热(fever of unknown origin, FUO)在临床较为常见,因其病因复杂、表现迥异、缺乏特异性,涉及内、外、妇、儿多个科室,给临床诊疗带来较大困难。1961年PETERSDORF等[1]提出把发热持续>3 周,体温超过38.3 ℃(101℉),且住院1周未能确诊者定义为FUO。我国在1999年全国发热性疾病学术研讨会将FUO定义为:发热持续2~3周以上,体温>38.5 ℃,经详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和常规实验室检查仍不能明确诊断者[2]。
FUO病因多达200多种[3],病因分类较多,按疾病种类可分为:感染性疾病、结缔组织病、恶性肿瘤和其他类疾病[4]。由于患者发热周期长,导致长期反复应用抗菌药物、非甾体抗炎药及糖皮质激素类药物,使临床不合理用药增多,给患者诊断及治疗带来诸多困难,延长了住院时间,增加经济负担。笔者在近3年的临床会诊中,协助临床医师参与全院86例FUO患者的用药方案制定,64例成功确诊并治愈或好转。现将笔者参与的几个典型案例分析总结报道如下。
1 感染性发热会诊
国内文献报道,感染性发热的病例占FUO总数的53.9%[5],与文献[6]报道亦相似。这类患者常急性起病,伴寒战高热,体征不典型,应用抗菌药物治疗后症状缓解不明显或呈加重趋势,且感染部位及病原菌不明确,经过全院多学科会诊及后期的详细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病理性检查等才最终确诊。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反复应用抗菌药物,但临床效果不明显,临床药师通过掌握的专业知识分析患者病史,可能感染的部位及病原菌,协助医师制定有效的抗感染治疗方案。
1.1典型病原菌致发热
1.1.1病例介绍 患者,女,41岁。2016年3月22日因突发上腹痛伴发热、意识不清、四肢无力、不能言语入住神经内科监护病房,初步诊断: ①急性脑梗死(双侧额叶、顶叶、左枕叶);②糖尿病酮症酸中毒;③左肾结石;④脓毒症。给予抗感染、改善循环、脑保护、胰岛素微量泵泵入控制血糖等对症支持治疗。治疗期间患者血糖控制尚可,脑梗死病情稳定,神志恢复,抗感染先后给予头孢哌酮/他唑巴坦+乳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哌拉西林/舒巴坦+替考拉宁+伏立康唑等药物治疗,患者仍持续高热,体温波动在39~40 ℃,给予赖氨匹林及吲哚美辛栓退热后,体温可降至37 ℃,但很快体温再次上升。血、小便、大便、脑脊液培养均阴性。2016年4月12日,患者入院第20天,查血常规结果示:白细胞11.18×109·L-1,中性粒细胞百分比81.4%,降钙素原(PCT)≤0.5 ng·mL-1,C反应蛋白(CRP)77.6 mg·L-1,仍持续发热,体温最高40.2 ℃。腹部彩色B超示:左肾下极皮质内见结石直径约1.4 cm。左肾下方见 3.1 cm×5.2 cm液性暗区环绕,透声差,考虑血肿、脓肿?2016年4月9日请泌尿外科医师会诊考虑肾周脓肿可能,后在B超引导下行穿刺引流,抽出清亮黄色液体约5 mL,送检培养,持续留置引流管,更换抗感染药物为亚胺培南西司他丁1 g,静脉滴注,q12h。患者穿刺引流后第1天体温有所下降,但第2天起再次出现高热,体温波动于39.0~39.5 ℃,2016年4月11日再次请泌尿外科会诊,考虑肾周脓肿不能确诊,无外科干预指征,遂于2016年4月12日申请全院会诊,明确患者发热原因。
1.1.2临床药师会诊分析 患者自入院后体温控制欠佳,合并糖尿病,且血常规升高,考虑发热与感染有关。根据患者临床表现及相关检查考虑发热与肾周脓肿可能性大,虽然穿刺液清亮,非脓性液体,但亦不能排除肾周脓肿感染可能。肾脏内科及泌尿外科会诊示:肾周脓肿容易误诊,例如临床症状不典型,有时表现为腹痛,肾区体征不明显;由于糖尿病合并症的存在,机体抵抗力低下,常无脓肿的典型表现;合并症糖尿病、肾结石、输尿管结石、尿路感染等疾病的存在,易混淆肾周脓肿的诊断[7],且由于合并症的存在,感染多为混合感染,易出现多重耐药菌。结合上述科室会诊意见,临床药师考虑:①随着广谱抗菌药物的应用,肾源性途径已成为肾周脓肿的主要致病途径,致病菌也随之转变为需氧革兰阴性菌为主,尤以大肠埃希菌、变形杆菌等最常见[8]。②患者自入院后使用抗菌药物覆盖杆菌、耐药球菌及真菌,但耐药杆菌尤其严重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的肠杆菌科细菌未能覆盖,结合患者病史及肾周穿刺引流后联合强效广谱抗菌药物亚胺培南/西司他丁体温曾下降,建议可在此基础上联合阿米卡星0.6 g,静脉滴注,qd。
1.1.3会诊追踪 会诊方案予以采纳。3 d后患者体温逐渐下降,最高37.6 ℃,同时穿刺液培养回报示大肠埃希菌,对头孢他啶、氨曲南、左氧氟沙星等耐药,对亚胺培南/西司他丁、庆大霉素、阿米卡星等药物敏感。继续上述药物治疗1周后,患者体温、血常规完全正常。经专科治疗并继续抗感染治疗1周,患者血糖控制平稳,脑梗死病情稳定出院。
1.2非典型病原菌致发热
1.2.1病例介绍 患者,女,38岁。主因“头痛、间断性发热4个月余”,于2016年1月14日入住我院。患者既往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狼疮性肾炎”1年余,规律口服醋酸泼尼松15 mg,qd,羟氯喹200 mg ,qd,服用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药期间曾发生肠穿孔,当时行手术治疗,后因头痛、发热在院外诊断脑脓肿,予以头孢曲松钠、莫西沙星、奥硝唑、氟康唑、美罗培南、万古霉素等抗感染治疗近2个月。此次再次发病入住我院,入院时患者头痛呈持续性胀痛,恶心,无呕吐,无四肢抽搐等,患者发热,体温高达39.0 ℃,入院后颅脑磁共振检查提示:左侧枕叶囊性病变,周围片状水肿,考虑脓肿吸收后改变,炎性肉芽肿形成。初步诊断:①脑脓肿(左枕叶);②系统性红斑狼疮,狼疮性肾炎;③直肠穿孔肠切除、肠造瘘术后。患者入院后脑脊液(cerebrospinal fluid ,CSF)常规:白细胞565×106· L-1,潘氏实验阳性++;CSF生化检查:蛋白质1.68 g·L-1,葡萄糖1.88 mmol·L-1,氯116.8 mmol· L-1。多次血培养、脑脊液培养阴性,给予万古霉素(1 g ,静脉滴注,q8 h)+美罗培南(1 g,静脉滴注,q8h)抗感染治疗,患者仍头晕、头痛、每日发热,体温最高39.2 ℃。2016年1月25日,请神经外科医院会诊,考虑脓肿较小无外科干预指征;同时,请风湿科医师会诊考虑系统性红斑狼疮稳定,暂不考虑狼疮性脑炎。由于患者病史长,使用抗菌药物时间长,多而杂,发热原因不能明确,脑脓肿病原菌不明确,遂于2016年1月27日申请全院会诊。
1.2.2临床药师会诊分析 患者明确系统性红斑狼疮后,服用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药近5个月出现脑脓肿,自发病后使用多种抗菌药物2个月余,病情反复,目前主要问题为持续高热,仍考虑脑脓肿引起可能性大。患者病原菌始终不明确,抗菌药物无法针对性治疗,根据患者病史及用药史,考虑:①80%~90%脑脓肿为多重微生物感染,多数情况下有25%为病原体不明者[9],建议仍需多次血培养及脑脊液培养,寻找病原菌。②入院前患者曾使用多种抗感染药物,覆盖革兰阳性球菌、革兰阴性杆菌、厌氧菌、真菌等,既往及目前用药品种均能透过血脑屏障,给药剂量正确,但患者仍头痛、高热,病情无好转,加之患者属于免疫缺陷人群,需考虑到不常见的病原体:如诺卡菌属、结核分枝杆菌、隐球菌等[9-10],故可将抗菌药物经验性调整为:停用万古霉素,换用利奈唑胺,因利奈唑胺不仅对耐药革兰阳性球菌有较强的抗菌作用,且对诺卡菌有效,CERCENADOR等[11]分离51例诺卡菌,分析评价9种抗菌药物的疗效,发现利奈唑胺具有最小的最低抑菌浓度(MIC)值,甚至包括耐阿米卡星和磺胺类药物的菌株。美罗培南入院后使用10 d,对阴性杆菌有强大抗菌作用,可继续目前剂量使用,因利奈唑胺联合美罗培南亦是颅内诺卡菌感染的备选方案[12],同时考虑到磺胺类药物仍是诺卡菌感染的首选药物,建议可经验性口服复方磺胺甲唑(TMP-SMZ) 3片,tid;③患者颅内隐球菌感染不能除外,可加用伏立康唑首剂6 mg·kg-1,q12h,维持剂量4 mg·kg-1,q12h ,静脉滴注;④患者属免疫低下人群,结核性脑脓肿亦不能除外,可先主要针对以上2类特殊细菌进行治疗,后期可在治疗过程中根据治疗反应,进一步完善检查,若仍无阳性结果,可请相关科室再次会诊,是否给予诊断性治疗。
1.2.3会诊追踪 会诊方案予以采纳。上述方案治疗1周后,患者头痛较前减轻,体温呈下降趋势,最高37.8 ℃,CSF常规:白细胞205×106· L-1,较前明显降低。继续该方案治疗1周后,患者脑脊液培养为鼻疽诺卡菌,验证了初次的会诊判断。药敏示对磺胺类药物、亚胺培南耐药,对利奈唑胺、阿米卡星敏感,故调整治疗方案为:停用美罗培南、伏立康唑、TMP-SMZ,继续使用利奈唑胺+阿米卡星治疗。患者病情一度控制良好,头痛较前明显减轻,CSF白细胞降至50×106·L-1,治疗有效。后因患者狼疮性肾炎复发,转至外地医院进一步就诊。
2 非感染性发热会诊
在非感染性FUO中以结缔组织病和恶性肿瘤常见,结缔组织病是FUO患者居第1位的非感染性疾病。国内报道系统性红斑狼疮、原发性干燥综合征、成人Still病等是常见的结缔组织病[13],但随着诊断技术和对疾病的认识提高,一些少见疾病如脂膜炎、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逐渐增多[14]。
2.1病例介绍 患者,男,47岁。主因“寒战、发热不适伴纳差15 d”,于2017年9月18日入住急诊科。患者入院前在当地医院给予清热、抗感染、补液等对症治疗6 d,无好转遂转入我院,入院时患者仍寒战、发热,最高体温40 ℃,伴腹痛,以上腹部为著,伴食欲减退,餐后腹胀感明显。无胸闷气短、无咳嗽咯痰、无尿频、无尿急等其他不适。入院后查血常规示:白细胞5.32×109·L-1,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80.4%,PCT≤0.5 ng· mL-1,CRP 112.0 mg· L-1,红细胞压积63 mm·h-1,肝肾功能无异常。胸部CT检查无异常,腹部CT示:阑尾区见斑点状高密度影,回盲部见脂肪间隙浑浊,见渗出影,临近腹膜增厚,考虑阑尾炎可能。初步诊断:发热待查:阑尾炎并阑尾周围脓肿形成。给予头孢他啶+奥硝唑抗感染治疗3 d,患者仍间断发热,最高体温39.2 ℃,同时患者出现腹泻,腹痛较前缓解不明显,临床医师考虑发热与回盲部病变相关,将抗菌药物调整为亚胺培南/西司他丁+万古霉素联合抗感染治疗。调整治疗5 d后,患者仍间断发热,体温高峰较前下降,最高38.2 ℃,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正常,PCT、CRP正常,红细胞压积 58 mm·h-1,无腹泻,腹痛较前有缓解,继续当前方案治疗。自2017年9月28日起,患者连续2 d体温再次升高,最高39.5 ℃,期间完善血培养、G实验、病毒全套、骨髓活检、肥达氏反应等无异常。免疫球蛋白、补体及类风湿因子阴性,ENA-AbSSA、ENA-AbSSB、ENA-AbRo阳性,抗核抗体1:320。患者发病至今体质量下降近10 kg。请普通外科医生会诊:患者CT提示阑尾炎,但腹部体征不明显,不考虑阑尾引起发热;风湿科医生会诊:患者虽风湿相关指标阳性提示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可能,但更多见于干燥综合征,患者仅表现抗体阳性,无临床症状,亦不考虑。感染疾病科医生会诊考虑:是否存在真菌感染及药物热可能?放射科医生会诊:不考虑阑尾炎或腹腔淋巴瘤可能,考虑脂膜炎可能性大,确诊需病理活检。因患者发热原因不明,广谱抗菌药物治疗效果不佳,遂申请临床药师会诊协助下一步药物治疗方案制定。
2.2临床药师会诊分析 综合各科室会诊意见考虑:①患者病史近1个月,以发热为主要表现,入院后初步考虑阑尾周围脓肿,给予强效广谱抗菌药物治疗,病原菌覆盖广泛,临床治疗效果不明显,考虑非感染性发热可能性大。②患者既往无基础疾病,真菌感染暂不考虑;患者入院使用相关药物之前已发热半个月余,药物热暂不考虑。③患者入院时实验室检查白细胞、PCT正常,中性粒细胞及CRP较高,给予亚胺培南/西司他丁+万古霉素治疗后降至正常,考虑前期可能存在感染,但给予治疗后以上指标基本正常,再次出现高热,且完善相关感染检查无阳性发现,考虑发热与感染可能性不大。结合风湿科会诊意见,同意放射科意见,脂膜炎可能性大。该病是一种少见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反应及纤维化病变[15]。其主要病理改变为肠系膜脂肪组织的变性、坏死、炎细胞浸润及纤维化。 目前公认与细菌感染、腹部外伤、手术、血管损伤、过敏反应、自身免疫反应等多种因素有关[16]。绝大部分患者均以发热、腹痛、腹泻、腹部肿块就诊,多误诊为腹腔肿瘤、肠梗阻、急腹症、淋巴瘤等[17]。④建议停用目前所有药物,给予甲泼尼松龙琥珀酸钠40 mg,静脉滴注,qd, 病情控制后逐渐减量改为口服药物。文献报道,脂膜炎尚无特效治疗,在急性炎症期或有高热等情况下,一般应用糖皮质激素,疗效明显[18]。
2.3会诊追踪 临床医师同意临床药师会诊方案。给予激素治疗第2天,患者体温即下降,之后连续3 d体温正常,无腹痛、腹泻、精神好转。因患者拒绝行病理活检,遂出院继续服用泼尼松20 mg,1个多月后自行停药。半年后,患者病情复发,再次就诊我院,病理诊断示肠系膜脂膜炎。
3 药物热会诊
药物热是临床常见的药源性不良反应之一。在我国药物热占院内发热2.5%~10.0%,其中抗菌药物致药物热占20%[19]。药物热常伴药疹,也有不伴药疹的单纯性药物热,无药疹的药物热给临床诊断增加了一定的难度,且药物热诊断缺乏特异性的诊断标准,主要采取排除性诊断判断用药与发热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只有在药物停用后体温消退才能确立诊断。药物热尤其与合并感染性疾病的发热较难鉴别,容易引起误诊误治。临床药师通过掌握药物热的临床表现及诊断依据,对于协助医生及时识别和处理药物热,进一步提高合理用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3.1病例介绍 患者,男,2岁。主因“腹胀、腹痛伴发热、恶心呕吐、停止排便排气5 d”入院,入院诊断:急性肠梗阻。患儿完善相关检查后在全麻下行“小肠切除吻合术”,术后诊断:①粘连性肠梗阻;②小肠异物并穿孔。术后间断发热,体温最高38.5 ℃,白细胞10.9×109·L-1,中性粒细胞百分比80.2%,临床医师考虑患儿术后合并腹腔感染,给予头孢他啶0.5 g,q12h+甲硝唑0.2 g,qd,静脉滴注,抗感染治疗5 d,患儿仍有低热,最高体温38 ℃,遂将抗菌药物调整为:美洛西林舒巴坦0.75 g,静脉滴注,q8h。调整后3 d,患儿体温逐渐趋于正常,一般情况可,无腹痛腹胀、无恶心呕吐。第7天夜间,患儿无明显诱因再次出现高热,体温最高39.2 ℃,白细胞5.65×109·L-1,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为62.1%,PCT≤0.5 ng· mL-1,CRP 20.63 mg·L-1。次日查看患儿引流管在位通畅,无脓性液体引出,继续予以美洛西林/舒巴坦抗感染治疗2 d,患儿仍间断有高热,发热时伴寒战,体温最高39.0 ℃,经给予对症处理后体温可恢复正常。由于患儿临床体征改善,但仍反复高热,发热原因不明,遂提请临床药师会诊协助治疗。
3.2临床药师会诊分析 临床药师查看患儿精神尚好,已给予流质饮食,无明显腹部不适。仔细询问患儿家属,患儿每日发热为午后显著,发热时不伴有皮疹及心率加快,综合患儿病史,临床药师考虑患儿由美洛西林/舒巴坦引起药物热可能性大。分析如下:①患儿经头孢他啶联合甲硝唑抗感染治疗,5 d 后体温控制不佳,换用美洛西林/舒巴坦,3 d后体温恢复正常,于治疗第7天夜间再次出现高热,在此期间治疗药物未做调整;②患儿精神较好,除发热外无其他明显不适,也没有新的明显感染病灶,且原来的感染病灶已经基本治愈;③患儿再次出现发热后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百分比、PCT均正常,仅CRP轻度升高;④文献总结的药物热临床特点有:患者一般情况好,药物热潜伏期为 4~22 d,绝大多数体温≥38.5 ℃ ,热型不规则,发热都集中在下午或者夜间,发热时不伴有心率加快[20];⑤患儿使用药物为临床报道发生药物热概率高的药物。文献[21-22]报道:抗菌药物、中药制剂和神经系统药物的药物热发生率较高,其中抗菌药物尤以头孢菌素类、青霉素类和糖肽类药物发生药物热的构成比最高。本例患儿发热特点基本符合上述药物热的临床特点,故高度怀疑。建议立即停用美洛西林/舒巴坦。
3.3会诊追踪 临床药师会诊方案予以采纳。患儿停用美洛西林/舒巴坦后第2天,未再出现发热,符合药物热停药后24~48 h内体温即恢复正常的规律。继续观察2 d后仍未再发热,遂办理出院。
4 结束语
目前,临床药师参与药物治疗会诊的范围呈逐渐拓宽的趋势,从单纯的药物品种、给药途径的选择,到药物治疗方案、调整解决药物治疗中的矛盾问题,再到复杂的不明原因发热,帮助医师诊断及处理药源性疾病的救治等,多角度、多方位体现了临床药师在开展临床药学工作的过程中,其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的不断提高。同时,也对临床药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挑战,需要在工作中不断学习与总结经验,与医、护携手更好地为患者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