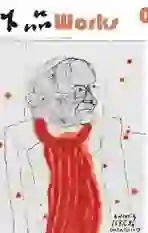我即众生
2020-02-10郑威容吴晓芳黄婧雅塞壬
郑威容 吴晓芳 黄婧雅 塞壬
自信,大方,亲和,这是塞壬给我们的最初印象。
这令我们略感诧异。此前,我们一直以为见到的,会是一位略带忧伤,气质清冷的女作家,因为在我们看来,一个经历过多年流浪,生活坎坷而复杂的人,心上总会带着点伤痕。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接下来的访谈过程里,我们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了塞壬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人性的坚守。她乐于踏入众生之中,感受生命的苦难与欢愉;而后带着悲悯和宽宥,于书写中关怀众生,感化众生。
“我即众生”,是她的写作态度,亦是她的人生态度。
郑威容:老师一开始说在评比赛的时候看到学生写的都是一些童年记忆、亲情友情、青春等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比较美好的东西。那在散文呈现里,对于呈现美好的部分还是呈现人性和社会丑恶的部分,您有没有什么倾向性的看法?
塞壬:首先,我所写的黑暗和丑恶最终都是为了呈现人性美好的部分。不是为了揭露而揭露,不是为了夺人眼球,而是为了透过人性的黑暗去看到人性美好的东西。举个例子,我写过一篇散文叫《祖母即将死去》。我的祖母被另外的男人爱慕,而且在我的祖父死后嫁给了我祖父的弟弟。这是连我的父亲都难以启齿的事,但是我的读者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认为我的祖母有什么污点,反倒能理解祖母为了家庭、为了所有人能很好地活下去而做了这样一个选择。读者在看文章的时候觉得祖母这个人是了不起的。我们在表达一个人的时候,写他不好的方面实际上要把他放在一个背景里,让他的选择有命运的原因在里面。《祖母即将死去》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因此,读者看到作品之后,反而认为祖母作为一个女性,表现出了人性的美好。我们在选择素材的时候,要关注能否产生对比和戏剧性的冲突。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导演。作家要对素材进行一番裁剪,才能更好地进行表达。
郑威容:可是如果说我最终的目的都是表现美好的一方面,会不会为了突出美好的一面而丧失了真实的想法,出现稍微掩盖真实部分的情况?
塞壬:我在作品中反复书写人性的冲突,是因为我认为散文最大的问题在于面对自己,在于纠偏。写散文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自省的过程。散文一味赞美是不行的,会显得空洞。因此,作为一个“导演”,我会安排一个冲突在里面,让它成为一个矛盾体,有对抗在里面,这样它看起来就会特别真实。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单方面的美好或丑恶是难以为继的。但是这里面,人性美好的部分一定是真实的。
郑威容:刚刚的讲座中老师说散文是写给自己的,您在写的时候是不关心读者的。可是当您的散文写完面世以后,它必然要面对读者。在读散文的过程里面看到一些解读您散文的文本,会把散文放在一个社会背景里面去看,比如说乡村的变化,广东钢铁厂在那个年代的变化,城市底层的生活变化。您在写的时候会考虑到这种现象吗?您认为是用来表达自我的散文,却被放在社会的背景下去解读,您有什么看法吗?
塞壬:没有考虑读者是在我成为专业作家之前。那时候写作我一定不关心读者,也不会考虑材料要不要纳入大背景或者是否要精心制造一个细节。但是在成为专业作家之后,我会考虑到非常多的细节,甚至是设计一个主题。比如说乡镇文化的没落性,这就是精心策划的、有目的的、有框架的写作。你说的被放在社会背景里去评价的散文都是这类主题创作。我今年三四月份还特意去做了流水线女工,在成为专业作家之前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我是专门为了写作才去体验生活的,因为只有亲身体验了才能写得生动。不仅如此,我还看了其他作家是怎么处理同一题材的。我会看别人写了什么,然后避开别人写的。专业作家的写作是要处处经营的,我想要独树一帜,想要以更好的角度和视点去创作,就要挑战难度,写别人没写过的。
郑威容:那您能分享成为专业作家后的一些经验吗?比如怎样才能做到独树一帜?
塞壬:第一,要研究其他作家的文本,关注他们有没有创新。第二,对其他作家关注的题材,要思考若是我自己去体验,会不会有新的发现。写作的时候,要做到同时代的同与不同。这并不意味着要和其他作家唱反调,而是要在相似的基础上发现新的东西,同时这个新的东西不能够违背事实。作家要找到一个不同的切入点,说同一个事实却能有不同的味道。举个例子,打工文学往往会涉及劳工的苦难、制度的不作为、工人在流水线流逝的青春等在大的格调中没有太大差异的内容。作品里展现出来的打工生活就是很辛苦的,身为一个作家,当你在书写相似题材时,你为了创新只书写工人的幸福快乐是不行的。这个时候,作家就要找到自己能创新而又不违背事实的点。比如说,几万人的工厂,有那么多工人十几年都在那里工作,为什么他们没有离开?亲身去了解体验了,就会知道:在工厂里,工人每个月有五千元的工资,而留在乡镇最多只能拿到三千元。而且工厂里有空调,还包吃包住,等于工人每个月可以净赚五千元。再比如说,作家可以深挖工人们有理想和热血的一面。就我的个人体验来看,工厂里有些人,拿了工资还买摩托车去搭客赚外快。而工厂里的男孩女孩谈恋爱,在外面租房子,过得也很热闹。工人们在平凡的生活里有他们的乐趣,他们不是只有痛苦的一面,没有人能生活在绝对痛苦的生活中。身为作家,就是要发现一个普通人生活的原生态,去体会他们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一个作家,有自己的视角,有新颖的角度,去书写其他作家忽视的未曾写过的一个点,这是非常重要而且有趣的,也是一个专业作家在同时代中面对同质化的题材,面对热门题材该做的事。我们生活的社会,题材实在是太同质化,很少有人生活在独特的环境里,大家都过着同样的生活,身为作家,就是要有发现的眼光。而去发现别人忽略掉的东西,就是我说的有挑战难度的事情。
郑威容:我很好奇您曾经的经历对您在写作中的影响,尤其是您乡村的经历和在广东的经历。您对这些经历和写作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是什么样的理解?
塞壬:当你想成为一个作家的时候,你的经历就是财富。不好的经历也是财富。当你有着复杂的人生经历的时候,就擁有很多财富。
郑威容:请问对于一个经历不丰富但又想挑战成为一个作家的人,在把他者转化成“我”的时候,由于自身经历的匮乏而没有办法写出比较有意义的故事的时候,您觉得该怎么做?
塞壬:这其实就是要做到“我即众生”,这不是一开始就能做到的,而是要经历千疮百孔的人生。很多人问我:“你怎么不会写空的,塞壬?”我是写不空的,但是很多人会,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一个办法去延续“我”。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天她非常兴奋地跟我说:“塞壬,我已经辞职了,在家里专职写小说。我要写小说,我不工作了。”半年之后她说:“塞壬,我只写了五千字。”这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参与到人群中去,要打开五识,接触这个现实世界。然后让你看到的人和事,穿过自己的身体,最后再看看留下来的是什么。在你身心过滤后留下来的东西,就是值得你去书写的东西。它就是反悟,就是文学。不工作就能写小说吗?我的朋友半年才写了五千字,这不是时间的问题,说自己没有时间写小说,没有时间搞文学创作都是假话,真正的原因在于你脱离了人群。脱离了人群你还能写什么呢?除非你有经年的储备可以写。走出去,接触人,接触世界的花花绿绿,去看去闻,用身体去接触,打开自己的五识,看一下什么东西在過滤之后留了下来,让自己和所有的现实同步,这就是我写不空自己的办法。如果你不能够做到众生代入的话,那就先走到人群中间去。
郑威容:从作家的角度,比如说阎连科,他会觉得现在的文学都是“苦咖啡文学”,很多事情我喝一杯咖啡就可以解决掉,而没有太多像老师您说的永远留在我们心中过滤不掉的东西。我知道写出能打动人的东西需要我们去融入人群,但即使写出来了以后内容依旧容易比较泛化,没有太触动人心的东西。那么从作家的角度,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您觉得还能否写出一些戳痛这个社会的东西呢?
塞壬:这是关于作家的社会担当的问题,这点非常重要。对于散文写作来说,如果作家掉在时代之外,这是悲哀的。有一种散文,我们称之为“文化散文”,比如说解读《红楼梦》,解读李清照的一些作品,或者解读张爱玲的一些作品。这样的作品它晚二十年,甚至是五十年,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这样的作品它没有明显的时代性,没有太多时代的因素注入其中。一个作家如果长期写这一类文字的话,我认为是失败的,因为他没有记录时代的声音。所以每一个作家在写的时候,要有一个“在场”。你处在这个时代,不可避免地就要写这个时代的特性,这个时代的人性。这样我们很多年后再来看这个时代,就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时候人们的价值和审美。文字的任务就是记录时代。另外,一个作家是逃脱不了时代的种种桎梏的。我们因为房价而疲于奔命;女性因为职场的种种压迫而感到困惑,性骚扰等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再比如现在很多人都不生孩子,不恋爱;现在乡村也没落了,到处都拆迁,搞房地产,整个时代全民都在拜金……这些事情真切地发生在我们周围,作家是没可能绕开的。国内绕开时代去研究前人作品的作家,就目前来讲,没有一个出大名的。这就证明了这样的散文写作是失败的。我觉得我们身处这个时代,没有人能够跳出这个生态川林,只要提笔必然就会有所涉及。这不是在刻意地承担社会责任,而是每个人都活在这个圈层,没有人能避开房子、孩子、婚姻、职场等现实问题。只要你写,你就必然在场,就必然会负起文学的这种担当。
郑威容:您刚刚在谈的过程中有稍微地提及一下您觉得您的散文不是小说,因为您觉得还是在里面表达了对世界的看法,表达了自我,而不是通过一个完整的故事去呈现一个价值观。但是您的一些散文,它是有一条完整的逻辑的,结构也是比较严谨,不是很散化的结构,那么我想问一下对您来说小说和散文有怎样的区别呢?
塞壬:我回答这个问题有点尴尬,因为我有多篇散文被编辑拿去当小说发表。我早期有一篇散文《1985年的洛丽塔》,当时编辑说要作为小说发表,我坚持认为我写的是散文,最后才能以散文发表。而另一篇散文《一次意外的安置》,《长江文艺》直接作为小说发表了。可见我的散文有明显的小说因素在里面。散文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就是“我向”叙事,而小说是一个“他向”的叙事,这就是散文与小说最大的区别。散文最终还是“我”在主场主导整个核心,是在表现“我”这个人的审美和价值。小说里很少有作家跳出来讲话的,它是小说里的人物在讲话。而散文是“我”以作家的身份在讲话。我的散文从头到尾贯穿着“我”在里面说话、议论。当然很多人觉得很模糊,但是我的散文本来就是有一点跨文体的,我觉得如果散文不添加一点小说的因素,不通过小说的因素去反哺散文的话,它呈现的容量、厚度和它的层次感都是不足的。因此就很难在文本上呈现一种复杂性,而是会显得单一和平面化,不能很透彻地呈现你要表达的东西。
黄婧雅:您的小说《虚构之美》里提到“我能不能在写小说的时候,‘我可以经常跳出来发一通议论”。那比如您的散文《1985年的洛丽塔》,就不断在叙事中对人物进行评价和议论,您觉得这可以算是您想写的“可以发一通议论”的小说吗?
塞壬:其实散文、小说都是文学创作。我觉得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不应该先入为主考虑要写一篇散文还是小说,而是应该从表达的需要出发。而且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都存在着“虚构”,散文也不例外。如果写作完完全全是写现实的话,那还需要才华干什么呢?《1985年的洛丽塔》本来就是一篇散文,但是很多人说它像小说。我觉得定义什么是散文、什么是小说根本不重要,作家的写作不应该关心体裁的划分问题,这个问题该由读者或评论家去界定,作家只要实现了清晰的表达就足够了。所以我不关心体裁的区别,只关心那些属于文学内核的精神是否得到了有效的表达。
黄婧雅:您在写《1985年的洛丽塔》时,前期对表姐的态度是羡慕的,后期对表姐发表的议论则是批判的。但看了您的诗歌《我的小表姐》后,发现最后一句“但我永远不会暴露出来是去做一个妖精的意愿”似乎又透露出对小表姐隐隐的羡慕和向往。所以想问一下,您在写这篇散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态,想表达什么样的情感呢?
塞壬:这篇散文想表达的是一个人的成长需要面对来自于成长疼痛的巨大黑暗,而且这黑暗将是你一个人的秘密,你要战胜这个秘密才能强大起来。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有很多黑暗的地方,每一个人的成长都千疮百孔,我在这篇散文中所写的少女的成长也有着这样的黑暗秘密。怀揣着这样的秘密,有的人会选择堕落,而有的人选择战胜它从而变得越来越强大,这就是这篇散文想要表达的精神。至于最后一句,是来自于张爱玲的《谈女人》:“正经女人虽然痛恨荡妇,其实若有机会扮个妖妇的角色的话,没有一个不跃跃欲试的。”做一个妖精是每个女人心里面的一个任务,即使是端庄的女人也有这样的愿望。那首诗歌是建立在上述的精神背景之上的,但我并不羡慕表姐那样的状态,即使最后嫁给有钱人成了阔太太,她骨子里还是自卑的。她在面对我这个文化人时会产生自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和她一样,而是像我一样好好读书,成为一个文化人。这是很多人在有钱以后,骨子里因为没有文化而产生的自卑感。
黄婧雅:您的散文《祖母即将死去》中的祖母,《1985年的洛丽塔》里的表姐、姨妈、母亲,《一次意外的安置》里的英子,这些女性角色的形象塑造都非常生动立体。请问您对书写女性角色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心得,在作家创作中对女性的关怀有什么看法吗?
塞壬:我觉得中国女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她们坚韧开阔、勤劳包容,她们具有一切美感、美质中最耀眼的部分。我们中国的女性几千年来受到男性的压迫,在男权社会里处于弱势地位。我对女性的情感源于她们创造了生命和她们在面对命运的压迫时那种不可思议的创造力和坚忍不拔的力量。在整个文学史中,一个作家如果写不好女性的话,就很难写出作品的深度。女性几乎跟所有的秘密、所有痛苦的根源,和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以及这个世界上的美息息相关,所以如果作家对女性在创造生命上的理解不够的话,就很难在文学的道路上走远。
访谈结束后,塞壬匆忙地赶往车站。事实上,三个小时前,她刚从车站过来。临走前,她突然回身问我们:“你们现在有没有同学写网文呀?我想学习一下,听说这个东西现在发展得很好。”
我们笑了,为她的可爱。
“人最可贵之处在于看透生活的本质后,依然热爱生活。”感谢塞壬,她让我们看到了“人最可贵之处”。也愿我们,永远保有热爱生活的能力。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