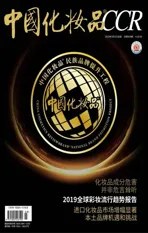调香有没有“理论”
2019-12-28特邀专家林翔云
文/ 特邀专家 林翔云

作曲、绘画、调香自古以来被公认为人类三大艺术。有关作曲、绘画的著作浩如烟海,各种学派、流派的理论多如繁星,令人目不暇接,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理论大师”,有时意见不一还要争吵一番,甚至大动干戈,互相批判,以求真谛。相对来说,有关调香的理论则寥若晨星,无处寻觅。
“知难行易”,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只要先在理论上有了足够的认识,实施起来就不会太难。调香工作应该也是如此,可惜十几年前翻遍图书馆、书店里所有有关香料香精的书籍,却发现几乎没有什么“调香理论”。有些所谓的“理论”只是香料香精香型的分类而已。我国“三个半鼻子”在半个世纪前创立的“八香环渡理论”和“十二香环渡理论”算是对调香工作较有意义的一套“理论”了,但同其他技术相比,只能算是“皮毛”而已。
调香是一门艺术AROMA BLENDING ART
其实每个调香师都有一套“调香理论”指导自己和助手、学生的调香与加香实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修正他的这套“理论”,不断完善,没有终止。只是绝大多数调香师仅把这些“理论”藏在自己的调香笔记里,不愿意加以整理,公布于世,与人分享。早期欧洲各国的调香师无不如斯,他们只把自己的理论用口头和笔记的形式传授给后代。
在合成香料问世前,所谓的“调香理论”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似为“粗糙”“简单”,其实未必尽然。试看中国古代宫廷里使用的各种“香粉”(化妆、熏衣、做香包用)、“香末”(用各种有香花草、木粉、树脂等按一定的比例配制而成,用于熏香)、日本香道(从中国唐朝的熏香文化传到日本演化而成)的“61种名香”和埃及的“基福”“香锭”、欧洲的“香鸢”以及后来进一步配制而成的“素心兰”香水和“古龙水”,调味料用的“五香粉”“十三香”和“咖喱粉”等就知古代深谙此“道”(香道)者并不乏人。
所谓调香,就是将各种各样香的、臭的、难以说是香还是臭的东西调配成令人闻之愉快的、大多数人喜欢的、可以在某种范围内使用的、更有价值的混合物。调香工作是一种增加(有时是极大地增加)物质价值的有意识的行为,是一种创造性、艺术性甚高的活动,但又不能把它完全同艺术家的工作划等号。
调香工作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一门技术。因此,调香理论也就介于艺术、科学、技术三者之间,并且三者互相贯穿,不能割离。单纯的化学家,不管是研究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化学还是物质结构,盯着一个个分子和原子的运动调不出香精来;化工工程师,手持切割、连接各种“活性基团”的利剑和“焊合剂”,同样对调香束手无策;而将调香完全看成是艺术,可以随心所欲者,即使“调”出“旷世之作”,没有市场也是枉然。
研究色彩,可借助光学理论;研究音乐,可借助声学理论;可是研究香味,却发现“气味学”还未诞生。要建立“气味学”的话,势必包含“化学气味学”“物理气味学”“数学气味学”“生理气味学”和“心理气味学”五个学科。因此,符合科学的、能指导实践的调香理论应包括上述5个学科的内容,再加上艺术的、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并将它们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调香师的工作是把2个以上的香料调配成有一个主题香气的香精,这个主题香气可能在自然界存在,如茉莉花香、柠檬果香、麝香等,也可能是人类创造的各种“幻想型香气”,如咖哩粉香、可乐香、力士香等,模仿一个自然界实物的香气或者别人已经制造出来的“幻想型香气”的实验叫作“仿香”,而调香师自己创作一个前人没有的香气的实验叫作“创香”。不管是“仿香”还是“创香”活动,调香师都是先把带有他要调配的这个“主题香气”的香料找出来,然后确定每个香料要用多少,如果不考虑配制成本的话,带有这个主题香气越多的香料用量越大。

我们知道,调香师手头上的每一个香料一般都带有几种香气,例如乙酸苄酯就带有70%的茉莉花香、20%的水果香、10%的麻醉性气味(所谓的“化学气息”),所以在配制茉莉花香香精时,乙酸苄酯的香比强值(香气强度值)只有70%对茉莉花香做出“贡献”,其余30%的香气被强度大得多的一团茉莉花香掩盖掉了。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70%的茉莉花香”是“动态”的,不是绝对的——当我们用闻香纸沾上少量乙酸苄酯拿到鼻子下面嗅闻时,我们马上会觉得它的香气里大约有70%的茉莉花香;再闻一次,就会觉得“茉莉花香”少了些许;再闻一次,又少了些许……直至闻不到茉莉花香、或者我们认为“根本就不是茉莉花香”时为止。其他香料的香味感觉也全都如此。人类的所有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肤觉都是这样,从对一个事物的“非常肯定”到“难以断定”到“模糊不清”。说一个例子恐怕人人都有同感:随便写一个字在纸上端详半天,你会越看越不像这个字,最后甚至对这个字产生怀疑。正是香气的“动态”特征让我们把香气与混沌、分形等等“现代数学”理论挂上了钩。
混沌数学与调香AROMA BLENDING ART
有人认为,20世纪物理学三次大的科学革命是: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如果从更大历史尺度来看,相对论、量子力学、混沌理论等可能是同一次科学大革命的不同战役,它们共同构成人类科学史上的第二次大革命”。

简单地说,混沌是确定性系统产生的一种对初始条件具有敏感依赖性的回复性非周期运动。世间处处有混沌,人们也天天在与混沌打交道,只是不注意罢了。就调香工作来说,每次调香,不管是“仿香”还是“创香”,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混沌学里面的许多规律性的东西,其中包括自己的经验总结,只是不知道或者不刻意去学习这一门“混沌学”而已。
混沌理论首先是数学的,其次才是物理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科学。从数学方面来说,数学历来有所谓“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之分,数学家可以全身心地研究他们的“纯粹数学”,像陈景润专门研究他的“哥德巴赫猜想”,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可以把数学家的研究成果“拿来应用”就行,不必做从头开始(其实永远没有“头”)的冗长的数学推理。混沌理论更是这样,如果都像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动力学家那样按照“寻找混沌的步骤:同宿点→横截同宿点→马蹄→数学混沌→收缩性→奇怪吸引子→耗散系统的物理混沌”去做的话,一辈子也别想跟混沌学沾边。还有一点,例如以“马蹄”为标准判断是否有混沌运动的话,斯美尔马蹄意义上的混沌在物理上未必都能看得到,这更说明没有必要去钻“牛角尖”。应用混沌理论于自然和社会实践时应该像微积分那样,我们随时都在用微积分的许多理论,但从来不去管它“极限”的纯数学概念到底现在弄清楚了没有。
混沌理论有许多可以被调香师用来解释调香实践中看到的现象,并可用于指导调香实践,作为调香师一种极其有用的数学工具。例如“奇怪吸引子”理论可以解释“谐香”现象——由几种香料在一定的配比下所形成的一团既和谐而又有一定特征性的香气,这一团香气是那么稳定,那么“顽固不化”,你再往其中加一些香料包括组成这团香气的香料,都很难改变它的香气特征(当然大量加其他香料把它的特征香气掩盖住是不算的),这在混沌学里,就可以算是一个“奇怪吸引子”。我们还可以看出这种“奇怪吸引子”具有“分形结构”:组成这团香气的香料单体在数量比例上和品种上都可调整而不大影响这一团香气的特征,例如“素心兰”可以有成千上万个配方,但调香师一闻就认出它的特征香气来。
大自然有许多现成的“奇怪吸引子”:茉莉花香、玫瑰花香、栀子花香等花香,苹果、草莓、菠萝、柠檬等水果香,檀香、沉香、柏木等木香,麝香、灵猫、海狸等动物香……吸引了千百年来所有的调香师努力要在实验室里把它们一个一个再现出来。一代一代的调香师也创造了不少人工的“奇怪吸引子”,如古龙香、馥奇香、素心兰香、东方香、“力士”香、“巧克力香”、“可乐香”等等。每一个调香师孜孜以求的就是在调香室里找到前所未有的、人人喜爱的“奇怪吸引子”,然后把它(们)大量制造出来供全人类使用。这跟作曲家“寻找”美妙的旋律一样,一组好听的旋律也是一个“奇怪吸引子”。
调香师怎样寻找新的“奇怪吸引子”呢?华罗庚先生推荐的“优选法”(包括黄金分割法)、正交试验法都是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目前的难度在于各种香料的理化数据(熔点、沸点、密度、折光率、旋光度、蒸汽压、在各种溶剂里的溶解度等等)太少并且不全;生理学和心理学数据更为稀少,只有一些香料的阈值,而且数据不统一,有的差别很大。不过,调香师还是能够用这有限的数据于“数学调香术”上。例如计算一个香精配方中头香、体香和基香三组香料的“总蒸汽压”,看是否“共振”(如25:5:1或16:4:1),如非“共振”的话,就重新调整配方使之达到“共振”,因为在混沌学里,“结构稳定”的吸引子才是“奇怪吸引子”,而“共振”的结构才是稳定的。
混沌理论已成为建立“数学气味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香气表达词语和气味ABC AROMA BLENDING ART
人类通过五大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肤觉(触觉)从周围得到的信息,以表示视觉信息的词语最为丰富,不单有光、明、亮、白、暗、黑,还有红、橙、黄、绿、蓝、靛、紫,更有鲜艳、灰暗、透明、光洁等模糊的形容词,近现代的科学和技术又进一步增加了许多“精确的”度量词,如亮度、浊度、光洁度、波长等等,人们觉得这么多的形容词是够用的,“看到”一个事物时要对人“准确地”讲述或描述,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困难。表示听觉信息的词汇也不少,我们很少觉得“不够用”。但一般人从嗅觉得到的信息想要告诉别人就难了——几乎每一个人都觉得已有的形容词太少,比如你闻到一瓶香水的气味,你想告诉别人,不管你使用多少已有的形容词,听的人永远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有关嗅觉信息的形容词甚至比味觉信息的形容词还缺乏——世界各民族的语言里都经常用味觉形容词来表示嗅觉信息,如“甜味”“酸味”“鲜味”等等,就是一个例子。现今已知的有机化合物约200万种,其中约20%是有气味的,没有两种化合物的气味完全一样,所以世界上至少有40万种不同的气味,但这40万种化合物在各种化学化工书籍里几乎都只有一句话代表它们的气味:“有特殊的臭味”。
由于气味词语的贫乏,人们只能用自然界常见的有气味的东西来形容不常有的气味,例如“像烧木头一样的焦味”“像玫瑰花一样的香味”等等。这样的形容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但已能基本满足日常生活的应用了。对于香料工作者来说,用这样的形容法肯定是不够的,他们对香料香精和有香物质需要“精确一点”的描述,互相传达一个信息才不会发生“语言的障碍”,最好能有“量”化的语言。早期的调香师手头可用的材料不多,主要是一些天然香料,而这些香料的每一个“品种”香气又不能“整齐划一”,所以形容香气的语言仍旧是比较模糊的,比如形容依兰依兰花油的香气是“花香,鲜韵”,像茉莉,但“较茉莉粗强而留长”,有“鲜清香韵”而又带“咸鲜浊香”,“后段香气有木质气息”。这样的形容对当时的调香师来说已经够了,至少他们看了这样的描述以后,就知道配制哪一些香精可以用到依兰花油,用量大概多少为宜。
单离香料、合成香料的出现和大量生产出来以后,调香师使用的词汇一下子增加了许多,甚至可以形容某种香味就像某一个单体香料,纯净的单体香料香气是非常“明确”的,一般不会引起误会。例如你说闻到一个香味像是乙酸苄酯一样,听到的人拿一瓶纯净的乙酸苄酯来闻就不会弄错。这样,调香师们在议论一种玫瑰花的香味时,就可以说“同一般的玫瑰花香相比,它多了一点点玫瑰醚的气息”,听的人完全明白他说的是怎么一回事。
外行人看调香师的工作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的脑子怎么比气相色谱仪还“厉害”?化学家也觉得不可思议,调香师是怎么把一个复杂的混合物“解剖”成一个一个的“单体”呢?难道他们的头脑真的像一台色谱仪?其实在调香师的脑海中,自然界各种香味早已一定的“量化”了,因为他们配制过大量的模仿自然界物质香味的香精,一看到“玫瑰花香”,他们马上想到多少香茅醇、多少香叶醇、多少苯乙醇……就可以代表这个玫瑰花香了;同样的,多少乙酸苄酯、多少芳樟醇、多少甲位戊基桂醛(或甲位己基桂醛)、多少吲哚……就能代表茉莉花香。这样,调香师细闻一个香水的香味时,脑海中先有了大概多少茉莉花香、多少玫瑰花香、多少柠檬果香、多少木香、多少动物香……接着再把这些香味分解成多少乙酸苄酯、多少香茅醇、多少柠檬油、多少合成檀香、多少合成麝香……一张配方单已经呼之欲出了。
调香师是把各种香料按香气的不同分成几种类型记忆在脑海中,然后才能熟练地应用它们。在早期众多的香料分类法中,都是把各种香料单体归到某一种香型中,例如乙酸苄酯属于“青滋香型”(叶心农分类法)或“茉莉花香型”(萨勃劳分类法),这个分类法在调香实践中暴露出许多缺点,因为一个香料(特别是天然香料)的香气并不是单一的,或者说不可能用单一的香气表示一个香料的全部嗅觉内容,所以近年来国外有人提出“倒过来”的各种新的香料分类法,例如泰华香料香精公司举办的调香学校里,为了让学生记住各种香料的香气描述,创造了一套“气味ABC”教学法,该法将各种香气归纳为26种香型,按英文字母A、B、C……排列,然后将各种香料和香精、香水的香气用“气味ABC”加以“量化”描述,对于初学者来说,确实易学易记。本书作者认为26个气味还不能组成自然界所有的气味,又加了6个气味,分别用2个字母(第一个字母大写,第二个字母小写)连在一起表示,总共32个字母表示自然界“最基本”的32种气味。兹将“气味ABC”各字母表示的意义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