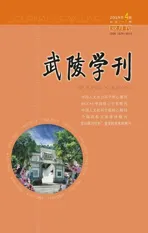《帕梅拉》的贞洁美德述行
2019-12-24张琳
张琳
(邵阳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邵阳422000)
塞缪尔·理查逊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书信体小说家,他的首部书信体小说《帕梅拉》,又名《美德有报》(Pamela or,Virtue Rewarded),讲述了年轻貌美的女仆帕梅拉以语言为武器,抵御男主人的威逼利诱,捍卫贞洁,最终赢得尊重嫁入豪门的故事。小说一经出版便引起热议与模仿,“成为英国小说史上第一本畅销小说”[1]。
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指出,“述行”即“说出一句话就是实施一个行动”[2]7,并将言语行为抽象概括为三种:“说话行为/施事行为/取效行为”。“说话行为指说出合乎语言习惯的、有意义的话语;施事行为指在特定的语境中赋予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言语行为力量’;取效行为指说话行为或施事行为在听者身上所产生的某种效果”[2]99。文学述行理论由言语行为理论发展而来,它既“关注文学作品建构文本内部世界的行为,也考察文学话语作为一种指向现实世界的实践行为,即文学在创造现实、改变现实或影响现实方面的‘行事’作用”[3]1。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的贞洁话语、社会语境规约和取效行为,探讨小说如何述行贞洁美德。
一、贞洁言语述行:建构女性美德典范
米勒认为:“文学作品具有一种‘世俗的魔力’,能够通过语词将一个虚拟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4]20小说《帕梅拉》通过女主人公向父母所做的贞洁承诺以及她对男主人的言语反抗,为读者展现了一场贞洁保卫战。在写给父母的第一封信中,帕梅拉向父母详述了前女主人去世给她带来的悲伤,并提及新主人B君对她的“慷慨大方”。富有人生经验的帕梅拉父母担心B君另有所图,回信告诫女儿要“严守贞洁”。他们强调:“我们亲爱的孩子要是失去了贞洁,这将会是我们无法忍受的痛苦,而且将很快把我们这把老骨头送进坟墓。”[5]14孝顺的帕梅拉回信承诺:“我宁肯死一千次,也不会以任何方式,成为一个不贞洁的人。”[5]15帕梅拉及父母的书信交谈是一种“特殊的述行性言语行为”,它不仅创建了帕梅拉向父母承诺这一件事,而且也隐含了故事的发展,即故事接下来述行的贞洁观一定会和第一部分一致。帕梅拉和其父母的言语既暗含了小说“贞洁至上”的主题,又拉开了小说一系列事件得以推进的大幕。
面对身份地位相差悬殊的B君的侵犯,帕梅拉以语言为武器保护自己。她善于运用语言自我塑造,反抗权威,其中较为突出的事件有“三个包裹”的选择和庄园囚禁事件。为彻底拒绝B君,帕梅拉准备离开B宅,临行前她准备了“三个包裹”。在向管家戴维斯太太谈及这三个包裹时,帕梅拉的言语意味深长。提及第一个包裹——老夫人赏赐给她的亚麻衣裙时,她坦诚自己没有权力接受,并说:“她把这些给我,是假定我穿着它为她服务,并为她美好的心灵增光。”[5]76这说明在帕梅拉心中第一个包裹象征着老夫人的深厚情谊以及她曾经在B宅的荣耀。对于第二个包裹——B君“赠送的礼物”,帕梅拉谈及时言辞冷淡,认为“有了它们,凡事都不会顺当如意”[5]76。因为第二个包裹意味着B君的邪恶与引诱。对于第三个包裹——为回家准备的土布衣裳,帕梅拉将之视若珍宝。她向“亲爱的第三个包裹”发誓:“如果我丧失贞洁的资格,那么就让我永远得不到你里面所包含的一块碎布。”[5]77通过对比三个包裹的象征意义,帕梅拉既将内在的精神行为外化成可见的符号,又遵循了小说开头她的许诺,她承诺严守贞洁,也会依承诺行事。
在遭到帕梅拉的坚决反抗后,B君改变策略,将帕梅拉囚禁于林肯郡庄园,试图以权力的高压对帕梅拉进行心理征服。但帕梅拉对之进行的言语反抗更为激烈。于是B君切断帕梅拉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并草拟一份“高尚体面”的协议,从经济等方面引诱帕梅拉。针对协议中的条款,帕梅拉逐一写下反驳意见。谈到惠及父母亲属,帕梅拉回复:“我永远亲爱的父亲和母亲宁肯在壕沟里忍饥挨饿或在臭气冲天的土牢里消瘦虚弱下去,也不愿按这样邪恶的条件,接受一位帝王的财产。”谈到珠宝、金钱、衣物,帕梅拉表示:“金钱并不是我的主要幸福”,“我将做出我力所能及的一切来维护我的荣誉”[5]135。面对权威的代表B君,帕梅拉智慧地“将美德提升到和财富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而让拥有美德的自己和拥有财富的B君站在平等层面”[6]。通过对B君协议条款的逐条反驳,以及二者之间激烈的言辞辩论,帕梅拉的言语拥有了实实在在的力量,她的反抗取得了胜利。小说描写帕梅拉的言语反抗,强调贞洁的重要性,使帕梅拉成功述行了“贞洁美德模范”。
二、社会道德规约:贞洁标准与清教美德
奥斯汀指出:“以言行事行为不是建构于意图或事实之上,而是建构于规约之上。”[3]15规约不仅与社会因素相关,也决定“什么场合由什么人该说什么话”。小说中,女仆帕梅拉捍卫贞洁的言行与18世纪英国的女性贞洁观、女性婚姻状况以及清教徒的宗教观相契合。
18世纪的英国,女性面临双重贞洁标准。中上层阶级女性必须严守贞洁,“因为所有的财产权都有赖于它”[7]107。下层阶级中的一些女性逐渐成为男性的玩物,讲究功利,追求财富,因为“18世纪英国的工业处于衰退时期,纺织业以及其他产业中很少需要女性劳动力”[7]107,未婚女子不再是家里的经济贡献者,反而被看成是家里的负担。出于经济原因,下层阶级中的一些女性甘愿沦为男人的情妇。因此,面对B君对女仆帕梅拉的放荡行为,上至邻里乡绅,下至家仆园丁都认为“这一类事太司空见惯、太普遍流行了”[4]127。
18世纪的英国,女性还面临双重婚姻处境。中上层阶级女性可以嫁给拥有头衔和金钱的男人,因为对他们来说婚姻是“社会地位平等的人之间的商业交易”[8]。而大多数下层社会女性很难找一个上层社会的男人做丈夫,除非她有一笔很丰厚的嫁妆,比如贞洁。因此,帕梅拉的父母严格教导她,在婚前必须守住贞洁,这是她提升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
帕梅拉的言与行还与清教徒的规约相符。一方面,帕梅拉的贞洁述行反映了作者理查逊的清教理想。18世纪的英国,宗教日益衰败,世风每况愈下,作为传统道德的忠实维护者,理查逊渴望通过塑造虔诚的帕梅拉这一道德模范,重振传统美德。另一方面,帕梅拉的贞洁述行也体现了作者理查逊的政治要求。身为书商的理查逊是一位中产阶级,他渴望通过自己手中的笔来重塑英国社会道德,他希望让具备美德、为人谦逊的帕梅拉们取代旧贵族阶级的纨绔子弟成为社会的道德楷模,也试图通过小说向中下层民众宣扬“英国梦”,即“只要诚实生活,坚持做正确的事情,经受住考验,就会得到丰厚的报偿”[9]。“美德”(尤其是贞洁)既是清教主义道德观的具体体现,又是下层社会实现阶级跨越的巧妙途径。帕梅拉这样的“道德楷模”无疑具有榜样的力量,可以唤醒世人的道德意识,符合当时读者的审美期待。
三、读者阅读取效:故事述行与社会反响
米勒认为:“阅读行为的伦理时刻向两个方向发散:一方面它是对某事物的一种反映、责任、应答和尊敬。任何伦理时刻都内含‘我必须’这道命令,但另一方面,这一阅读伦理时刻又导致别的行动,它进入到社会、制度和政治领域。”[10]因此,《帕梅拉》的贞洁道德述行对读者产生的阅读取效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故事中人物的阅读取效行为,即故事中的人物如何接受和理解他人的言语,以及如何通过对他人言语的理解推动故事的发展;一是作品对读者现实生活产生的效果。
小说中,B君对帕梅拉的态度经历了恣意调戏—理解体谅—感动尊重的转变。一开始B君反对帕梅拉在信中描写在B宅发生的事,并责备她“冒失”地将B宅“暴露”给全社会[5]164。但是随着他读的信越来越多,他渐渐被帕梅拉的文字所吸引,也为帕梅拉贞洁自持的品德而感动。B君向帕梅拉承认:“你的写作方式和超越你年龄的许多感想使我非常着迷,正是这些原因让我无法控制对你的爱。”[5]116即便遭受了诸多反对,B君仍迎娶帕梅拉为妻。B君的言行不仅验证了帕梅拉贞洁言行的文内成功述行,也实现了帕梅拉贞洁自持而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愿望。
在现实生活中,《帕梅拉》作为一种建构的力量,进入并影响了阅读者的个人生活。首先,帕梅拉的故事以及其美德得偿的经历引发了当时社会的巨大反响,小说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欧洲各阶层人士从掩卷而泣的富家小姐到目不识丁的农民都曾围坐讨论这部作品。读者间形成了两大阵营:帕梅拉党和反帕梅拉派,并就贞洁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与《帕梅拉》相关的戏剧、歌剧、诗歌、蜡像、绘画成为文化生活的热点。此外,中下阶层的女性更加重视贞操及道德力量,以帕梅拉“为蓝本来学习举止、风度和教养”[11]蔚然成风。《帕梅拉》还为社会分层、抬升中下阶层人士的地位开辟了一个通道,成为中产阶级积极自我塑造、自我提升并全盘革新道德规范的宏伟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小说《帕梅拉》中,下层女仆帕梅拉以语言为武器捍卫贞洁,向心怀不轨的B君表明了严守贞洁的决心,成功塑造了女性道德模范形象。面对阶级身份差距悬殊的B君,帕梅拉将贞洁美德提升到和财富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而赢得B君尊重,最终美德得偿。《帕梅拉》紧贴社会道德热点,符合宗教社会规约,小说的贞洁话语不仅述行性地建构了故事,也影响了文本内的人物与文本外的阅读者,它的成功是社会、作者、作品和读者统一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