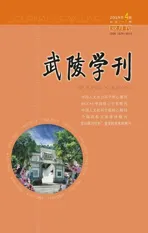近现代小说批评中的圆融观照思维
2019-12-24周娅
周娅
(长沙学院影视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湖南长沙410022)
中国古代文论中对“圆融”的理解,多偏向以“博观”之识鉴赏“圆照之象”,于文辞、字句之间品评体悟;或以高迈的目力“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化执着为虚通,依恃瞬时觉态含英咀华,观照、传达篇章意境之美。虽不乏“圆”的通透颖悟,却鲜有突破文章本身的气度,不免失之漫漶感性。近现代学人在艰难世道前彻底挣脱了梏然自大的保守心态,以开放的胸襟接纳西方文明,秉持“善怀疑、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与一己之臆见”[1]的理性态度获得一种系统圆照的通达智慧。近现代小说批评的圆融观照思维方法,由此具有了合纵古今、连横中西的开阔格局,以及打破学科壁垒、理论区隔的圆智贯通。
一、“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
学贯中西的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慨然宣称:“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2]310他于文中逐一分析。所谓“学无新旧”,针对的是“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的极端思想,对新旧学术应辩证圆整地“尽其真”“求其是”,探究“所以成立之由”;所谓“学无中西”,展现了他具有超前意识的融合视野,“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谓“无有用无用”,更是出自一种深刻的圆转意识,“今不获其用”的无用之学,“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后世当能用之”。此外,王氏还坦承“一切艺术,悉由一切学问出”,这就足以解释他为何偏爱于将文学放置于一个跨越时空的学术系统中进行研究,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从《屈子文学之精神》到《宋元戏曲史》,皆是如此。
陈寅恪对王国维的这种系统圆融视野极其欣赏,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评价道:“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之众人所能共喻。”[3]所幸的是,王国维因其具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而在文学批评方面取得令后世仰止的成就,开启了一条融汇古今中西的现代转型大道。在近现代小说批评史上,有识之士沿此通途,以通达的圆融观照思维方法指点小说、激扬文字,共襄中国文艺复兴大业。
(一)“存于邃古”,“及于方来”
王国维的“学无新旧”说申明学术的发展自有一个流转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有机圆满的生命体,今人当以超越的姿态融合古今,以科学的、史学的眼光珍视“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2]311的传统,把握学术发展的历史连续性和内在统一性。即便近现代文学史上对传统叛逆得最为彻底的先锋,也不得不按照传统“及于方来”的既定轨道,割不断与传统联系的同时,超越性地去延伸、创造新的传统,而这新传统也是他们置身于传统的长河中,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新的理解和阐释。
鲁迅作为近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爱国主义作家、批评家、学者,他所痛斥的种种“国粹”并不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而是古代传统中“与蛮人的文化恰合”的“吃人,劫掠,残杀,人身卖买,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4]之类劣根与痼疾。面对真正的传统文化精髓,“我们不但是文艺上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5]。也就是说,鲁迅并不是一刀切地批判所有传统,而是在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重估后予以甄别、剔除与整合,“整理国故”就是在此意义上提出来的。具体到小说批评的发展建设上,明清小说评点擅长对单篇独章的文辞结构予以圆融观照,但无人涉足对小说史的整体构建;打破中国小说自来无史局面的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正是鲁迅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阶段性成果,一份为中国古典小说正名添价、足以彪炳中国文化史的辉煌著作。在这部专著中,鲁迅用他独到的现代学术眼光评介了中国小说史上绝大部分重要作品,耙梳钩稽了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建立起小说史的现代研究框架,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一道成为中国学术向现代转变的“双璧”。鲁迅不仅在对小说史的研究上胸怀超越古今的圆融观照的通达,在对《红楼梦》等优秀古典小说的批评上同样深具科学与史学并举的现代意识。一方面,他没有悬置历史时代的因素单独评析作品,而是将《红楼梦》吸纳到小说史乃至文学史的辽阔学术视野中,在总览中国小说的发展演变进程中,对《红楼梦》的艺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红楼梦》被后来的学者抬高到“文学的圣经”的位置,与鲁迅的推举不无关系;另一方面,鲁迅既将高鹗的续书与前八十回圆览成一个有机整体,又辩证地指出高鹗的续作生硬拼凑了一个不真实的拙劣的大团圆结局,与戚蓼生在《石头记序》中对结局未竟反而有一种不圆满的圆满的领悟遥相呼应。“即有即无原为道,非有非无亦是真”,化执着为虚通的圆通思维是古今批评家共有的民族智慧,这种思维的智慧超越古今界限,通过一部经典小说对接起来,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圆融相续?
鲁迅古今超越的意识不止体现在小说史的创建和具体小说的批评上,在历史小说创作方面也彰显出鲜明的古今交融的历史小说观。《故事新编》里的8篇小说从现实的立场去观照古人的言行事迹,借古人古事影射当下问题,激发现代人的爱憎之情和民族自信心。《〈故事新编〉序言》中说:“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6]虽为自谦之语,实则道出了他创作历史小说古今同台的艺术特色。对此,茅盾作出了准确精当的评价:
鲁迅先生以他特有的锐利的观察,战斗的热情,和创作的艺术,非但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而且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7]
茅盾看到了鲁迅特有的精深透辟的“史笔”,领会到鲁迅正是以古今交融的通达思维去全盘考虑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诠释传统与革命的关系时,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即使在生活受到猛烈攻击的地方,如在革命的时代,远比任何人所知道的多得多的古老的东西在所谓改革一切的浪潮中仍保存了下来,并且与新的东西一起构成了新的价值。”[8]无论改革者个人的意愿如何强烈,传统的力量都会穿透时光和革命的阻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成新的传统。1948年朱光潜在思考文学的变革时也曾说:“文学是全民族的生命的表现,而生命是逐渐成长的,必有历史的连续性。所谓历史的连续性是生命不息,前浪推后浪,前因产后果,后一代尽管反抗前一代,却仍是前一代的子孙。”[9]朱氏此论既可与王国维的“学无新旧”说互训,又从文学的微观视角印证了伽达默尔对传统的判断。文学自有其内在连续的生命特性,小说作为文学家族中异军突起的一支,其发展也一样遵循生命成长的必然过程,小说批评又怎能把小说的生命截然分为传统与现代的两段?超越古今的圆融观照,就是让小说和小说批评拥有自然流转的健康生命,在传承与发展的历史轨迹上不断生发新的价值。
(二)“东海西海,此心此理”
“东海西海,此心此理”[10]是王国维提出“学无中西”说的心理同感前提。依地域界限划分出来的中学西学,实质上都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既无对立之别,也无优劣之分,只有在平等互生的前提下“互相推助”,才有可能追求圆整完满的人类真理。超越中西,就是去除人为的对抗,以博大的世界一体的胸怀消解“中学”“西学”二元对立的文化幻象。
近现代小说批评在寻求自身现代性启蒙的过程中,确实有过分倚重西方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的倾向。压倒一切的救亡主题总与启蒙主题如影随形,这就影响了文论家、批评家向西方学习的心态,导致了学习时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使小说批评的现代性转型出现舍弃传统直取西方的盲目性,而不加甄别的拿来主义模糊了对小说创作发展的正确导向性。这种弊端的发生,归根到底还是时代、历史条件的局限导致的超越中西的圆融思维缺失。
事实上,全盘西化的误区并没有遍布整个批评理论界,除开少数文化激进主义者,多数意识清醒、视野开阔通达的文化传薪者仍然表达和坚守了审慎、理性的批评态度。而且随着与西方文化的密切接触,批评家逐渐培养起自主选择不盲从的科学意识,批评过程中打破中西方思想的隔阂、超越中西文艺观念界限、感性与理性兼长的范例也在逐渐增多。
《〈红楼梦〉评论》是中西思想意识交相辉映的典范之作。文章以“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11]开首,以叔本华的生命哲学为体系框架,通过中国老庄的哲学思想和西方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共同论证,揭示了人的悲剧性存在本质。中西合璧的通达气势,世界性的美学眼光,“使得王国维的小说评论超越了一般的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文艺学和文艺美学研究,而直探文学批评的本体论核心”[12]。
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吴宓学贯中西,对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和传统儒家文化兼收并蓄,并在美国新人文主义美学创始人白璧德教授的亲自指导之下,形成了对中西文化共通性的认识。1920年,吴宓发表《〈红楼梦〉新谈》,运用大量的外国文学论著和文学形象来比较分析小说主人公宝玉的思想性格,将人物形象化成一座直达人类共通心灵的艺术桥梁。需要格外注意的是,无论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还是吴宓的《〈红楼梦〉新谈》,文章的思路都不是将批评对象屈从于西方文化的意愿,用《红楼梦》来印证西方的文论。他们只是敏锐地感受到《红楼梦》与西方文化、宝玉和卢梭及堂吉诃德的应和与相通之处,然后凭着强烈的学术兴趣行之成文,这中间不存在中西文化孰优孰劣、孰主孰从的问题。超越中西的圆融通达,其根基就在于中西主体地位的平等,超越才可能在平等交流的互动过程中获取现实的可能性。惟有清醒地把握了这一点,才能彻底摆脱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13],真正理解圆融观照的“通达”的睿智,以及在近现代现实语境中的行之不易。
二、“‘理’有所通,心有所感”
明清小说批评中不乏圆融观照批评思维的昭显化用,其中包含一种物有所通、心有所感的具体方式,即运用五官感受、六根圆通的通感去品评小说的方式。此处的“物”指的是打通了彼此界限,能与外界万象互通感受,主体心灵随之沉潜体验的身体感官。近现代小说批评中,随着批评家视野的进一步开阔广博,圆融观照思维之通达早已突破单纯的感官体验,它超越古今中西,同时也消弭了“有用无用”的学科界限。文学作为不同学科、不同文化领域表征的意义,早已被古人认同并以身践行,文史哲从来就是涵容一体、自古一家的,古人从来不会仅从单一的对应关系方面去简化对复杂文学现象的理解。虽然这种慧识受到了现代科学体系学科划分的不小冲击,但随着新历史主义、新感觉主义、读者接受理论、精神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等文艺思潮和批评方法的涌起,越来越多的西方文论家也纷纷认识到文学的跨学科性。比如德国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伊塞尔就曾感慨:“我们关于文学难以从本体上界定这样的意识直接源于古典主义遗留下的难题。因此像‘文学性’及‘诗意’一类术语,只是掩饰自主艺术难以继续自我确证的时代的真正的持续性本质。文学不是自足的东西,因此它难以自我繁衍。”[14]文学总是溢出学科划分的界限而“圆照”普世文化,同时它又有赖于不同学科、文化领域的反哺和滋养。有鉴于此,特将“物有所通,心有所感”的“物”置换成“理”,以此表明圆融贯通本身的臻进。“理”既包涵“有用无用”的各文化领域的“学理”,也可指代具体批评过程中使用的“理论”方法。由“物”至“理”的过程,是小说批评从有质有形的“形而下”向无质无形的“形而上”的提升进程,更是人类文明“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后的自我升华之旅。
(一)“无用之用”的会通
按照王国维“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2]311的理解,世上本不存在“有用无用”之辨,“不学无术”,学科之间圆融会通才可造就整体的学术系统。因此,要想充分展开文学研究,就不能执着于一隅,而要摆脱偏狭的视阈,以通观的眼光,从相关学科中借鉴适宜的方法理论,获取文学自身涵天负地的无穷体认。王国维本人的文学研究,早已自觉地在各相关学科领域内铺展开来,并取得丰硕成果。
作为近现代文学批评先驱者之一的周作人,在《怎样研究中国文学》一文中观点鲜明地指出:“所谓文学不过是‘文化’里的一部分,故而研究国文的范围一定要放大了,像哲学,史学,外国文学,经济之类,算一块儿,才是整个儿的文化集团也就是每个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们所需要的。”[15]他之所以会对郁达夫《沉沦》秉持肯定维护的批评立场,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为《沉沦》正名,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综合性地运用文化人类学、性心理学、图腾理论、比较文学等方面的跨学科知识,敏锐地意识到《沉沦》的主题是真实表达现代青年普遍存在的灵与肉的冲突:“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16]周作人以博雅的学识,宽容的胸襟,会通的思维跳出彼时文艺批评界的思想藩篱,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新人新作。
近现代小说批评史上,就跨学科文学批评研究而言,潘光旦的《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更是一部不能不提及的典范之作。潘光旦在20世纪早期先后求学于清华学校高等科、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在奉行通才教育的清华,他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熏陶,刻苦汲取古典文化,又在开放通融的教学氛围里博学多识,阅读了包括弗洛伊德著作、霭理士《性心理学研究录》在内的各类书籍,这使得他的思想非常活跃,学术视野极其开阔。在此期间他依据传统的笔记、传奇、戏剧,写下了最初的《冯小青考》,这篇别出新意的论文获得梁启超的格外赏识,期许他可以朝着科学和文学两条道路上发展。之后,潘光旦远赴重洋学习优生学、遗传学等自然科学,又广泛涉猎心理学、文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具备中西文化的深厚学养后,他尝试从民族精神健康的立场,科学地反思中国古老的儒家文化。在此基础上,他又开始寻找有关小青的材料重加厘定,并重点探讨了她的变态性心理,增补了《小青之分析》和《精神分析之性发育观》,1929年以《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的书名订正再版。
从《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的成书过程可以见出,这本与众不同的批评著作绝不是仅凭文学的爱好和知识,以单一的文学批评视角就能完成的。潘光旦早年切身的生命体验,历史研究学习中史料的积累和因此养成的史学意识,精通英文而学习性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的相关知识,传统典籍打下的深厚国学根底,广泛涉猎触类旁通的艺术敏感,所有这些复合在一起,才促使他“觉察她是所谓影恋的绝妙的例子,于是就借了梁任公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班上责缴报告的机会,写了一篇《冯小青考》”[17]。时隔4年之后,潘光旦着手修订补充初稿时,他的学术积累已扩展到人文自然学科的各个主要领域。尤为可贵的是,潘光旦此时忧国忧民的情怀,促使他以更为严谨的科学态度辩证地对待中西文化。他深感中国文化具有西方不可比拟的优势和深度,但同时儒家思想对“中庸”的误解导致民族文化风格日渐保守,民族品质趋于平庸化,亟需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的启蒙。正是具备了学贯中西的丰厚学识和观照通衢的目力,所有“有用无用”的知识、思想、精神、见识会通融合,才最终成就了这本直抵人性深处、倾注人文关怀、深具思辨品格的批评著作。
为什么在稗官野史中常见的人物形象无法勾起其他人的研究兴趣,为什么更多的隐蔽地反映中国妇女性心理的作品被漠视,或者被人云亦云地平面化解读?与潘光旦的文学批评对比之后,就不难理解何以王国维会面对学术同人发出如此真切的呼唤:
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世之君子可谓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者矣。[2]312
(二)“曼声浩歌”的涵容
古典小说批评与近现代小说批评最大的区分之一,是前者立足于自我的圆融,以各具手眼的美学思想观照小说文本,批评功能常以“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自洽;后者站在救亡图存的文化阵地前沿,对传统文化的信仰开始产生动摇,“独饮独语苦无赖,曼声浩歌歌我二十世纪太平洋”[18],面向西方谋求超越时空的圆融通达,涵容多种理论方法为我所用,促使小说带动文学重建,进而实现文化启蒙。虽然近现代小说批评追寻现代性的步履难免有踉跄、踏空甚至倒退之时,但从整体情况来看,基本保持了一个稳健理性的姿态,对内自审而不自卑,对外涵容而不膜拜,在接受多种批评理论和方法主张的同时,将民族小说的精神根须伸进世界一体的文学沃土里。
近现代小说批评的历史波澜壮阔,新质异念纷至沓来,千头万绪,在此仅择取一个时间截面粗略来看。自20世纪30年代始,异域的文艺思想、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的涌入呈井喷之势。与西学东渐的前期相比,批评家以更开阔的视阈,吸纳涵容更加多元的理论方法,中国现代小说批评与创作由此迎来了发展黄金期。
来自友邦苏联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一直参与到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之中。三四十年代发生在苏联文艺界的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争的批评理论文章,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国内,对中国现代小说批评价值取向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茅盾就是其中一位深受影响的无产阶级文学批评家,他主张小说创作应该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反映生活:
文艺家的任务不仅在分析现实,描写现实,而尤重在于分析现实描写现实中指示了未来的途径。所以文艺作品不仅是一面镜子——反映生活,而须是一把斧头——创造生活。[19]
有据于此,茅盾认为田汉的《梅雨》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它“除了‘革命的浪漫主义’而外,还相当的配合着‘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20]。同样的,茅盾之所以推崇鲁迅小说,尤其是对《阿Q正传》评价甚高,在于他敏锐地看到了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
《晨报》副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我读了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国龚伽洛夫的Oblomov了![21]
除了源自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之外,对30年代小说批评产生重大影响的左翼思潮主要转运自日本。中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各种途径吸纳左翼文学思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普罗文学观。冯乃超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书籍》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当时日本文坛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留学苏联的蒋光慈发表《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倡导为民主革命服务的小说创作与批评;创造社、太阳社引进辩证唯物主义批评方法,重视小说的政治性与工具性,而相对忽视它的审美特性,正如洪灵菲在《普罗列塔利亚小说论》一文中指出:“它的特性是唯物的,集团的,战斗的,大众的。”[22]
值得关注的还有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它为近现代小说批评建设注入了巨大活力。西方思潮对中国近现代小说批评的最大冲击,体现在思维方式和批评语体的重构上。茅盾曾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谈到西方思潮的渗入对于批评家的影响:“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果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该是更注意些的目的。”[23]也就是说,以茅盾为代表的批评家已经警醒到了,学习西学不仅学其作品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学习迥异于自己的批评思想和思维方式。
不仅如此,语言作为思维自身的要素之一,它是思维得以实现和传达的工具。当小说批评家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并想外化为文字表达时,批评语体的改变就不得不提上日程。且看梁实秋的一段批评文字:
吾人欲得一固定的普遍的标准必先将“机械论”完全抛开,必先承认文学乃“人性”之产物,而“人性”又绝不能承受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支配。我们在另一方面又必先将“感情主义”撇开,因为“人性”之所以是固定的普遍的,正以其有理性的纪律为基础。常态的人性与常态的经验便是文学批评的最后的标准,纯正的人性,绝不如柏格森所谓之“不断的流动”。人性根本是不变的。[24]
梁实秋曾受过美国新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的系统教育,他主张的批评标准是文学艺术特有的规范和秩序,也就是文中所言的“人性”。这段文字,一方面采用了现代学术论文的论证方式和句式结构,另一方面又在多处出现了“机械论”“人性”“科学”“实证主义”“感情主义”“理性”等学术术语。这种教授风格的文学批评,使其有别于传统的批评语体,而富于现代学术语体的科学理性。
近现代小说批评史上多元化的艺术主张、批评思想,嬗变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都被批评家兼收并蓄地用于小说批评的开拓发展上,极大地推动了小说批评高峰期的到来。而从小说创作实绩来考察,无论是小说作品数量呈现大幅增加的趋势,还是小说流派日渐纷呈、作品风格渐趋多样的态势,都说明这个时期的小说批评因涵容多种理论的圆融性,对小说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综上所述,可得如下两方面认识:第一,近现代正当古今巨变之际、中西文化之冲,西方学术理性逻辑的思维方法与中国传统的圆融观照思维交汇互补,使得传统批评之树在异质思维碰撞化合的激发下绽开适时适景之花。近现代小说批评延续着明清评点“圆照”文辞、字句、篇章的旨趣情致,又在西方理性思维的开启下拓展了批评视野,依凭通达的理性智慧超越古今、中西,会通多种学科,涵容多元文论,开启了一个艺术化与科学化并行不悖的批评时代。第二,传统圆融观照思维方法与异域的理性逻辑分析方法在批评家有意融合的努力下,有时相互补充,引发批评新质的衍生;有时彼此颉颃抵触,带来批评的异化与畸变,引起文化界的反思与探讨。离合渐进的过程中,需要整个社会不急不躁、虚静以待,任何盲目的激情或偏执的理论都不利于批评思维的真正深化。具有现代特性的批评,应是“现代”时空条件下有容乃大的本土化批评,它既不是西方学术聊作摆设的附庸,也不是传统思维泯灭活力的后缀。惟其如此,小说批评的现代转型才能踏实地立足本土,具有自己独立的学术品质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