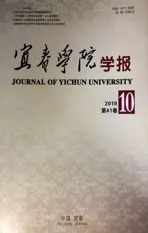《道德经》“其犹橐龠”与《易经》“翕辟成变”思想比较
2019-12-16贺志韧
贺志韧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其犹橐龠”和“阖辟成变”分别是《道德经》和《易经》这两部为中华文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的著作中的两种十分独特的思想。它们的独特性在于它们都引用了一正一反的两个隐喻在其中充当重要的角色,而且同时承担了各自所属经典中的核心概念“道”和“阴阳元气”的本质属性。“其犹橐龠”和“阖辟成变”所倾向的哲学特征都在于对作为宇宙的根源及本质的存在之物的动态描绘,这二种动态描绘体现了一种高度一致的特性,那就是它们所要反映的主体都是空性的、无形无相确又无处不在的宇宙最高本体,它们的运动方式都是一种你来我往、循环往复、永不停息的交互式运动。因此鉴于这种各方面的高度一致性,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两种思想进行详细的考证和解释,并进行对比研究,考察出它们这种一致性背后的根源以及其差别所在。
一、关于《道德经》“其犹橐龠”思想的考辨

那么作为风箱或大袋子的“囊”又是如何同像笛子一样的乐器“龠”联系上的呢?王弼认为:“橐,俳橐也。龠,乐龠也。橐龠之中空洞,无情无为,故虚而不得穷屈,动而不可竭尽也。”[1](P14)在这里,“俳”可能有两种意思:一是指优俳、俳舞、俳乐之“俳”,即由优伶表演的供贵族娱乐的歌舞节目,那么“俳橐”可能就是在进行俳舞或俳乐之时的一种大袋子形状的道具;一是作“排”的通假字,“俳橐”即指用手推动的风箱。总之,按王弼的意思,不管是风箱也好,大袋子也罢,还是像笛子一样的乐器也好,它们的形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即“中空”。王弼认为《道德经》中之所以要引用“橐”“龠”这两个词来比喻“道”,意思就是要说明“道”是一种“无情无为”的没有任何生物情感、喜怒哀乐情绪和任何具有人为性质的刻意的行为动作。正因为“道”具有这样的空性,所以它能够“虚而不得穷屈,动而不可竭尽”,能够永远保持勃勃的生机。楼宇烈支持清代文人易顺鼎的观点,认为王弼将“橐龠”分开来解释是错误的。楼认为“橐龠”指的是一个东西,就是风箱,“‘橐龠’,俗称风箱,橐是外椟,龠是内管”,即认为“橐”指的是风箱外面空壳状的木箱子,“龠”指的是风箱里面用来推拉起风的木杆子。陈鼓应的观点与楼宇烈的观点是一致的,陈引用了南宋范应元和元代吴澄的注释来表明自己的观点。范应元说:“囊几曰‘橐’,竹管曰‘龠’。冶炼之处,用龠以接囊橐之风气,吹炉中之火[5](P81)”。吴澄说:“橐龠,冶炼所用,吹风炽火之气也。”[5](P81)这些学者都认为“橐龠”就是冶炼用的风箱。我们抛却楼宇烈和陈鼓应对王弼关于“橐龠”一词具体解释的不同意见,从总体上来看他们对《道德经》本来意思的把握,就会发现楼的立场是赞成王弼的,即认为“道”就像“橐龠”一样,是一种没有情感和故意动作,能够持续运动、永葆生机的神秘而且伟大的存在。吴澄甚至对“橐龠”一词进行了抽象化的延伸,认为“橐”象征太虚,是一种包含万事万物的场的存在;“龠”象征元气,它在太虚这一场中流行、运动,推动了万物的生长、变化[6](P6)。因此可以说“道”同时具有两种涵义,一是作为万物生长发育、运动变化的场所,一是指万物生长发育、运动变化的动力因。这两种涵义在分类的不同上有差异的,但是在实际存在的状态中却是合而为一的,都只是一个“道”,并不是另有一个太虚和元气两种事物的存在。元气就在太虚之中,太虚就是以元气的形式进行运动、变化。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之一苏辙对“其犹橐龠”思想的解释更为深入,他不仅仅是站在前人的立场上用证明的眼光看问题,还换了一种思维角度,用证伪的眼光从反面的角度来说明“道”的自然和无为的重要性。他说:“排之有橐与龠也,方其一动,气之所及,无不靡也,不知者以为机巧极矣。然橐龠则何为哉?盖亦虚而不屈,是以动而愈出耳。天地间所以生杀万物、雕刻众形者,亦若是而已矣。”[7](P5)王弼进一步认为:“天地之中,荡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穷,犹若橐龠也。愈为之则愈失之矣。物树其慧,事错其言,不慧不济,不言不理,必穷之数也。橐龠而守数中,则无穷尽。弃己任物,则莫不理。若橐龠有意于为声也,则不足以共吹者之求也。”[1](P14)对“道”的“无为”性进一步进行阐发,认为越是故意为之越会造成更多的损失,这同佛家的“随缘”思想很接近。王弼由此认为任何事物的思维能力和言语表达能力都是极为有限的,如果过分地使用智能和语言,就会到达穷尽的地步;应当要像“橐龠”一样始终保持中空、无为的状态,一切行为随顺自然,抛却掉小我意识,融入到天道之中,才能够真正有所作为。可以说,王弼关于这一段章句的解释基本上与老子的思想是想吻合的。在这里有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对“守中”这个概念的理解,《道德经》中“守中”的“中”与儒家“中庸”的“中”是不同的,儒家的“中庸”指的是一种不偏不倚、有理有节的为人处世态度。而《道德经》中的“中”指的是一种“中空”的空性存在,即“道”的存在。“守中”即是守“道”,是对“道”的随顺。
汉代的河上公所注的《道德经》是从道家的养生学说来进行注解的,书中对该段章句的解释为:“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天地生万物,人最为贵,天地视之如刍草狗畜,不贵望其报也。天地之间空虚,和气流行,故万物自生。人能除情欲,节滋味,清五脏,则神明居之也。橐钥中空虚,人能有声气。言空虚无有屈竭时,动摇之,益出声气也。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开舌举,必有祸患。不如守德于中,育养精神,爱气希言。”[8](P18)河上公认为正是由于天地之间是空虚的,才可以会产生和顺之气的流行,阴阳才能和合,万物才能生长;人应当寡思少欲,少说话,少为外部的事情所困扰,注重自己内心德行的修为,这样才能蓄养精神,避免祸患,才能获得长生。很明显,河上公的解释是一种“六经注我”式的过度解释,虽然与《道德经》原文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但总体上已经大不一样了。《道德经》原文中并没有明显地提及关于养生的事,“多言数穷”也并不能当作说多了话就会招引祸患来理解。
综上所述,虽然多家关于《道德经》中“其犹橐龠”思想的观念略有差异,但是其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结合《道德经》原文,我们可以看出,“其犹橐龠”指的是“道”具有空性,即“道”不是作为一种实体的存在,不是显性的,而是隐性的。是一种“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9](P40)的无形无相,但却“大象无形,大音希声”[1](P37)的无处不在的客观存在。“道”正由于其空性,所以能够包容万物,“为天下溪”[1](P74)。“道”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它无时无刻不在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循环往复的变化、运动,“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怠。”[1](P45)这种运动同时又无时无刻不在遵循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守中”,即维持空性,不落实相。因此“其犹橐龠”的思想是蕴含着《道德经》中整个“道”的体、用两方面的内容的。但是单就“其犹橐龠”这一词汇本身而言,按照除王弼以外的一般研究者的理论而言,它更侧重的“道”的用的方面,即”道”的运动、变化、作用是像风箱一样的来回往复、生生不息的。
二、“阖辟成变”思想的涵义
“阖辟成变”语出于《易经·系词上传》:“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干。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10](P380)“阖”是关闭的意思,如成语“关门阖户”;“辟”是打开的意思,如词语“开辟”。为什么说“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干”呢?孔颖达《周易正义》曰: “阖户,谓闭藏。万物若室之闭阖其户,故云‘阖户谓之坤’也。”[11](P289)他认为“阖户”是关门之象,用来象征关闭、收藏之义,大地是万物的收容、生养之所,所以称为“阖户”。 李鼎祚《周易集解》曰:“虞翻曰:阖,闭翕也。谓从巽之坤,坤柔象夜,故以闭户者也。辟,开也。谓从震之干,干刚象昼,故以开户也。”[12](P923)即虞翻认为巽卦是风的意思,象征柔弱。巽卦在坤卦之上,象征大地进入夜幕。夜幕降临是关门闭户之时,所以“阖户谓之坤”。震卦是雷电的意思,象征刚强。震卦在干卦之上,象征天穹刚刚露出阳气,白昼来临。白昼来临是人们开门之时,所以“辟户谓之干”。可以看出,《周易正义》和《周易集解》中关于这句话的解释是从完全不同的两个角度来考虑的,前者是从大地容纳、生养万物的功能角度来考虑,后者则是从夜晚和白昼降临的时间角度来考虑。二者都有其解释的合理性之所在,如果仅就《周易》文本自身来看,似乎前者的解释更为恰当,后者略存在一些过度解读的嫌疑。
解释完这句话后,紧接着就是要讨论关于本文的主题之一“阖辟成变”的涵义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必须同时结合上文关于“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干”和下文“往来不穷谓之通”的解释。《周易正义》认为:“‘一阖一辟谓之变’者,开闭相循,阴阳递至,或阳变为阴,或开而更闭,或阴变为阳,或闭而还开,是谓之变也。‘往来不穷谓之通’者,须往则变来为往,须来则变往为来,随须改变,不有穷已,恒得通流,是‘谓之通’也。”[11](P289)《周易》作者认为“阖辟成变”的意思就是阴阳之间的相互交融、转换,即阳老则生少阴,阴老则生少阳,认为阴阳转换就是万物生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这种转化并不是随机的、偶然的,而是事物的形态自然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自发产生的,是不以人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转化生生不息、永不停止,所以称为“往来不穷”,因为它使得万物发展自然、顺畅,所以“谓之通”。 《周易集解》引用三国时期吴国虞翻的《易注》和东汉时期荀爽的《易传》的意见认为:“虞翻曰:阳变阖阴,阴变辟阳,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也。荀爽曰:谓一冬一夏,阴阳相变易也。十二消息,阴阳往来无穷已,故‘通’也。”[12](P924)由此可以看出,虞翻的观点在这里和孔颖达的观点相一致了,虽然前面二人关于“阖”和“辟”用词的原因是根据天和地的空间视角进行考察还是根据夜幕和白昼降临的时间视角进行考察上有所分歧,但是在“阖辟成变”的问题上都采用了阴阳转化的解释。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殊途同归的效果,是因为地和夜幕都是属于阴性,天和白昼都是属于阳性,所以无论“阖”与“辟”对应的是空间上的大地、天空因素还是时间上的夜幕、白昼因素,其在根源上所对应的都分别是阴与阳。孔颖达认为《易经》中之所以要提出“阖辟成变”的概念,其目的是为了“言圣人以利而用,或出或入,使民咸用之”[11](P290)孔教导人们要向圣人一样能够因势利导地根据天地自然的规律而随时出入变化地机动性地处理事务,使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周易集解》则引用三国时期吴国陆绩的观点:“圣人制器以周民用,用之不遗,故曰‘利用出入’也。民皆用之,而不知所由来,故谓之‘神’也。”[12](P924)陆的观点陷入了一种具体的形而下的解释层面,没有孔颖达的解释妥当、贴切。
王弼的观点又有所不同,他认为:“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翕,敛也。止则翕敛其气,动则辟开以生物也。干统天首物,为变化之元,通乎形外者也。坤则顺以承阳,功尽于己,用止乎形者也。故干以专直,言乎其材;坤以翕辟,言乎其形。”他将“阖辟成变”转化为“翕辟成变”的概念,并将“翕”与“辟”都对应于“坤”,认为它们都是大地的功能,而不是像孔颖达一样认为“阖”对应的是“坤”的功能,“辟”则对应的是“干”的功能。王弼的创新之处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将“翕”与“辟”同“静”与“动”的哲学观念对应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的思维,动静关系的讨论也由此一度成为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讨论范畴;一是将“翕”与“辟”同“材”与“形”这一组哲学命题对应起来,形成了“道”的本体论的建构。
“翕辟成变”的思想发展到近现代之时,被熊十力抬高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高度。熊十力认为:“翕辟同为纯一之本体所显现之两作用,乃相反相成,相待相涵,而为万化之源。”[13](P26)熊的观点很明显受王弼的影响很大。由于熊“翕辟成变”的思想在王弼魏晋玄学思想影响下又加入了很多的佛学思想内容,离《易经》的本旨相去较远,所以此处仅出于行文周密的原因略为提及,不再详加阐释。
综上所述,《易经》中的“阖辟成变”的思想是关于天地阴阳的运动、变化问题的,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的形成和发展的根本运动规律都是阴阳二种基本元气之间的互相交感、转化。“阖”即是阴,“辟”即是阳,“一阖一辟谓之变”就是说阴与阳二种元气同时并存就会产生运动、变化,人们应当按照阴阳元气的变化而按机行事,因时因地地处理事务,这样就能与天地相感应,达到圣人的境界。
三、二者的异同
如上文所述,《道德经》中“其犹橐龠”的思想是一种对“道”的运动形态的描述,是一种形象的譬喻。《易经》中的“阖辟成变”的思想是一种关于阴阳元气生化万物的机制的陈述,也是一种形象的譬喻。这两种譬喻之间存在一些相关的联系,成就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一)相似性
1.二者都是关于事物起源和发展规律的探讨。“其犹橐龠”说的是事物的运动变化都蕴含在“道”之中,是“道”像风箱一样循环往复的运动变化所产生的。
“阖辟成变”说的是事物的运动变化都是阴阳元气相交相感、相互转化所引起的,就像门的打开和关闭、白天和夜晚的降临一样周而复始、来回不辍。
2.二者所阐述的终极运动规律都是来回往复式的。“其犹橐龠”就是说“道”的运动规律就是像风箱的抽动一样前后相继、出入不断。
“阖辟成变”就是说阴阳元气的转化规律就像门户的开合、昼夜的转换一样按时交接、永不停歇。
“道”和阴阳元气这种往返式、交互式的变化模式反应出了《道德经》和《易经》的辩证思维特征,也反应出了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朴素辩证思维意识。这种意识是建立在对一切事物现象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全面考察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它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观念,那就是发展,它们只看到事物的此消彼长、循环往复的过程。而没有看到事物在这种此消彼长的过程之中有个逐步积累、逐步变异的发展过程,因此是朴素的。正如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形态应当是曲折前进的,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平面的左右摆动。
3.二者所阐述的运动的主体都是空性的作为最高本体的存在。“其犹橐龠”的运动本体是“道”,“道”是一种无形无相的最高的本体,它存在于万物之先,万物因它而生成、发展;它存在于万物之中,是万物生成、发展的根本规律。
“阖辟成变”的运动主体是阴阳元气,阴阳元气也是一种无形无相的最高的本体,是生成万物,并推动万物发展变化的基础,与“道”的性质高度一致。
无论是“道”还是阴阳元气,作为一种最高的宇宙本体,它们必然是具有先天的和超验的属性的,必然具有包容一切、贯穿一切的性质,这是作为形而上的本体的基本要求。否则就不能为万物生成之母和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
(二)差异性
1.“其犹橐龠”的主体是“道”,“阖辟成变”的主体是阴阳元气。《道德经》中的“道”虽然和《易经》中的阴阳元气有着如上文相似性中第三条所说的诸多相似性,但是在根本上还是有区别的,“道”是一种不可言说的、很难界定其实唯物还是唯心的根本存在。阴阳元气则很明显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思想,是物质形态的存在。在《道德经》中,阴阳元气并不是作为最高的存在形式出现的,它们只是“道”生化、衍变而出的,是“道”的流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P20)中的“二”指的就是阴阳元气。它附属于“道”,是“道”与万物之间的媒介和过渡阶段。《易经》中则没有作为最高本体存在的“道”这个概念,而是把“元”作为最高本体,“元”就是阴阳二种元气。《易经》是根据太极八卦图而作的,而太极八卦图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阴阳二气,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存在,并不存在一个像“道”一样的绝对一元的存在。
此外,“道”的外在形态是柔性的,“上善若水”,是像水一样的包容万物的、居于万物之下的柔性存在。阴阳元气则是同具柔性与刚性的,阴气属柔,阳气属刚。即虞翻所说的“坤柔象夜”“ 干刚象昼”。
2.“其犹橐龠”的运动形态是隐性的,“阖辟成变”的运动形态是显性的。因为“道”是一种不可感知、不可言语、无形无相的隐性存在,所以其运动变化的形态必然也是隐性的,这种变化形态只可凭借纯粹的逻辑推理才能够略微加以把握。阴阳二气则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虽然它们也无形无相,但是在生活中凭借日升月落、天生地藏等自然现象能够利用感官直接感知,并形成经验性的综合判断。
3.“其犹橐龠”思想提出的目的和“阖辟成变”思想提出的目的有所差异。“其犹橐龠”思想提出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学习、仿照“道”的空性特征,做事要以“无情无为”为原则,凡事不可太刻意,要抛却掉小我意识,融入到天道自然之中。“阖辟成变”思想提出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的行动按照阴阳元气的变化而按机行事,因时因地地处理事务,这样就能与天地相感应,达到圣人的境界。看起来,二者都是讲究随顺自然的,但是前者重在“无情无为”,反对人为造作,并且最终是要将自我完全融入到“道”之中;而后者重在见机行事,要求有所作为,最终是要实现自我的成圣成贤。由此可以看出,道家和儒家在价值取向的方面有着根本的不同,道家的是以否定小我而成就大我为宗旨的,具有更强的超脱性;儒家则是以通过小我的最大化而带动大我的一同实现的,具有更强的现实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