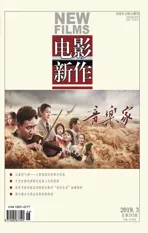流动的乡土经验与静观美学—论李睿珺电影的价值取向和叙事选择
2019-11-15李钦彤
李钦彤
百年中国乡土电影可以分为左翼苦难叙事、阶级斗争的乡土和文化反思的乡土等历史阶段①,如表现农村社会矛盾和反抗的第一部左翼电影《狂流》,或者是表现农村苦难却也寄托诗化理想的《小玩意》;表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李双双》《槐树庄》;呈现后革命时代文化启蒙的《黄土地》,揭示现代文明与传统农耕文化冲突的《人生》《被告山杠爷》。乡土成了乌托邦,或者是革命动力的苦难渊薮,农民则在历史客体和历史主体之间转换。乡土成了知识分子文化想象的产物②。李睿珺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路过未来》悬置价值判断,以事实判断呈现乡土经验。电影以注重事件过程的叙事形式和舒缓的影像节奏,表现时代变迁中的个体命运。
一、在地、进城、生态与童心
以户籍制度为平台,中国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资源和权利的等级分配使得城乡在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和社会声望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城乡对立不仅是文化冲突,更是权力差距。中国城乡结构的层级化以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乡土中国的地理版图上同时存在着农耕文化、工业文明和消费文化,三者互相渗透,错综复杂。在这样的语境下,乡土中国发现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冒险,获得快乐和成长,去改变自己和世界,但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和所知道的一切。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流动的现代性到来,改变了人类的状况,“‘液化’的力量已经从‘制度’转移到了‘社会’,从政治转移到了‘生活政治’—或者说,已经从社会共处的宏观层次转移到了微观层次”③。
既表现在乡农民的生活,也展现进城农民的生活,“艺术家的任务并不是激起人们对虚构情境的同情或憎恨,而是使他们回顾他们自己和其他人正在做的事情,并根据真实事物的本来面貌进行思考”④,李睿珺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路过未来》等电影通过流动的乡土经验展现了城乡冲突,钩沉历史变迁中的个体体验。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揭示了现代化鼎革中乡村的变迁,乡愁于焉弥漫。丈夫/父亲的缺席,造成妻子生活的艰辛和情感的寂寞,也在父子情感交流上设置了障碍。“送情郎送在一里地墩呀,留下我小妹妹一个地人呀,妹妹在家愁地很呀”,歌词流露出女子难言的惆怅,农村在工业化进程中所承担的苦难以具象方式体现在留守农村女子身上。智娃的心事不会告诉父亲,“我才不会让他知道呢”。不仅如此,老人为避免同儿媳住在院子里的一些尴尬来村口打牌,“住在一个院子里,也别扭地很,出来散散心焦”。《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表现了两兄弟一路的对峙、关心、冲突与和解,并由此引出背后的社会变迁。一路走来的兄弟发现昔日水草丰茂的草原被金矿所取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兄弟两人相对无言,跟随着长镜头的移动凝视着眼前的裂变,远处天空的浓烟和脚下的土地,兄弟两人甜蜜而苦涩跟随着下班的父亲回家。
《路过未来》表现当下被现代化进程远远甩在后面的进城农民,他们失去土地,失去工作,后来因为试药失去身体。他们无土地立足,亦无力购房。斯宾格勒曾说过,拘役和自由,是区分植物性的生存和动物性的生存的差异所在。《路过未来》中进城农民希望摆脱被束缚于土地上植物性的生存,去城市寻求动物式的自由多元的生活。但这不过是幻象,他们终究不过是被奴役的羊群。返乡的耀婷父母发现昔日的住房成了羊圈,这是他们处境的象征性表达。植物性的生存已湮灭不见,动物式的自由多元的生活更是虚无缥缈。电影最后用一个超现实镜头表现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身穿白衣的耀婷骑白马而去,另一个耀婷在沙漠中蹒跚而行,看着白马渐行渐远。
除了表现城乡冲突,李睿珺电影还体现出一种全球生态意识。生态意识的立意就是要突破“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万物有灵”,旨归在于“诗意地栖居”。依据海德格尔的论述,诗意栖居就是要“拯救大地”,拯救大地远非利用大地,甚或掠夺、耗尽大地,而是要放弃对大地的征服和控制,使之回归其自然本原状态, 从而使人类恬淡自然地生存在大地之上。
以悲悯姿态凝视中国乡土的变迁,这体现了导演李睿珺的一颗童心。李贽在《童心说》中指出,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有童心,则无时不文,无人不文。童心就是真心,是出于人的自然本性的真情实感。李睿珺电影呈现了乡土的真实变化和真实情感。正是一颗童心,电影才会呈现女儿马存花刀下花瓣一样的西瓜,才有了智娃哭孙悟空一场戏。看着孙悟空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智娃泪流满面,爷爷劝他说,孙悟空明天就出来了,智娃的回答是“不是明天,是五百年”。
二、反戏剧性的静观美学
巴赞曾说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最大的变革在于叙事结构,淡化情节,注重松散事件。罗西里尼《游击队》的叙事并不像链轮上的链条那样环环相衔,我们的思路必须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就仿佛人们为了跨过小河,从一块石头跳至另一块石头。所以,巴赞这样评价罗西里尼,“他们的作品特别注重现实的再现,而不是戏剧性的结构”⑤。
如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李睿珺电影叙事以反戏剧性结构表现时代浮沉。《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将故事背景从缛丽阴湿的南方迁移到雄奇壮阔的北方,以甘肃张掖农村为叙事空间,表现迷恋土葬的老马的人生境遇与人生体验。黄色土墙,绿色苇塘,生活其中的人们做棺材、打牌娱乐、堵烟囱、放马、割湖、看坟、八月十五敬月亮。
和大卫·里恩的想法一样,李睿珺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也是在沙漠拍摄;同样没有明星,只有两个孩子;没有爱情,连女性角色都没有;没有动作,《阿拉伯的劳伦斯》至少还有几场宏大的沙漠厮杀。《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表现一对兄弟和两只骆驼穿越沙漠回家,一路上是戈壁荒滩和断壁残垣,伴随着两兄弟对立的小情绪。等他们满怀期待地回到家乡,以为是水草丰茂,未曾想家乡已变成甚嚣尘上的金矿和浓烟滚滚的工厂。《路过未来》由松散的事件构成,失业返乡、工厂上班、买房、试药、住院等等,直面城市打工者的日常生活。
与松散的叙事形式相匹配,电影在影像上呈现出舒缓节奏。在当下消费文化语境,专心致志的个体凝思成了落落寡合的行为,与此相对的则是涣散迷乱的大众消遣,“电影退化成武斗场,为达到吸引观众注意力的目的,画面剪辑毫无规则(速度越来越快),使得电影成为不值得任何人去全身心关注的无足轻重的东西”⑥。李睿珺电影则走向相反的道路上。“节奏则是从镜头按不同的长度(对观众来说,这就是同时取决于镜头的实际长度和动人程度不等的戏剧内容的时间延续感)和幅度(即心理冲击,景愈近,冲击愈大)关系将镜头连接起来中产生的”⑦。《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与《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极少出现特写、近景,更多是中景、全景和远景,有着大量远景/长镜头。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电影开场即利用长镜头表现老马画仙鹤的过程,摄影机缓慢移动。前一个镜头是老马院落牵马的全景,随后两个镜头是老马牵马走在乡间小路和在苇子湖放马眺望远处的全景。前一个镜头是湖边老马祭奠朋友的远景,下一个镜头是湖上天空中飞翔鸟儿的远景。前一个镜头是老马和苗苗去看坟墓的远景镜头,继而是马存花及其他妇女为玉米喷农药的全景/长镜头,接着是马存花劝说老马离开坟墓的全景/长镜头,最后是祖孙三人骑自行车归家的远景镜头。电影表现村中老者在村口大树下娱乐时连续用了四个自左而右的横移的长镜头。第一个横移展现老马经过沙子上玩耍的孩子,然后来到树下打牌娱乐的老人中间;第二个依旧横移,又一个老者到来,一个孩子走来让其中一位老人回家吃饭;第三个横移镜头中一个妇女让一位老人回去吃饭;第四个镜头中第一个回去吃饭的老人回来了,代替被妇女叫走的老人继续打牌。智娃和苗苗在芦苇塘边大树下挖坑埋葬老马这场戏,电影更是连续使用了两个全景/长镜头,一个时长6分钟,一个时长7分钟。与舒缓的节奏相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亦注重真实的环境音响,八月十五月夜下昆虫的鸣叫,风吹树叶的声音,以及湖边的水鸟叫声。而《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在呈现兄弟两人沙漠之行时,多采用远景别的长镜头,缓慢移动,看着兄弟穿越沙漠,停留歇息,晚上睡在人去楼空的房子。《路过未来》依旧不乏远景或全景的长镜头,如地铁下出租房一家人的谈话,大片玉米地中掰玉米、砍秸秆的农民,新民出租屋外被林立高楼包围的绿地。
三、心灵和民生的真实风景
电影中的风景既包括自然风景,也有人文景观。作为电影表现对象的自然不会是中性的背景,自然是场面气氛的载体,在自然风景中创作者可以融入主观体验,“风景是影片中最自由的因素,最少承担实在的叙事任务,最能灵活地表达情绪、感情状态、内心体验”⑧,因此,自然风景成了人发掘后的一种面孔,“不是所有随意描写的地方都是风景。客观存在的、现实的自然界不是风景。装饰艺术的任务就是把隐蔽在自然景物中的这张面孔找出来,突出展示,并赋予一个框架。摄影机的场面调度、各种基调的选择、自然或人工采光都是手段,人借助于这些手段改造客观存在的自然景观,创造作为艺术本质的主观关系”⑨。风景既有创作者的主观理念,亦和文化意义紧密相连。按照巴拉兹·贝拉的观点,人文景观亦是风景,正如艺术从纯自然中塑造了风景那样,电影把人造自然和工业环境也变成了含义深刻、富有表现力的风景。电影创作者可以通过风景的表现注入情绪、理念。
《黄土地》把乡土风景看作文化主体,它取代了情节和人物成为电影中心。黄土地和黄河作为文化积淀象征,表现了文化所具有的束缚和养育的双重功能。《巫山云雨》则一反《黄土地》张扬的集体意识形态,转而寻求个人心理体验。电影中的风景不过是人主观情感的投射对象,承载着人的喜怒哀乐。同样是表现个体,《三峡好人》无意寻求主观心理投射,而是表现客观的生存状态,揭示人和风景之间的关系。韩三明拿着印有三峡夔门风景的10元钞票站在夔门前,印有毛泽东头像和自然风景的钱币改变了自然风景,也改变了人的命运,从而揭示了告别革命语境下资本、自然和人之间的互动。
李睿珺电影延续了章明和贾樟柯电影的创作道路。《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水草丰茂的苇子湖,牵马于途,饮马于湖,萦绕不去。来到女儿马存花家的老马会带着苗苗来绿草清水的池塘,电影用固定远景/长镜头进行呈现。电影还有人文景观,电视中的仙鹤,以及椅子背上的仙鹤。这些风景皆是老马心理体验的投射,是他对传统生死方式的念兹在兹。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有光亮中的风景,如象征昔日自由诗意生活的白马,以及暗示自然剧变的前景模糊绿草和背景清晰汽车的镜头。相对于光亮风景,黑暗中的风景更为重要。电影两次用手电筒来照亮黑暗中的风景,一是在断壁残垣的房间,一是在无人问津的山洞,兄弟两人看到房子主人离家前遗忘的全家照片,看到壁画张骞出使西域,也看到“人民公社好”的报纸。历史湮灭不见,现实亦在革故鼎新,告别革命后资本正在剧烈改变自然和人的命运,未来不可知。《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利用黑暗中被照亮的风景表达现实裂变超出了想象。正是基于此,电影用一个运动长镜头表现兄弟两人看到滚滚浓烟的工厂,无法理解却也无能为力,只能无言地跟随父亲归家。
《路过未来》有自然风景,被沙漠侵蚀的坟墓,被资本流转的土地,亦有人文景观,高楼林立,高铁或地铁快速驶过。站在窗前的耀婷放眼望去,四周全是高楼,中间是仅存绿地。资本改变了风景,也改变了人的命运。过去已不可得,现实千疮百孔,未来虚无缥缈。
四、细节缺失和无力整合
电影中的乡土是百年知识分子文化想象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土电影中的乡土呈现为三副面孔,一副表现为对农耕文明和田园理想的绿色生态的向往,站在文化守成的立场怀念乡村牧歌式的生活;一类是对城市文明热烈的红色诉求,追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一种是对乡村文化黄色桎梏的审视和批判。
人们在告别革命中开始憧憬现代化前景,落后愚昧的乡村被看做不现代的象征,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精神心态也再次被新时期电影置于批判的境地。《黄土地》《乡音》《人生》《湘女萧萧》皆是代表性作品。作为参照,对城市的现代化生活向往成为乡土电影的另一种姿态,《人生》《乡音》《上车,走吧》表现了乡民对城市的追逐。随着工业化负面后果日益被人们所重视,乡土电影也开始质疑昔日批判乡村的启蒙话语,反思乡村的现代性诉求,从生态整体意识审视乡村,把乡村看作绿色的生态家园。乡村生活和精神文化成了与现代性分庭抗礼的力量和元素,成了负面后果频发的现代化的解毒药,如《乡情》《那山那人那狗》等电影。
面对当下乡土经验出现的新因素,李睿珺电影没有采用之前乡土电影的价值观念,既没有从启蒙视野把乡土看作黄色桎梏,也没有从文化守成立场把乡土看作现代化负面的解毒药,一个绿色的乌托邦存在,而是悬置价值判断,以事实判断的方式直面乡土的问题种种。
李睿珺电影的不足并非有论者所言说的文化守成姿态,而在于其试图整合当下流动的乡土经验,整体表现在地的乡土经验和流动的进城经验,但缺乏生活细节的支撑,导致叙事有些浮泛。《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从侧面揭示现代化鼎革中农村的变迁,并没有直视农村的现实种种。就如同电影开场被蒙上了红布的镜头,现实问题被柔化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专注于沿路之上各种文化符号的变迁,却相对绕开了草原如何变成金矿这一更为尖锐现实的表现。《路过未来》没有呈现出玉米地的劳累感,也没有表现出试药的身体损伤痕迹,买房的焦虑感亦没有表现出来。同样是表现流动的乡土经验,戛纳电影最佳剧本《幸福的拉扎罗》做得更好。电影乡土部分展现了在地的生活细节,种植、采摘、放牧、养蜂等等,犹如当年的《木屐树》。在“跳接”剪辑后,拉扎罗跨越时空,从乡村来到城市。电影以拉扎罗来观照意大利历史变迁,既有农民的苦难,也有贵族的没落,二者皆被现代化遗弃。侯爵夫人儿子的绑架自己将闹剧酿成了悲剧,冒雨前往的拉扎罗失足坠崖。拉扎罗去银行要回侯爵夫人被夺去的东西,却遭遇现代人的暴力。电影有些像《卡比利亚之夜》,在每个段落的最后时刻,闹剧都转变成了悲剧。乡村与城市,纯净与鼎沸,现实与魔幻,闹剧与悲剧,《幸福的拉扎罗》意在呈现整体性的现实。
细节的缺乏使得李睿珺电影呈现出概念化的创作倾向。“电影的精神是唯物主义的;它是从下而上的”⑩,电影不会从一个预先规定的观念出发,然后进入物质世界来给这个观念寻找例证,而是从物质材料出发,取得线索后再逐步走向某个问题或信念。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特点在于对当前现实的密切关注,而在如何关注现实上,其做法是从不让现实屈从某种先验观点。这就要求电影要解决事件过程和戏剧性要求之间的关系,既要尊重事件的真实时间流程,打破观赏性常规,又要具有戏剧性的魅力,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各富有意义的事件。
细节缺失不仅带来概念化,也使得其舒缓影像存在流于冗长而沉闷的美学装饰的危险,因为段落镜头只有根据美学或者戏剧需要去使用才能显得合理。
结语
李睿珺电影创作关注社会革故鼎新中的个体命运浮沉,悃愊无华,人事变迁、历史变幻,化为影像排闼而来。如柴伐梯尼所言,只要发掘,每一件琐细的事都将变成一个金矿。如果掘金者终于来到这无限丰富的现实的金矿,电影在社会上将起重要的作用,未来的李睿珺电影需要对现实进行严格、耐心和仔细的探索,发掘事实的本来面目。
【注释】
①凌燕.回望百年乡村镜像[J].电影艺术,2005(2):87-92.
②杨远婴.中国电影中的乡土想象[J].电影艺术,2000(1):66.
③[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33.
④[意]柴伐梯尼.谈谈电影[A].电影理论文选[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117.
⑤[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崔君衍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360.
⑥[美]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M].陶洁,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35.
⑦[法]马赛尔·马尔丹.电影语言[M].何振淦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120.
⑧[俄]爱森斯坦.并非冷漠的大自然[M].富澜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316.
⑨[匈]巴拉兹·贝拉.可见的人 电影精神[M].安利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74.
⑩[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物质现实的复原[A].杨远婴编.电影理论读本[C].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