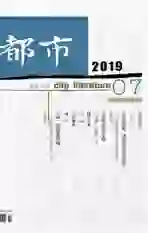文学的基本故乡
2019-09-10闫文盛
闫文盛
悖论
我只是写出了一种虚伪的宁静,我心中的纷扰浩浩荡荡。
散文的伦理
以散文的形式介入日常生活,对于我们中的多数人来说都容易得很。当然,又似乎不唯如是,对于当下的诗歌和小说创作者,日常生活无疑也是最大的素材库。从事文学艺术,以期从最简单和直接的角度来记录岁月的流逝,来反思命运的深沉,渐渐成为我辈与生活之间构成的一个最大协约。
但是,作为一种古老的文体,散文的基本伦理迄今并未界定清晰。与文体特征已经得到确证的诗歌、小说和戏剧相比,散文写作的界限似乎远为含混,其语义空间自当更为多元。因此,对于有野心的写作者来说,散文的这种可以上下俯仰、左右驰骋的巨大包容性就具备了特别的意义。野心可以向四面开展,写作从此变得繁复丰厚,而各类风格就孕育在这种无限敞开的探索之中。
散文化的散文
当下我们散文创作中的问题多多,远未达到我们所期待的样子。倒是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目前的散文终于写得非常“散文化”了(非“妙手偶得之”)。过于“散文化”当然不好,它建立于一种已经趋避不开的“写作同化”。不同的散文作家之间、一个作家不同的散文文本之间,同质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思想和艺术的体量远远不够)。能够做出拓宽散文边界的创作者(不局限于散文家)少之又少,有理想“破”和“立”且身体力行地做出了成就者少之又少。相对于我们在文学源头处的创世之祖,我们仅仅乎安然于肤浅的世俗者多矣。
当然,仅仅乎安于世俗,是我们对自身才华的俯就而非开拓。开拓自我似极艰难,它须有对你所携灵肉最为无情和深可见骨的切割。这是我们体贴于生命宇宙的一个预期,远非一些“散文化的散文”———更非心灵鸡汤和小清新的笔墨可以比拟。因为这种切割所带来的分量会无比的重,它是在应对着文学要实现什么的提问———是在向生命的来路和茫茫无尽的归期展开追索,而不是仅仅在标榜你完成了一次“散文叙述”。这种“散文叙述”,如果不能深刻地影响阅读者的心灵,它就是无意义的。这种写作,谈不上任何自我见证的自由。
伟大的创造者一定是“无知”而“有力”的。无知,源于某种凝视空茫无极处的冲动;有力———我是在赞扬某种笔墨的铭刻之能和勾勒之精准。现在我谈论散文,其实更愿意在一个宏大的文体层面上展开,我反对“过于散文化”,就是在反对固步自封地谈论创作。目下,我们所从事的散文事业的边界为什么需要拓开?根子上,是我认为它的狭小已然在桎梏我们的思维。真正的散文(文学)是生命感觉的大写意,是技艺的升华和灵魂的淬火。真正的散文,是无用之用。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我们当中的确有过一些奋勇地找寻路径而力求打开文体的努力,优秀作品很多。有才具的作家很多。但是,天才中的天才、作家中的作家少之又少。谈一个非常简单的事例,是我在进行创作的前后可以流连的文本大半都不是散文,尤其不是中国当下散文。散文这种文本实践自身对我的启迪意义降低了。我在思考我与这个世界关系的时候,我在感到空虚茫然、枯燥乏味的时候,读中国散文很少能让我感到慰藉。我觉得当下太多的作品是无效的,它们的经典性不够。那种文章之法中应有的弦外之思太少了。在这里,我远远不是仅从经世济用的文章之道上谈问题。再强调一遍散文的艺术尺规,我说的是,散文(文学)更当为无用之用。
什么样的散文是好的?我认为是和深度思考力并行的,贴着事物肌骨进行描摹的,是根除了直接而粗陋的算学法的,是孕育了自身、之母体、之子嗣,且仍在绵绵不绝地生殖的———是超越了当下“散文化的散文”意义上的,是融汇了诗歌的精神、学术的简练、小说和戏剧的文字推演之能的文章合体。换句话说,谈散文的问题,万不能孤立于散文内部而谈。在构成散文“文体的边疆”诸要素中,言说的刺入感、悲伤得寥廓的诗歌性、灵魂的真切落地(自我震慑和反省)、韵律上的复合旋绕,仍是我最看重的。至于其他问题,目前看来,似都不是问题。
灵魂之神情的捕捉
剥除芸芸世象的陈皮,散文写作终归会落实在“大风吹过弯曲的柳枝”这样有关命运物件的沉思和事物蕴意的追踪与辨析上来。而人、事件、物之为思考的载体又只是一个体现风之流动的过程,我们最终呈示的文本却远不会滞留于此。越过中介直陈文本是可以的。(忽略物的中介性,提炼文的骨骼,追求无法之法。)所谓言之简,意之赅,无外是站在为文的根基上谈问题。所以,此处我所谈之文,只是关切艺术情性之根本的识辨之文。这里,我不想多谈散文写作中写实的成分(物的摹写),而更想谈的是我们为文之中“精神的抵达”,即我们“灵魂之神情的捕捉”。
散文表达之匮乏
在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的中国当下散文创作中,目前我们仍然缺乏高度自觉地注目人的存在境况,仍然缺乏和时代之关系高度合拍的作品。即我们经常在回避基本的时代情绪(虚假的散文表达之病根)。我所认为的四十年中国散文仍有滞后和衰腐气,不是指跟进时代进展的表象不够,而是指没有追踪和捕捉到这个时代所带来的本质变化。我们仍在以疏离之笔妄想表达时代罢了。就我们的文学创作来谈,其真正的疑虑恰在这里。
我的散文观
散文可以有千萬种变化,所谓“文无定法”,但对我来说,散文之万变而不离其宗。我的散文之宗,即类于一切文章之宗。散文在我这里,可以涵盖写作的全部蕴意,但它并非一种被泛文章化了的无门槛的文学体裁,相反,它最应该获得“一种追求本质性修辞的高级文法”。何谓本质性修辞?我指的是去掉了一切饰物,可以自在言说的、近于无修辞的本真状态。没有多余的话,一切都是不言自明的。凡有言,皆是必然之言,凡不言,皆因其俗赘无益言。哗众取宠和简单流行是没有用的。因一切本质之外,皆非本质,因一切本质之内,皆为本质。所以本质性修辞即是一种语言所在的澄澈之姿,它是修辞的“闪闪发亮”。散文秉持一种沉思的慈悲,它是关乎一切存在之书。一种沉思的修辞之书!
建造一座大厦或许是不够的,更深的建造或许是一座城堡,一个国度,一颗星球,甚至是整个宇宙。(《文学的基本故乡》)
两类写作
或有两类写作:一类是无限清空的、回退式的、指向世界之原始和纯净之本相的,空虚的、无物的、看不见的、幻想式的、多余的、不可能的;一类是纷繁的、喧哗的、貌似无限增值的,烟火气十足的、叙述的、对话的,预计到各种可能性的、密实的,甚至是表演式的、故事化的、适应性强的。但是,这两类写作各自的精微之处,我们几乎很难同时掌握。长期以来,我觉得技由心出,只要有刻苦的自我训练,几乎可以攻无不克,可是目下却觉得这几乎是荒谬的。我们积其一生,能够取其一端,深入其中,获得自己独属的特色就属万幸了,若要兼备,几乎像要同时占据自己的正反两面一般,几乎像要同时获得自己形象的实体和在地面上的投影(将其“实在化”)一般。这类贪婪大体是无意义的。但是,一想到作为人的孤立和形式上的局限,我就有一种念天地之悠悠的怅然之感。
“苦难对我们的教育”
如果是在和平年代,没有生离死别的缠绕,我们的心灵所思,却为何总指向那复杂深沉的激烈、无穷的躁动……通俗地讲,一些心灵的自我设问、自我挣扎、自我安抚、自我设限,会时时触碰到它的边疆……
的确,我总试图以一种尽可能逼近真实的讲述来复原那些理解力的纠缠。我确信我已经做到了一部分。但是很不完整。我确信我一直在这样做。以十年的长度,或可以呈现一个漫长的样本,百万字的篇幅(《主观书》)。涉及文学的追溯、心理层面的蒙昧、一种力求抵达和自我开释的企图……
各种忘我之思,总在反复。未必会有答案。
世间万物,神秘地死生。这个大的、令我们时或沉闷、时或昂扬热情的循环,如何能够演绎得那么清晰?
可以以言语穷尽的(看似穷尽的),也本来只是一些浅层面的设问,它们不是根本性的、挑战思维极限的。因为心灵的驰骋不会停滞,所以,无妨因循一定之规,无妨以完成之局来粗暴地界定任何事物。
世界和时间都是开放的。
但心灵之墙会抑制我们的意志。其实何必如此?怎能如此?
所谓,“我们对自我的没有间隙的捕捉,即便疲惫却仍然亢奋的心灵”,都是情感之外的东西在泛起涟漪,无关对错和爱恨。只是,它们在牵引着我们,构成一种平静之下的心灵战争。
那些爆破的部分,方是创造力的起点。
我在疲惫之中的反思意味着心灵的不平静。或许是自设的苦难,但它们已经极其微小,所以,只能是自我理解力的延伸。是自恋和自尊的过度引述在起作用。在细微到极致的探考中,也很难做到求同存异。
但是,心灵的幅度,又的确需要自然打开。需要用力打开。需要不设防地打开。只有自我保护的企图,无异会形成牢笼般的束缚。
我捕捉这些材料,回思我的不宁静的源头。写下我对于存在之思。这种描摹是自然而然的,我没有经济的谋划,克服对于时间流逝的恐惧,努力地接纳我所能接纳的一切事物。
我努力放纵自己的敏感和努力地抑制自己,形成一种日日递进的思考力的反弹。我们的确有不同程度的心灵的灾难,这本来无可掩饰,否则我们不会献身于艺术。
我不大认可离开这种探考之后,还有更大的文学主题。家国之思未必大过心灵的宇宙,汪洋般的风浪。所以,贴近思之本质,不必作伪的书写,才最让我倾心。
如果妄图掩饰,可以选择他途。因为我们人生之难局的伸发,会在不断的自我心灵的砥砺中进行强化,它使我们对自我的认定变得更加多义或混乱。弄不好,这可能是灾难性的。
文学,既腾空和释放,又重新界定了我们的灵魂。它是我们迷幻心灵的容器。
它自身也是致幻的、感官的、穷究的、苦难的、辉煌的。
我有时又不大相信“世俗”可以引导文学,也不一定迷信于生活和多数人的结论。但这所有的种种,都形成自我搏斗的一部分。
没有任何救赎。文学真正的蕴含,是与生存同构的。是沧桑的、永恒的、灵异的、坚持的、本色的、渲染的、离别的、伤痛的。
所以,这是一个反思力的现场。苦难和对话都是它的材料。没有结局。
沒有事件。
没有任何具体的时间。
它穿透一切,可达于人类之存在的思维的尽头。
所以,我为了我们整体而写作。这没什么大错。
一切原本如此。平静而缄默,只是喧嚣的内核和思之本质。
雌雄同体
伍尔夫说过,优秀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确然如此。伟大的灵魂,综合了岩石般的坚硬峻峭和柔若细水的性情,这几乎是一个完整的“人”的复现。只是,这一种灵魂的伟大,也有它微妙的局限。它似乎多半会将“伟大”的属性集中于它所致力的那个领域,譬如伟大的文学区域,伟大的艺术、政治、经济区域———我几乎很难想象这种雌雄同体的伟大会同时作用于一个人所能触及的全部时空。“雌雄同体”是一个人的物我共存、正反相合?还是无私无我的知觉?在我所喜欢的葡萄牙作家佩索阿的情书中,我发现了这样的句子:“我喜欢你的信,它们异常甜美,我喜欢你,因为你也很甜美……”(佩索阿情书,选自《坐在你身边看云》,程一身译)这样的句子至少表现了写作者凝神的伟大。它是不是雌雄同体的?一个伟大艺术家的柔情蜜意,收敛了他岩石般的坚硬和对人生的刻苦,而以一种阴柔的力来呈现他沦陷在爱情中的思念之美。但他思念的终结却不是这种相思之力的协调和抵达,而是根本上的拒绝。与我们世俗的想象相反,许多伟大的哲学家、艺术家都是独身一人以终老的。他赋予整个人类一种浓烈的爱与思念,他爱卑苦而值得悲悯的人类全体,但他遗恨无存,残余不剩。他的“雌雄同体”印证于人被“分裂”之后自我追索的结果。他的两个自我(双面)互为滋补,方可形同一人。而万物存在于世却不如此,一“人”也并非完整和十全十美的自足。我们之所以将“雌雄同体”而能互为补益的灵魂视作伟大的灵魂,也正是因为在世间,阴阳混融之于层次荆棘之中更有一种自我保全之效。
文学与时间
文学为何物?
它是否必须在相对固定的时空中存在?
它是否可以超越时间性?
写作这么多年来,我经常思考的问题常常围绕以上几个要点而展开,但漫长的写作实践和思考实践都不可能带来永恒的答案,随着写作和思索的加深,迷惑也随之越来越深。按照常规理解,在文学所处理的几个重要命题中,时间显然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母题。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博尔赫斯的大量写作都在处理时间问题。围绕“时间”这个母题,产生出对人之为人的有限性的大量恐惧和悬疑,产生出爱情和情感的迷失,产生出对宇宙(自我内在宇宙与洪荒的穹苍)的源流的种种思考和探索,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没有一个永恒的句子,可以一劳永逸地涵盖所有。像“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诸如此类的叹息真是所在多有。但我们能够说,后来者的追忆和书写就是对前人情境的一种模拟、重复吗?
我并不这样认为。尽管,在某种层面上,我们的感觉确实与先人的体悟有众多的交叉。但是,时空的加速变幻、个体处境的不断异化,都渐渐地催生出一些更为隐秘和幽微的新的精神体验。这种体验未必是古人的笔墨可以穷尽的。尽管,同样处在时间中,但毕竟已经是新的维度、新的段落、新的场域。能够激发文学创作的具体元素在发生变化,则表达路径自然会有相应的更新。顺着这个思路下去,则不同的时代显然会产生不同的文学。那么,这个答案就是问题的终结吗?
我也并不这样认为。或许可以这么表述,从形式层面来看,不同的时代会产生出不同形式(深度)的文学,这种不同会更多地体现在使用语言的层面(语境的特殊性)。但是,我的更多的疑惑却在于,在这种不同之中,是否就蕴涵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学母题?如果母题有变更与开拓,上述结论就是成立的。而事实究竟如何?在我们这一新的波次人类文明的演进中,是否已经出现了文学母语的更迭?
现在,我想陈述的是,在一个被大幅度拉伸所形成的理解时空中,我们如何来再度回归时间和空间的精微,如何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势之下来形成我们的“精神性的文学”。我将这种不断地走向自我辩诘和形而上思考的时刻称之为“日常性的超逸”。我将这种运思的体悟称之为“灵魂的经典时刻”。
激情“缓缓降临的历程”
我们应该捕捉每一种思维中的精妙时刻,那些充满了自我审视和灵魂扩张力的时刻,应该将这样的时刻赋予创世的属性,充分爆破它的各种维度上的能量,让它的神秘性企图变成自我感受力的极大蕴藏———的确,复制这样的时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多重唯一的复合(唯一的爱与激情、唯一的生死性的欲念、唯一懵懂中的难以捕捉的欲望的涨溢感)。应该将这种承纳和阅读的感受记录下来,以抵消我们注视着时光流逝自我衰败而一事无成的疾苦,以抵消我们灵魂的逐渐残缺(狂妄、悖逆、嫉妒、负恩、自私、刻薄、嗜杀),以抵消我们庸庸碌碌地度过时光(平淡而荒芜生活的事实)的悔恨。所有这些主观的雷同就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经历的“日常生活”。
在我们漫长的阅读记忆中,经典著作无疑都繁缛、负重,它们是多重复合的奥义书。面对这样的著作,我们的品尝事物的味蕾(触须)自当全方位地打开:在每一个昼夜中,选择思绪最为澄明的时刻去面对它;应该最充分地理解阅读的难度,强烈地压缩和释放自己的好奇心、归属之心,勇敢地面对它;在无法做到完整把握的前提下,不要苛求、追逐阅读的完整性,要诚恳地面对自身阅读的局限,预留出极可能诞生的阅读的空虚和荒诞感。
缓缓地体恤日常生活的简单、卑微的灵魂,从它的远离经典时刻的冗长的流淌中挖掘出诗来,庶几可以成为恢复和建立我们生命之尊严的唯一的使命?经典著作融汇的是我们共同的人类经验,它即便采用极端的形式也不可掩盖其穿越时光、衔接古今的深层动机。在这样的人类性著作面前,我们为什么会有远远超越面对一颗简单、自视灵魂的阅读感受,大概正与这种高浓缩有关。阅读的空虚也恰恰建立在这里,因为我们面对的仿佛不是人力可及的创作,而是真正的造物本身:世界的概括就是如此,它的万语千言也不过就是对宇宙叹息的一种模拟。
时光是氤氲常在的,但我们的感觉却一直在流逝。我们几乎很难铭刻和重塑生命中的每一种激情“缓缓降临的历程”,所以每一个个体的创作经验都可能成为对他者之自我见证的有力补充。这或许可以解释我们常常如臨其境的“似曾相识”,我们的的确确,既是唯一地亲历了生命,又的的确确,曾在他人的经验中活过。这样的沟通起点完善了我们身处宇宙中的孤寂之感,而经典艺术的成就又突出地强调了它在一种庄重而透明的阅读容器中的强烈闪光。
灵魂的经典时刻,不是对庸常岁月的拒斥。日常经验的洪流既蔚然成阵,不可阻挡,则我们所有的用力(书写和阅读)都不是反向的对抗而是一种向着事物核心的凝视和掘进。蕴意丰富的经典性著作对我们的阅读经验确实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我们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里便真正地进入经典著作“不可摹写的命运构造”,在这个意义上,阅读和写作几乎都同样艰难。所以,缓缓地降临(始终有丢弃和残缺)几乎是一个必要的程式,我们由此成为灵感工程的匠人而不仅仅是一个神秘、短暂的享受者。
我们?
综合上述,则如果我们心怀理想,自我的恐惧和压迫便是势所必然的。一方面,我们是唯一的生命个体,我们立足于这个世界(这一类时间:此刻)的所有体验都不可能被他人所完全取代,由此,似乎每个人都有成为一个创造者的必要性和自足;另一方面,世象开始向更加多元化转化,我们能够目光如炬地穿透和把握时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或者说,当下的我们必须身兼更多的自我教化方才可以更称职地去从事这种灵魂的转化工作。这种自我砥砺的潜在指向,便是我们无日不在其中的巨大现实:时空“已然不是那个时空”,人类的精神成长在不断地衍变,那我们还能够在旧日的窠臼之中生存和筑巢吗?
关于我们的文学使命的探讨便需建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我们都从时代和自身之中加速整合和分裂,那些旧有的文学形式已经散发出难掩的“陈腐”之气。旧日形势之所以如此,与时代的缓慢进展,人心(道德)的从古(依赖性)极度相关。但是今天,我们的文学却已然无法仅仅依靠稳妥地聚焦、凝目就可以完成。那些纷繁的事物更趋于破碎和无穷的表象,与之对应,我们灵魂的聚散也更加令人迷失(瞩目)。我们该如何识得(进入和建立)“灵魂的经典时刻”?
“文学的基本故乡”
回归到前文所及的几个问题上来:
文學是为人学吗?是为时间之学?是为宇宙学?物理学?精神学?宗教(上帝的语言)和哲学?
文学必须对应于时代而存在吗?
文学是否可以超越时间?
文学必然要落地吗?(以“人”之存在和行为推演为其中介?以具体的时代为其面罩“包裹躯体的污垢与清洁”?)
文学的基本故乡何在?
我仍然不知道答案。但我想,文学显然不是简单的历史学、地理学。文学显然不止于传奇、故事和演义。文学也不能够仅仅停留于别的领域即可触及的高度。换句话说,我所认为的文学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存在之思”(语言的存在之思)。是与寰宇星空共进退的人类之思。
如果一切仍没有答案,但今天的探讨,我想它至少呼吁我们建立一种更高的文学。在一个被扩大化的“世界”(大时间)的语境下来回味、体验我们的主观之思与客观外物呈现世界的差异性。在一个大的时空背景之下,我们的文学源头就可以变得更为宏阔一些。一些在我们既往的文学生态中比较鲜见的存在样式是否也可以被我们更进一步地学习、借鉴和包容?
佩索阿曾经比较过站在不同的精神台阶上的两类人:“高级人与低级人之间的区别,高级人与低级人之间某种动物性兄弟的区别,具有讽刺的单纯品质。这种讽刺首先表明,意识已有所自觉,而且通过了两个台阶:苏格拉底说‘我仅仅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他这样说的时候便抵达了第一个台阶,桑切斯(16至17世纪葡萄牙哲学家)说‘我甚至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他这样说的时候,已抵达了第二个台阶。我们在第一个台阶武断地怀疑自己,这是每一个高级人将要抵达的一点。我们在第二个台阶既怀疑自己也怀疑自己的怀疑,简单地说,到了这一点,作为人类的我们,在一段还漫长得很的时间曲线里,算是已经看见了太阳东升,看见了崎岖地表那一端长夜的倾落———这是一个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抵达的台阶。”(《更大的差别》,选自《惶然录》,韩少功译)
至此,我觉得我的所有的言说已经基本完结。文学的领土仅仅是一部万象之书吗?不,在根本性的“润物细无声”的沉浸之思中,文学的最高领土应该是一部忘却之书。真正的文学应该建立在我们所看不到的另外一个宇宙(观察的升腾)的开启和泯灭之处:是自然而然的文学!不是对自我,而是对存在本体的忘却和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