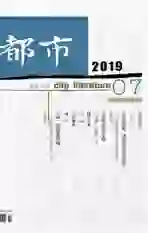在雨中注视铁塔
2019-09-10阎扶
阎扶
采地衣
你们坐在里面打牌。你们四个,可我只记得你一个。刚才你在坐南朝北的大楼上,转眼到了这里,一面坐东朝西的小二楼上。你们在二楼上,楼下的铜腥味儿,没有传到二楼上来。
我从阴暗的过道出来,站在楼梯口。楼梯口好像一个小阳台,水泥地面。
这个小二楼,像是大楼的耳房。
不是那个小二楼,那个小二楼与此相似。曾有一年时间,每天我都上下设于楼外的旋转楼梯。也是水泥做的,栏杆油漆剥落,下雨时发出铁锈味儿。在那二楼楼梯口,也形成一个小阳台。一株高高白楊紧挨阳台,像一只猫依偎着主人。
那年秋天,树叶每天从树上落下,老让我想起摇落一词。
就在我低头时,忽然发现水泥地面上,几个灰色的、薄薄的、柔软的地衣。
为什么水泥地面上,长出地衣?我弯下腰,采它们。在我手心里,它们像一个个小耳朵,迎风招展,越来越大。
小二楼前,种着一排密不透风的塔松。塔松高大,没白杨高,但比它粗。塔松下面虽有阴影,但是水泥铺就。就是长地衣,也应当长在树下,不该长在与树半腰平齐的阳台上。那时我不记得有这排塔松,仿佛为了视线开阔,它们消失了。
我看到在阳台下面、前面,一直朝向西边的广场北边,水泥地上,缀满这些来自乡野的真菌藻类复合体。它们不是暗黑色,而是灰色,就像从水泥地下钻出来,带上了一层水泥灰,或者,为了不让人发现,故意成为灰色,在水泥地面上若隐若现。它们不像星星一闪一闪。
但我还是发现它们了。没有人发现它们,它们仿佛为我生长。现在我想,也许是车间飘散出的铜灰落在上面,把它们染灰了。这些铜灰,让我们拼命地咳嗽、吐痰,还有一些人眼膜结上一层阴翳。
我甚至忘记你的笑声了,你咯咯不停的笑声。那时,你的手指抽出一张牌来,压在乱七八糟一堆牌上,牌越来越厚。我下了楼,去采地衣。
那些灰色地衣,像是水泥地面长出了许多耳朵,像是水泥地面下,住着许多人,那一刻,他们不安于地下黑暗、宁静、寂寞了,商量好似的,偷偷钻出地表。它们兴高采烈,却又小心翼翼,甚至胆战心惊。
但还是被我发现了,被我一个人发现了。当我踏进它们中间,它们一定有些后悔,可是来不及钻回地下了。他们在二楼上打牌,吵闹的声音传到这里,它们还以为他们被某件欢乐的事情吸引住了,却不料他们中的一个,我,突然来到了它们中间,猝不及防。
以前,星星点点的小白花迷人眼,不曾想到它们也会。
就像面对一本杂志,不知该从哪儿看起。这么多的一长溜地衣,大大小小,缀满水泥地面,也让我无从开始。脸发红,心突突跳,眼睛有些花,有些潮湿。每当好事突然降临,我总是这样。
我把它们一个一个采出,就像拾起地上一枚一枚分币,有些失了秩序。我的手心肯定放不下它们,我也没带包,那刻都把它们放到哪里去了?我不停地采啊采,怀着巨大的秘密巨大的惊喜。也许我的双脚还踩烂一些,它们那么柔软。有的连根而起,有的,像小时候在乡下时听的,撅根了。
在这奇异的、梦境一般的图景中,我忘记了你,忘记了他们。
放生麻雀
一大一小两只麻雀,不知怎的撞进屋子。它们惊慌地飞,乱了方寸。不时撞上玻璃,掉到地下,一冲而起,碰到屋顶。划着大而碎的圈子,时高时低,试图逃离误入的牢笼。
逮住它们,缩小它们活动范围。我把它们赶进里间,关门。门在背后砰地一声,吓了一跳,它们更惊慌了。
还有足够力气,我要做的,就是消耗它们力气。不停地追赶,不让它们休息。不让它们喘息,落在任何一个点上不动。要让它们时刻飞翔,一直处在空中,休想停下来,整理一下翅膀,让羽毛偃息,梳理羽毛,让两只红色小脚分开,抓紧附着物,或者地上。
它们多么惊慌,不停地划过我的头顶,有时就从我的肩膀上擦过。有时,我的手离它们只一寸远,要是迅捷,定能一把抓住。但它们还是飞了,瞬间飞过我的耳朵,一片小白毛飘过眼帘。
两间房子在半坡上,坐北朝南,阳光充裕。两只麻雀,不知怎的从阳光里,窜入阴凉的屋里来了。它们不是燕子,黑色燕子被我们允许,到房梁上筑巢、育雏,把黑白分明的屎拉到灶台上面。它们是麻雀。它们在屋檐下做窝,都要小心翼翼。但是现在,居然闯进屋里来了。
不用找长竹竿扑打它们,不用,这么小的空间,一会儿它们就会累了,落在地上。
它们休想逃脱,它们已是囊中之物,只争来早与来迟。多玩耍一会儿,也能多高兴一会儿。
不知什么时候,那只小的,停在了大的背上。大的带着小的,在屋子里回旋,速度显然放缓下来。放缓下来,我才以现,一大一小两只麻雀,相连一起飞翔。它们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节省体力,还是出于怜爱?大的作为母亲,把小的背在背上,好让孩子喘口气,休息一会儿。
奇异的一幕,把我看呆了。两只鸟儿正好利用时机,缓缓地、疲倦地、一下一下地围着我飞。
奇异的一幕,让我想起那只绿锈斑斓的鸟尊,大的背上,停着一只小的,大鸟转过头去,顶羽仿佛梳了一个高髻,显得利索而又俊美,小鸟高昂起头,朝着它的母亲,眼里透出无限可怜。
我已忘记追赶它们,这一大一小两只麻雀。它们这一动作,让我真想喊来别人,一起欣赏。但我不能开门,它们会趁机逃走。
我只能屏住呼吸,万分迷惑地盯住它们。盯住它们不放,发现背上小麻雀,正在一点一点缩小、缩小,越缩越小。为了减轻母亲负担,小麻雀正在缩小。在越来越慢的飞行中,我看到大的不变,小的越来越小。我已停止追逐它们,我也累了。但是大的背着小的,还在不停地飞。
小麻雀越缩越小,直到消失不见。忽然看到大麻雀嘴里,衔着一粒小虫,直直的,无限透明,仿佛一节小树枝。莫非是小麻雀变成,一定。大麻雀想要把自己孩子衔在嘴里,好轻易地逃走。
仿佛一节小树枝,无限透明。
正在盯住之际,大麻雀脖子忽然一缩,那节小树枝,那粒小虫,进了它的肚子。只是一下,一下就不见了。它不可能把它放在肚子里带走,这样做,也许只是为了不使孩子落入人手,不忍看它遭受即将到来的折磨。
它们到了我的手中,一大一小,小的在大的肚子里。小的在大的肚子里,大的因此显得沉重。为那感人一幕,我决定放生。打開里间的门,打开外间的门,向着阳光,松开了手。但那只大麻雀,却突然掉到地上,不知由于疲倦,还是绝望。
在雨中注视铁塔
注视铁塔,它高高在上,耸入云端,它的尖细之顶有红色小旗在飘,它在麦田里,麦子在雨中更加青翠。
我们站在一间小屋檐下,我们被雨挡住。
像所有野外小屋一样,小屋简简单单,仿佛一个村里人。小屋用土坯垒成,泥巴糊得光洁。金黄麦秸,有时从泥中蹦了出来。小屋也有柱子、横梁与椽子,都不很直,也不很粗,毛里毛糙,都不成材。小屋总是非常神奇,搭建它们的,都是一些格格不入的村里人。
注视铁塔,它有美丽的几何图案交错,它有工业文明的强大、凛然不可侵犯之势,它从麦田里拔地而起。
我们站在小屋檐下。我从来不认识你,但我们就认识了。你比我大,你是那位同学的姐姐。他有一位哥哥,也有一位姐姐。你的个子,就在弟弟与哥哥中间,不高也不低。你留着齐耳短发,乌黑发亮,那种短发使你看起来,有股假小子的味道。你的眼睛很大,眼白很多。
你们的家就在村子当中,就在村中大路边上。
我记起你的弟弟,他总是与一辆二八自行车相伴,这使他在以后人生道路上,显得有些孤独,不善与人打交道。听说他现在住在县城里,住在火车站对面不远,住在铁路家属院里。
我记起你的哥哥,他个子高大,上唇总是留着短短黑髭。他进入渴望的另一种生活里,他有些自豪,也有些不自在。他的声音洪亮。他也曾在麦田里搭起过一间小屋,不过不在这里。
我喜欢看雨,尤其喜欢看大雨下在青翠麦子上。那是一幅壮观景象,仿佛古老的天地仪式,仿佛为了麦子成熟,进行的一次劈头盖脸的打击,仿佛为麦子进行的割礼,之后它就无人管束,开始更加艰辛、更加庄重地成长。是啊,青翠麦子已不再属于月光、微风与萤火了。
雨越下越大,看得我心花怒放。
当铁塔倒在我们眼前,我们才发现,差一点儿砸着我们。没有“嗵”地一声,也没有“噗哧”一下。它是突然倒在地上的,不是渐渐地、缓缓地倾斜,最后忽地一下倒在地上的。
你的弟弟、哥哥,两个人从铁塔上走了下来。他们原来呆在铁塔尖顶,承受了这么长时间风吹雨打。他们没有一丁点儿伤,虽然铁塔是一下子倒地,不是渐渐地、缓缓地倒下来的。弟弟笑嘻嘻的,脸色有些苍白,他肯定吓了一跳。哥哥那么凛然,仿佛为了在小的面前摆出一副老大姿态,努力压下了心中惊惧。
我们应当走过去,他们走了过来。
走吧,咱们一起吃饭去,哥哥说。
我们四个人,朝西南方向走去。
越过公路,对面就有饭店。这一家子男性,是纯粹物质主义者,他们知道怎样更好地填饱肚子。他们父亲,我还记得眼中,总是露出既自卑、又鄙夷的神色。我还记得在红花落地的街市中间,他经营的那个小食货摊子,摊子上那盏呼呼生风的马灯照亮顾客的脸,也照亮他算计的脸。
你与他们不一样,你的行止、你的眼神,更重要的,你是一位女性。
你是为了缓和这一家人而生的,你是大树之间的一枝牡丹,你降临他们———弟弟与哥哥———之间,肯定带有一种校正作用。那会儿我忘记了,你是走在之前、之后,还是之中。我只记得雨过天晴,彩虹隐约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