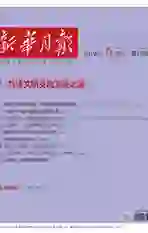“革命者应该是有情意的人”
2019-09-10石岩
石岩
周秉德家客厅醒目的位置,挂着著名的《沉思中的周恩来》。1980年代,这张照片的发行量就超过了9000万张。周恩来生前并没有看到它,照片由意大利摄影记者焦尔乔·洛迪拍摄,在意大利公开发表,并由使馆工作人员带回中国。
1949年,12岁的周秉德进入中南海,跟伯伯周恩來、伯母(注:亦称呼为“七妈”)邓颖超生活,直到1964年结婚离开。她此后也是伯伯家的常客。从少女时代起,细心、温和、开朗的姑娘就是伯父伯母和父母之间的桥梁。1957年,秉德写信给父亲,讲起和伯伯度过的有趣的周末:
星期天,我和维世姐姐(注:周恩来养女孙维世)都来看他了。他谈到在重庆时,与老朋友去吃饭馆。到一家小饭馆,楼上只有三桌,正好闲一桌。他们占用了。别桌人们都去看他,与他握手,他说:我和他们都握手了,都满足了,我又告诉他们请他们不要下去嚷,惹得很多人来,结果他们也都不嚷出去。我们说:你在北京就不行了,人这么多!他一听,立刻说:为什么不行?今天我就可以请你们到外边去吃午饭。
那天中午,周恩来先带着孙维世和周秉德去东单的“康乐”,满座。周恩来想起东华门的“萃华楼”,1946年“三人小组”谈判(指1946年周恩来代表中共、张治中代表国民党、马歇尔代表美国组成的三人小组,对停止军事冲突进行的谈判)时,他与马歇尔等人在那里吃过饭。萃华楼有座,五个人要了米饭、馒头、五菜一汤,花了十元二角。回程路上,周恩来兴致不减:“陪你们玩了三个钟头!”
与伯伯、伯母谈话后,周秉德都会把重要内容追记下来,重要家庭会议则在现场记录。周恩来去世次年,中共党史专家胡华对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注:字同宇,周秉德的父亲)的一份采访记录,邓颖超赠给周秉德母亲王士琴的照片,妯娌间的便条,都被细心保留。凡此种种,让周秉德新书《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充满大历史中看不到的细节:

1964年,周恩来夫妇连续两个周末召集周家在京三代十几口人,开家庭会议。邓颖超做开场白:我们这个家有各种关系——父子、母女、婆媳、兄弟姐妹,还有党团员,党团员与非党团员的关系,大家都是新中国的主人,应该建立起平等、民主、和睦、团结的关系。兄弟之间、父子之间的认识,会有矛盾,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邓颖超讲完就到了午饭时间,妇女、孩子们跟她一起到厨房端菜端饭,不到半小时吃完,大家又在客厅坐定。周恩来双臂抱在胸前,一边踱步一边历数家史:周家的“封建根子”在绍兴,祖父中过前清功名,父辈都拜过绍兴师爷,父亲老七老实,不会扒钱,家里就破落了,以至于母亲过世后无法满足外祖母家厚殓的要求,棺椁厝在庙里几十年。
周恩来九岁时,生母和嗣母相继过世。10岁到12岁,他当家两年:借钱、典当、应付讨债的人,按照大家庭的规矩迎来送往,从小深深感受世态炎凉。他12岁被伯父接出去读书,先在东北,后到天津,“五四”时对家庭有了认识,知道旧家庭没法奋斗出来,但对父辈充满同情。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由中宣部出版局、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中央电视台发布的“2018中国好书”评选榜单揭晓,《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入选。记者对周秉德进行了采访。
“他要有时间看书就好了!”
记者:你12岁就跟伯父伯母生活在一起。这种安排是因为家族上一辈就有兄弟间代为抚养子女的传统,还是伯父伯母为支持你的母亲出去工作,想为她减轻负担?
周秉德:我父亲原来在天津做党的外围工作,以贸易客栈为掩护,给解放区提供棉制品、医疗器械、药品等。1949年4月我父母从天津到北京,伯伯夜里12点多才能回到香山的家里,跟我父母聊聊家常。那时他向我父亲交待:你应该有个正式工作,但不应该由我来安排。伯伯让他去上华北大学,9月份毕业,分配了工作。伯父找到他的领导:周同宇的工作职位要低,待遇要少,因为他是我的亲弟弟。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裙带关系,更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他也不让我父亲用周恩寿这个本名,让他用字。
爸爸职位低,房子就小了,两间西晒的厢房加起来二十多平方米,不通风。我小弟弟出生后,头上痱子满满的。我那时已经上初中了,不太用妈妈操心,伯伯让我住到他家,纯粹因为父母家住不开。
记者:一开始你住在书房,据你观察他爱看什么书?
周秉德:他要有时间看书就好了!有一回伯伯说他在发奋读《家》,已经读了36页。我们听了都笑他。我到北京时,伯伯与国民党的谈判刚刚结束(注:指1949年4月的北平和平谈判),要参与指挥解放战争,同时还得筹备政协召开……1949年11月7日伯伯搬到西花厅,属于政务院范围,之后弟弟妹妹也来了。平时我们上学,周末和寒暑假都回到西花厅的家里。
记者:西花厅的周末是怎样的?
周秉德:伯伯没有周末,只是加了我们几个孩子。有时候暑假我们在家,他快回来,七妈就打发我们到二道门等。他下车看到我们,就知道是七妈的意图——让我们陪他走几百米,放松一下。这时候他会跟我们聊几句学校的事,有时候唱唱歌。我们长大之后,话题之一是动员晚婚少育:咱们国家虽然地大物博,但资源有限,为了子孙后代,要求女孩子25岁以后,男孩子30岁以后结婚。我们没有一人违背他的意愿。
记者:杨尚昆在日记里写过,农历二月十三是你伯父的生日,但“他不愿让多人知道,故无人去庆贺”。
周秉德:对,生日从来不过。不过(伯父过世后)伯母每年2月初会把我或我和先生找去聊天,吃个点心。其实那是她的生日,我们也不说破。我记得唯一一次过生日是1988年,她84岁,把我们兄弟姐妹都找去了。我们一人出5块钱,给她买了个蛋糕。那时她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一吃东西就呛,所以没能和我们一块吃。我们在厨房,她在房间里,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吃面,然后切开蛋糕合影。
记者:周总理以儒雅、潇洒著称,他在家会不会指点你们穿衣和行为举止的风度?
周秉德:基本没有,他主要就是讲节约。他的儒雅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南开中学的“容止格言”也起到很大作用。他一生都整齐得很,里面缝缝补补,但外面一定整洁、笔挺。
“叫我‘亲妈’当然好了,可是你自己的媽妈会怎么想呢”
记者:书里有一张照片,伯母带你去机场送伯伯,一般什么场合她会带你去机场?
周秉德:极少极少。那次是伯伯出访亚非十四国,正好是个礼拜天,她就带着我和一些工作人员送行。印象中,带我上机场就那一次,然后又带我们去陶然亭凭吊高君宇和石评梅的墓。他们对高君宇和石评梅的感情很深,多次带我去陶然亭。1965年,北京做城市规划,伯伯特意强调要保留高、石之墓。他说,爱情和革命不矛盾。
记者:你的伯母有特别随和的一面,书里摘录她留给你母亲的字条,非常家常。
周秉德:那完全是家里人对家里人。我存了两张伯父和伯母的结婚照,一张在广州,一张在汕头,都是当年七妈送给我妈妈的,还在相片背面竖写着年月日、摄于哪里。我们家在那个西晒的小厢房里住了四五年,伯伯的秘书看不下去了,帮着联系。我们搬进广宁伯街附近机织卫胡同的一个小院里,院里还住着另外两家人。
机织卫那个家就大一点了,一道隔扇隔成两间。一间我父母住,还有一块相当于客厅的地方,两三个人来可以待一待,我父亲在那有个书桌。另一间我弟弟妹妹住。有时候伯母中午到我们这来,正赶上我父亲在睡觉,她就在书桌上留个条:
今天来看你们,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觉的睡觉,我参观了院子回去了……
这样的字条我妈妈都珍藏着。有时伯母来送东西,一点水果、两条咸鱼,她知道我妈妈爱看歌舞,芭蕾舞票也送来。有时候他们不穿的衣服,拿给我们改一改,或者有个席子不大用了,也拿给我们。有一回是周末,我要回家看妈妈。西花厅又小又香的白兰花开了,伯母用白线把花串起来,串三支,别在自己的衣扣上,再串一串,用叶子包起来,让我给妈妈。
记者:书里写有一年西花厅的海棠开了,伯母带你们赏花,怀里抱着一个精致的洋娃娃。
周秉德:七妈曾经对我说,1927年她难产,儿子未能成活,赶上“四一二”白色恐怖,中央决定让她从广州赶往上海。她一路劳碌奔波,产后没有休息,医生诊断她不能再生产了。新中国成立后一些老同志跟农村的夫人离婚,再找大学生、文工团员。七妈也跟伯伯说过:我生不了孩子了,你还是再找一个。伯伯说:你胡说八道什么?他们的感情非常深厚。伯母是1904年的人,进城时才四十多岁,很希望有小孩。她不光有个漂亮的布娃娃经常抱着,还有一个小小的木制玩具,国外带来的,一上弦几个小娃娃就转,还有音乐,她经常打开来听。
记者:看得出来,她挺渴望做母亲的。这种情况下,你有一次叫她“亲妈”,她说你叫“亲妈”当然好,可是你的母亲会怎么想,挺难得的。
周秉德:可不止叫了一次。我第一次见她是1949年的8月28日,宋庆龄到北京,她陪着来的。汽车一辆辆开走,伯母就看到我了:这是秉德吗?我说:对呀,大妈你好。我按照天津的习惯,第一次看到伯伯叫“大爷”,看见七妈叫“大妈”,他们都给我纠正了。伯母说就叫她“七妈”吧,可能觉得“大妈”有点大众化,张大妈李大妈都可以叫“大妈”,“七妈”就不一样了。我给听成“亲妈”了,后来就那么叫,弟弟妹妹也跟着叫。她起初没在意,直到有一次我给她写信,抬头是“亲妈”。她回信说:你叫我“亲妈”当然好了,可是你自己的妈妈会怎么想呢?让你叫我“七妈”,是因为你伯伯排行排七。
记者:那你伯母为什么抱怨伯伯大男子主义?
周秉德:有一次是何香凝过生日,伯伯交代秘书:给何老送一个花篮,以我的名义。七妈听见就问:怎么就以你一个人的名义?我还做过她的秘书呢。伯伯赶紧说:对对对,有大姐,一块儿。七妈还跟我说过,她一辈子不管钱,伯伯更是不管。有时候伯伯问秘书:我现在有多少钱?伯母听见就很生气:他连“我们”都不说,只说“我”,大男子主义!在那之后,她曾经交代秘书,她和伯伯分开记账,到月底伯伯只剩两毛六分钱。这个做法只短暂地实行过。
“这是他一辈子的遗憾”
记者:你的伯父伯母爱你们,但从没想过把哪个孩子据为己有。
周秉德:我们有一个六爷爷。建国后,伯伯和我父亲只有两位长辈还在,一个是他们的亲婶母——八奶奶,再一个就是他们的堂叔,我们叫六爷爷。他们都曾被伯伯接到北京。六爷爷是亲属中唯一一个建国之后由伯父批准任职的,当过中央文史馆馆员。
六爷爷是绍兴师爷出身,中过举人,还给袁世凯当过秘书。我当时特别不理解,袁世凯不是坏人吗?伯伯说,六爷爷给袁世凯做秘书时共产党还没诞生,而且大节不亏,袁世凯一宣布称帝就辞职回了老家。六爷爷来西花厅,伯伯和伯母亲自到大门迎接。伯伯经常向他请教晚清和民国的政府建制,听得特别认真。其实让秘书查查很容易,伯伯想让六爷爷感到自己在新中国是有用的。
记者:你在书里写,六爷爷过八十大寿,周总理下厨做了两道淮扬菜。《周恩来传》里也提到过,1918年,南开学校校董严修去北美考察教育路过东京,他当时在日本求学,每天都去看严修,还亲手烧菜。
周秉德:我知道他的狮子头做得很不错,有时还给厨师挑毛病:你这个狮子头不对头,少了马蹄。可他自己对吃又一点也不讲究,跟农民一起吃饭特别自在。一碗黑色的高粱米,一小口菜,吃得兴致勃勃。没有隔着老远,围着多少护卫。
记者:你提到伯父想写一篇叫《房》的小说,他说过具体想写什么吗?
周秉德:那可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曾祖父是一个县官,很清廉,没有置办土地。他一去世就没有俸禄了,也没有地租收入。祖父那一辈有兄弟四人,家族大排行分别行四、七、八和十一。伯父的十一叔刚结婚就去世了,所以他一岁就过继给十一婶。他九岁时,半年之内生母和嗣母相继过世。他自己做主租了条小船,带着两个弟弟把嗣母的灵柩从淮阴运回淮安,和嗣父合葬。办完丧事,他最亲的人就是八叔和八婶了,八婶是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有一个孩子,就这么六个人一块过日子。开会的时候就说,他从小就感受到世态炎凉。家里已经穷成那样,墙上还贴着条子,亲戚的生日、祭日都在上面,到日子借钱也要随礼。他恨透了封建社会旧礼教那个虚套子。
记者:他对父辈有极深的感情。
周秉德:是。1938年国共合作,武汉文艺界开会,他简短发言就要告辞离场,那天我爷爷到汉口。亏得老舍先生把讲话记录了下来。他说:是暴敌让我们分离,现在又是暴敌让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让我们更加团结。
记者:武汉转移到重庆的三四年也是他们父子共处最长的一段时间,最后你的祖父得病,七妈亲自侍奉左右,但伯伯并没能送终。
周秉德:这是他一辈子的遗憾。当时他小肠疝气住院,爷爷不久也住院了。伯伯在病床上还记挂着爷爷的生日,写信嘱咐七妈:如果老人要按正日子过生日,我可能还没出院,如果他愿意等我,就晚点过生。不过老人一般信老礼儿:晚过不吉利,那你就迁就他一下……没想到爷爷在生日前一天去世,伯伯没能见到最后一面。
记者:伯父伯母为你祖父写的讣告很感人。
周秉德:李敖寄来了讣告的影印件。他说,从1942年7月15日到7月19日,共产党党报(注:指《新华日报》)头版连登三天讣告,“显考”“讳”“府君”“男恩来”“弃养”“抱恨终天”“媳颖超”“随侍在侧,亲视含殓”等等,全是对传统孝道的遵守。
“革命者应该是有情意的人”
记者:毛主席有一篇文章说,共产党被长期造谣成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
周秉德:对,说共产党人六亲不认、共产共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当年新四军领导之间有矛盾,与国民党之间也常有摩擦。伯伯想去看看,但蒋介石不准他的假。当时国共合作,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国民党代表有时候是陈诚有时候是张冲。张冲出主意:蒋介石很讲孝道,你说去祭祖扫墓,他就准假了。结果还真是。伯伯到了安徽云岭解决了新四军之间的问题,之后又到浙江拜访了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并做了地下党和新四军干部的工作:黄绍竑在国民党里还是很进步的,要多跟他交往……总之做了很多统战工作,并且真的去祭祖了。他先到绍兴,见了一位在当地比较有名望的堂姑父,然后又找到自己太祖一辈的一位长辈,把钱给他,让他准备两桌祭餐。然后他到祖居,让太祖坐正位,共产党不讲叩头,他就向太祖三鞠躬,之后带祭品上了坟。
1950年代中央提倡火葬,他跟七妈决定:我们连骨灰都不要保留。土葬改火葬是一场革命,火葬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们要做这样的革命者。八奶奶来北京的时候,说咱们家的房子都破了,漏雨了,你当了总理,得把咱的房子修一修。他说不修,坏就坏了,塌就塌了,特别是他出生的那一间,千万不要修,不要让人家参观。他一再反对死人占活人的地,想带头把我们家的坟平了。
但这么做有很多障碍,首先是老家的坟。解放之后,我父亲和六爷爷几次提出想回老家看看,他都不让,怕惊动地方。我父亲说:你不是想平坟吗,我去办。伯伯还是不同意。后来考虑到他的堂侄参军后每年都要回家探亲,就让堂侄去办这件事,这一支13座坟一块儿给深埋了。伯伯事先征得我父亲同意。但浙江还有更早的祖辈,伯伯提出平坟时,他一个远房婶母还在世,想不通。伯伯也尊重她的意见,临终之际拜托伯母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等婶母去世,族中再无人反对时把祖坟彻底平了。他尊重每个人,不会说:我是对的,这件事你们得听我的。他可以等。
记者:所以他是革命者,也是有情人。
周秉德:革命者应该是有情意的人。黄埔一些将领放出来,他找他们聊天,带他们游颐和园,在大牌楼前合影。1960年,他把南开的同学请来吃飯,让我爸爸作陪。伯父的老同学张鸿诰是我妈妈的大姨夫,他布菜时问:纶扉(注:张鸿诰字纶扉),士琴管你叫大姨夫,我可怎么称呼你呀?张鸿诰说:各论各的吧,你还叫我大哥,同宇可要随士琴叫我大姨夫。不是老同学之间地位悬殊,就不知道怎么相处。客人告辞,他一家赠一小包花生米。那时候花生要出口,他稍微有一点供应。
记者:由于癌症的折磨,周总理最后的时光非常痛苦,听说他听越剧来缓解癌症的疼痛。
周秉德:这我不知道。当时我想去看伯伯,七妈说不行,中央规定亲属都不让去,只允许她一个人去。我急了,七妈才让我跟伯伯通电话,说了二十多分钟,我怕他累,就匆匆挂断。我从回忆文章中知道,他在病床上听过总政文工团的《长征组歌》。他们给他专门演过一次,没有观众,录给他看。不过他是喜欢听越剧,讲过小时候奶奶带他乘船回老家,一个地方有戏台,他们在水上听。他对袁雪芬、王文娟、徐玉兰都很关心。有一次我出差去上海,伯母还让我替她看看袁雪芬,我去广州时还让我看望红线女。他们交往很深,是懂行的,七妈京剧唱得很好。
他住院的时候,我送给他的小书签,还有草编的茶杯垫,后来七妈都还给我了,留给我当“念想”。我结婚,七妈准备了很多东西,像嫁女一样:缎子被面、毛毯、枕套、成对的茶杯、玻璃磨花的糖罐儿……伯伯的礼物是七妈在庐山含鄱口拍的风景照。我的床头从来没挂过结婚照片,一直就是七妈拍的庐山。
(摘自4月25日《南方周末》。标题有改动,正文有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