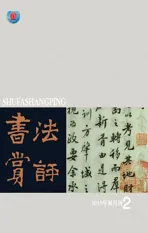“八大怪”轶事(下)
2019-07-02■林奇
■林 奇
那些年,如果你在师大校园里看见一个穿旧式青布衣裤,拎着个黑布口袋,瘦小而单薄的“农村老太太”,低着头在瑟瑟秋风中疾步行走,那一定是游寿——“八大怪”中的唯一女性。
游寿,1906年生于福建霞浦的一个教育世家,高祖是进士,林则徐的老师,父亲是举人,长期主持福宁书院。她早年在福州女子师范读书,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共青团,后为躲避军阀抓捕女扮男装逃回老家,19岁那年就任霞浦女子高等小学校长。之后又就读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获学士、硕士学位。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她来到江西参加了雷洁琼组织的妇女抗战救国运动,雷洁琼在回忆录里多次提到她。后又受中共委派,以战时妇女指导员身份在当地开展抗日活动。
1941年,她辗转到四川,先是在四川女子师院教书,接着来到抗战时期文化精英的聚集地李庄,在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当时那里有三位女性因才华出众而引人注目,那就是林徽因、曾昭燏和她。后来,她相继在中央图书馆、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师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解放后,由于遭遇“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压力,加上她认为东北考古工作落后,很多遗迹尚待发掘,就主动要求支边,于1957年来到哈尔滨。
游寿是通晓金文和甲骨文的少数学者之一。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曾忧切地问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先生,通识金文和甲骨文的学者有几位,王列举各家,其中就有游寿。

游寿先生(1906—1994)
游寿眼睛很“毒”。在哈尔滨附近的皇山顶上,她说,一定有古人类曾经生活在这里。大家一找,果然,不仅找到了很多石器和陶片,还发现了猛犸象骨骼化石。她认定史书中记载的北魏祖先鲜卑人发祥地石室,就在大兴安岭,当地文物部门据此考察,终于发现了嘎仙洞石壁上的祝文。她回福建老家探亲,大年初一便出去考古,向村民刨根问底,找遗物顺藤摸瓜,确定霞浦县赤岸村为唐宋福宁湾重镇,日本文化圣人,遣唐使空海和尚的登陆地。
考古奔波野外,游寿和助手经常是灰头土脸,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她们怀抱破罐子碎石头乘车,引来猜疑的目光,以为是疯子、讨饭的。有人忍不住好奇,问她们是做什么的,游寿说,挖祖坟的。众人大惊,解释后才恍然大悟。
“文革”时,她家的贵重文物、字画、金银首饰,存折等被抄,“文革”后国家有政策给一定补偿,让她写份详细的清单,她只简略地写了几件,仅得千元。她有一枚很有价值的北周大钱当时也被抄走,虽有线索可查,她却说,追紧了,会毁掉的,于是不了了之。有次家中被盗,丢了几件珍贵的玉器,公安部门组织破案几天未果,她说算了,不要追的太紧,只要不弄到国外,在谁手里都一样。
游寿的书法寓巧于拙,秀而不媚,是清代李瑞清、胡小石金石书风的重要继承人,与康有为的女弟子萧娴并称“南萧北游”。 面对络绎不绝的求字者,她无论远近生熟,有求必应,分文不取。在书法课上,她发现谁写的不好就给做示范,学生因敬畏不敢求字,有机灵者故意不好好写“吸引”她来示范,趁机取出早已备好的宣纸,留下墨宝。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省政协委员,她待遇相对不低,常拿工资接济亲朋,自己却一件衣服十几年不换,睡的是折叠床,坐的是折叠椅,家图四壁——四壁全是图书没有家具。出差在外,大多时候是挤公交车,住普通房,吃小食店。学校附近菜市场的营业员一度以为她是捡菜叶子的老太太,当得知其是知名学者后,惊讶不已。
她的书法作品很少有大幅,主要原因是没有一个能铺开大张宣纸的写字台。她的文房四宝也很粗糙,低廉的纸墨,普通的毛笔,砚常常就是半个塑料肥皂盒。有时要写字,发现毛笔用完忘洗,笔头已经干硬,她用手指搓几下就用,照样出好字。一次在河南岳飞庙,平时很少主动写字的她写了幅字,见助手疑惑,她说,桌子上那笔,真好。
她虽壮游多地,但乡音不改,初上她课的学生一时难以完全听懂,她就不断在黑板上写字,弄得满身都是粉笔灰。学生不忍,上去给她擦,她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老师就是吃粉笔灰的。
有学生上课睡觉,她从不发火,而是耐心絮叨,从父母都是社员如何不易,说到不好好读书将来如何为国家服务——她不说为人民服务,习惯说为国家服务。
但要以为她是个好脾气,那就错了。当年在李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因与所长傅斯年在治学理念等一些问题上有冲突,她愤然留下“平生志在为学,岂较区区作驽马恋栈耶”一语,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她从事研究工作数年的当时中国最高学术单位。


游寿先生书法作品
红卫兵“破四旧”,要砸文物室,弱不禁风的她却挺身而出,拦在门前怒吼:要批判就批判我,这里的东西一样也不能动!那群天不怕地不怕的狂热青年一时惊呆,竟默默地退却了……
“文革”中“八大怪”不是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就是“资产阶级杂家”,都成了“牛鬼蛇神”,白天挨批斗,晚上住“牛棚”。系主任和书记作为他们的“黑后台”也被揪了出来,领着他们一起在校园里游街。这十个人有的打锣,有的敲鼓,边走还要边唱嚎歌。嚎歌,也叫牛鬼蛇神嚎丧歌,是当时“牛鬼蛇神”们被逼迫唱的一种自我丑化自我侮辱的歌曲。歌词大意是:我是牛鬼蛇神,我对人民有罪,把我砸碎,把我砸碎。游寿的又细又尖的闽东口音显得格外突出,后边跟着看热闹的一群孩子哈哈大笑,并学着她的腔调喊:把我砸碎,把我砸碎……
私下与同事聊天时,游寿忧心地说,现在这么乱,年轻人容易学坏啊。
说“八大怪”毫不在意个人的荣辱得失,这不大可能,但似乎真的没看他们计较。是世事洞明后的孤傲,还是沧桑阅尽时的无奈?不管怎样,只要形势一允许,他们就毫不懈怠,马上又出现在讲台上。
他们大都是小时候读私塾,民国时期读大学,接受的是旧式教育,国学功底非常深厚。他们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品质。拥有它们的历史系变得引人注目,让人向往,连外系的行政人员也想来历史系工作。当时老师的讲义都拿到印刷厂统一印,他们的讲义最受印刷工人的欢迎,不仅字迹工整好认,更能欣赏到精湛的书法艺术。学生们照集体相,有意把他们请来,不只是要留个纪念,还在于日后可以拿出来显摆。现在,显摆已经变成了缅怀。
“八大怪”之名本是侮辱嘲讽,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名字从开始那天起,大部分人就没当成是贬义,现在早已变成对八位先生卓尔不群的敬称了。
“八大怪”们出生于上世纪初,相继陨谢于上世纪末。他们经历了中国历史翻天覆地的变化,是进步事业的献身者,是政治磨难的受害者,也是国家发展的推动者。他们儒雅、博学、隐忍、朴素,逆境中坚守自我,顺境中全心投入,彰显了安贫乐道的文人气度和独立卓绝的名士风骨。他们是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最光荣的开始,无论这个时代大学精神如何缺失,我们拥有过他们,就不至过于惭愧。
回顾往事,不胜唏嘘。斯人已逝,当年的文史楼如今也已了无痕迹。但他们的精神一直萦绕在那里,时时提醒我们不忘坚守。

游寿先生1930年摄于南京

游寿先生在居室作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