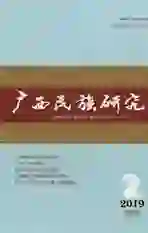后现代主义对香港国家认同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2019-06-10莫文希冯庆想
莫文希 冯庆想
【摘 要】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取向主要包括:反对权威、中心、本质,崇尚随机性、多元性、相对性;放逐作为主体的个人,逃避责任,消解终极意义的追求;颠覆时间向度,沉浸于游戏短暂刺激中,标新立异。在后现代社会语境下,香港对国家的肯定中包含一定的否定性,难以形成统一的爱国价值共识;香港国家认同的建构属于碎片化低度整合方式,难以实现国家主体对香港的系统“询唤”。鉴于此,要改善香港国家认同,就必须主动掌控意识形态话语权,树立政治权威,凝聚“一国”价值共识;积极推进国民教育体系构建,系统塑造港人的国家观念、民族情感与历史意识;促使爱国爱港媒体承担社会责任,占领舆论前沿阵地,向西方错误思潮亮剑。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香港;国家认同;一国两制
【作 者】莫文希,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1。冯庆想,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科研博士后。广东广州,510275。
【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2-0023-005
后现代主义是当代西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正如王治河所言,“从影响的广泛性上看,在二十世纪,除了马克思主义,大概就属后现代主义了”[1]9。当代香港已经从工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诸如追求个性、上街发声、质疑权威等后现代价值表达方式在社会转型中不断得到强化。一些港人似乎并不满足于传统理性化、科层化、世俗化的国家政治参与模式,而是更倾向于借助非政府组织、街头政治、民间运动等形式表达自身诉求。当中央对国家政治底线进行划定,香港社会不同的意见便随之冒起。种种迹象表明,港人价值观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与影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以后现代主义价值取向为切入点,着重分析港人与国家之间认同关系构建的思想文化困境,进而探讨应对之策。
一、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价值取向
(一)反对权威、中心、本质,崇尚随机性、多元性、相对性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权威、中心、本质都是西方传统理性外化的衍生品,理性与上帝把人的内在规定性放置在一种去异存同的确定性结构中,压抑了人本质的差异性、丰富性、多样性。他们认为后现代话语应该终结这种表征独断权力关系的规范性产物,解构把万事万物都化归于某种普遍性的理论范式,将人的主体性从封闭的、可视的权力空间中释放出来,在追逐随机性、多元性、相对性的过程中,抛弃确定性、一元性、绝对性的羁绊,推倒主体间紧张的竞争关系及其背后的等级系统。他们的价值取向不在于价值理念本身的标准,而在于对待价值理念的态度,推崇宽松、随意地看待不同理论争鸣、思维碰撞、价值观冲突。简言之,后现代主义没有绝对的价值评判标准,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是与非。
显而易见,后现代主义把人的主体性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其强调人的个性、自由、开放,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人的想象力与思维空间,为人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充裕的流动性。然而,后现代主义者以一种极端的思想形式把作为社会单元的人从社会结构中抽离出来,放置在一种理想化而非理性化的价值体系中,拷问社会权威、中心、一元结构对个人随机、边缘、多元诉求的侵蚀。须知,权威与随机、中心与边缘、一元与多元等范畴绝非只是一种只有张力的对峙结构,这些反映生产资料、政治权力、文化资源占有不对称的关系,固然会对人的生存境况产生冲击,但不可否认的是,只要社会系统能够利用权威方式实现零散资源的有序聚集与配置,那么对人所处的社会秩序就具有一定积极的导向与整合作用。然而,后现代主义一味拆解权威主体地位,完全遮蔽权威结构的一些合理性,极易滑入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轨道。
(二)放逐作为主体的个人,逃避责任,消解终极意义的追求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作为主体的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可忽略不计。换言之,个体在社会中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个体的行为无法控制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它们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逻辑关联。因此,个体无须背负社会附加给自身的沉重责任,所谓责任只是压抑主体意志自由、限制主体行为选择的无形枷锁,个体有必要挣脱这种现代主义者一厢情愿的强制与加持,重获主观精神的自由。当责任、义务、担当在个体意义重构体系中的在场性被消灭,深度意义的模式逐渐被平面化、碎片化、庸俗化,所谓的终极意义追寻就不复存在,一切皆有可能,每一种意义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如此一来,后现代主义者丧失了精神意义的超越维度,纯粹以破碎世界的表达形式获取某种不确定意义的填充,来抵抗生活意义的虚无与飘渺,就如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分不再展开思想与理性的羽翼。
主体的放逐、責任的缺失、意义的消解,必然导致后现代主义追随者的国家观念、社会职责、家庭担当变得非常薄弱。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无穷的随机性与流动性中消殆,难以凝结成彼此共享的纽带。当共同体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概念,那么,威胁社会本体安全的变量必然剧增。倘若个体对事、对己、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都没有了“应然”的规定性,也无须在“实然”层面为主体的选择、行为、后果承担相应的成本与风险,那么如此社会形态何以健康稳定发展?马克思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是无所谓的。”[2]579显然,后现代主义逻辑中的人是脱离社会关系的人,是被后工业文明异化的人。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者以一种错位的范式转换试图抵抗现代性对人主体性的吞噬,可惜却找不到造就自身生存困境的根源,最终在精神沉沦中逃避责任,放弃承诺,消解永恒意义的追寻。[3]
(三)颠覆时间向度,沉浸于游戏短暂刺激中,标新立异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时间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过去、现在、未来不是一个完整的时间序列,它们之间没有线性承接与因果联系;过去无法影响现在,现在无法决定未来,未来尚不可知或根本不存在。时间链条的拆解与断裂不仅决定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历史观念“只是一堆记录确已不存在的事件或时代的纸张、文本、档案”[4]205,而且也导致了他们的理想信念不存在于未来的时空之中。王岳川指出,“后现代不重过去(历史),也不重未来(理想),而重现实本身”[5]15。然而,过去、未来遭到后现代主义者无情的放逐后,其现实的时间维度实际处于失重不协调状态。他们对现实的社会文明与生存境况表现出极度不满,却又拒绝寻找指向未来目标的灯塔以及突破现实困境的通途,“只能在当下的生活中追求偶然的、暂时性的满足,使生命降格为凡庸琐屑的享乐,蜕变成本质上消极的过程”[6]。
个人此时此刻的感受与喜好被强推上生活的主轴,这就是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笔下的后现代社会中呈现的一种游戏状态。在不确定的、随机的、无限循环的游戏参与中,体验对权威、中心、本原消抵的冲击与快感;在标新立异、及时行乐、戏仿调侃的过程中,表达对现实的不恭与不屑。显而易见,后现代主义者的游戏人生态度是一种非理性的、偏激的、自戕的情感宣泄,解构了个体生命的尊严感与崇高性,消解了社會价值中某些相对明确的共识与标准。从中亦可发现,后现代主义者的历史意识、未来观念没有连续性与同一性的衔接,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症状。缺乏过去经验的导向与未来目标的铺陈,就难以从现实中生成认同感,唯有透过游戏情景代入与感官刺激体验,以求异、寻新、荒诞的方式满足主体原始的纵欲本能。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丹尼尔·贝尔、哈贝马斯、詹明信等著名学者把后现代主义的盛行视为西方社会精神信仰陷入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
二、后现代社会语境下香港国家认同的困境
(一)从认识层面看,香港对国家的肯定中包含一定的否定性,难以形成统一的爱国价值共识
在传统的政治思维中,国家认同是传统价值理性的衍生品。作为一种威权中心主义的本体论存在,国家认同具有一元性、明确性、本源性的意义所指,在社会价值序列中被赋予了优先的位置。自觉认同所属的国家包含社会主体的一种“应然”的价值伦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爱国天经地义”等传统政治价值在社会精神场域占领道德制高点。然而,当传统政治逻辑进入后现代语境中,随之而来的是价值多元主义、自由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对国家认同的价值祛魅与意义消解。
在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社会特征的香港,“‘香港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有着一种不确定性:在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的同时,却不认为民族主义可以凌驾于其他道德价值之上,也不会无条件地接受一切以国家为先”[7]。可见,香港国家认同的结构中内置一种否定式的价值尺度,在“香港人都爱国”的肯定表态背后,仍隐藏着对国家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国家既作为一种实体存在,又作为一种观念存在,然而,现实的存在与想象的存在并不是同一的共在,二者之间具有异质性。现实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现实的主体是现实本身,对对象性存在是一致的;现实的中国对香港存在,同时也对内地存在。想象的存在是一种主观能动的存在,实施想象的主体是随机的,想象之外的客体对象是确定的,想象的行为极易受到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干扰。当想象的主体是香港,它所呈现的中国,不一定存在内地的想象中;当想象的主体是内地,它所呈现的中国,也不一定存在香港的想象中。因此,在意义自由流动、价值开放多元的后现代社会环境下,思维与存在的非对称性传导到香港主体的认知心理、文化思维、政治立场与历史经验中,必然会产生主客观认识的差异,反映在港人对国家不同的情感与态度中。
从逻辑思想的三段式来看,香港传统爱国左派及普通民众对国家产生自豪、忠诚、归属的情感是对国家认同规定性的知性追求,属于正题;香港反对派对国家保持排斥、抗拒、否定的心态是对国家认同价值理性的否定,属于反题。但这并不是黑格尔哲学语境中的“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8]172,而是形而上学视角中的“一切规定都是否定”,不仅对国家内在给与定性的否定,而且对中心之外的边缘也予以否定。香港反对派成员完全出于为否定而否定,在拆解国家的一切在场、颠覆香港固有的秩序的同时,也消解了自身的普遍理性,把否定意识推向极端。香港建制派对国家的态度基本是既肯定又否定,属于合题。建制派人士肯定的是国家与香港唇齿相依的关系,否定的是“两制”社会之间的政治摩擦,他们对国家的态度相对温和,有别于极端激进的反对派。然而,传统爱国左派及普通民众屡受挤压,建制派不时被架空,反对派却占据了香港话语权的高地。这种格局不断拉开香港主观认知的中国与客观的中国之间的距离,由此产生的差异、矛盾与冲突不仅是后现代社会的产物,更是香港国家认同的困境所在。
(二)从实践层面看,香港国家认同的建构属于碎片化低度整合方式,难以实现国家主体对香港的系统“询唤”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指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是社会主体性的自我建构的物质基础,它承担着生产社会群体的“政治潜意识”的任务,以意识形态方式发挥其功能作用。国家主体通过家庭、学校、宗教、工会、传媒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动建构社会主体真实生存状况的想象性关系,形成国家大写主体与社会小写主体之间“询唤”与“应答”的互动机制,从而实现社会大众对国家的认同。换言之,在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中,国家、民族、历史等主体并不会主动呈现其自身的价值属性,它们往往借助新兴传媒、教育系统、学术会议与大众文化等物质载体的传播,塑造社会大众的国家归属、民族情感和历史责任。
然而,在长期的英国殖民统治历史中,香港与国家之间并不存在系统的对话与交流机制。香港回归后仍然延续以个体为本位的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在国民教育、德育模式、公民身份与社区文化等方面都存在国家、民族、历史的价值空场,相当部分香港人主观感觉自我与国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香港后现代社会中,崇尚多元、追求个性、放逐物欲的“去中心化”价值取向,不仅不断解构国家的意义深度,而且助推香港国家认同的建构方式走向碎片化、平面化与零散化。对大部分香港人来说,他们在游历天安门、万里长城与人民大会堂等器物体验中激活历史意识;在升国旗、唱国歌与戴国徽等仪式和规范中产生对国家赞许、冷漠或抗拒的情感态度;从香港媒体对国家新闻的解读中形成对国家的主观评价;利用两地经贸交流、文化交往所产生的生活感受来显现国家正反形象。这些国家认同的建构途径除了协助香港人提升他们对国家情况的基本认知能力外,并不涉及系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渗透。
客观、全面与理性的认知是建构香港国家认同的基础,对国家萌生的情意、忠诚与信仰等非理性因素则是推动香港人自觉把国家认知转化为爱国行为的关键。但在外在观感的刺激与内在价值的塑造中,香港都缺乏国家主体主动、系统与长期的“询唤”与教化,反而是部分本土媒介基于商业利益定位或迎合党派政治动机,诱导香港市民有选择地记忆与遗忘国家的存在,消解港人的国家价值观,加深香港与内地的社会心理隔阂。由此可见,港人与国家的认同关系从历史断裂到现实嫁接的过程中,一直面临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这正是香港国家认同建构所面临的困境。
三、后現代社会语境下改善香港国家认同之策
(一)主动掌控意识形态话语权,树立政治权威,凝聚“一国”价值共识
首先,以中央权力为基本保障,依托“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改变传统重经济政策统战、轻意识形态引导的治港思维,把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提升到战略高度,利用政治意识形态的空间穿透力,有序持续地弥散国家影响力,主动“发声”回应自由放任、挑战国家政权的思想文化乱象。其次,以国家宪法与香港基本法为基本遵循,以善治、法治、民主为治港目标,充分发挥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国务院港澳办、中联办等政治组织的工作效能,依法推进中央对港政策下沉至社会各个阶层,消解自下而上的对抗力量,夯实政治权威合法性来源的社会基础。再次,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基本载体,促使国家政治权威人格化,发挥中央领导人与香港特首的领导核心作用,构建富有亲和力、感召力、说服力的政治话语,在情感与理性的平衡中凝聚“一国”价值共识,让香港市民自觉认可、自愿服从、主动捍卫国家的崇高性、严肃性与魅惑力。[9]
(二)积极推进国民教育体系构建,系统塑造港人的国家观念、民族情感与历史意识
首先,香港特区政府要适当调整传统“积极不干预”施政理念,在国民教育方面应当“有所作为”,落实教育、文化职能部门推行国民教育的责任,通过师资培训、资助活动、发放津贴、政策倾斜等途径,加大公共教育资源的有序投放,扭转香港基础教育以民间办学为主力的局面,构建以政府教育为主导、学校教育为基石、社会教育为补充、家庭教育为辅助的四位一体国民教育体系,形成一种平衡“一国”和“两制”的新型港式国民教育模式。其次,深入反思《国民教育与德育科》独立成科受阻根源,在重启民意咨询之前,成立专业的国民教育推广组织,充分做好国民教育的宣传、解释、指导、监督工作,先尝试在香港小区域范围内实施国民教育试点,积累经验与教训,再由点带面,渐进推广。再次,以系统塑造港人的国家观念、民族情感与历史意识为目标,通过课程改革指导、教学资源共享、学术沙龙活动与内地文化交流等形式,将趣味性、整体性、时代性、体验性贯穿于香港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从港人主体的认识、情感、心理、行为等层面提升其国家认同。
(三)促使爱国爱港媒体承担社会责任,占领舆论前沿阵地,向西方错误思潮亮剑
首先,改善爱国爱港媒体人的生存与发展条件,提升他们的责任意识、专业素养、创新能力与环球视野,客观全面构建精细化的新闻报道框架,实现信息汲取与信息整合的紧密结合,推进感性认识中国向理性分析中国的升华,提供一个让香港受众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瞭望祖国的资讯平台。其次,构建合理有效的补偿与激励机制,平衡爱国爱港媒体在国家利益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取舍,发挥其充当中央、港府、政党与市民之间沟通、交流、认同的桥梁功能,形成一种良性的政治组织、传媒机构与社会大众相互制约、评价、监督的机制。再次,注重线上社交传媒的互动与线下爱国爱港团体的同盟,紧紧把握社会主流民意的脉搏与走向,提升传播效率与反馈速度,主动占领社会舆论前沿阵地,合力反击诸如《学苑》《苹果日报》等“反中反共”媒介的语言暴力与立场偏见,有理有据地批判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对港人国家价值观的解构和冲击。
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0]539。可见,意识形态的流变与文化思潮的涌动对一个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不容小觑,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在香港后现代社会语境下,如何消解香港国家认同的离心力,把绝大多数爱国爱港人士的力量凝聚到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与新挑战,亟需学界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指南。
参考文献:
[1] 王治河.后现代主义辞典[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2]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林华敏.我们何以差异性地共存?——从萨特到列维纳斯的他人超越论问题 [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4] [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6] 任鸿杰.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取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2).
[7] 吕大乐.从港人身份认同看回归十年[J].同舟共济,2007(7).
[8] [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9] 李海波,谢平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使命与党的建设新要求[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RESEARCH ON THE IMPACT AND COUNTERMEASURE OF POSTMODERNISM ON HONG KONG'S NATIONAL IDENTITY
Mo Wenxi,Feng Qingxiang
Abstract: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postmodernism mainly includes: opposition to authority, center, essence, advocating randomness, pluralism, relativity; exile as the subject, evading responsibility, eliminating the pursuit of ultimate meaning; subverting time dimension, immersing game short-term stimulation, it is unconventional. In the post-modern social context, Hong Kong's affirmation of the state contains certain negativity, and it is difficult to form a unified consensus on patriotic values. The construction of Hong Kong's national identity is a low-level integration of fragmentation, and it is difficult to realize the "inquiry" system of state subject to Hong Kong.In order to improve Hong Kong's national identity, we must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ontrol the ideological voice, establish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converge the "one country" value consensus; a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systematically shape the Hong Kong people's national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t urged the patriotic Hong Kong media to assum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ccupy the frontiers of public opinion, and sing the sword to the West.
Key words:Postmodernism; Hong Kong; national identity; one country and two syst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