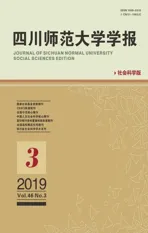试论北魏士族铨叙依据的“资”
2019-06-03
(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长春 130012)
魏晋南北朝官僚铨叙之常制为九品官人法,其运作程序归结起来就是计资定品授官,居中发挥决定功效的核心要素即本文所要探讨的“资”。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虽是异族政权,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却将华夏门阀士族制元素融会贯通并推向极致,相关的政策法规和丰富的史料记载便成为透视该体制全貌的重要素材。北魏文献中不乏“资”的实例,作为朝廷选拔官僚的基本依据,其对仕途和待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应该引起学界的高度注意。现有成果诸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注]〔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中国学者祝总斌先生《材不材斋史学丛稿》[注]祝总斌:《材不材斋史学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阎步克先生《察举制度变迁史稿》[注]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和《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注]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张旭华先生《九品中正制略论稿》[注]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陈长琦先生《官品的起源》[注]陈长琦:《官品的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尽管在制度总体方面贡献突出,但对北魏的具体情况缺少连续关注;新近又有日本学者漥添庆文先生《北魏后期的门阀制——起家官与姓族分定》[注]〔日〕漥添庆文:《北魏后期的门阀制——起家官与姓族分定》,徐冲译,《中国中古史研究》第六卷,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量化分析世资与起家层级的对应关系。故笔者试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沟通士族制发展的首尾两端,即魏晋与北魏的内在关联,着重考察北魏对“资”的操作运用,管窥门第社会的机理和逻辑,进而揭示北魏社会进化的潮流趋势,至于研究方法和具体结论妥当与否,还望专家不吝赐教。
一 前人成果的归纳概括
要弄清北魏士族语境下“资”的特定含义,首先要了解其在士族制的源头魏晋时期的初始状态。对此,有几家观点应该重视。祝总斌先生围绕士族门第“二品系资”问题展开探讨:“二品是上品,应由德充才盛者取得。可是西晋竟正式增加一个标准——资。换言之,如果资不够,即使德、才合格,一般也不能取得‘人品’二品。这在门阀制度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所谓资,汉魏之时多称阀阅。如前所述,阀阅本来仅指个人当官的功劳与资历。由于资历中可以包括功劳,多半体现功劳,逐渐便简称为资。后来资亦包括父祖的功劳与资历,于是又有了门资、世资等熟语。由于当官的功劳、资历与官位高低往往一致,所以‘系资’的最简便办法,便是按本人或父祖官爵高低来衡量。”[注]祝总斌:《材不材斋史学丛稿》,第159页。总之,一个人的“资”包括自己和父祖的功劳、资历,可由家门整体的官爵水平集中量化体现。
陈长琦先生将“资”的诠释同“资品”一词联系起来,指出:“‘资’在文献中有多种用法,是一个含义颇广的概念。常有‘门资’、‘世资’、‘官资’等。……门资就是一个家族既往的、世代累积的社会政治及文化资源。它反映的是一个家族、家门既往的社会政治、文化地位,并影响着一个家族当下及未来的社会政治、文化地位的走向。……门资是一个家族世代累积的社会政治文化资源,因而又往往称之为‘世资’。……(官资)资途,无疑是指官途。……文献中亦有资品的用法,并用于称呼这个附属于个人的品。”[注]陈长琦:《官品的起源》,第94-98页。简言之,“资”有三种内涵:其一是家族长久积淀的深厚底蕴;其二是个人的仕宦资历;其三是基于门第世资评议人才的资格等级,即所谓资品、乡品、人品、中正品等。
张旭华先生则认为:“晋代所言之‘资’有家世门阀、任官资历和中正品第三种含义。那么,在上述三义中,何则与‘资品’之‘资’最为契合呢?依据史传,‘资品’之‘资’乃是指第二义而言,也就是指任官资格、资历与资次,而与家世门第无关。‘资品’连称,通常是指官职升迁时对于本人的任官资历与所获乡品的一种综合要求,并非是专指中正品第一项。”[注]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第159页。可见,他对“资”的界定与陈长琦先生如出一辙,只是对“资品”的理解别出心裁、新颖独到,在他看来,该词组中的“资”不是厘定乡品所依据的门第世资,而是与乡品并列的官资履历。
阎步克先生也持类似的看法:“魏晋时所言之‘资’略有三种。其一为一般所言之资格、资历。……其二为中正之品第。……其三谓士人之门阀。”[注]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139页。他后来又深刻阐发古代系之于人,而非附丽于职位的品位分等现象,具体落实到六朝即形成与“资”紧密联系的“门品秩序”。他说:“官僚等级制中潜藏着的品位萌芽如得东风送暖,开始抽条生花。九品中正制度应运而生,朝廷上各种散官名号不断委积繁衍,从中发展出了‘清官起家迁转之途’,日益发达的‘清浊’观念对应着士庶之别、文武之别和官吏之别。它们与士族门阀的传统门第构成的错综复杂局面,就是所谓‘门品秩序’。……这一阶段德、才仍为评定人品的极重要标准。不过与此同时,中正的品状已逐渐向权贵倾斜,进而向士族门阀倾斜了。除能力、功绩和资历等行政考虑之外,官僚开始依照新的范畴,也就是依门第范畴而被区别为不同层类。”[注]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366页。概括可知,门品秩序涉及的“资”涵盖其所述的资格、中正品和门阀三类情况。
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对“资”的解释虽然精彩周详,然放眼整个国际汉学界,方知皆非首创。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东洋史京都学派第二代掌门宫崎市定先生已有明论:“‘资’有两重意思,称‘门资’、‘资荫’等的时候,‘资’是根据家世而自然赋予其人的资格,和‘门第’、‘姓第’,或者单称为“第”的意思相同,就是先天的资格。但是,‘资’还有表示通过个人的经历后天取得的资格的意思。”[注]〔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257页。宫崎氏尽管把“资”的含义归纳为“先天的家世”和“后天的个人”两层,但实际包含家世背景、门品等级和履历资格三项环节。中日两国学者虽视角、立场各异,却有着共同的学术追求,故而在长期隔绝的状态下殊途同归、不谋而合。
总括以上,“资”作为魏晋官场司空见惯的高频词汇,既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朝廷铨叙的依据。其内容涉及个人及父祖先世的仕宦资历和功劳业绩,只是为方便统计核算,才简化为以官爵品秩为基本单位。基于此,它又形成一种永久附着于人身的资格等级,在门第至上的士族社会决定仕途前景、施展空间和资源分配,从而有效建构固化、封闭、世袭、垄断的阀阅体制。明乎于此,再将北魏的情况与之比较,便不难显现二者在中古士族制发展轨道上的关系。
二 北魏“资”的具体内容和计量方法
比较而言,“资”在北魏文献中出现的频次绝不少于魏晋,且相关操作渐趋成熟稳定、规范有序,研究赖以顺利展开。有理由相信,经历汉化和士族化风潮洗礼的北魏在官僚铨叙方面能够做到唯“资”是从。宣武帝正始二年(505)四月乙丑诏:“任贤明治,自昔通规,宣风赞务,实惟多士。而中正所铨,但存门第,吏部彝伦,仍不才举。遂使英德罕升,司务多滞。不精厥选,将何考陟?八座可审议往代贡士之方,擢贤之体,必令才学并申,资望兼致。”[注]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八,第198-199页。引文句式上下互举并列,末尾的“资”照应先前的“门第”,证实它确实包含门阀因素。出土材料中亦不乏类似记载。如《皇甫驎墓志》:“景明元年中,旨格初班,简选台资,穷尽州望,除君为别驾。”[注]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1页。《崔芬墓志》:“乡部望资,弓车不已。”[注]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2页。都强调铨选应资、望兼顾。需要说明的是,在贵族社会,分别基于家世、德才的“资”与“望”其实并不矛盾,高门名望聚拢一流资源和机遇,在培育卓越情操素养上自然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恰如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先生所说:“六朝贵族本来具备两个特征:一是高贵的家门,二是出众的个人人格。二者原本不可分割,一种高贵的家门养育卓越的人格,而卓越人格使家门越发高贵。”[注]〔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97页。客观公正地评价,往往门第越尊显,治世的志向和才干就越出类拔萃,基层民众反馈的乡论舆情相应地越积极正面,二者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关系。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在优质资源过度集中的情况下,高门第本身就意味着高品质。那种受阶级斗争影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僵化思维,甚至刻意迎合意识形态歪曲事实的手法,都是背离唯物史观的。过去片面夸大士族坐享富贵、腐朽寄生的消极面,掩盖其自我抑制、弘扬公义、勇担责任的积极面,无疑是选择性认知的偏差。
北魏“资”的门阀因素由哪些部分组成,这是值得深究的问题。就现有材料来看,起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官职。史载,孝文帝太和年间,著作佐郎成淹为慕容白曜鸣冤:“臣伏见故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济南王慕容白曜,祖父相资,世酋东裔,值皇运廓被,委节臣妾。”[注]魏收:《魏书》,卷五○,第1120页。此处的“资”应指慕容白曜的先人充任宰辅的资历。二是爵位。史载,孝明帝时,萧梁犯边,彭城王元劭上表:“伪竖游魂,窥觎边境,劳兵兼时,日有千金之费。臣仰籍先资,绍飨厚秩,思以埃尘,用裨山海。臣国封徐州,去军差近,谨奉粟九千斛、绢六百匹、国吏二百人,以充军用。”[注]魏收:《魏书》,卷二一,第584页。因言及捐献彭城封邑的衣食租税和役吏,故这个“资”是继承父辈的王爵。三是皇族身份。《元周安墓志》:“具彰于玉牒,允备于金腾者矣。……同资帝绪。”[注]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247页。墓主世系为景穆皇太子之孙,汝阴灵王之子,明载玉牒的“资”定为高贵的皇家血脉。总之,北魏的“资”囊括官职、爵位和皇族身份,系体制内范畴,至于不易量化的政治表现和功劳业绩则汇聚其中并以之为媒介间接体现。
北魏的“资”既是家族阀阅的反映,势必会有世代的严格要求。前引慕容白曜的“资”只追溯父祖两代。台湾学者毛汉光先生甄别士族门第把标准设置为曾祖、祖父和父亲三代,理由源自孝文帝厘定胡汉姓族的诏令[注]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44页。。这应是当时通行的惯例。孝明帝熙平二年(517),江阳王元继抗议剥夺拓跋疏宗的祭祖资格,表奏曰:“臣曾祖是帝,世数未迁,便疏同庶族,而孙不预祭。斯之为屈,今古罕有。……伏见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铨衡,取曾祖之服,以为资荫,至今行之,相传不绝。而况曾祖为帝,而不见录”[注]魏收:《魏书》,卷一○八,第2763页。,明确将“资”的上限划到曾祖。与之相印证,北魏根据家传、谱牒、行状如实撰写的墓志标榜阀阅多数溯及曾祖,现存的高道悦、李璧、张卢、石育、赫连悦、崔混、张瓘、李挺、于纂、李颐、陆绍、杨颖诸志[注]分别参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104、118、126、306、275、326、314、350、200、179、235、61页。皆为实例。实际上,中古大族寻根溯源不必过远,因为一朝士族皆因缘际会、趁势崛起的新贵,长盛不衰的旧族非常罕见,门第主要取决于现世轩冕,而非祖先的荣冢枯骨[注]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4-55页。。当然也不能太近,毕竟士族资望的形成实难一蹴而就,必备深厚的内涵积淀,按照当时社会流动的一般水平至少需要三世,俗语所谓“三代以下无贵族”就是这个道理。美籍华人学者何炳棣先生特别强调三代履历考察社会血液循环的标志意义[注]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6页。,无疑是有历史根据的。
北魏的“资”涵盖三代阀阅,若以每代平均25至30年计算,跨越时段将长达近百余年。其所累积的厚重资历既有入魏后的,处理起来还较容易;恐怕也少不了前朝的,这就牵扯到如何对待前朝旧资的问题。祝总斌先生研究发现:“北魏建国至显祖时从未清定士族,所云‘高门’、‘中第’,自依五胡十六国以来,特别是慕容宝之制。随着汉化的推行,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一方面对鲜卑贵族固然不得不以当代三世官爵为标准;另一方面对汉人重定士族高下,则似乎是以魏晋官爵为主要标准,至少定第一流高门是如此。”[注]祝总斌:《材不材斋史学丛稿》,第196页。换言之,前朝旧资,北魏一概接受并承认,其效力获得充分尊重。典型事例如《王曦墓志》:“曾祖谧,苻世侍中。祖儒,荧阳太守。考彪,魏世振威将军、黑城镇将。”[注]王沛、王木铎:《北魏王曦墓志简析》,《洛阳考古》2016年第1期,第73-76页。世资涉及前秦。《李璧墓志》:“曾祖尚书,操履清白,鉴同水镜,铨品燕朝,声光龙部。祖东莞,乘荣违世;考齐郡,养性颐年。”[注]于芹:《李璧墓志探析》,《中原文物》2016年第5期,第72-75页。世资涉及后燕。遑论前朝,即便对峙的敌国资历也能在北魏平等地置换官职。献文帝时,刘宋徐州刺史崔道固二度归降,颂扬北魏的宽宏:“臣资生南境,限隔大化,本朝不以卑末,委授藩任。”[注]魏收:《魏书》,卷二四,第629页。足见,北魏对本朝内外的资历一视同仁,以维护士族门第的连续性和一贯性。
北魏“资”的功用是比较门阀等级和确定职务待遇。孝明帝孝昌年间,大臣袁翻与朝廷讨价还价,上表曰:“窃惟安南之与金紫,虽是异品之隔,实有半阶之校;加以尚书清要,位遇通显,准秩论资,似加少进。语望比官,人不愿易。臣自揆自顾,力极求此,伏愿天地成造,有始有终,矜臣疲病,乞臣骸骨,愿以安南、尚书换一金紫。”[注]魏收:《魏书》,卷六九,第1544页。其实就是介意安南将军、都官尚书与金紫光禄大夫在“资”上的差别得失。所以,“资”应是既能代表家世整体水平,又可比照计量的一个确切数值。史载,高阳内史崔振,“高祖南讨,征兼尚书左丞,留京。振既才干被擢,当世以为荣。后改定职令,振本资惟拟五品”[注]魏收:《魏书》,卷五七,第1272页。。崔振汇总先世官资,特别是其父五品太守得来的“本资五品”定为加权后的平均数,因世资的内容主要是官爵品级,它自然也以“品”为单位。《魏书》卷一一一《刑罚志》所云“本品之资”,亦可为证。必须强调的是,所谓“本资”,不光是宫崎市定先生所说“以其个人的能力所到达的地位”[注]〔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257页。,实乃包括本人在内全族政治势力的浓缩,它与直接衡量门第的人品、乡品、资品或中正品还不是一回事,两者之间尚需按特定比例换算搭配。
三 北魏“资”的层位等级
如前所述,北魏的“资”首先是统计家世阀阅的结果,数值高下决定了门第等级和身份地位,具体的对应规则详见唐代谱学大师柳芳所论:“‘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注]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卷一九九,第5678页。此乃普通的庶姓臣僚,凌驾其上者还有堪称天潢贵胄的皇帝三世以内的骨肉至亲[注]刘军:《试论北魏王朝的“宗室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113-118页。。北魏士族等第依次为天潢贵胄,膏粱、华腴(合称膏腴),甲、乙、丙、丁(合称四姓),划分的标准即由三世官爵或皇室血缘构成的“资”。令人困惑的是,引文中所列代表性官职的品级该用哪部职员令衡量。宫崎市定先生和毛汉光先生不约而同地援引太和十九年(495)定姓族之际业已颁行的新品令,得出的结论如下:膏腴层位的三公正一品,尚书令正二品,仆射从二品;四姓层位的尚书、领军、护军、九卿、方伯(上州刺史)正三品,散骑常侍、太中大夫从三品,吏部郎中正四品,正员郎正五品。[注]〔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267页;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146页。问题在于,新令品分正从上下,如何能算出前引崔振那般品数齐整的本资。况且,按照法学常识,律令一般遵循从旧即时原则,往往不具备溯及既往的“溯及力”,前太和时代(甚至包括东晋、南朝和五胡十六国)产生的世资怎能生搬硬套太和末叶的官品标尺。同理,漥添庆文先生采用太和十七年(493)试行的前职员令加以衡量亦不合适。[注]〔日〕漥添庆文:《北魏后期的门阀制——起家官与姓族分定》,徐冲译,《中国中古史研究》第六卷,第137页。故而,笔者推测“资”的计算应以通行北魏前期、品不分正从的晋品令为基准。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十二月,廷议员外将军陈终德为祖母守丧仪制,关于他是否具备“士”的身份,太常卿刘芳认为:“案晋《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无从,故以第八品准古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从,若以其员外之资,为第十六品也,岂得为正八品之士哉?”[注]魏收:《魏书》,卷一○八,第2795页。佐证用太和品令核算“资”存在无法解决的技术障碍,不如晋令简便精确。所以,上述推想并非毫无理由。
按唐代杜佑编撰的《通典》卷三七《职官·秩品二》所载晋品令:膏腴层位的三公一品,尚书令、仆射三品;四姓层位的尚书、领军、护军、九卿、散骑常侍三品,方伯四品,吏部郎中五品,正员郎六品,太中大夫七品。分别解算均数,求得各自的概略区间:世资一至三品者为膏腴,处于士族上层,为一流高门;世资四至五品者为四姓,处于士族下层,为一般高门。经过这番转换,代表家世阀阅的“资”便与出身等第直接挂钩。据此,北魏文献中的士族人物,只要算出他三代(至少能保证两代)的世资均值,就能在门阀序列中找到相应的位置。
反映家世阀阅的“资”建立士族的门第等级,唯簿伐是从九品官人法根据门等授予不同的乡品。这样一来,“资”就顺理成章地对接贴附人身的仕宦资格,未来仕途的起点、终点以及连接二者的晋升通道便由此奠定。北魏确有乡品的概念。《元瞻墓志》:“后为汝南王以茂德懿亲重临京牧,妙简忠良,铨定乡品,召公为州都,委以选事,区别人物,泾渭斯叙。”[注]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228页。因其是“资”的综合评估,才产生“资品”的别称。高阳王元雍谏宣武帝考陟:“臣又见部尉资品,本居流外,刊诸明令,行之已久。”[注]魏收:《魏书》,卷二一,第554页。能够标识流内、流外身份的只能是乡品,足证该词是与乡品相通的官方术语。不过,北魏史料中鲜有乡品或资品的直接记录,这是因为它与起家官常按相差四等的比例搭配。通过分析起家信息便可知晓,时人对此心知肚明,秉承“常事不书”原则的史乘渐渐就忽略了。[注]〔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66页。那么,只要借助起家折射的乡品,就能探明“资”与乡品的兑换关系。
笔者遍检完整保存家世履历的北魏墓志,筛选晋令标准下世资、起家信息俱全的材料列如表1。表1充分显示世资、门第、起家官、乡品四者之间的对应规律。若有效滤除人生和官场中诸多偶然因素,以晋令为标尺的常制下:世资一至三品的膏腴子弟,例以五品官起家,授一品乡品;世资四至五品的四姓子弟,例以六品官起家,授二品乡品。众所周知,中正划定乡品数级有九,然二品为士族身份的底限。此外,凌驾庶姓臣僚的皇家至亲独享四品官以上起家的“宗室选”,特授超品乡品,不在中正评议范围之列[注]刘军:《新出元渊墓志所见北魏超品宗室的仕进特征——兼论城阳、广阳二王冲突之实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174-180页。。实际上,世资岂止限定起家释褐,仕途巅峰在很大程度上亦受其左右。前述天潢贵胄拥有出任宰辅、位极人臣的资格,膏腴拥有跨越象征中央核心权力圈的三品九卿线的资格,四姓拥有跨越象征公卿大夫层位的五品官僚线的资格[注]刘军:《北魏门阀士族制度窥管——以新见封之秉墓志为中心》,《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第157-164页。,即是证明。北魏士族计资定品就在超品至二品的范围内展开,处于整个乡品序列的最顶端,其与寒庶的鸿沟势若天隔,即便本阶层内部的壁垒亦清晰明辨,中古贵族制社会的核心机理“流品”信条由此表露无遗,居中起到隔断作用的正是家族累世积淀的“资”。这种“资”在“量”上的差别显而易见,但在“质”上的层级档次却只有利用乡品为媒介才能阐明。

表1.北魏墓志中的官爵世资简表
备注:“资料出处”一栏中的缩写,“汇”为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疏”为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版),“洛”为齐运通《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中华书局2012年版),“墨”为叶炜、刘秀峰《墨香阁藏北朝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其后数字为所出页码。
四 北魏铨叙对“资”的操作运用
铨叙是指审查官僚资格、业绩,确定职位授予和升降的过程。在士族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北魏洛阳时代,世资门第堪称决定铨叙的第一要素。《韦彧墓志》:“高祖孝文皇帝定鼎嵩瀍,亲简人门,太和十九年,钦公高辩,顾谓仆射李思冲曰:才明如响,可除奉朝请,令优游道素,以成高器。”[注]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128页。《王昞墓志》:“选部取人,尤重门德,遂以访第入仕。”[注]叶炜、刘秀峰:《墨香阁藏北朝墓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32页。可谓实况。针对这种选材倾向,韩显宗批评说:“今之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门望,不复弹坐。”李冲亦表达类似看法:“若欲为治,陛下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注]魏收:《魏书》,卷六○,第1339、1343页。反证家世背景受重视的程度。那么,作为门第缩影的“资”,在铨叙的技术环节到底怎样操作,这是颇值得深究的问题。
随着北魏士族制日臻完善,“资”的强大效能在登仕阶段即已体现。首先,家族的“资”呈报官府备案,一经确认就会自动生成相应的仕宦资格,再交由尚书吏部酌情安排起家事宜。史载,宣武帝永平四年(511)七月,“诏改宗子羽林为宗士,其本秩付尚书计其资集,叙从七已下、从八已上官。”[注]魏收:《魏书》,卷一一三,第3004页。这里的“资集”应为本人资历与先祖世资的合并,新令从七至从八品换算旧令为五、六品,刚好处于士族的起家层位,符合宗子羽林脱胎换骨后“士”的身份。孝明帝时,文武官员比肩入仕,“时羽林新害张彝之后,灵太后令武官得依资入选”[注]魏收:《魏书》,卷六六,第1479页。;权臣元叉秉承帝后意旨,“奏立勋附队,令各依资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叙”[注]魏收:《魏书》,卷八一,第1793页。。这些抚慰代北武人之举措必是比照士族常制拟定的。“资”对起家的影响,除使天潢贵胄、膏腴、四姓各自拉开一级距离外,还能左右象征声望度、效力值和利益回报率的清浊职务的归属。如《染华墓志》:“君统基承绪,在于旧京。于时普选高门子,蹔卫皇宫,乃出身应召,得为领表。及迁鼎洛邑,料隔清浊,既夙厕混流,释褐乖分,太和廿年除皇子北海王常侍。”[注]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124页。正是因为染华世封侯、伯高爵,拥有一流世资,才让他在侍从武官中脱颖而出,率先改换典型清职。进而推知,“资”的档次越高,猎取清职的概率越大,于清流行列的班位也就越靠前。
仕途迁转,不同的职务阶梯对应特定的“资”,惟有符合条件,方能入围候选。《元暐墓志》:“琐门注望,其来日久,将委喉唇,事资执戟,除给事黄门侍郎。”[注]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217页。意即志主的门资堪任门下省的次长。正史中频见类似情况。孝文帝褒奖李彪:“彪虽宿非清第,本阙华资,然识性严聪,学博坟籍,刚辩之才,颇堪时用,兼忧吏若家,载宣朝美,若不赏庸叙绩,将何以劝奖勤能?可特迁秘书令,以酬厥款。”[注]魏收:《魏书》,卷六二,第1389页。说明常态下清望至极的秘书令必匹配头等的门资,而才华横溢的李彪只是破格提拔的特例。又史载:“刘腾,字青龙,本平原城民。……吏部尝望腾意,奏其弟为郡带戍,人资乖越,清河王怿抑而不与。”[注]魏收:《魏书》,卷九四,第2027页。戍主执掌要地防务,责任重大,故苛求门资,绝非贱民役吏可以染指。刘腾兄弟近乎士家的城民之“资”与戍主之职格格不入,落选完全在情理之中。
北魏官场竞争激烈,优仕通道异常拥堵,“资”的高卑直接影响晋升次序。孝明帝末年,天下扰攘,“灵太后诏流人所在皆置命属郡县,选豪右为守令以抚镇之。时青州刺史元世俊表置新安郡,以(邢)杲为太守,未报。会台申汰简所授郡县,以杲从子子瑶资荫居前,乃授河间太守。杲深耻恨,于是遂反。”[注]魏收:《魏书》,卷一四,第355页。门资领先者优先递补实缺看来是约定俗成的惯例,一旦违背势必引发争端。史载:“(贾)思同之为别驾也,清河崔光韶先为治中,自恃资地,耻居其下,闻思同还乡,遂便去职。州里人物为思同恨之。及光韶之亡,遗诫子侄不听求赠。”[注]魏收:《魏书》,卷七二,第1616页。此例,清河崔光韶凭借山东首望无与伦比的门资,在州府中不甘屈居次等士人贾思同之下,足证“资”是维护仕途升迁秩序的根本。
作为仕宦资格,“资”与官职位阶紧密地匹配联动,形成“升官升资,降资降官”的互动机制。于是,朝廷可以通过“资”的调节有效改变官员的仕进轨迹。凡有功劳勋绩者,加官进爵,“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阶,散官上第者,四载登一级”[注]魏收:《魏书》,卷二一,第553页。。宦资阶级水涨船高,自然推动仕途高歌猛进。反之,惩罚怠惰非违,“资”会被不断贬降,前程随之一落千丈,直至除士籍为民,褫夺公权。宣武帝延昌二年(513)裁议官当条例:“官人若罪本除名,以职当刑,犹有余资,复降阶而叙。至于五等封爵,除刑若尽,永即甄削,便同之除名。”[注]魏收:《魏书》,卷一一一,第2879页。以“资”当刑固然是统治者的特权,但也要看到它重挫世资阀阅、摧毁家门基业、辱没先祖遗烈、殃及后辈进取严酷无情的一面,实则为力度仅次于死刑的重罚。特殊情况下,为激励犯官戴罪立功,遭削夺的“资”可以恢复,连带自动授予相应的官职。史载,太子家令崔模,“以公事免。神龟中,诏复本资,除冠军将军、中散大夫”[注]魏收:《魏书》,卷五六,第1252页。;司徒主簿裴仲规,“父在乡疾病,弃官奔赴,以违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义阳,引为统军,奏复本资”[注]魏收:《魏书》,卷六九,第1533页。。节闵帝普泰元年(531)二月己巳登基诏:“除名免官者,特复本资,品封依旧。”[注]魏收:《魏书》,卷一一,第274页。更加证明“资”与实际官职的关联,国家正是利用这个机理调控官僚集团的组织人事。
五 余论
北魏沿袭魏晋门第至上、按“资”铨叙之传统旧制,且在界定、诠量和操作上日益规范细致,标志着拓跋族文明进化的矫健步伐。北魏“资”的含义与魏晋大同小异,包括家世阀阅、乡品等第和仕进资格,三者协调配合、内在统一,共同编织中古北方贵族制门第社会的历史景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北魏的士族体制与魏晋一脉相承,其宗旨都是贯彻“流品”之核心要义,即实现根据家世背景把持不同空间、担当不同角色、履行不同责任、享受不同资源,各居其位、各司其职、各安其命、各得其所,彼此隔绝、互不干扰的身份利益格局。[注]刘军:《从释褐看北魏“膏腴”群体的身份特质——以出土墓志为基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38-145页。北魏治国理政便奉此为圭臬,《元寿安墓志》:“任当流品,手持衡石,德輶必举,功细罔遗,泾渭殊流,兰艾自别,小大咸得其宜,亲疏莫失其所。”[注]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191页。即真实意图的描述。一言以蔽之,就是实现统治阶级的自我再生产、身份地位的再复制、资源权益的等位再传递,满足既得利益群体需求的体制游戏。
不过,在中古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依“资”取士自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名门望族乃物质和精神养分荟萃之地,兼具浓郁的道德礼仪氛围,自幼接受熏陶、境遇优渥的贵胄子弟必定素质出众、人格健全,照比那些从底层打拼、饱尝艰辛磨难导致心智残障,且难以摆脱“补偿效应”和“新皈依者效应”困扰的寒门素士,显然更适宜充任政府和基层自治体的领导者。孝文帝选官偏袒士族的缘由:“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注]魏收:《魏书》,卷六○,第1343页。就是客观事实的反映。学者大多批判九品官人法只重簿伐,无视德、才之弊端,把二者摆在势不两立的位置,殊不知高门大族业已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和人才培养的重镇[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0页。,单是门第本身就代表了品质修养,又何必画蛇添足另寻贤德之士?门阀士族的统治能够维持五、六世纪之久,并创造出异彩纷呈的中古文明,难道不是旺盛生机的表现?但就宏观长远来看,集中资源培育特定人群,是以剥夺其他社会成员本应享有的发展权利为代价的,势必造成对流停滞、阶级固化,公平正义便无从谈起。总之,中古名族源于绝对排他性的成功,绝对不是扼杀庶民潜质的理由,惟有真正实现资源和机遇的对等开放、充分保障社会循环移动自由顺畅,中国社会才能焕发永恒的活力,宋明近世社会取代中古门阀社会的内在逻辑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