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马建标看传媒背后的政治
2019-04-16熊玉文
熊玉文
大众传媒(也称媒介)在西方国家发挥舆论监督功能,享有“第四权力”的美誉。然而,大众传媒在近代中国,自晚清落户起,就被赋予众多角色,承载政治功能,反而使其最基本的社会功能缺失。马建标新著《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在纷乱的西方与中国、个人与群体、书生与军阀、宫廷内斗与政党政争等千头万绪的关系中探幽寻微,抽丝剥茧,为我们描绘了媒介在近代中国所充当的角色;而所有这些角色,都与当时的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媒介在近代中国形成政治化的傳播特色。同时,一些精英人士意识到媒介的传播功能有时能起到权力和枪炮所不能起的作用,因此有意识地利用媒介去攻击对手,美化自己,通过媒介运作来实现权力诉求,使权力媒介化。传播政治化与权力媒介化是近代中国权力与媒介互动的基本特性。启蒙与救亡:传播政治化的两个表现
媒介传播政治化表现有两点:一是媒介在近代中国被赋予“启蒙”使命,以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替代中国传统的家族王朝思想。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60年的中外战争可以说是西方国家对中华王朝的战争,战争的结果使“睁眼看世界”的中国有识之士认识到传统天下观必须改变。
媒介在近代中国的启蒙首推对民族国家观念的启蒙。该书选择了几个代表人物来反映媒介对国人的这种启蒙。王韬,当其在欧洲游历被工业文明强烈震撼时,开始怀疑天朝观念,致力于中国文明改造。其回国后创办《循环日报》的目的就是要“把报刊作为传播新思想的公共媒介,以此推动晚清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P51)。创办过七八家报纸的“舆论界巨子”梁启超与王韬办报的目的一样,也是将“报纸媒介纳入了近代中国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域”(P81)。经过王韬、梁启超等人的启蒙,国人逐渐抛弃“忠君”观念,实现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变。
如果说王韬与梁启超是坐而论道的话,那么孙中山则是起立而行,以艰苦卓绝的实际行动促使国家观念在中国生根发芽,将中华民国创立在中华大地上。该书挑选王韬、梁启超和孙中山作为代表来叙事,这既反映了作者选择代表人物的独特眼光,也反映了作者对民族国家观念进入中国进程整体把握的功力。
二是媒介在近代中国被赋予“救亡”使命,以民族主义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正如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观念不可分一样,“救亡”与“启蒙”之间也不可分。民族国家观念是西方侵略带给中国的痛,也是西方侵略送给中国治痛的药,以民族主义反西方侵略成为国人救亡的必然之路。
商务印书馆创立于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时代赋予了中国近代印刷业一个救亡的角色。马建标认为商务诞生时有一个强烈的使命感,即以培育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为己任,并在这个领域中“充当中国理性的民族主义的提倡者”(P135)。鉴于这样的使命感,清末时期商务出版的《最新修身教科书》摈弃了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希望以爱国、平等、博爱等新的政治价值来培育新的国民。
通过印刷业来影响国民教育,商务可算是一个开创者,以学校为阵地来唤醒青年的救国参与意识,蔡元培治理下的北京大学可谓开路先锋,与北大相结合的《新青年》杂志掀起的思想狂飙使学生在民族主义刺激下走上了街头政治。马建标在对权力与媒介的考察中,剖析蔡元培在读书与救国之间的两难处境,以其“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一政治口号的提出来彰显这位北大校长与时俱进的爱国精神。
一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媒介对威尔逊“十四点”的鼓吹,尤其是对“民族自决”的鼓吹,使民族主义在中国成为压倒一切的潮流,把国人的“救亡”意识和“救亡”活动推到了最高潮。然而,巴黎和会仍是强权的胜利,国人终于认识到依靠威尔逊主义救亡的虚幻,被迫选择了列宁主义。在该书中,作者将“一战”期间的国际传播作为中国救亡的分水岭,为我们分析了面对“救亡”,国人在威尔逊“神话”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之间作出的抉择,列宁主义从此成了“救亡”最好的“批判的武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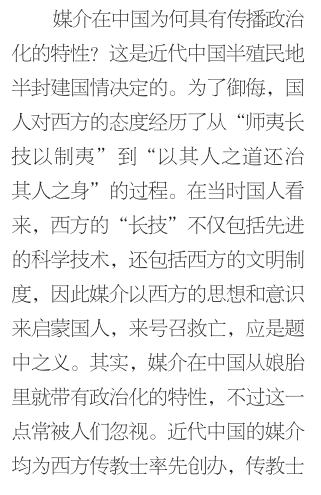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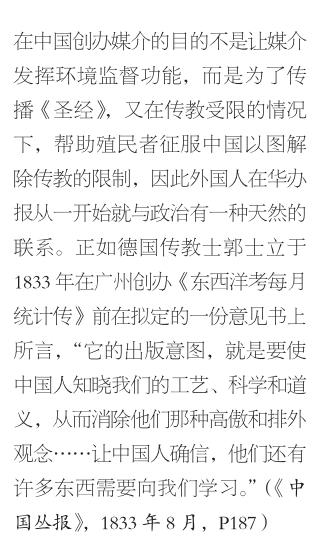
权力媒介化以诉求更大的权力
媒介是一种能力,它是人的身体的延伸;媒介是一种权力,它是人的意志的延伸。近代中国媒介走向传播政治化的时候,权力也在接近媒介,以媒介为通道实现个人意志的张扬。分析该书的整篇布局,可以发现作者设计了两条叙事线索,一条为前面所讲的传播政治化,即媒介与政治的合轨,媒介以政治使命为主要诉求;另一条是权力媒介化,即权力与媒介的合谋,权力以媒介为手段来诉求更大的权力。
在该书中,权力媒介化表现为盛宣怀对电报局的创建和吴佩孚对电报的利用。盛宣怀筹办过许多近代企业,但真正使其飞黄腾达的却是电报事业。盛宣怀以电报事业为阵地,以手中之经济权力去兑换政治权力,再以政治权力获取更多的经济权力。因办理电报有功,盛宣怀奉旨简放天津海关道,后又被授予督办全国铁路总公司事务等,成为近代著名的官僚企业家。盛宣怀对电报事业的创建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从李鸿章的幕府升格为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也改变了中国人的认知方式和话语方式。五四时期,国人对欧洲战场和巴黎和会的了解主要通过电报获取新闻,也是在五四时期,国人对时局意见的陈述纷纷以通电的方式表达,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直隶第三师师长吴佩孚“与世俱进”,在报纸上迭发通电,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主张国内和平,公开反日立场,同情学生运动,在话语权上实现新突破。在这场权力与媒介的合谋中,盛宣怀建立起自己的媒介帝国,将触角伸向全国各地,最终官至邮传部尚书和“皇族内阁”成员之一,吴佩孚则利用电报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爱国者”的形象,成为当时一颗迅速崛起的政治新星。
权力媒介化有时还表现为媒介成为权力阴谋的工具。该书为我们刻画了一些政客在拉帮结派或韬光养晦时,或多或少会将媒介用之于明争暗斗之中的场面,丰富了权力媒介化的另一种表达。“丁未政潮”是清末上层统治内部矛盾的一次大爆发,对晚清政局有重大影响。当以奕劻、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和以瞿鸿禨、岑春煊为首的“行在派”内斗达到白炽化程度之际,袁世凯利用瞿鸿禨对报馆泄密引起慈禧的不满将其扳倒,又伪造岑春煊与康有为师徒在上海《时报》报馆门前的合影照片将对手逐出北京。然而,获胜的北洋派并未能将优势保持太久,第二年袁世凯被开缺回家。为了麻痹载沣,袁世凯将“洹上渔翁”的照片刊登在《东方杂志》上,把自己装扮成与世无争、超然物外的模样,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才伺机而出。从1874年王韬作为中国人自己办第一份中文日报《循环日报》算起,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国人已将权力媒介化到无孔不入的境地。
媒介来到中国,就像工业技术革命来到中国一样,势不可挡。当然,媒介本身就是工业技术革命的一部分。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媒介却无法发挥社会功能,只能将政治功能当作其主要任务,不遗余力地对国人进行启蒙教育和救亡动员,对民族主义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P23)各种权力在追逐自身利益时,不由自主地将目光转向媒介这一新生事物,企图借此营造声势,塑造形象,或污损他人,争取利益最大化。这是媒介在近代中国的主要作为,也是作者在该书中对媒介行为的基本考察。由于该书作者将近代权力与媒介互动时间的下线锁定在1919年前后,可以说作者的考察基本上是全面的。
不应忽视权力与媒介的对抗
通读该书,觉得作者给我们稍稍留下的遗憾是,对权力与媒介的合谋描写多,对两者之间的对抗着墨少。既然媒介在近代中国主要发挥政治功能,那么媒介就会自然成为政党和帮派博弈的筹码。以权力来控制媒介,以媒介来对抗权力,在民国初期频繁发生。且不说有些记者为对抗权力付出生命代价,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全国新闻记者有60人被捕,24人被杀(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P1055),仅政府层面的权力与媒介之间的对抗在1919年前就有多起。
1913年,袁世凯为打压国民党,钳制舆论,封闭报馆,逮捕记者,形成 “癸丑报灾”。民国元年500多家报纸,经过袁世凯的摧残,只剩下139家。1918年9月,段祺瑞以“损坏邦交、扰乱秩序、颠覆政府”等罪名,查封揭密其与日本秘密签订军械借款内容的8家报纸。此种行为被时人认为“不特民国所未有,亦前清所未有”(《北京报界之借款厄》一,《申报》1918 年9 月28 日,第6版),其中《晨钟报》《国民公报》等大部分报纸为刚与其决裂的研究系所控制,带有明显的党派政争的痕迹。而徐世昌当选总统后,以舆论对抗段祺瑞派的武力,与研究系合作,利用权力,恢复被封禁的《晨钟报》等研究系报纸,将《晨钟报》改名《晨报》继续出版。1919年5月2日,《晨报》和《国民公报》同时登出研究系成员林长民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社论,引起国民警觉,引爆五四运动,使段祺瑞派受到重大打击。
可见,媒介作为一种传播最快捷影响最广泛的新型工具,对中国人的思想意識转变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正因为如此,也获得了各种权力的青睐。马建标的《权力与媒介》是我们认识这种变化和“权力与媒介”互动的进阶之作。该书所留下的遗憾,让我们对马建标不禁产生了新的期待。
(作者系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