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托海杯·第五届西部文学奖授奖词 答谢词
2019-04-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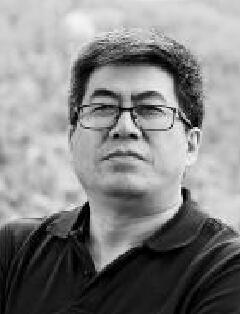

小说奖
鬼 金:《光之深处》(载于《西部》2017年第3期)
授奖词
在小说中重生,抑或在摄影中重生?这样的诘问既是对主人公的,也是对作者的。假如没有现代意识的灌注,《光之深处》将会深陷于故事的泥淖。小说中存在两种声音:一个女声,一个男声,自说自话。小说中充满了等待,“你”在等待金骁熙重新归来,“我”在等夭亡的小琪。光之深处走出的是逝去的亲人。小说写出了日常生活的诗意,绝望中的诗意。人与人之间时光交错、错综复杂的怀念构成了生命本体的生活面貌。《光之深處》用文字开掘出摄影艺术的美及特质,这源于作者对摄影的偏爱、认知。小说的成功不是依赖于庞大的故事体系来支撑,而是深入故事的内核,凭借娴熟的语言掌控能力,从细微处一点点打动人心。
答谢词
我是幸运的,写作这么多年,这是第二次获杂志的小说奖。感谢《西部》杂志。在我得到消息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是一个语音的祝贺,但我还是不敢相信,我要等着名单公布出来。看到名单的时候,我在吊车上,那一刻,我怔住了,想哭。这是真实的感受,不是矫情。真的想哭,想想这么多年的写作多苦,多孤独!一边倒着夜班,一边在业余时间写作。看来,这份苦是值得的。我用小说保存着精神和灵魂的纯洁,让写作成为我生存之外的另一种生活,不让我的生活失衡。是小说救了我,让我这么多年都没有沉沦在生活的“水深火热”之中。在“水深火热”的生活之中,我甚至有那么一丝绝望、无力。我的希望是在虚构的文字中找到的。我的文字充满了疼痛和自我救赎的意味。我企图在黑暗中寻找光,让找到的光照亮我前行的道路,让我的道路不会因此而黑下去。我说过,在看到消息的那一刻,我想哭,面对一个欲哭无泪的世界,我没哭。我就想喝一瓶啤酒,多么简单的奢求啊!是的,我不是酒鬼,但那一刻,我想喝一瓶啤酒。就像我多年前在吊车上触电之后,跑回家,从楼下买了一瓶啤酒,拎上楼,坐在阳台上,边喝边号啕大哭。
《光之深处》写于2016年4月23日至5月19日傍晚。那个时间段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我相信一定是发生了什么的。我用小说保存着时代的划痕。小说开头写到了拍照,这几年来我开始街拍,通过街拍与这个世界紧密相连,我看到的那些人和事物,让我更加清楚认识了这个世界的真相。我用小说保存划痕,我用照片保存证据,在这个东北的小城。这个奖也是遥远的西部对东北这个孤独的写作者的奖励。这不是靠个人人脉得来的奖励,而是靠小说本身,这是令我自豪的。这也是对我这么多年来写作的鼓励。谢谢!
临近午夜,我下班后,从工厂出来,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看到路边的烧烤摊还亮着灯,我真的去喝了一瓶啤酒,只是一瓶,作为对自己的那一刻想哭的奖励。我举杯对着对面的另一个我说,祝贺。边喝啤酒,边盯着那悬挂的昏黄的灯,犹如苦胆。光犹如胆汁。是啊,这么多年我不都是在黑夜里“卧薪尝胆”吗?在黑暗中想象着光明,在死亡的书写中寻求着生之意义,探寻着人性在这个时代中的美丑善恶。我在悄悄地凿破黑暗,让光从罅隙渗透出来,渗透出来……
唉,那瓶啤酒真好喝呀,有着麦芽的香甜和滋生出来的对这个世界的爱!
李 健:《泰克拜》(载于《西部》2017年第5期)
授奖词
“木垒河”是李健小说创作的关键词,《泰克拜》仍属于这个范畴,但有所突破。《泰克拜》讲述了泰克拜、天谷这对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为了得到希娜儿的芳心而展开的精彩、动人故事。哈萨克族习俗、民国历史、多元文化等元素的并存,增添了小说的好看性和厚重感。小说人物形象塑造传神,泰克拜最终跨越爱情的盲目、茫然,成为胸有大爱、有担当、有大义的男子汉。尤为难得的是,小说还塑造了有血有肉、个性独特、具有典型性的人物群像。《泰克拜》中压抑了太多苦难,没有充分释放出来。我们期待着作者实现下一次的突破。
答谢词
这是我第二次领取一个文学奖项。它于我而言,意义非凡。
原本,我的职业是医生,写小说是因为医生当不下去了。我在这个行当里待了二十多年,这是父亲为我选择的职业。我父亲恪守“身怀一技,遍行天下”的古训,所以,他为我选择了这个任何时候都不会饿着的手艺。之所以说在医生这个行当里待了二十多年,而不是干了二十多年,是因为我实在不是一个当医生的料。我无法安心坐在那张破旧的办公桌前,消耗我的生命。那时候,我二十岁出头,正是“左牵黄,右擎苍……西北望,射天狼”裘马轻狂的年岁,于是,我停薪留职下海了。一位朋友跟我说,做生意是要有杀父之心的,你没有。我跟他说,我去做个儒商。事实证明,朋友是对的。我的确淘了些金,可那些金就像海沙,在一片“儒商”的称誉声中,从指缝间流走了,一粒也没留下。
屋檐下的风筝——这句话最初是我爷爷揶揄我父亲的,后来。我父亲又把这句话送给了我。我对这句话一直心怀抵触,我不信我的天空只有屋檐那么高,我真正的写作也就从这时候开始了。
经商虽然没有给我积攒下物质财富,但这些经历丰富了我的人生。2006年我被抛上岸的时候,已经一文不名。那年我已年过不惑。好在我骨子里的坚韧还在,对天空的向往还在,依然如年少时一样茂盛,像一棵茁壮的树,于是有了今天站在这里的我。感谢《西部》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从这里看到更远更辽阔的天空;感谢关心我、帮助我的家人和朋友,是你们让我一个人走在路上时不感到孤单;我还要特别感谢这些年经历的形形色色的人和形形色色的事,是你们让我面对这个世界时,多了一份坚韧。
余笑忠:《每一次回望都有如托孤》(载于《西部》2017年第5期)
授奖词
当代诗歌已经越来越无法脱离叙述,无论是对梦的叙述,还是对死亡的表达。叙述本身已经构成一种抒情。每一次回望都有如托孤,有着一种类似环保的绿色情结,回环于诗中的,是一种对于美好的回望,而那些回环往复的文字,又似梦中呓语。在现实的种种困境中,唯一一只放走的鸽子给我们以出路;在梦的深渊中,唯有睁开双眼才能摆脱盲目的跟随。在这样的语境中,余笑忠的诗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伦理、新的思考,并在诗意的掘进中展现新的希望。
答谢词
很高兴能有机会再次来到新疆。上次很荣幸应《西部》杂志社之邀参加“新诗百年·天山论剑”盛会,这次来到美丽的可可托海,领取高贵的西部文学奖。天倾西北,西部之“高”自不待言;言其贵,则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以“寻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为己任的《西部》杂志,既有开放、包容、多元的大格局,又有纯粹、敏锐、不俗的气质。因此,我十分珍视“西部文学奖”这一荣誉!
与其他外地获奖者不同的是,我备感荣幸,因为能够与杰出的翻译家、诗人李以亮同行,一起领取本届“西部文学奖”。我从他的翻译文本中获益良多,在此,我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和由衷的敬意。当然,令人高兴的还不止这些,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向与会的老师和朋友、向优秀的同道请益。
在新疆,无论是在天山瑶池还是在可可托海,给人感觉最强烈的不外乎两点:一是新疆风景之美,而绝美的风景背后往往是最疼痛的山水,这是自然造化注定的;二是新疆地域之广袤,在这里,最快的速度也会显得很慢,而个体的人会感到格外渺小。
这也许是肤浅的风景观,但以此检视自己的写作或许恰如其分。写作中常常伴有疼痛,如何从疼痛中创造出独特的语言风景,于我而言是终生都要面对的课题;写作是服从命运的感召,荣誉有时会眷顾我们,在其鼓励下我们也许会跑得更快一点,但一己之力终归是有限的,甚至是渺小的。
诗人沃尔科特说:“日子是长大的女儿,离开我们的臂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要幻想去独占什么,而是要听从神秘的召唤,一路追随它。我在一首诗中说过:“像寒露后盛开的木芙蓉/它的名字是借来的,因而注定/要在意义不明的角色中/投入全副身心。”
再次感谢《西部》杂志社给予我的鼓励。但愿我的写作无愧于这里的山水、这里美丽的风景给我的启迪。
陈 末:《拉利亚组曲》(载于《西部》2017年第6期)
授奖词
很难用“新疆诗人”来概括陈末及其诗歌创作,她的诗作并无西部狂欢的气息,而天然具有沉郁的底色。《拉利亚组曲》是意大利作曲家路易吉·莫扎尼为悼念死去的女友所做的古典吉他曲,是一曲悲歌。陈末继承了这种含蓄、深情的风格,在废墟中写出了浪漫,写出了深挚的怀念。应该看到,《拉利亚组曲》是一部热烈的快板,即使在祭曲当中,也保持了适度的热情。陈末说:“每一个孤立无援的身体,都是一堵死灰复燃的墙。”是为《拉利亚组曲》最好的脚注。
答谢词
人所做的事情不是太多。比如复生。
我想,一定有一批潜伏在我们体内的庞大的诗群试图让我们与生活慢慢和解,而发现这些长眠在体内的词语,就是一种诗化的过程。这其中,我最为崇尚的,就是那些与自我救赎有关的、不断容纳灵魂体态的、贴近于更多诗意灵魂的词。这些词语,天生具有一定的攻击性,且尤为主动,它会接连不断地找到你,激活你,发现你,让你陶醉在一种相互发现并和解的诗意中。这种相互和解的过程,仿佛一把迎风而立的巨扇,它有着古典而抽象的画面,有着动感而立体的玄妙,它舞动,在空气中,一切的日常都是从扇面上吹过的风,一切立体的感受都是热与冷的降服,它还会发出风一样的呐喊,仿佛它就代表灵魂原本的模样,在空旷而黑暗的舞台中央完成它的上场与落幕。经过近二十多年的诗歌體验,我个人,把存放在我体内的这批词语统称为“灵魂的复生”。
我相信,每个人出生后,都会带着一批明亮的词,干净而纯洁,散发着其特有的味道。但成长中的生活,使词语开始变味、变种、变异。甚至,我们也开始利用这些变性过的词语为我们降低了的人生标准来开恩。我们说话,我们说谎,我们谈论,我们辩解,我们自言自语,我们羞于启口……我们沉默,或者彻底消失,然后任由别人为我们串起新词来消遣。但,词语与人一样,浮在深渊之中,还会有更深的深渊盯上你。于是,我们要学会从一个词语的顶部翻身跃向另一个词语的根部,去学会向所有高贵的词语低头。具体在一首诗歌的创作中,就是用一个旧词打破另一个旧词的边界,从而形成一种新边界的无限性,这是我所追求的,也是我所神往的诗意表达之所在。
我喜欢在诗歌中呈现向内与向外两种意象。向内,是完成自我精神的救赎与复生;向外,是探寻外部世界与自我精神融通的独立性。当这两种意象同时涌现在思考中,我便尝试打破词语本身的惯性空间,用一种近乎残酷的拆分,形成词语与语句之间的嫁接。这种尝试,使渺小的诗歌结构形成了某种庞杂的诗意氛围,有陌生感,也有试验性,当然,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程去形成一种完整的诗性。我盼望着这种新的尝试,可以让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情绪的阅读者,置身于一种词语的迷宫,或者一片情绪的森林,我退出诗歌,而他们则可以在这个迷宫与森林中肆意狂欢,释放对复生之生的旁白与爱。我总是想起纳胡姆·格拉策为罗森茨维格撰写的《生平与思想》所浓缩的那句话:“诗性的狂喜从天上的王座流淌进了人的心中,沿着巨大的弧线一次又一次地回旋着,这就是在启示的领域内一次又一次被发现的思想,无论在这个领域之内还是在这个领域之外,它都曾一次又一次地被遗忘……”我想呈现的,正是这种“被遗忘”。
“语言是墓碑!”
每一座墓碑之下,都是一座诗歌盖好的房子,都埋葬着一个失意一生的巨人,而我们能做的,只是把那些充满诗意的瞬间刻在他者的墓碑上。最后,我要借助弗朗茨·罗森茨维格的这句名言结束我对诗的浅论,也是一个“老诗人”以“新面孔”荣获第五届西部文学奖的特殊感怀!我想,我们都明白,诗人从来都不是独自在写诗,我们只不过有幸做了许多失意者的替身,为沉默的人类发出一些诗意的致敬而已。
再次感谢我的故乡新疆,感谢《西部》,感谢手中这座沉甸甸的奖杯!我会好好珍惜,以此为新的起点,写出更多诗意的作品。
江少宾:《风吹落日》(载于《西部》2017年第2期)
授奖词
永恒的乡村只存在于文学中,故而《风吹落日》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风吹落日》是诗化的,乡村是与世无争、淡然静美的,充满落日的余晖和宁静;人们生活在时间之外;万物相类,“狗皇帝”与人拥有真正的平等。它又似一部小说,描摹人性的复杂斑斓,彰显出作者对乡村现实的忧患意识、切身思考,以及裹挟其中无法抽离的无奈和痛感。诚如文章结尾:“夕阳西下,风吹落日。小村牌楼像一幅尘封的油画。”于人物、事件之外,作者给予乡村艺术品般的尊重、敬畏,这种态度与当下乡村现实及其写作迥然有别,令人起敬。
答谢词
感谢《西部》杂志对我的鼓励。西部文学奖是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奖项,前几届散文奖获得者久负盛名,他们是散文阵营里的领跑者,多年来,我一直在追赶他们。这一次,馅饼从天而降,我被砸中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既开心,又惶恐。
《风吹落日》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篇散文,一万五千字,含《失窃的村庄》《时间与声音》《桃花痴》《死于旷野》四个单篇,这四个单篇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在我写乡村的诸多篇章中,《风吹落日》可能是“小说化”最明显的一篇,它有人物,有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但这些只是它的外衣,内核依旧是“散文”。散文叙事自有其伦理。在多年的散文写作中,我始终秉持底层立场、新闻视角、多元叙事的原则。我在乡村长大,现在又是一名记者,记者是一个和社会良心有关的职业,我看到的新闻事件及其背后的真相,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素材库,日积月累,它们既支撑了我的散文写作,也注定了我的写作姿态。新闻结束的地方,散文出发了。当然,想象力是文学的基本功,虚构也不是小说家的专利,我也愿意承认,若非部分地借助于想象,我便无法完成《时间与声音》这一节,无法更好地呈现空巢中的“那些人”。
文学是人学,既要直击纷繁复杂的世相,也要逼视幽微深邃的人心。
散文是一种见情见性的文体,它对写作者的消耗太大了,大体量的写作势必会导致质量上的平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有烟火气息的、有生命体验的散文,读这样的散文,能触摸到作者的呼吸、心跳和体温。
文字自有其命运。《风吹落日》写于2015年。午睡之后灵光乍现,桃花、国平、冬至大爷纷至沓来,我打开电脑,从下午一直写到深夜,一气呵成,有如神助。这样的状态太罕见了,和获奖一样可遇而不可求。好在,写作是文学生命的长跑,我希望自己跑得更远,跑得更久。谢谢。
吴连增:《文学,不会衰老》(载于《西部》2016年第9期)
授奖词
作为一名在《西部》杂志社工作近二十年的编辑、主编,吴连增用深情的笔调道出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既有甘甜,也有苦辣。《文學,不会衰老》写出了时代变革下文学刊物所历经的阵痛、迷惘,写出了一代编辑人坚守文学阵地矢志不渝的决心、信念。该文的写作有广阔视野和良苦用心,为作家与文学编辑立德立言。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捍卫文学的尊严,保持文学期刊的艺术魅力。这是十分可贵的”。作者的文字如岁月流淌,铺展出编辑之间、编辑与写作者、读者之间的真情故事,堪称《西部》六十多年画卷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答谢词
得知“可可托海杯·第五届西部文学奖”的获奖者名单,拙作也名列其中,心情甚是激动。我确实没有料到,评委会会将散文奖评给已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作者。我想,这不仅是对一篇作品的肯定,更是对一个年已老迈却还笔耕不辍的老作家的鼓励。
其实,我并不情愿用“安慰”这样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谦逊,但我必须由衷地道一声“谢谢”,谢谢《西部》杂志长期以来对我的眷顾和润泽。我不仅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部》一直重点扶持的作者,也是沐浴着改革的春风有幸进入《西部》的一名老编辑。苦辣酸甜六十载,风霜雨露半个多世纪。为了共同的文学事业,几代编辑同仁辛勤耕耘、乐于奉献,我既是见证者,也是亲历者。我们不会忘记那些值得珍重的岁月,为文学的复苏,为西部文学的崛起。我们有过喜悦,有过困惑,有过徘徊,但始终执着地坚守着文学。这就是我写《文学,不会衰老》的直接动因。
我深知自己正一天天地走向衰老,即便能保持稍好的精神状态,想飞也飞不高了。令我欣慰的是,目睹一批又一批矫健的文学青鸟集结于西部,又不断地从《西部》起飞。古语云:“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中国西部的《天空》的确很雄阔,很壮美。我们会看到更多的青鸟在这里搏击风云。
周庆荣:《我的思考永远未完成》(节选)(载于《西部》2017年第2期)
授奖词
理论之上,更需要胸怀。周庆荣对诗性的解读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个人“生活的见识”,理论说不上宏阔,但从容、稳健,具备充分的文学性和哲理性。字里行间,自有优雅与豁达。《我的思考永远未完成》且有感性的成分,有爱,有恨,有“黑暗和过度的诅咒”,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批评的趋势。一种作家视角下的批评和文学观照下的理论,是我们一直期待的,因为它更多地保有人文关怀,而不只是空洞的说教,它更多关注对生命意识的阐释,更多地用诗意观照、解读、提纯并启迪人生。
答谢词
在感动于可可托海美好的秋天之时,我要首先感谢评委们把这届西部文学奖评论奖授予本人,我估计,这极有可能将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获得与诗歌评论有关的奖项。
作为一名诗歌写作者,更具体地说,按照我自己多年来一直所执着的,一名散文诗的写作者,我始终对真正的评论家充满敬畏。因为评论他人的作品,除了自身的文学素养和美学基础外,还需要一颗独立公正的心,一个能够尊重他人劳动和对社会始终坚持独立判断的灵魂。
六七年前我开始陆陆续续写下的对散文诗的系列思考,我自认为离真正意义上的诗歌评论相差甚远。我一直主张在“大诗歌”的认知上实现对散文诗写作的观察和理解,针对以往散文诗写作存在的对美、修辞和轻易抒情的状况,提出可借鉴分行新诗发展的脉络,通过散文诗叙述中方便接驳思想的优势,使散文诗这一文体的在场意义得以实现。
由于散文诗写作的惯性,写作者极易忽略对目标事物本质的探究,容易在表象上用力。由于没能读懂事物而让事物委屈,其结果必然是削弱了散文诗对读者应该具有的启示性效果。兼之人们通常具有的习惯性记忆,以致于一提及散文诗,似乎就是清浅风月之作。
解决散文诗写作者对散文诗文体现实中的焦虑,主要是靠我们自身观念的更新,要充分自由地以文章的方式来写出真正的诗歌。我们的田野上生长不同的庄稼,每一种都有其丰收的理由。高粱和玉米本身无优劣之分,哪种更被土地接纳,主要是看谁能够克服一切不利于生长的因素,最终能够长成丰收。
相对于分行诗,散文诗远未丰收。我的思考就是从散文诗写作者需要通过自省,强化散文诗之外的素质训练,看重自己对事物本质发现的独特性,从而使散文诗作品产生阅读魅力。这就是我在思考中所提到的“意义化写作”。需要说明的是,诗歌写作有时恰恰要警惕意义先行,相反,一些看似无意义的诗句因为唤醒读者的生命经验而后才具有意义。当初我做这样的提倡也只是针对散文诗一直以来存在的美好过度、修辞过度和抒情过度现象。
《西部》今年第五期的头条是散文诗专辑,作为一名散文诗写作者,我必须说出自己的感谢。这是刊物的包容,更是刊物的编辑同仁对散文诗发展的支持。
我们所处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认真思考。我们的思考能否带给人们启发、鼓舞,这取决于我们写作者的思考是否真正在场,是否真正有效。
最后,谨对《西部》的文学同仁给我本人的鼓励和支持致以诚挚的感谢!
李以亮:《亚当·扎加耶夫斯基随笔选》(载于《西部》2016年第4期)
授奖词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是波兰当代最具世界性声望的诗人和小说家,波兰“新浪潮”诗歌的重要代表,作品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和形而上的追求,善于在日常事物中拈取诗性的璞玉,并在语言的作坊里予以悉心的雕琢与蚀刻,以翻陈出新的技能營造了一种奇异的审美刺激,为人类的想象力提供了一个新的标高。他的随笔堪称其诗歌智慧的散文式呈现,让人深思,又颇具阅读的惬意。李以亮先生是国内极有实力的诗人,对汉语有足够的敏感,且怀有深远的文学抱负,致力于外国文学尤其是东欧文学的译介。《亚当·扎加耶夫斯基随笔选》较为精准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思想和文字风格,为现代汉语和随笔写作提供了典范性的文本。
答谢词
首先,我衷心地感谢《西部》,因我绵薄的努力和成绩所给予我的嘉奖。作为一名还在路上的文学翻译的探索者,你们对我的激励和提携,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深深地感谢你们!
自新文学发生的上世纪初起,翻译就一直艰难地伴随着它的整个发展进程。进入以全球化为特征的二十一世纪,现代汉语文学更是不可能局限在一个封闭的语言文化系统里生长。事实上,它也的确在求新、求异、求丰富的多种要求中不断成长。我们不仅需要一个可以参照、借鉴、学习的他者,我们更需要将自己融入歌德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展望过的“世界文学”的图景。
文学翻译,一般的理解,可能只是一种“拿来”,但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拿来”,如果没有深入到异质文化的深层肌理,如果没有伴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如果没有浸透创造者的心血,“拿来的”也许只是某种自欺的赝品。翻译需要克服“巴别塔的诅咒”,需要超越眼前无数的障碍,需要怀抱“同情之理解”,需要工匠般细心而持久的劳作和创造……这是每个从事翻译的人都会体认到的,完全地、完美地做到这些,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十几年前,我作为一名自恃而默默无闻的写作者,深切地感受到了个人写作遭遇的难以突破的瓶颈,而我完全不想继续那种重复的无效的写作。于是我自觉地、心甘情愿地将主要精力转向了翻译。这些年里,我感到了充实,享受到了沉静,也领受到了一种由专注带来的幸福。在翻译过程中,我也遇到一些困惑和困难,那时我便默默告诫自己,不必过于急切,也无须惶恐于时间的流逝。生命的智慧在于从容,伟大的艺术需要恒久的耐心。
乔治·斯坦纳说:“伟大的翻译比伟大的文学更为少见。”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翻译这一领域里,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已拥有众多成就卓著的翻译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的愿望是:秉持初衷,砥砺心力,不负我亲爱的期待者的期待,反哺我为之魂牵梦绕的缪斯。
再次感谢《西部》,感谢美丽无比的新疆。我爱你们!
(小说奖、诗歌奖、散文奖授奖词由刘涛撰写,翻译奖授奖词由汪剑钊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