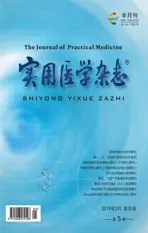心脏因子与冠心病的研究进展
2019-04-02吴叶顺杨春杨玲
吴叶顺 杨春 杨玲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内科(江苏常州213003);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麻醉科(武汉430030)
心脏作为具有分泌器官的功能逐步受到关注与重视,正常或应激状态下的心脏可分泌特异性因子,这些因子在维持心脏稳态、应对细胞损伤及心肌重塑等过程中发挥不同的生理作用,进而影响心脏疾病的发展,同时也可经由内分泌途径参与远端器官组织及全身代谢的过程,这一类心脏分泌物被称为“心脏因子”(cardiokines)[1⁃2]。心脏因子的表达在心脏不同的生理状态下具有显著差异,这些分泌的蛋白质是维持正常心脏功能所必需的,并以自分泌或旁分泌方式在心脏细胞通讯中发挥重要作用,抑或在病理性心脏损伤中调节在心肌细胞及成纤维细胞的改变,及参与炎症过程,发挥其对心脏的调节性保护或有害作用[3⁃4]。随着研究深入,我们团队总结并认识到心脏因子已成为具有评估心脏功能及辅助临床诊断的新型生物标志物,有可能拓展为心脏疾病治疗的新靶点[2]。
目前已识别的心脏因子有数十种之多[2],其中心房利钠肽(atrial natriuretic peptide,ANP)和脑利钠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BNP)在心血管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后判断等方面已得到广泛应用[5],它们主要在心肌中合成,并以自分泌或旁分泌方式直接影响心脏细胞生理功能,对心肌重塑产生有益作用,BNP 的血清浓度已成为心力衰竭的诊断指标之一并已应用于临床急性心力衰竭的治疗[6⁃7],亦有研究发现基因重组人BNP(新活素、奈西立肽等)可通过lncRNA EGOT 调节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PI3K)通路以改善心肌细胞缺氧损伤[8]。ANP 与BNP 临床应用的成功使其他心脏因子作为心脏疾病新型生物标记物的前景备受关注,白介素(Inter⁃leukin,IL)⁃33、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1(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21,FGF21)、卵泡抑制素蛋白⁃1(follistatin⁃like 1,FSTL1)、分泌性卷曲相关蛋白⁃2(secreted frizzled⁃related protein,Sfrp2)、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MIF)及神经调节蛋白(neuregulin,NRG)等为代表的心脏因子在冠心病中的相关研究也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学术热点,现本文将就其在冠心病中的生理作用展开综述,以期其能为冠心病临床及基础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1 IL⁃33 与ST2 蛋白
IL⁃33 是IL⁃1 家族的新成员,是ST2 蛋白的特异性配体,当心肌细胞和成纤维细胞受到牵拉刺激时,心肌成纤维细胞表达IL⁃33 上调,同时也释放大量的可溶性ST2(sST2)[9]。据报道IL⁃33 可通过ST2 跨膜受体(ST2L)激活核因子NF⁃κB 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在冠心病相关的多种炎症免疫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减轻心肌细胞凋亡及调节心肌梗死后的心脏功能障碍;而病理过程中产生的过多sST2 与IL⁃33 结合后将竞争性抑制其与ST2L 结合,从而阻断IL⁃33/ST2L 信号通路,使其拮抗心肌细胞肥大和心肌纤维化作用减弱[9⁃10]。此外,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可降低sST2水平而间接使IL⁃33表达增高,增强IL⁃33/ST2L信号通路作用,减少梗死后心肌的炎症反应和纤维化[11];β受体阻滞剂可通过增强IL⁃33/ST2L 信号传导,降低sST2 的表达,明显减轻心梗后心肌纤维化[12]。在冠心病人群中的研究还表明IL⁃33/ST2通路的基因多态变异可增加罹患冠心病的风险[13]。
LIU 等[14]研究指出急性心肌梗死及不稳定型心绞痛组患者的血清IL⁃33 水平明显低于稳定型心绞痛组和对照组,且与病情严重程度相关。血清sST2 水平可独立于现有临床指标提示心肌梗死和心力衰竭后不良结局,且梗死后早期sST2 水平(入院后24 h)具有最大价值[15],2017年美国心力衰竭指南已将其推荐为可提供附加危险分层价值的生物标记物[16]。
2 FGF21
FGF21 由209 个氨基酸组成,分裂后可形成181 个氨基酸长度的成熟蛋白,是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家族的一员,其既往被认为主要来源于肝脏,但新近研究发现心肌细胞及心脏微血管细胞也可表达FGF21 以调节心肌重塑并减少心脏损伤[17]。FGF21 可与存在于心脏细胞表面的特异性受体FGFR1c 结合而发挥其生物作用,这一过程需要辅助因子β⁃Klotho 的参与;FGF21 的N 末端与FGFR1c 结合,C 末端与β⁃Klotho 高亲和力结合,组成的复合物可以使受体自身磷酸化并激活下游胞外调节蛋白激酶信号通路,这被认为是FGF21 细胞内作用的主要途径[18]。
LEE 等[19]在对3 528 例2 型糖尿病患者平均3.8年随访中发现147 例(4.2%)患者在随访期内患冠心病,且这些患者的基线血清FGF21 水平显著高于非冠心病患者,通过多因素Cox 回归分析发现基线血清FGF21 水平(取最佳界值206.22 pg/mL)能独立地预测冠心病的发生(HR1.55;95%CI,1.10~2.19);在无糖尿病史的患者中,基线血清FGF⁃21 水平亦与Framingham 危险评分呈正相关[20]。受损的心肌细胞及内皮细胞可分泌FGF21 至体循环中,发挥其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脂质代谢及促进体重减轻等作用,从而间接减缓动脉粥样硬化进展,减轻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使用FGF21 类似物以及FGF21 受体激动剂的保护性作用已在小鼠实验中得到支持[21],其具有潜力成为冠心病治疗的新型药物。
3 FSTL1
FSTL1 是选择性结合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超家族成员的细胞外调节剂,亦被称为转化生子因子⁃β 诱导蛋白⁃36,在心肌缺血、心脏压力超负荷等情况下,FSTL1 表达显著上调,以发挥保护心肌细胞、减少缺血再灌注引起的心肌细胞凋亡等有益作用[22]。最新研究认为心脏中成纤维细胞是FSTL1 的主要来源,FSTL1 的表达在心肌梗死后缺血区的成纤维细胞中显著增加,而在心肌细胞中表达无明显变化[23]。
在动物实验中发现特异性FSTL1 基因敲除的小鼠模型心肌梗死后的成纤维细胞活化及分化减弱,在缺血性心脏组织中细胞外基质如胶原和纤维蛋白的生成也明显减少,相应的增加了心脏破裂而引起的病死率,这些发现揭示了FSTL1 可刺激早期成纤维细胞激活分化的新功能,提示其对心肌梗死后预防心脏破裂、改善左室重构的保护性作用[24]。OGURA 等[25]也在小鼠及猪模型中发现FSTL1 蛋白可显著减少缺血再灌注后的心肌梗死面积,这一作用可能是通过上调腺苷一磷酸激活蛋白激酶(adenosine 5′⁃mo⁃nophosphate⁃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信号通路及阻断骨形态发生蛋白⁃4 依赖的细胞凋亡、炎症反应过程而实现的,同时FSTL1 的过表达也可使缺血再灌注损伤最小化。这些研究结果提示FSTL1 有可能成为改善心肌梗死后心脏重塑的新型治疗靶点。
FSTL1 作为具有保护作用的心脏因子除了在缺血性心脏疾病中发挥作用外,也可分泌至外周,进而对其他疾病的发展产生影响。野生型小鼠模型及特异性FSTL1 基因敲除的小鼠模型进行肾切除手术后,特异性FSTL1 基因敲除的小鼠模型表现出更严重的尿白蛋白排泄,肾小球肥大和肾小管坏死后的肾小管间质性纤维化;相反,给予肾切除术后的野生型小鼠表达FSTL1 的腺病毒载体,上述症状及炎性反应显著改善;此外,FSTL1 处理培养可减少人类肾小球系膜细胞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引起的促炎细胞因子表达,而抑制AMPK 信号通路后FSTL1 的这一抗炎作用不再发生[26]。以上结果证实了FSTL1 减轻炎性反应及改善纤维化的作用,揭示了其在缺血性心脏疾病中的应用潜力。
4 Sfrp2
Sfrp2 是Sfrps 家族最强的Wnt 信号拮抗因子,先前研究指出Wnt 信号通路的成员广泛存在于晚期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中,并且与血管炎症、内皮功能障碍、内膜增厚、钙化等动脉粥样硬化特征性改变等密切相关[27]。作为应激诱导型心脏因子,Sfrp2 在心肌梗死后的啮齿动物心脏中的表达显著上调,且表达Sfrp2 的细胞呈现成纤维细胞外观,表明心脏成纤维细胞是该蛋白质的主要来源[28]。
Sfrp2 可通过抑制典型的Wnt 信号传导在干细胞的细胞保护、抗凋亡、促血管新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最近的证据表明,Sfrp2 亦可不借助Wnt 信号传导而调节梗死后心脏的心脏纤维化。Sfrp2 可直接增强骨形态发生蛋白1/Tolloid 样金属蛋白酶的前胶原C⁃蛋白酶活性,从而导致胶原沉积的增加;Sfrp2 基因敲除小鼠表现出胶原含量和纤维化的减少以及心肌梗死后心脏功能的改善;而更深一步的研究表明Sfrp2 对骨形态发生蛋白1 活性具有双相作用,高浓度的Sfrp2 在体外抑制骨形态发生蛋白1 的活性,而低浓度的Sfrp2 增加了骨形态发生蛋白1 的活性;并且心肌梗死2 d 后,将治疗剂量的Sfrp2 直接注射入梗死的大鼠心脏可减少心脏纤维化及改善心脏功能[29]。此外,在小鼠梗死周围的心肌细胞间注射间充质干细胞可导致血管密度增加,梗死面积减小,改善心肌梗死后心脏功能的恢复,这些有益作用归因于Sfrp2 的旁分泌功能[30]。
5 MIF
MIF 是一类高度保守的与炎症疾病密切相关的因子,在心脏中可由心肌细胞表达储存。在心肌梗死后,坏死心肌细胞即刻释放MIF,导致其在血液循环中的水平升高[31],且心肌梗死后循环中的MIF 浓度与心肌梗死的面积密切相关[32],因此MIF 有望成为心肌梗死诊断及预后评判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MIF 通过与细胞表面受体CD74 的相互作用可刺激AMPK 活化,促进心脏中的葡萄糖摄取;MIF 缺乏可导致局部缺血区AMPK 信号转导和葡萄糖摄取减少,加重缺血区的心脏损伤[33]。在动物实验中,老年小鼠心脏在缺血期间显示AMPK 活化障碍并MIF 表达减少,而外源性MIF 可增强缺血期间的AMPK 活化并改善这些心脏的泵血功能[34]。缺血/再灌注后的MIF 缺陷也将导致c⁃Jun 氨基末端激酶活化的增加及心肌细胞凋亡[35]。因此,MIF 作为保护性心脏因子,至少可通过2 种机制来保护心脏免于缺血/再灌注损伤:在缺血期间增强AMPK 活化并抑制再灌注期间c⁃Jun 氨基末端激酶激活。这些研究表明MIF 可保护心脏免于缺血性损伤,并且在缺血期间对MIF 依赖性信号通路的操纵有望成为预防心脏损伤的新型策略。
相关文献报道MIF 基因的⁃173G/C 位点的多态性与冠心病关系密切,且MIF 具有细胞特异性以及启动子多样性等方面的特征[36],即心肌梗死后不同细胞来源的MIF可能发挥着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生理作用。研究人员使用心源性MIF 缺陷小鼠及白细胞MIF 缺陷小鼠进行实验,发现后者心肌梗死后心脏破裂的发生率较低,而与之相比,前者不仅心脏破裂发生率高,且心脏未破裂小鼠的心室扩张及功能紊乱的发生率也明显增加[37]。据此推测,只有来源于心肌细胞作为心脏因子存在的MIF 才能改善心肌梗死预后、保护心脏功能,而来源于浸润炎症细胞的MIF 则作用相反。类似的,在心肌短暂缺血缺氧后,心源性MIF 占据主导而发挥保护心肌作用,而随着缺血缺氧时间的延长,程度的加重,炎性细胞释放的MIF 逐渐增多,由其引起的炎症反应最终加剧心肌损伤[38]。更深一步的研究发现不同来源MIF 的这种双重作用可能与其半胱氨酸⁃81 残基上的亚硝基化修饰相关[39],亚硝基化MIF细胞内积累的有益作用可能为心肌缺血损伤的治疗提供新的途径。
6 NRG
NRG 是表皮生长因子家族的成员之一,在心脏中NRG主要由微血管内皮细胞和心内膜表达,并且局部缺血损伤可刺激其分泌[40]。心肌细胞表面存在NRG 的酪氨酸激酶受体—ErbB[41],NRG 与之结合从而发挥促进血管生成、逆转心肌重构、减少细胞凋亡和减少氧化应激等作用,近来发现NRG 也是心血管系统中重要的信号蛋白,在心脏发育成熟以及心脏功能维持方面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42]。HEDHLI 等[40]研究表明缺氧损伤可诱导人心肌内皮细胞表达和释放NRG,且NRG 能减少人心室肌细胞的凋亡;将成年小鼠心肌细胞与人脐静脉、小鼠肺微血管、人冠状动脉内皮细胞共培养也能够保护心肌细胞免受缺氧⁃复氧损伤诱导的细胞凋亡;而NRG 基因缺失或内皮细胞中NRG 表达沉默将导致心肌缺血后收缩功能恢复受损及冠状动脉结扎后梗死面积的增大。此外,NRG 还可能直接对心脏成纤维细胞起作用而抗纤维化[43],其诱导IL⁃1α的产生以及促修复因子(促血管生成素⁃2、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等)的分泌,通过旁分泌信号在心脏修复中发挥作用[42]。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心脏内皮细胞来源性心脏因子NRG 对缺血心肌具有保护作用,有可能成为治疗冠心病的新靶点。
综上所述,心脏因子可辅助冠心病特别是急性心肌梗死临床诊断,评判临床预后,并为开发新的冠心病治疗靶点提供理论依据,明确心脏因子的生理作用及机制可为冠心病的诊疗提供新的途径和思路(表1)。然而,心脏因子在体内作用机制复杂,其可能与调节细胞分化凋亡、介导炎症过程及参与脂质代谢等密切相关,且部分心脏因子在冠心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促进心脏损伤修复或加重心脏功能失衡的作用尚存在一定的争议,需后续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探讨。

表1 心脏因子在冠心病中的生理作用及应用前景Tab.1 The roles of cardiokines in CH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