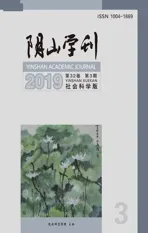孟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四重奏”
2019-03-02林於明
林 於 明
(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1700)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1]4。这句名言流传至今已两千多年,但其中的观点依然没有过时。尤其是在中西政治交流与碰撞日益频密,“人类命运共同体”初现雏形的今天,对不同政治哲学进行对比分析是一个越来越值得探讨的问题。孟子和亚里士多德作为东西方文明中的两位思想巨人,在各自所属的文明中对政治哲学做出了卓有成效和影响深远的探索,他们所奠基的政治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后世政治构建的蓝本,尤其是他们在各自的文明领域内所展开的对人的“共同命运”的深刻诠释,在今天更加值得思考和弘扬。
一、时代更迭的变局与顺应历史的改革
孟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都充满强烈的扭转时势的使命感,从历史背景上看,双方又都面对着极为相似的境况。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经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希腊语世界,迎来了重大的时代变局,各邦国间的竞争日益加剧,不同的政治理念陷入日益严重的对立,随着战争的结束到来的并不是和平,而是贸易衰退、贫富分化、土地兼并,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动荡让整个希腊世界陷入长期动荡,伯利克里和梭罗等一众希腊圣贤开创的“黄金时代”至此走入黄昏[2]。
在孟子所身处的春秋时代的中国,现实则更为残酷。经历了骊山烽火和平王东迁,周室衰微,时局日坏。随之而来的是乾坤倾摇,天下骚动,昔日相安无事的大小诸侯,在各自的一己私利的驱使下,日益对立,势成水火。更重要的是,许多重要的政治原则,被弥漫于各诸侯国的“唯利是视”之风所侵蚀,普天之下成为一片利益角逐的战场[3]。孟子出生之时,春秋乱世已延绵百余年,面对各国纷争的混乱现状,这位与亚里士多德几乎同时代的思想家凭借“舍我其谁”的精神,努力为天下构想着一套“拨乱反正”的方案,与同时代的许多有识之士一样,他首先想到的是对当时的政治哲学进行改革。
由于孟子的政治哲学构建时不乏理想主义情怀,故而时常被视为不谙当时“变法”之道的复古主义者,但事实是这位虔诚而睿智的思想家在维护“三代”传统的同时,也丝毫不缺少对现实的冷静认识。在孟子看来,春秋时代的天下之所以剧烈动乱,原因就在于诸侯国都只顾眼前利益而置“天下”的长远未来于不顾,各国一方面固步自封,一方面又野心勃勃。面对这样的局面,为了警醒诸侯,孟子奋袂直呼:“厄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4]10,他甚至还直言不讳地说:“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4]165。不过在批判的同时他也很注意从正面向诸侯们提出劝告,比如“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4]168。并且,孟子非常重视大国的示范作用,并以“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来规劝大国在“法先王”方面做出表率[4]57。他的这些主张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他对某种在今天被称为“实质正义”的追求,他的改革所立足的不是某种抽象的程序化构建,而是人民的实际生存境况。
与孟子相比,亚里士多德虽然并未提出类似孟子那样明确的政治改革的口号,但他对希腊城邦政治的研究倾向却非常明显地体现着这种倾向。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哲学上的改革倾向较孟子似乎要更加细致具体,他不仅在理念上对前人的政治理想进行了继承,还从学术层面对古希腊的城邦政治进行了全面总结。为探寻前代古希腊城邦政治中某些值得传承的带有共性的特质,他与他的学生先后对将近一百六十个希腊城邦的政治模式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其目的就在于试图从中找到恢复城邦政治生机活力的可行办法。虽然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与伦理学分离开来,但在从事具体的政治研究时,亚里士多德始终偏向于从伦理层面对政治的基本原则进行考察,因为在他看来政治学与伦理学的差别主要在于:前者的研究主要偏向于“共同的善”;后者的研究更偏重于“个人的善”。立足于城邦与人之生活的有机关联而展开对政治哲学的研究,这始终是亚里士多德所坚持的理论路径,这种研究方式本身就体现着他对从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经柏拉图而一直传承着的希腊先贤的古典主义传统政治哲学的继承与发扬。而且他由此研究而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被理解为是早期希腊政治哲学的更具理论性的再现,或许亚里士多德本人可能不大会承认这种说法,但其中所存在的明确的传承关系已被后世学者所证明——麦金泰尔在这方面进行过说明[注]麦金泰尔的相关论述在《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中多有体现,譬如:1.“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性只有依据一种他本人不承认、也不可能承认其存在的传统才能被确定。正因为亚里士多德与其他古希腊思想家一样,缺乏任何我们所谓的那种特定的历史感,从而这不仅妨碍他承认自己的思想乃是某种传统的一部分,而且严重限制了他的叙事观”。2.“正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理论把古典传统构建成一种道德思想的传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牢固地确立了他的诗人前辈们只能断言或暗示的东西,从而使古典主义传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传统”。。
二、“共同命运”的恢复与政治基石的巩固
任何政治哲学都必然有其作为理论之基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就是“城邦”和“公民”,并且他强调,这两者并非是截然二分的两种东西,而毋宁说是一种相同的东西在两个不同层面的表现:其宏观表现是城邦,其微观表现则是“公民”。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志在重新唤醒他那个时代的希腊人对于城邦—公民之间的共同命运的觉悟,因为在他看来,城邦不仅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更在于它承载着所有人的“共同命运”和人作为人的基本属性。更具体地说,只有在共同体的生活中人才能真正懂得“友爱”——这是一个对希腊人来说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只有在城邦中才有可能过上一种幸福、自足且有德性的生活,这也是形成古希腊传统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因素。所以他说:“如果一个人离开了城邦还能生存的话,那他要么是神,要么是兽”[1]8。
城邦的整体利益之所以被视为最高原则,正是渊源于希腊的城邦与公民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命运关联。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在处于“黄金时代”的古希腊,城邦的成员与城邦之间向来就是“小我”与“大我”的关系,换言之,两者之间具有“同构性”,或者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作为人的公民所聚居的城邦是相对于公民而言的宏观意义上的“人”——就像柏拉图所分析的那样[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城邦与人的“同构性”的描述是这样的:人的灵魂由理智、激情、欲望三部分构成,这三者分别存在于人的大脑、胸腔、胃中,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关系。以此模拟,一个城邦也应该由统治者、武士、劳动者三部分构成,他们分别代表着理智、激情、欲望。统治者应该具备的德性是智能,他们负责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配,武士的德性是勇敢,他们保护城邦不被侵犯,维护城邦内部的秩序,劳动者的德性是节制,他们应懂得控制欲望,辛勤劳动,提供生产数据和生活资料,三个等级的人各司其职,各尽其力,这个城邦就能实现正义。亚里士多德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并沿袭了这种看法。。
虽然和所有西方思想家一样,亚里士多德也强调自由的作用,但这个概念在他的政治哲学中是被置于在一种非常清晰务实的意义上理解的,更具体地说,一个人的自由是通过对城邦的公共命运的积极关切——亦即对城邦事务的积极参与——来体现,如果脱离这种以共同命运为背景的现实条件,自由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变成了一种空洞的东西。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与孟子的政治哲学都建基于一种对“命运共同体”的深刻理解,如果说在前者那里“命运共同体”是城邦,那么在孟子那里则是“天下”。孟子的天下显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一种时空泛指,而是一种有着明确政治内涵的概念,更具体地说,就是由各诸侯国及其下属的无数氏族之家所组成的那个有着内在命运关联的天下。如果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哲学的首要关系体现为“城邦”与“公民”的同构性关系,那么在孟子那里,这种首要关系则体现为“天下”与“家国”的整体性关联。
当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孟子所维护的“天下”是专指周天子的天下,相反他那条著名的政治口号——“五百年必有王者兴”[4]109——或许能更直观地体现出他对日益衰微的周王室的态度。实际上孟子的“天下”不仅是指处于华夏文明所及之处的各个政治实体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更是指这些政治实体之间久已存在的共同命运。因此,当魏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时,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要“定于一”[4]12,不过他并没有说这个“一”到底指代谁。由此可见,在孟子看来由谁来定天下于“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天下必须重新定于“一”,亦即使天下的“共同命运”得到恢复和巩固,这显然不仅指各诸侯国在一个统一政权之下的重聚,更是指普天之民在一种共同命运之中的重新团结。这其实是孟子政治哲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因为这是进一步引申出“王道仁政”的前提,其中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一方面天下必须要“定于一”,另一方面这个目标很难实现,由此推理,要想实现此目标就必须有一套极富远见的政治理念,而什么样的政治理念最有远见呢?那无疑就是“王道仁政”了。
因此“定于一”是孟子的整个政治哲学的基本出发点,若是没有这一点,孟子的其他主张——包括最核心的“王道仁政”——就很难推出来,因为如果仅仅只是为了实现一国一家的安定,那么未必非要行“王道仁政”不可,还有其他很多方式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但如果要“得天下”,那么在孟子看来则必须行“仁政”不可,因为“不仁而得国者,有之也,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4]328。也只有由此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孟子何以凡事都要从“天下”的角度进行立论的原因,因为“天下”在他眼中已不仅仅是政治行动的对象,更是一种共同的命运,是他的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面向未来的价值核心重构与再造
由于在孟子的理解中,天下重归于安定的前提是“定于一”,故而推行“王道仁政”就显得格外重要——这就引出了孟子的政治哲学中最核心的支点。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孟子在倡扬“王道”的同时要不遗余力地反对“霸道”的原因。或许以孟子之智,不可能看不到“霸道”所能带来的各种速效的短期利益;但以孟子之贤,又注定了他不会赞同“霸道”,因为他很清楚,这种政治哲学讲究的是“以力服人”的“力政”,如此一来,不仅天下纷争永无平息之日,由此引发的诸侯“嗜杀”势必愈演愈烈,以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4]13。当然,各国诸侯未必主观上都有“嗜杀”的变态倾向,齐宣王“以羊易牛”的举动就是最好的例子,但在客观上,“嗜杀”与“霸道”及“力政”确实又有着很强的因果性,并且与孟子所重视的“民心所向”完全背道而驰。孟子的政治哲学一直反复强调“民心”的重要性,这与周初所倡导的“天听自我民听”的观念一脉相承,这也是他敢于为自己的“仁政”和“王道”赋予政治上的至高合法性的底气所在,因为在他看来任何推行“霸道”和“力政”的诸侯都不可能使民心悦服,哪怕他们“以力假仁”,也终究不免于成为“三王”“五霸”的罪人[4]287-288。相反,如果遵“王道”而行“仁政”那么情况就会是“民之归之,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4]13而一旦这样的局面形成,结果将是“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4]325。
实际上孟子对其“王道仁政”的立论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方面他强调的是“仁政”和“王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则突出“霸道”与“力政”的局限性。在孟子看来,用“霸道”平定天下,在当时他所能看到的局势之下还没有可能,因为各国的力量相差还并不悬殊,任何一方都不具压倒性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想凭一己之力扫平诸侯非常困难,即使一时得势也很难持久,因为“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赡也”[4]74,故“虽与之天下,不可一朝居也”[4]293。孟子的这种看法在他与齐宣王有关“王之大欲”的政治对话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注]事见《孟子·梁惠王上》:齐宣王向孟子求问作为“霸道”之典范的“齐桓晋文之事”,并在其间隐晦地透露了自己的“大欲”,孟子则一语道破齐宣王的“大欲”无非就是“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并直言齐宣王的大欲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实现,无异于“缘木求鱼”,理由是“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这就非常直白地提醒齐宣王“霸道”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是仅凭齐国现有实力不可能做到的。以此为据,孟子像齐宣王建议要行“仁政”,认为行“仁政”将会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并且能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这样一来,“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也由此,孟子顺理成章地推出了他在重构社会价值方面的核心主张,那就是维护“天下”的“共同命运”所赖以存在的基石——仁义。当然,秦国在后来的战国纷争中的最后胜出,或许会对孟子的这种政治哲学形成一定的非难,但其传二世即亡的命运,又何尝逃脱了孟子的“不可一朝居也”的预言?
如果说孟子所认为的社会价值的核心是“仁义”,那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个核心则非“公正”莫属。“公正”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绝不仅仅只是一个伦理概念,而是具有某种形而上意味的伦理实在,因为这是整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概念,代表着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最本质追求。公正的意义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是多层次的:一方面它是维系城邦政治良好运转的基石;另一方面也是个人所应该具有的基本德性——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一切个人德性的核心。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学的大厦之基是“德性”,而德性之基则是公正,因为“公正乃是一切德性的总汇”[5]94。值得强调的是,亚里士多德对于公正的探讨总是与现实生活的实践性保持着一种紧密的呼应,正如他所说:“公正就像其它德性一样,是在实际活动中生成的,正如建造房屋才能成为营造师,弹奏竖琴才能成为操琴手。同样,我们做公正的事情才能成为公正的”[5]31。
不过,公正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之所以重要,不仅体现在它对个人德性的重要性,更在于“在各种德性中,惟有公正是关心他人的德性”[5]95。这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公正不是一种抽象笼统的东西,而是与城邦人民的共同命运的维护紧密相关的,事实上,在上述两种意义上的公正之中,前者是高于后者的,即城邦的公正高于个人的公正。并且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人是否能让内心的公正始终与城邦的公正看齐,是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正的人”的重要标准。而成为“公正的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不仅关乎一个人能否获得真正的幸福生活,也关乎着城邦的持续和谐和稳定。
始终不能忽视的是,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公正”是以城邦为基准,在层面上说,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维护一种可使希腊人实现对“幸福”之追求的“共同命运”,故而他说他所探求的不仅是一般的公正,而是政治的或城邦的公正。亚里士多德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对“公正”进行细致阐释,其最终目的不仅在于辨析“公正为何”,更在于借此探讨“公正何为”,即要以“公正”为原始坐标,为希腊城邦政治的新生探寻一种具有可行性的方案,并因而也使希腊公民能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获得幸福生活。
四、对于制度基础的前瞻性擘画
任何一种负责任的政治哲学,最终都必然会落实到政治生活的运行上来,在这方面孟子和亚里士多德都给出了明确的主张。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基于“公正”这一“最高正义”,他以是否能最大限度保证“公正”为基本标准,对城邦政治进行了两种分类:“正宗政体”和“变异政体”。亚里士多德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借此重新构造一种特定的完美政体,而是希望通过这种对比和分类来确立政体之正义性的基本原则,对此他说得很明白:“应该牢记政体每一类属的各个品种,知道了有多少品种还得明白每一品种的政体是怎样构成的”[5]185。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比选择什么样的政体更为重要的是,选择什么样的原则来进行城邦政治的构建,虽然他一直都在寻找着一种“最优政体”,但他更看重政体的价值原则而不是政体的表象。更具体地说“最优政体”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意味着一种能使“公正”这一德性以各种形式贯彻到城邦政治之中的政体,亚里士多德为此设置了最优政体需要遵从的三大基本原则:法治、平等、公共利益。
“法治”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对“公正”进行界定和衡量的准则,因为人与人的生活总是相互牵涉的,且“公正自身作为一种完满的德性,它不是笼统的一般,而是相关他人的”[6]。如果一个人要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首先就应该明白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界限,这种界限由于不可能总是得到所有人的忠实遵守,因此就需法律来予以明确。
而“公共利益”之所以需要被强调,则因为“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1]95,这就意味着公共利益不仅是公正之德性在现实层面的具象化体现,同时也维系着城邦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一致追求。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从来都不是脱离人的实际生存境况的理论抽象,而是基于人对于幸福生活之追求的某种共性,故而他才会说:“对于每一个人和对于城邦共同体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群,最优良的生活必然是同一种生活”[1]138,并由此而更进一步说:“一种善即或对于个人和对于城邦来说,都是同一的,然而获得和保持城邦的善显然更为重要、更为完满”[6]。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亚里士多德主张“无论对个别人还是对城邦的共同体而言,最优良的事物是相同的,立法者应该把这些事物植入公民们的灵魂中去”[1]146,而维护公共利益就是在履行这一使命。事实上,虽然亚里士多德将政治学和伦理学分作了两种学科,但他对政治的理解始终还是从伦理的方面出发的,因为政治在他那里的最高作用在于维护城邦及其所代表的一种有德性的幸福生活,简而言之,城邦政治要为人们的幸福负责。既然要维系“公共利益”,那么“平等”就理所当然地要同时得到保障,因为在一个正常的城邦中,如果公民之间的平等得不到保证,“法治”也将很难维持。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的最高使命是探寻一种“最优政体”及其原则,那么相同的使命在孟子那里则体现为对“王道仁政”的阐发。“王道”和“仁政”从形上和形下两方面构成了孟子心中最理想的政治形态。“王道”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代表着一种正直无私的政治哲学,所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个概念在孟子那里被赋予了一些新的含义,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重民”和“保民”,在他看来政治的最高合法性在于符合“天意”,而“民心所向”则是“天意”的根本表征,因此他非常强调“保民而王”。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孟子才有足够的底气在“尊君”“尚同”的思想风靡天下之时高扬“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大旗。
与抽象层面的“王道”所对应的是现实层面的“仁政”,其基本特征在于:通过“与民同乐”和“尊贤使能”而行“不忍人之政”,其前提则是“不忍人之心”,正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4]79,这一点体现在具体层面上,就是要按照人民的实际承受能力制定合理的“宽政”。但所谓的“宽政”在孟子看来也不是一味地向民众进行超出国家承受能力的政治许诺,正所谓“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4]294。正因如此,孟子更强调国君对于国情的全面体察,而非对某些道德教条的片面奉行。故而当齐宣王以“寡人有疾”为由不行“仁政”时,孟子以“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指出行“仁政”的关键不在于执政者的一些个人习惯,而在于要有“乐民之所乐”的政治觉悟,因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4]33。
孟子的“仁政”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尊贤使能”,更具体地说就是“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4]75。孟子同时强调,“尊贤使能”很难一蹴而就,形成这种局面的关键在于重造“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的良好局面[4]298-299。这就意味着打破社会阶层之间如地壳般坚硬的阻隔,释放各阶层内部的人才潜力,从而为国家的发展注入持久后劲,一旦有这种局面,那么“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4]29。由此可见,孟子与亚里士多德在制度构建的具体主张上虽有不同,但两者的理论核心却颇为一致,那就是要把复兴建立在一个“公”字之上,两者的区别只在于各自具体的政治语境有所不同。
五、结 语
亚里士多德和孟子的政治哲学,相互之间存在着极强的思想共识和精神默契,虽然那时双方都被重洋峻岭所阻隔,但彼此之间可贵的共识也足以引发更多的思考。当今世界,以多元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在孟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是有其根基的,尤其是这两种政治哲学都追求共识而非差异,注重实质而不是形式。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并不强调某种特定的政治表象而注重考察政体的内在实质是否公正,其所追求的“自由”也非空洞抽象的自由,而是极具现实意味的自由;相应地,孟子的政治哲学看重的也不是抽象的“政治合法性”而是现实的“民心所向”,他的政治哲学所追求的是“天下”的长远利益,而不是一时一地的优势地位,所有这些,无一不是今天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镜鉴,因此如何扩大两位圣贤的这些共识的现实意义,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