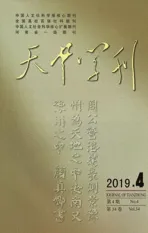弃“仙”取“圣”
——论潘德舆基于儒家诗教的李白接受
2019-01-19蒋润
蒋 润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李白与杜甫向称诗国双璧,孰优孰劣,难分轩轾,可是在很多人眼中,李白地位实在不如杜甫,历史上虽也有如欧阳修这样扬李抑杜的例子,但据实而论,扬杜抑李的趋向才大占上风,这从李杜二人的诗集注本数量即可略见一斑。后人尽可称杜甫为“集大成”,为诗中之圣人,其诗可学,其人可法,但很少有人认为李白是“集大成”,更多的人认为李白诗只可赏,不可学,李白人格亦多瑕疵,不似老杜醇正。在传统“诗教”观念下,李白如同不受羁绊的闲云野鹤,始终让人觉得飘忽不定。
但是李白是否确实如此,又非一确论。抑李者固然不妨在“诗教”的视野下鄙夷“诗仙”,一个推崇李白而思想活跃的人,也不妨标举“诗仙”而搁置“诗教”。但是,作为既推崇“诗教”,又喜爱李白的诗论家,就不得不在“诗教”与“诗仙”这两者中找到一个平衡,清人潘德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服膺朱熹之说:“作诗先看李、杜,如士人之治本经,本既立,方可看苏、黄以次诸家。”以李、杜为诗中之经,既为诗“经”,则必重诗教。那么,如何将后人眼中飞扬跋扈的“诗仙”纳入其“诗教”体系,就成了潘氏亟须解决之问题。在其所著《李杜诗话》①里,潘德舆通过弃“诗仙”之名而取“诗圣”、标举太白之复古与学问、辨正太白之出处等策略,在李白诗批评中贯彻了他的诗学观念。他的论述,既让我们看到了李白诗所具有的多种向度,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了潘德舆身处嘉道之时力尊“诗教”的诗学取向。
一
潘德舆对朱熹以李、杜诗为“本经”说法的第一个回应,是他选取李、杜二人之诗所编的《作诗本经》。在《作诗本经》序中,他明确地将李、杜诗在诗学上的地位与《诗经》在经学上的地位相连:“《诗》三百篇,不尽出于圣人,孔子断以为经,万世奉为定论而经之,三代而下,诗足绍三百篇者,莫李、杜若也……朱子虽未以李、杜之诗为经,而已以李、杜之诗为作诗之经矣。”[1]445以李、杜诗为诗中之“经”,就必须矫正时人对李、杜的误解,比如“大李之才而骇其变,服杜之学而憎其朴”[1]445之论调。在李白这里,最先需要矫正的,就是“大李之才而骇其变”的观念。
李白为诗人中才华一派的代表,久为人所论定,如《海录碎事》即云:“唐人以李白为天才绝,白乐天人才绝,李贺鬼才绝。”[2]由其天才,则以为其诗无法可循,《沧浪诗话》云:“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3]169又云:“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3]170飘逸则如飞仙幻变,莫可究诘,杜甫诗如孙吴,皆有法可循,而李白诗如李广,则变化错综,难知踪迹。因其诗之幻变,渐渐生出李白诗不可学的论调,如胡应麟《诗薮》:“李、杜二家。其才本无优劣。但工部体裁明密。有法可寻。青莲兴会标举。非学可至。”[4]李白诗既不可学,就不能作为诗学准的,所谓“大李之才而骇其变”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逻辑结构。潘德舆既要反对此点,就要力排后人加在李白身上的神秘色彩。他的方式,就是首先摒弃“诗仙”这个称号。他先引朱熹的话云:“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潘德舆以为此语为最知太白:“古今论太白诗者众矣,以朱子此论为极则。他人形容赞美累千百言,皆非太白真相知者,以本不知诗教源流。故子美为‘诗圣’,而太白则谓之‘诗仙’,万口熟诵,牢不可破。究竟仙是何物?以虚无不可知者相拟,名尊之,实外之矣。”[5]175“不知诗教源流”即指上文所述以李白诗为天才不可学的说法。潘德舆以为这些说法明虽赞美,但暗地里却引人疏离了太白,就像“诗仙”这个称号一样,虚无不可知,人虽然羡慕却绝不会亲近。因此,他对“诗仙”这个称号进行了质疑:“若缘谪仙之号定于贺监,谪仙之歌赋于同朝,少陵赠什亦尝及之,遂为定评。不知贺监老为道士,回惑已深;明皇好仙,朝列风靡,无稽品藻,何足效尤;少陵特叙其得名之始云尔,非以为确不可易也。且贺监又尝目之为天上星精矣,岂可从张旭‘太湖精’之例,以‘诗精’目之乎?若见太白咏仙者多,乃以‘诗仙’当之,则高如郭璞,卑若曹唐,亦将号以‘诗仙’耶?”[5]175潘氏这番驳论其实并不得当,“诗仙”流行后世,未必全是因为贺知章与唐明皇的标举,所以通过批评二人人品不足来否定“诗仙”之名实属无稽,以为太白咏仙诗多遂号“诗仙”,也非抉微之谈。但是他否定“诗仙”这个名号,是为了避免人们对李白“名尊之,实外之”,所以结果远重于论证。“诗仙”之名既不恰当,当以“诗圣”代之,潘氏云:“朱子以其从容法度为圣,何等了当!杨升庵曰:‘太白为古今诗圣。’语据朱子,颠扑不破。”[5]175以“诗圣”代“诗仙”,并不是说要扬李抑杜,因为在后文中,潘氏又说:“三代以下之诗圣,子建、元亮、太白、子美而已。”可见在他眼中,“诗圣”并非某一人之专称,诗人人品既高,诗作又足以为后人模楷,则可称“诗圣”。以“诗圣”称李白而摒弃“诗仙”之名,第一,可扫除李白身上的道家气息,而归于儒家的醇正;第二,可破除李白诗的神秘色彩,免得时人以“不可学”而疏远李诗。
二
李白诗既可称“诗圣”,那这“圣”处在哪儿?就潘德舆的论述来看,一在李白诗之能复古,二在李白诗之忠厚,三在李白诗之功力。潘德舆在《李杜诗话》第五条中,引严羽《沧浪诗话》云:“观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太白天才豪逸,语多卒然而成,学者于每篇中识其安身立命处可也。”潘氏对此中“安身立命”一语大加称赏,以为其极有见地。这其实也代表潘德舆认为李白诗可学处即其“安身立命处”,李白诗的“安身立命处”何在?潘氏云:“吴子华所谓‘太白诗气骨高举,不失《颂》咏、《风》刺之遗’者,即其‘安身立命处’矣。”[5]177这句话引吴融之说,值得注意处有二,一则“气骨高举”,一则“不失《颂》咏、《风》刺之遗”。“气骨高举”,固为李白诗最主要的特点,如叶燮不许李白之才,对他的“气”却极为推崇,可见这是李白诗最具特色之点。“不失《颂》咏、《风》刺之遗”,则关系到潘德舆最为重视的一点,即李白诗能复古道,上接《诗经》。
潘德舆论诗,最重“诗教”,尤以《诗经》为论诗准的,他在《养一斋诗话》开篇即说:“‘诗言志’,‘思无邪’,诗之能事毕矣。人人知之而不肯述之者,惧人笑其迂而不便于己之私也。虽然,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之诗,物之不齐也。‘言志’、‘无邪’之旨,权度也。权度立,而物之轻重长短不得遁矣;‘言志’、‘无邪’之旨立,而诗之美恶不得遁矣。”又说:“《三百篇》之体制、音节,不必学,不能学;《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也。神理、意境者何?有关系寄托,一也;直抒己见,二也;纯任天机,三也;言有尽而意无穷,四也。不学《三百篇》,则虽赫然成家,要之纤琐摹拟,饾饤浅尽而已。今人之所喜,古人之所笑也。汉、唐人不尽学《三百篇》,然其至高之作必与《三百篇》之神理、意境闇合,而后可以感人而传诵至今。”[5]5―7故而在潘德舆这里,诗惟能上溯《诗经》方为好诗,李白诗之所以能称“圣”,实由于他能上挹《风》《骚》。在《李杜诗话》第十条中,潘德舆即以复古为标准,道出李白诗高出储光羲、王昌龄等人的缘由:“太白尝言:‘齐、梁以来,艳薄斯极,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其一生式靡起衰,全在古风、乐府。储、王、高、岑诚一代之翘秀,顾其志非以古道自任者也,恶得与太白争席哉?”[5]180因太白诗能复古,故能超人一等。所谓能复古,不是像明代李、何等人那样的徒事摹拟,而是一种精神气韵的相通,就是如上引《诗经》的神理、意境一样,能做到有寄托、直抒己见、纯任天机、言有尽而意无穷。在论述李白七言古诗时,潘德舆就对王士禛将李白与岑参相比不以为然,他以为与李白比起来,岑参虽然奇峭过人,但也只是达到人力的极点,“天弢未之解”,不如李白诗能出之自然。李攀龙等人以初唐的七古为标准,以为李白七古不佳,也为潘德舆所讥,他认为“诗之古与不古,视其天与不天而已矣”,所以以天然而论,李白的七古才是真正的佳制。
在潘德舆看来,李白诗的复古,还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体裁上,而是一种全面的复古,他在阐述李白五古时说:“太白胸次高阔,直将汉、魏、六朝一气铸出,自成一家,拔出建安以来,仰承《三百》之绪,所谓‘志在删述’、‘垂辉千春’者也,岂专主《选》体哉!”在论五律时也说:“按太白复古之功不独在乐府歌行,于五律亦可见。《李诗纬》所谓‘太白五律,犹为古诗之遗,特于《风》、《骚》为近’,是也。”[5]181―183
能复古,则诗能“厚”,不至于轻佻浮薄,潘德舆在《养一斋集》卷首即云:“诗只一字诀,曰厚,厚必由于性情,然师法不高,乌得厚也?”[1]250他这一说法直承《沧浪诗话》“取法乎上”之说,即李白能师法《诗经》《楚辞》,故而根本质实,后人仅以其才而夸誉之,实在是未能懂李白诗佳处。在《李杜诗话》第十条,潘德舆就对王世贞的说法大加嘲笑:“太白树复古之伟功,王氏谓其极才人之能事而已,亦浅矣哉!”[5]180
除了论李白能复古,潘德舆还对李白的才学进行了辨正,即人皆以为李白才胜于学,甚至认为李白作诗纯恃才气,潘德舆以为不然,他引方弘静之说,以为太白在匡山下读书十年,在浔阳狱中时,犹读《留侯传》,可见李白诗之精妙,亦由于学力精纯,并不是纯恃天分[5]190。
前人称赏李白,皆由于其才高,纵横捭阖,人所难及,但潘德舆对此一翻旧案,独抉发出李白之复古与学问,以为这是李白诗的根本所在。潘德舆在其《太白楼放歌》中云:“幸哉论诗爱复古,此意不为先生羞。”[1]341可见他对自己这一论述颇觉自信。
三
李白诗之所以能复古有成,根本又在于李白之人品。
《李杜诗话》第九条云:“葛氏立方曰:‘李白乐府三卷,于三纲五常之道数致意焉。虑君臣之义不笃也,则有《君道曲》之篇;虑父子之义不笃也,则有《东海勇妇》之篇;虑兄弟之义不笃也,则有《上留田》之篇;虑朋友之义不笃也,则有《箜篌谣》之篇;虑夫妇之义不笃也,则有《双燕离》之篇。’按此条于太白诗能见其大,太白所以追蹑《风》、《雅》,为诗之圣者,根本节目实在于此。后人震眩其才,而不知其深合古诗人之义,故誉之则谓其‘摆去拘束’,如元微之;毁之则谓其不达义理,如苏子由,皆大误也。”[5]179此段中最要者,即“李白乐府三卷,于三纲五常之道数致意焉”与“太白所以追蹑《风》、《雅》,为诗之圣者,根本节目实在于此”两句。潘德舆认为李白之所以能复古,能以“诗圣”为名,根本在于李白对儒家纲常礼教的服膺,以人品论诗品,故人品愈高,诗品愈好。能复古固然好,但若人品不佳,也不足观。与此相对的,是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对陈子昂的痛诋,以为陈子昂诗虽能复古,但其人则小人,所以其诗必不可学,“人与诗有宜分别观者,人品小缪戾,诗固不妨节取耳。若其人犯天下之大恶,则并其诗不得而恕之”[5]7―9。潘德舆以为“诗教”与“圣教”二者不可分,德行始终应高于才华,而陈子昂谄事武则天,所以潘德舆对他深恶痛绝。
在李白这里,潘德舆面临了颇为复杂的问题:第一,李白诗确实不完全合于儒家礼教,里面夹杂了很多道家之言;第二,李白与永王璘的关系是李白一生中的一大疑点,也令后世评价者聚讼不休。
在潘德舆的“诗教”视野下,已经由“诗仙”转化为“诗圣”的李白,有必要进行最后一次清洗,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诗之圣者”,他的诗也由此才能成为“经”。
首先看潘德舆对永王璘事件的辨正。潘德舆说:“太白于永王璘一案,千古物议之所丛集。诗以教人忠孝为先,此事不辨,亦安用诗圣为哉!”[5]188潘德舆紧守孔子“大德不逾闲”的观念,对这一影响李白评价的关键事件进行了考证,并对前人种种说法加以辩驳。
潘德舆首先要判断的,是李白依附永王璘究竟是自愿还是被胁迫?他的答案是后者。潘德舆引新、旧《唐书》和李白诗集,以及他人关于此事之论断加以分析,觉得李白附永王璘是出于胁迫而非自愿,《旧唐书》云李白“在宣州谒见,遂辟从事”是误记,曾巩所谓李白在永王败后才逃走的说法也有问题。依照潘德舆的考证,李白一开始是隐居庐山,永王璘起兵,李白被胁迫入军,但他马上就逃走了,永王璘所赐予的财宝与官爵他都弃若敝屣,所以并不存在主动依附的问题。
蔡絛说李白“学本出纵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藉之以立夸功耳”“大抵才高意广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难”“若其志亦可哀矣”②。潘德舆先觉得此说“似能为太白末减厥罪”,但是接着就立马反驳,以为这似是而非。因为若照蔡氏的说法,李白就算本怀忠义之心,他的行为也还属于趋附永王璘,其罪名就难以洗脱,而且他想借永王的势力来立功名,就是包藏了私心,人格更不醇正。所以潘德舆力反此说,以为“仍非究明此案根末者”。至于王稚登在《李翰林分体全集序》中说:“灵武之位未正,社稷危于累棋。璘以同姓诸王,建义旗,倡忠烈,恢复神器,不使未央井中玺落群凶手。白亦王孙帝胄,慨然从之……夫璘非逆,从璘者乃为逆乎?”[6]潘德舆更指为大违史实。潘氏的考证是否准确,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大可疑问③,但他的态度是异常坚决的,因为这是关系到李白出处大节的问题,潘德舆决不能稍加宽贷,正如他必须辨明杜甫与房琯的关系一样。
对李白诗中所杂的异质思想,潘德舆也加以承认,并不曲为之说,不过他认为李白之所以如此,乃是愤激于世俗的混乱,他的指向还是紧紧与入世相连的,“必谓其‘凌倒景’、‘游八极’、‘折若木’、‘飡金光’等语,尽如骚人之寓言而为之讳,诚属多事。然亦由其志大运穷,如少陵赠诗所谓‘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者,乃愤而为此轻世肆志之言……譬如刘伶、阮籍之遁于酒,不可谓其纯正,亦不能笑其荒愐者也……夫太白咏仙咏佛,虽云游戏神通,终属瑕疵,不得曲护。后人于李集旁涉异教之作,学其寓言讽世者,而弃其惑溺不明者,斯为善学太白者耳。”[5]186―187在潘德舆看来,李白崇尚仙道,不过是他的小小瑕疵,与其忠君爱国并无妨碍。
在《李杜诗话》第二十一条中,潘德舆更引刘鉴、杨遂之说,以论李白的气节,以为“世人徒夸其纵横任侠之风,缥缈出群之想,而不知其忠义勃发,直抉大奸,非徒以草《清平调》、赋《行乐词》了事。”又说:“诗有本原,不可不究。性情既厚,心声乃精……太白作诗本原,与《三百篇》相表里,而虚锋掉弄之小才,狂吟烂醉之恶习,信不可以藉口学步矣。”[5]192
经过潘德舆的一番论说,李白由“诗仙”变为“诗圣”的过程即告完结。李白作为“诗圣”,其人品醇正,虽有小疵,但大节不亏,其人可法;其诗根柢学问,力复古道,并非虚无缥缈无迹可寻,故而其诗可学。
四
潘德舆在“诗教”的视野下,对李白进行了新的审视,他对李白诗歌人品的辨正都有很大的价值。不过,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他在李白诗批评中对“诗教”与“诗仙”关系的呈现,而这展现的正是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正统与异端之争。“诗教”是中国文学的正统,只有符合这一正统,作品才能称之为佳作。在潘德舆的论述之中,“诗仙”李白毫无疑问是符合这一正统观的,但是他对前人成说的谆谆辩驳以及对“诗仙”这个词的鄙弃都表明了李白的异质性。在上文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潘氏的辩驳并不是完美无缺,里面也有很多漏洞,但是他的这种辩驳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价值,即它体现出潘德舆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在树立文学经典时,是如何绞尽脑汁地清洗这些经典以便让它们归于纯正的。这种行为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源远流长,《文心雕龙》对《楚辞》的辩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潘德舆李白诗批评中对正统与异端之争的呈现,我们可以分作两层来看:第一,这是中国诗歌正统与异端之争的大传统;第二,这种正统与异端之争在清代所展现出的具体特色,是为小传统。
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是一种“大文学”观念,这种观念一方面表明在中国古代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文学概念,文学往往与整体文化相关联,很多文本都可以称为文学,另一方面又表明中国古代的文学话语体系常常与思想、政治话语相交杂,并不是独立的。在中国思想与政治话语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严分正统与异端的区别,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矣。”又说:“放郑声,远佞人。”便是这一观念的早期体现。发展到后来,这种观念成为一种正统论。正统论须有“正”有“统”,“正”即是一种标准,“统”是依此标准而产生的时间与空间上的统系。中国文化在儒家学说定鼎一尊后,在意识形态上,“正统”之“正”就是儒家的观念体系,由此在政治上有“政统”,在思想上有“道统”,谁承续儒家观念体系,谁就是正统。这个观念在中国影响很大,尤其明显的是中国的史学,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即为对此加以阐发的巨著。
史学上的正统论比较复杂,而且相对来说显性,其实在中国文学话语中,也始终有一股正统论之潜流。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当然其内涵也有着不同的变化,比如在最早的《诗经》批评中,“正”与“变”往往与现实政治相关,现实政治清明,则诗为“正”,现实政治混乱,则诗为“变”。后来“正”“变”含义有所变化,能遵“温柔敦厚”的“诗教”,或者说能以儒家经典为法的,则为“正”,否则为“变”,如刘勰明标“原道”“征圣”“宗经”之宗旨,即表明了此种“正统观”,要求后世作者“辨物正言”“正末归本”。到了唐代,这种正统观体现为“复古”,即以《诗经》《楚辞》和汉魏风骨为尚,而将齐梁之诗视为与“正声”相悖的诗国异端。李白其实也是这一正统论的拳拳服膺者,比如他在《古风》中叹息:“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等,其实就是在标榜文学中的正统④。不过,在李白身上有着比较复杂的情况,他既是文学正统论的服膺者,又时时溢出正统之外,成为后世正统论者眼中的异端。因为他的浪漫精神、仙道思想以及种种放诞的行为,让人们很难像看待杜甫那样去看待他,所以在评论者那里,就难免觉得李白驳杂不纯。这样的议论很多,比如赵次公云:“李、杜号诗人之雄,而白之诗多在于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罗大经云:“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苏辙云:“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而不知义理之所在也。”其他如陆游谓李白“识度甚浅”等,指不胜屈,即使不贬斥李白,也尽量敬而远之,推崇其才气而对其思想多有贬抑,认为其“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⑤。放在李白身上的“诗仙”这个名字,亦正如潘德舆所说,有时候也起着“名尊之,而实远之”的作用。
潘德舆作为拥有高超文学鉴赏力的批评家,不可能忽视李白诗歌所蕴含的巨大价值,但是作为秉承“诗教”正统的批评家,他又不得不认真考虑后世批评家对李白的种种驳难。刘勰在《辨骚》中对《楚辞》的论断,是肯定其“依经立义”“同于风雅”的一面,认为《楚辞》“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真正继承了《诗经》的传统,而又自有新变。继承《诗经》传统,这是大端未失,那么即使《楚辞》有诡奇谲怪的一面,也无足轻重了。潘德舆论李白,用的也是同样的策略:首先必须保证李白大节不亏,这就是他花很长篇幅来辨正李白与永王璘关系的原因;其次,要发掘李白的正统因素,他推重李白的能复古道而不是推重李白的才华,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最后,尽量清除李白的异端色彩,所以在他这里,“诗仙”应当改成“诗圣”。有了这三点保证,李白就完全合于“诗教”了。对于一些难以辩驳的问题,比如李白身上浓重的仙道色彩,潘德舆也就听之任之,只是以“小德出入可也”的态度,告诫人们那是李白不可学的瑕疵而已。从刘勰到潘德舆,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正统与异端之争,或者说正统收编异端的这个统系,似乎一直绵延不绝。
五
在清代,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在乾隆中叶以后主导诗坛,影响极大。“性灵派”诗学以其独创性与反传统性,构成了对古典诗学主流精神的一种叛逆。在潘德舆活跃的嘉道时期,江南仍为“性灵派”的风潮所影响,但是“性灵”的余风已日益走入绮靡软弱之中,加上嘉道时期整个社会的动荡,一批士子开始重新倡复古、讲“诗教”,潘德舆即其中之一。其弟子鲁一同在《安徽候补知县乡贤潘先生行状》里说他:“年二十六乃尽弃科举进士之业,力求古人微言大义。其宗旨以为挽回世运,莫切于文章,文章之根本在忠孝,源在经术,其用在有刚直之气以起人心之痼疾,而振作一时之顽懦鄙薄,以复于古。”[7]400可见他平素操守之一斑。
潘德舆的人格反映在他的文学批评上,就是以提倡“诗教”来矫正“性灵派”的纤巧。首先,他认为诗歌当有社会作用。在《仙屏书屋诗序》中,即明白道出:“诗之教严矣,先儒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承君政,述己志,持人之行也。”[1]449其次,他认为诗须浑厚质实,尤其须取法《诗经》,学习古人。诗求“厚”,已见上引,而他在《养一斋诗话》中说:“吾学诗数十年,近始悟诗境全贵‘质实’二字,盖诗本是文采上事,若不以质实为贵,则文济以文,文胜则靡矣。”[5]45这与“性灵派”后期重自我表现的风气全然不同。在潘德舆眼中,“性灵派”这些与传统诗学相违逆的东西,多少算是异端,他在给鲁一同的书信中,极论当时风气之弊:“今考据虽托名经学,实皆泛引细故陈说,用相夸奓,不问经之垂训何意也,其词章英隽,益泛益夸奓,去圣训弥远,综而论之,能以考据词章发撝圣人之心者,前数十年或有之,今未之见也。”[1]477在《诵芬堂诗序》中他也说:“士日攘臂于其中,未有从事于性情者,然亦有之,空灵以为性,而不知其为仙佛之邪说,流动以为情,而不知其为声色之丑行。诗主性情之说愈盛,而诗教亦愈敝,盖今之性情,非古之性情也。”[1]450他所认为败坏“诗教”的“诗主性情之说”,正是“性灵派”的主张,而当时人们的文学创作也过于夸诞,“去圣训弥远”,潘德舆要复“诗教”、张“圣训”,就得大力反对这些东西。他需要以传统的态度,力斥他眼中的异端,并且身体力行,通过批评来重新建构已经被歪曲的诗歌“正统”。
“性灵派”对李白的接受,更多的还是注目于他的天才与个性,如“性灵派”之殿军张问陶即被誉为“青莲再世”⑥,他的诗论十分注重自我表现,才情横溢,而且其人亦颇有狂态[8],其《颇有谓予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云:“诸君刻意祖三唐,谱系分明墨数行。愧我性灵终是我,不成李杜不张王。”[9]278张问陶特别推重的是李白的狂放不羁,在答毕沅的诗中自谓:“莫讶上书狂欲死,山东李白是乡人。”其《闰四月十九日雨后就田桥饮酒夜过张孝廉园亭灯下得长句二首》云:“闲愁似梦寻无迹,醉语如诗妙有神。不作平常文字饮,清狂才称谪仙人。”[9]184《过阳湖怀稚存》云:“爱我猖狂呼李白,看君光气夺齐桓。”都以“狂”为李白之特色[9]537。
潘德舆论李白与此不同,他力主太白学力精纯,能复古道。他说:“世人徒夸其纵横任侠之风,缥缈出群之想,而不知其忠义勃发,直抉大奸,非徒以草《清平调》、赋《行乐词》了事。”对时人以清狂目李白大不以为然。他认为李白最值得崇尚之处,在人品之敦厚与思想之忠直,而非他的狂放,人们只注意李白外在的狂放,反而会失去李白最精髓的东西。他褫夺李白“诗仙”的名号,应该也有此考虑。
在清代的具体语境下,潘德舆李白诗批评展现出的正统与异端之争,表现为一个保守的“诗教”主义者对较为叛逆的“性灵”话语的反拨。他一方面苦心纠正历史上李白的复杂接受,另一方面又立足当下,通过对李白提出新的阐释来重新确立“诗教”正统。潘德舆的李白诗批评,虽然有其个性的迂阔处,但亦有其典型意义:展现了嘉道以后清代诗学的新变;是中国文学“正统论”绵长谱系的一环。作为“正统”的“诗教”,如何对作为“异端”的“诗仙”进行收编,潘德舆的批评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其实在“诗教”与“诗仙”之外,中国文学的正统与异端之争,还有着很多的变体,文学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永远值得追问。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是一个文学批评者始终需要面对的问题。
注释:
①潘德舆(1785―1839年),字彦辅,号四农,江苏山阳人,著有《养一斋集》《养一斋札记》《养一斋诗话》等。其《李杜诗话》三卷,本为潘德舆《作诗本经》的《通论》部分,但后来单独拿出,附到《养一斋诗话》后。此书宗旨,是以李、杜为诗歌之典范,通过对前人相关评说的辨正,展现出李、杜诗的价值。其中卷一论李白,卷二、卷三论杜甫。潘德舆的论说不同于前人之处,在于他的体系性。他并不是截取李、杜诗的某些佳句来进行评论发挥,而是实实在在地将李、杜二人全体提出加以评论,是非常完整的作家论而非零星的评点。在评论李白的部分,他共分了二十二条,次序很井然:第一条是总说,相当于《李杜诗话》的序,论及《李杜诗话》的缘起及宗旨,第二条至第七条总论李白之诗风与人格,第八条至第十条论李白乐府,第十一条论李白的五古,第十二条论李白七古,第十三条总论李白律诗,第十四条论李白五言排律,第十五条论李白五绝,第十六条论李白七绝,第十七条辨李白诗之仙道色彩,第十八条辨李白诗之萦情富贵,第十九条辨李白与永王璘之关系,第二十条论李白之学问,第二十一条论李白之气节,第二十二条辨李白之殁。其特色在于每一条前皆广引前人说法,然后下自己按语加以辩说,条理明晰,论证有力。
②此说出自蔡居厚《蔡宽夫诗话》,非蔡絛语,潘德舆误引。蔡居厚语可见《宋诗话全编》第一册(凤凰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 版)第610 页。
③李白之从永王璘,是出于胁迫还是自愿,今天学者的研究几乎都倾向后者。李白在开始确实是心甘情愿跟从永王璘的,至于永王璘是否叛逆,今天还有着不同的说法,具体可参考邓小军《永王璘案真相——并释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文学遗产》2010年第5期)、《李白与永王璘谋主李台卿——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诗笺证》(《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以及武秀成《唐玄宗〈停颍王等节度诰〉真伪祛疑及其史料价值》(《古典文献研究》2015年第2期)。
④唐人倡“复古”,未必是为了复古,而更多的是在借复古来建立统系,取得话语权。这种文学上的建统在后来古文运动中展现得尤为明显。
⑤诸家论说皆见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附录四《丛说》(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533―1538页。
⑥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四有《张船山先生事略》(岳麓书社1991年5月第1 版,第1147 页),中云:“船山先生,张姓,问陶名,字仲冶,四川遂宁人。相国文端公鹏翮曾孙也。生于山东之馆陶。幼有异禀,工诗,有青莲再世之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