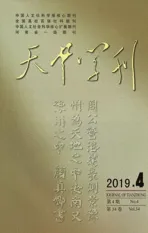从“富贵异心”到“才拥双艳”
——相如聘妾与长门买赋故事关联演变的叙事文化学分析
2019-01-19汪泽
汪 泽
(青岛大学 历史学院,山东 青岛266071)
作为司马相如人生故事的两个重要片段,“茂陵聘妾”与“长门买赋”不仅常被诗人词客引为典故,也广泛流传于通俗文艺与民间故事之中。事实上,两个故事片段皆不见于正史,诞生之初亦无逻辑关联。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载“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1],是“茂陵聘妾”故事的最初记载。卓文君《白头吟》有题无辞,刘宋沈约《宋书· 志· 乐》恰有同名古词五解,表达女子遭弃哀怨之意,不题撰人。“长门买赋”见于梁萧统《昭明文选》所录《长门赋》序言:“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2]712
《史记》所载相如文君婚恋始末为以上两故事之前奏。《司马相如列传》称相如家贫无业,应临邛令王吉之邀客居都亭。王吉缪恭相如,富人卓王孙以之为贵客,邀至家中宴饮。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挑之。文君亦心悦相如,与之夜奔,归成都。相如家徒四壁,王孙怒而不与分钱。相如携文君还临邛,令文君当垆酤酒,自着犊鼻裈涤器市中;王孙耻而杜门,经亲友相劝,不得已分其资财,相如文君始富居成都。后相如因辞赋得幸拜官、荣归蜀地,王孙自往和解,悔使文君晚嫁相如。
从基本的情节要素来看,“茂陵聘妾”与“长门买赋”表现出趋同性,各自讲述了一段婚姻破镜重圆的故事,“重圆”的主动权掌握在男性手中,而令其回心转意的关键皆在于女方诗文的感发。更有趣的是,两个故事中共同出现的历史人物司马相如扮演了截然相反的角色,前者为负心的夫君,后者为弃妇的代言。在司马相如故事的传播与重释过程中,二者由分而合,其间的逻辑纽带与思想关联伴随时代背景渐次发生变化。本文以中国叙事文化学为方法论依据,通过相关故事文本梳理和文化、文学内涵阐释,对“相如聘妾”与“长门买赋”故事的关联演变加以分析。
一、唐宋——富贵异心
(一)唐代——“文君欢爱从此毕”
按照诗歌发展的客观规律,相如、文君生活的西汉前期,尚不可能出现如《宋书》之《白头吟》一般成熟整饬的五言诗。但题名及内容的相关性不可避免地使其发生了混淆。初唐李善《文选注》云:
《西京杂记》曰:“司马相如将娉茂陵一女为妾,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沈约《宋书》,古辞《白头吟》曰:“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2]1327
从现存材料来看,李善首次将匿名古词《白头吟》的著作权给予卓文君,使其融入了相如文君婚恋故事体系。这一误读得到了后人的追随与响应,《白头吟》与司马相如故事共同流传,并产生了不容小视的经典作用;后世出现的一系列同题诗作,大多咏写相如文君情事而模拟古词怨弃之意。行至唐代,李白作《白头吟》二首,将“长门买赋”与“茂陵聘妾”两个故事前后连缀,置于因果链条之中:
此时阿娇正娇妒,独坐长门愁日暮。但愿君恩顾妾深,岂惜黄金将买赋。相如作赋得黄金,丈夫好新多异心。一朝将聘茂陵女,文君因赠白头吟。(其一)
闻道阿娇失恩宠,千金买赋要君王。相如不忆贫贱日,官高金多聘私室。茂陵姝子皆见求,文君欢爱从此毕。(其二)[3]247―248
“阿娇”为志怪小说《汉武故事》中陈皇后闺名,“千金”为《文选· 长门赋序》“黄金百斤”之变。李白笔下,长门作赋得金(加之谒帝拜官)成为相如异心聘妾的直接动因。在中国传统社会,这一逻辑关系的设立确有合理之处。战国时期,《韩非子· 内储说下》即有寓言称:
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4]
《三国志· 魏书》裴松之注引佚史《典略》曰:
上洛都尉王琰获高干,以功封侯;其妻哭于室,以为琰富贵将更娶妾媵而夺己爱故也。[5]
《资治通鉴· 唐纪· 太宗永徽六年》记唐高宗朝许敬宗宣言:
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6]
韩非本意在于证实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相异之理,《典略》之文常被引作妻妾互妒之典,许敬宗为高宗改立武后张目,但皆从客观上揭示出世人于经济条件、政治地位改善后置妾易妻行为之普遍,风习之恒久。唐代社会思想开放、经济繁荣,歌宴享乐之风盛行,姬妾伫蓄的规模亦极庞大。在《旧唐书》中,妓妾之有无多寡俨然成为评判贵族官宦奢靡与否的标准:
孝恭性奢豪,重游宴,歌姬舞女百有余人。[7]2349
博乂有妓妾数百人……骄侈无比。[7]2357林甫晚年溺于声妓,姬侍盈房。[7]3241
载在相位多年,权倾四海……名姝、异乐,禁中无者有之。兄弟各贮妓妾于室……[7]3414
专事奢靡,广修第宅,多畜妓妾,以逞其志。[7]3414―3415
稷长庆二年为德州刺史,广赍金宝仆妾以行。[7]4061
覃少清苦贞退……位至相国……家无媵妾,人皆仰其素风。[7]4492
公著清俭守道……无妓妾声乐之好。[7]4937
可见“姝子皆见求”,对于“官高金多”者而言,绝非夸张。晚唐崔道融《长门怨》云:“长门花泣一枝春,争奈君恩别处新。错把黄金买词赋,相如自是薄情人。”[3]8288“薄情”指茂陵一事。相如异心聘妾与武帝“君恩别处”同为喜新厌旧的薄情之举,请薄情文人作赋感悟薄情帝王,错施黄金亦不能复幸。李白诗以因果关系罗织情节,而崔氏关注到司马相如在茂陵聘妾与长门买赋二事中截然对立的角色意义,突出负心男子为弃妇代言写怨的反讽色彩,促进了两个故事在思想层面的合流。
(二)宋代——“文君见弃如束薪”
宋代题名《白头吟》的诗歌作品继承了太白笔下司马相如富贵异心的内涵。南宋王炎诗云:“临邛旧事不记省,千金多买青蛾眉。”[8]29689王铚诗以文君口吻道出:“我方失意天地窄,君视浮云江海宽……我怜秀色茂陵女,既有新人须有故。请把阿娇作近喻,到底君王不重顾。若知此事为当然,千金莫换长门赋。”[8]21286曹勋亦有《白头吟》:“相如素贫贱,羽翼依文君。一朝富贵擅名价,文君见弃如束薪。”[8]21040
以上诸作中,曹勋诗最值得关注。其诗字面未及“长门”“茂陵”二事,然“富贵”“名价”“文君见弃”与其意旨类同。而通过细节对比,亦可发现曹勋诗与以李白诗为代表的同题作品之间存在着内部差异。同样从相如文君婚恋故事的历史原型出发,李白渲染出二人贫贱相守的挚爱深情,“文君欢爱从此毕”偏重于相如在精神层面的移情别恋;曹勋却强调了初时女强男弱的经济依附关系,“文君见弃如束薪”更具现实弃妇的意味,道义谴责的力度更强,文君形象也更显憔悴无助。在某种程度上,曹勋诗似赋予了相如婚变故事“书生负心”的时代主题。
赵宋王朝实行文官政治,素有“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之称,且科考规则更为成熟,以“弥封”维护公平公正,杜绝知举徇私,不尚家世背景,中第即授官,贫寒书生进身仕途的可能性大于前后历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身份转换令其他阶层艳羡不已。显宦富豪抱着巩固地位、扩张势力的目的,亦积极拉拢新晋士子,“榜下脔婿”渐成风气。宋彭乘《墨客挥犀》称:
今人于榜下择婿号脔婿……其间或有意不愿而为贵势豪族拥逼不得辞者。有一新先辈,少年有风姿,为贵族之有势力者所慕,命十数仆拥至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略不辞逊。既至,观者如堵。须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丑陋,愿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谢曰:“寒微得托迹高门,固幸。待归家试与妻子商量,看如何?”众皆大笑而散。[9]
此事亦见于范正敏《遯斋闲览》,盖为小说家言。但在博人一笑的同时,这条轶闻引申出一个严峻的问题——若寒门新贵在中第之前已有妻室,然面对“脔婿”之行,难免有人或难禁跻身上流、平步青云的诱惑,或迫于权势的压力,抛弃贫贱之妻而另结婚姻。以此造成的家庭悲剧引起了社会关注,“书生负心”成为通俗文学的一大主题。据明代徐渭《南词叙录》记载,宋光宗年间的永嘉杂剧以《赵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居首,二者皆为书生婚变悲剧;在“宋元旧篇”中所录《林招得三负心》《陈叔万三负心》等,或为同类题材。现存早期南戏《张协状元》亦演书生负心故事,以张协与贫女复合而终。这些故事虽结局有别,但书生孤贫之际得发妻扶持资助,及至高中厌妻弃妻的情节模式极为近似,书生形象亦极为不堪。由此证实了此类题材的流行性以及大众对文士发迹易妻行为的普遍愤恨。
《西京杂记》中司马相如欲聘茂陵女的轶事本未涉及人物的经济、政治状况,且虽聘妾但未弃妻。曹勋在延续李白诗“富贵异心”思路的同时,突出了相如贫时得助、发迹弃妻的情节要素,或许正是将对贫女、桂英、赵五娘等糟糠弃妻的同情之泪洒给了卓文君。宋代话本《风月瑞仙亭》敷演相如文君情事,现存残本不含婚变情节,但相如进京面圣之前,文君的反复告诫始终围绕着“苟富贵,勿相忘”的主题:
文君曰:“日后富贵,则怕忘了瑞仙亭上与日前布衣时节!”相如曰:“……小生怎敢忘恩负义!”文君曰:“如今世情至薄,有等蹈德守礼,有等背义忘恩者。”相如曰:“长卿决不为此!”文君曰:“秀才每也有两般:有‘君子儒’,不论贫富,志行不私;有那‘小人儒’,贫时又一般,富时就忘了贫时。”长卿曰:“人非草木禽兽,小姐放心!”文君又嘱:“非妾心多,只怕你得志忘了我!”
夫妻二人不忍相别。文君嘱曰:“此时已遂题桥志,莫负当垆涤器人!”[10]
《风月瑞仙亭》极具代表性地迎合了罗烨《醉翁谈录· 小说开辟》对民间说话之内容意图的概括——“噇发迹话,使寒门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11]。民间艺人对“小说”内涵的理解,再次印证了宋代士人发迹弃妻之社会问题对文艺领域的深刻影响。
二、明清——才拥双艳
对相如负心的谴责至宋室灭亡后似稍有缓解。元代实行四等人制,官员主要从蒙古、色目人中选拔,汉族文人地位急转直下,且由于科试的歇止,在很长时间内断送了仕进的可能。书生发迹弃妻的故事主题减弱了现实针对性,长门买赋与茂陵聘妾的关联主要维持在精神层面。元代侯克中《谩赋》云:“长门一赋万黄金,写尽深宫怨女心。莫怪长卿知底蕴,茂陵曾见白头吟。”用一时间副词“曾”将“聘妾”提至“买赋”前,意谓相如先时因负心之举令妻子作词怨弃,深谙弃妇之苦,方能为其写心。作者对相如有所谴责,但仍将其视为弃妻怨女的知音,或与此时书生广受同情而逐渐正面化的境遇有关。
明清两代揭示相如代赋《长门》而自身负心的诗作不少,明代有何乔新《无题和李商隐韵宫怨》、宋应升《宫怨》、徐媛《宫怨》、呼文如《刺血寄生诗》、胡奎《长门怨》,清代有程晋芳《汉宫词》、谭莹《长门赋》、尤珍《咏古》、潘素心《琴心》、顾宗泰《司马相如》、徐梦元《司马相如》、王昶《司马相如》、钟璜《戏题司马相如传后》、沈学渊《司马长卿故里》、屠粹忠《司马长卿》、蔡殿齐《咏卓文君》、蔡衍鎤《文君怨》、朱鹤龄《卓文君》、陆元鋐《临卭杂咏》、乐钧《杂兴》、薛敬孟《闺怨三十韵》、吕兆麒《读书有感》等。但与此同时,作为新生文体的传奇戏剧却以歌唱或说白的方式对此加以解构。明人韩上桂《凌云记》中相如自云“争奈俺文君这时想我,亦却像长门一样……赋文倒做了自己的招词断”[12],孙柚《琴心记》称“帝后失宠,愿以黄金买赋;至如世间夫妇,一旦爱弛,将何以回恩义”[13],清代许树棠《鹔鹴裘》则有“笑君王轻将爱毁,我夫妇偏能好完”[14]。
宋代乃至元初书生忘恩负义的婚变悲剧,经由元末以来的改造,大多演变成多情才子坐拥双艳的团圆结局。明清相如婚变故事也不再以微时依附、发迹弃妻为着眼点。大量的诗歌和戏曲作品仍将长门贻金作为相如置妾的前提,但命意却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仍谴责其富贵异心,另一部分则表现出主人公喜新不厌旧、置妾不弃妻的多情与艳福,后者成为这一时期相如婚变故事的新看点。明代许潮《汉相如》有侍妾蜀锦自表来历:皇后千金买赋,相如以黄金百两买妾房中,目的是与文君做伴。《凌云记》中这一倾向更加突出。司马相如作《长门赋》得千金,浮浪子弟引之结识茂陵女子郭佩琼,相如爱郭才貌,取百金为聘,亦云“待要他佐桑蚕,非敢是分宝鉴”[12],表示纳妾后夫妻恩情不减之意;后文君《白头》寄怨,相如悔悟,遣郭氏另嫁,然文君亦自悔过激,最后佩琼由武帝赐相如完娶,文君欣然接受。
明清之际,文人法若真作《当垆歌》,长门买赋与茂陵聘妾的逻辑关联再次发生了变化:
狂士才横天地空,怜才唯有蜀女子……长门赋买千金贵,茂陵读之心如醉。买去长门青草幽,嫁君一意到白头。白头吟,怜一心,两贤还相妒,一枕商与参。茂陵偏浓词赋癖,琴台原不恋黄金。一朝皑皑山头雪,弃掷茂陵杜鹃血。流连台上凤凰鸣,不顾空闺泪断绝……尔执厨下炊,我截黄葛缝。但愿同事一心人,耐可联镳入汉宫。[15]
唐代以来,陈后买赋所带来的丰厚物质资本被视作相如聘妾的先决条件,《凌云记》表现出茂陵女郭佩琼“纵不得翰苑清华,也须是词坛俊杰”的量才婚配标准,但情节上仍将卖赋得金作为前提。《当垆歌》则以茂陵女读《长门》爱相如之才为结缘契机,把相如聘妾提升至因才相感的精神层面。文君反有了负面意义——以《白头吟》维护住自我的爱情,却使另一个无辜女子沦为弃妇。站在顾全双方的角度,作者提出二女同心怜才、共事一夫的设想。
《凌云记》《当垆歌》通过重释相如婚变故事所表达的男性才子“拥双艳”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尤其就后者而言,表面以倾情弱势女子为旨归,实际依然透露出男权中心视角,此种视角的生成与泛化亦有其社会背景。
明代隆庆、万历以降,国运于内政腐朽、边患危机之下渐趋末造。智识阶层对国家前景感到失望焦虑,又无力扭转乾坤;在吏情日巧、文网日深的情形下,他们更需要来自女性的柔情慰藉。沦落者面临“夫子偃蹇,而失举案之礼”“时事坎坷,而乖唱随之情”[16]的尴尬,渴望红颜知己的垂青与陪伴;发迹者更致力于“刻稿娶小”,将“一官一集一姬人”[17]视作个人成就、社会名望以及文化品位的象征。书生才子取次花丛的行为也被视为风流佳话而不加苛责。明末清初的文人陆圻作《新妇谱》,以父亲的口吻教导出嫁女儿及世上妇人“能容婢妾,宽待青楼”,因为“风雅之人,又加血气未定,往往游意倡楼、置买婢妾,只要他会读书、会做文章,便是才子举动,不足为累也”[18]。
然而站在现实立场,“妻娇妾美,而又皆贤,是尤不可得之致”[19]。一些人遂把内心的需求诉诸笔端,获得虚幻的满足。我们发现,描写男女婚恋、以双艳(甚至数艳)同归一夫为结局的叙事文学作品于明代后期渐成规模;坐拥双艳的男主角多被定位为卓越的才子,这在提升作品格调的同时,也有为现实文人吐气之意。
以司马相如为主人公,凭借其辞宗赋圣的历史地位和普泛影响,无须过分标榜、虚夸声势,即可达到目的。然而在其他一些作品中,所谓的才子身份难免与其卑俗的实际表现发生错位[20]。严格意义上的才子佳人小说在明末清初大量问世,对此进行了合理的修正,存情去欲的同时强调出因才相感的恋爱实质。在才子佳人小说中,诗赋成为必不可少的媒介,才子的文学天赋具有无与伦比的感召力量,可以压倒金钱与权势,俘获不止一位佳人的芳心;爱才识才的佳人彼此之间亦相认同,甘愿共事一夫而毫无妒意。
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说,“夫妻妾同居,隐忍相安者,十或一焉;欢然相得者,千百或一焉”[21]。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家庭温暖与妻妾柔情存在着明显失真的成分,更像是文人一个个聊以自慰的美梦,他们在经历了破国亡家、出处两难的震荡挫折之后,以虚幻的诗意和谐、美满团圆疗救世人的心灵创伤。
与韩上桂等人相比,法若真恰好生活在才子佳人小说盛行的时代,其对相如故事的剪辑编排更能体现当时流行文体的内容特色。前人眼中“长门买赋”对“茂陵聘妾”的物质功利意义被刻意推翻,茂陵女纯然因《长门赋》之真才挚情一心相许。而此前文君亦是慧眼怜才而择相如为夫,按照才子佳人小说的情节套路,应与茂陵女惺惺相惜,夫、妻、妾三人共结琴瑟之友。
自《凌云记》《当垆歌》出现以来,如是的设想几乎空前绝后,正因如此,《当垆歌》表现出绝无仅有的代表意义。清人屈大均《临卭行》、王鸿绪《拟行路难》、李星沅《琴台》等重咏二事,又回到得金富贵、喜新厌旧的轨道上。这是长期以来《白头吟》主题诗歌的创作惯性使然,也与现实状况有关,毕竟才子佳人小说式的思维逻辑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存在。
尽管本文选取了极为微观的视角,仅仅聚焦于两个故事片段的内在联系,但作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具体而微的尝试,在社会文化因素外,亦需考虑文学文体对故事流变的规范作用。这是对以往小说戏曲同源研究、民间故事主题研究等在文学分析方面非自觉状况的补救,也是叙事文化学之学术主张与理论价值的彰显。于司马相如人生故事层累叠加的过程中,汉代正史本传自具传奇化色彩,魏晋以来的轶事笔记和伪托创作使其踵事增华,唐宋时期则进入了守成过渡的阶段。从守成角度来说,唐宋诗词在有限的篇幅内以韵体叙事,将前代的故事片段浓缩整合,于起承之间生成新的因果联系。宋代话本完成文白语体之过渡,为相如婚恋主题在通俗文学领域内的演绎延展打下基础。明清戏曲凭借篇幅优势和综合艺术广泛熔铸文本信息,并催生出新的情节人物以壮大故事规模;出于塑造正面主角形象的需要,前代故事中的负面因子在道德情感各方面被加以解构;用代言说唱形式表现主人公的精神心理,赋予司马相如自我辩白与倾诉的机会,使其更易得到读者观众的理解与同情。而戏曲的演唱传播又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诗文作品的回流反哺。
综上所述,自“茂陵聘妾”与“长门买赋”两个故事走向合流以来,其内在联系大体呈现出随时变迁的特点,作者对故事情节要素的组织提炼与婚恋文化的发展演变状况相适应,与此同时透露出人情世风的不同走向。从文学自身角度来说,体裁形式的更新发展,亦能为故事形态及其内在逻辑的改变提供某些机遇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