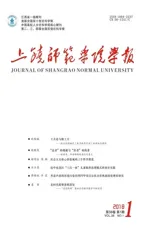论中央苏区“三位一体”儿童教育治理模式的初步实践
2018-03-21
(龙岩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福建 龙岩 364012)
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根据地,由赣南革命根据地和闽西革命根据地两部分组成。苏区的儿童教育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根据苏区实际状况,针对儿童开展的教育活动,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教育实践。本文所讨论的苏区儿童教育中的“儿童”,从年级的角度进行划分,特定指小学阶段(初小和高小),不包含学龄前即幼儿教育阶段。
苏区时期,苏维埃政府作为工农政权的具体运行机构,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初步形成了政府、家庭和社会团体相结合的教育治理模式。对于“治理”的认识,学术界迄今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是,可以达成共识的理解是“多元主体参与管理”“协调和持续互动”。本文比较赞同学者褚宏启和贾继娥的说法,他们认为:“教育治理是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利益群体和公民个体,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进行合作互动,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的过程。此处的国家机关是广义的,包括行政机关(政府)、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执政党机关(党委机关)。”[1]其实,如果对中央苏区的教育状况稍加梳理,就会发现苏维埃政府除了自身进行了诸多的教育实践外,还通过群团组织检验学校教育的实效,加上家庭教育的补充,已经初步具备了“教育治理”的思路,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教育治理模式。
一、苏维埃政府是苏区教育的主要推动者
苏区教育的发展,最为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认识到儿童及其教育的重要性,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时期就指出“儿童是革命的后代,是新社会的建设者,同时也是目前参加革命斗争的一员。”[2]在夺取政权后,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为发展儿童教育事业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是成立了较为完整的文化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中央层面设有教育部,下设各局,分管高等教育、初等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省、县和区的教育管理部门也称为教育部,下设普通教育科和社会教育科,乡政府一级设有文化专员负责本地的教育管理。自上而下的教育行政体制为中央教育政策的传达提供了有利保证,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模式延续至今,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是及时出台教育方针、法规和政策。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实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3]把“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在《宪法大纲》中予以明确,对于苏区人民不啻为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在《宪法大纲》的总统领下,系列关于教育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陆续出台。如1933年10月苏区文化教育大会通过的《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决议案》,1934年2月颁布的《小学教员有待条例》,1934年2月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1934年4月颁布的《苏维埃教育法规》等。除了中央一级,地方政府还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以议案或会议精神的形式对教育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规定,如《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决议案》(1934)、《中共莲花县委通知第四号——关于学校教育问题的指示》(时间不详)、《永定县第十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案》(1930)。这些议案或会议精神,有的针对全部教育形式,有的则特指小学教育。据统计,“从1931年至1934年中央和地方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教育的纲要、条例、章程、办法、决议,有41项之多。”[4]
三是广泛建立新式学校。学校是实施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教育方针和政策的主体,各级政府广泛建立的新式学校,保证了党和政府教育方针的有效实施。所谓的新式学校,区别于赣南、闽西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旧私塾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期间建立的学校。这种“新”不是表面上的校舍外观等方面的改观,相反,很多新式学校仍旧建立在原来的校舍基础上,有的甚至是祠堂和庙宇。这种“新”最本质和最重要的体现在师资队伍和教材上。1932年1月,湘鄂赣省大冶县要求“凡四书五经、国民党书籍、封建歌曲一律禁止教授”[5],封建的、反动的知识再也无法在新式学校中传播,摆在苏维埃政府面前的当务之急的任务就是如何解决教师和教材。苏维埃政府各级文化教育机构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妥善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在教师(教员)的选拔上,苏维埃政府把政治信仰坚定作为选拔教员的重要条件之一。一方面,利用开办师范培训班的方式培养师资,另一方面注重从旧知识分子中选拔教员。采取“内培”和“外引”相结合的办法,保证了苏区小学教师队伍的相对完备和稳定。为了解决教员们的生活问题,苏维埃政府积极动员群众在耕田等农业生产方面予以帮助,保证了教员能够将主要精力放在教学活动中,有利于学校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
在教材方面,主要采取自主编印教材的方式。“30年代中央苏区彻底废除了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封建主义的复古教育以及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取消了旧学校的反动课程,新编了包括政治教育、军事教育和生产、生活教育的新教材,据不完全统计,共编写新教科书130余种。”[4]根据陈洁的研究,中央苏区比较有代表性的小学教材至少有34种,本文经过甄别,整理后如表1所示[6]。
从教材的名称、种类和印刷情况看,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教材种类齐全,既有《国文》《数学》,也有《农业》《地理》,甚至包括《体育》《音乐》等;(2)教材编写的主体,既有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也有各县苏维埃政府文教部门,还有工农红军政治部,编印的主体呈多元化;(3)有些书籍印刷质量较好,甚至使用了当时较为稀缺的彩色印刷技术;(4)图文并茂,很多教材附有插图,使得教材更富有趣味性和可读性。
四是规范教育实施过程。为了保证教育方针、政策的有效实施,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巡视制度,及时掌握了各地教育的实际开展状况。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修正的《教育行政纲要》中针对巡视与报告单独设了一章,详细规定了巡视的目的、巡视的具体程序,对乡教育委员、区教育部、县教育部、省教育部的巡视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定。
五是老一辈中共领导人对教育的重视。中共早期领导人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对中央苏区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示范和推动的作用。毛泽东、徐特立、任弼时、陈云、瞿秋白等人深入调查、了解苏区教育实际状况,起草切实可行的教育法规,甚至亲自指导、筹办学校。如毛泽东曾于1929年10月在上杭苏家坡指导当地人民创办了一所平民小学,并亲自给学生们上课,极大地鼓舞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办学热情。

表1 中央苏区有代表性的小学教材统计
续表1

序号教材名称出版时间编辑出版(印刷)单位容量备注26《识字课本》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红军学校翻印32开石印27《国语教科书》1934年1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审局出版32开石印28《算术教学法》(第一册)1934年6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审局编印32开,约20000字铅印29《科学常识》1934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审局编印不详不详30《各种赤色体育规则、田径赛训练法体操》1933年7月第一版,1934年7月重印不详32开雕版印刷31《少队游戏》1934年4月少先队中央总队部出版32开石印32《竞争游戏》1939年4月中央出版局出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辑,中央印刷厂印刷32开石印33《儿童唱歌集》1933年5月中央教育部编辑,福建省苏区苏动感化院出版32开石印34《赤色国语》1930年不详1100字木刻线装
二、家庭教育是苏区教育的必要补充
中央苏区的主要区域与客家人的生活区域基本上处于重合的状态[7],这也就意味着苏区儿童教育离不开传统客家文化教育的影响。客家先民来自中原,由于战乱等原因,背井离乡,南迁至闽粤赣边区定居,在与当地居民的长期融合下,形成了具有中原文化又有当地特色的客家文化。客家文化有很多特征,其中之一表现为“崇文重教”。
客家人重视教育有诸多做法和特点。一是注重学校建设。明清以前,主要表现为大兴书院。据统计,明、清期间龙岩地区先后办有书院239所[8]。在苏维埃政府掌握政权后,这些书院经过改造,变成了新式学堂,成为普及文化知识和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二是树立族规,繁荣教育。客家人保留了中原家族聚居的特点,把兴学育才作为家族的重要职责之一。他们把繁荣教育,勉励后人读书的思想以楹联的形式流传下来,如宁化石壁客家公祠楹联“爱国爱乡恭敬桑梓通四海;重礼重教力行孝悌播五洲”;被誉为“土楼王子”的福建永定振成楼的楹联,如“干国家事;读圣贤书”“振作那有闲时,少时、壮时、老年时,时时须努力;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要关心”;永安县“安贞堡”的“洗耳不闻尘伪事;留心只读圣贤书”“十年攻书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仕于攻书,十载寒窗灯火苦;儒生及第,一朝魁榜姓名香”,这些楹联表达了读书人寒窗的艰辛和祖上对读书人的殷切期望。三是捐资兴学。客家华侨热心捐资兴学,其历史由来已久,这也是客家人崇文重教的表现之一。客家人捐资兴学的主体至少包括两类人。一类为侨胞,他们大都接受过家乡的教育,主要是私塾教育,而鲜有完整完成学业的。这些人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到海外发展,但他们心系家乡关心教育事业,“当在异国他乡站稳脚根或取得成就时,排解心中遗憾的方式之一就是让子孙尽量多地接受教育,也愿倾其所有让尽可能多的家乡晚辈接受教育。他们也许更多的是从历史的责任上去考虑家乡的教育问题。”[9]客家人如梅州华侨丘燮亭先生,青年时去雅加达打拼,后兴办实业,曾在家乡建立时习轩,供青少年读书识字。20世纪初,捐资创办三堡学堂,1913年与乡贤创办私立中学。再如龙岩永定下洋的胡文虎先生,他从20 世纪20 年代开始,陆续捐助东南亚和中国的学校,其在国内捐资的学校数量,尤以福建和广东为最,既有高等院校,又有中小学校,既有职业学校,又不乏教会学校,捐助对象大到整个学校,小到图书馆、运动场,甚至桌椅等设备,可谓无所不至。客家先贤捐资助学的举动,更加激励后辈努力读书,为国效力。另一类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乡绅阶层,这一阶层既包括卸任或者被贬回乡的官员,也包括即将踏入仕途之路的读书人。“士绅作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介,他们由于考试、仕宦、荫封等途径,在地方上成为领袖,在与国家的协调中,他们也促进着国家的法律制度、道德伦理、文明观念的扩张……”[10]部分乡绅阶层充当了塾师的角色,他们在宗族私塾或者若干个宗族合办的村落私塾中任教,传播了文化,教化了村民子弟。这种现象直到这一特殊阶层的消亡。客家人重视教育的传统,使得中央苏区教育的土壤犹存,为苏维埃政府开展教育实践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三、活跃的群团组织是对苏区儿童教育成效的“总检阅”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未来的社会的主人”,但因革命形势的需要,苏区儿童教育无疑带有鲜明的革命性。除了学校教育,活跃的群团组织可谓是对苏区儿童教育效果的总检阅。当时,存在于中央苏区的群团组织主要有少先队(成员的年龄为17-24岁间)和儿童团(8-14岁,后来调整到6-14岁,与小学生的年龄大体一致)。湘赣苏区于1930年之后成立了县和省的儿童团机构,儿童工作的方针、儿童团干部的任命等事项由共青团决定,重要活动和任务也由同级或上级共青团组织布置和下达[11]。儿童团有了领导组织,既在政治上保证了其先进性,又对其具体工作有了准确的指导。
儿童团为建设、繁荣苏区的教育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促进了文化的普及和提高。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中央苏区普遍建立了列宁小学。在政府法律的要求和政策的引导下,儿童拥有了真正的受教育的权利。小学生基本上都是儿童团员,他们自身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还积极动员不愿让孩子(尤其是女童)外出上学的家庭,提高了小学的入学率和儿童的文化水平。第二,繁荣了苏区的文化生活,活跃了苏区的政治氛围。儿童团员积极开展唱歌跳舞等文艺活动,通过出墙报、写标语等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英雄事迹和革命道理,有力地抨击了封建制度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他们的社会活动是对课堂上学习革命思想的具体实践,这一儿童组织也日益成为苏区宣传工作的重要力量之一。第三,维护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客观上,中央苏区中仍旧存在搞封建迷信、赌博、吸食鸦片等不良现象。儿童团积极配合苏维埃政府,宣传这些活动的危害性,参与到禁鸦片、禁赌、禁缠足、废除童养媳等活动中,在移风易俗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第四,儿童团是军事活动的有效补充。儿童团员目标小,不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站岗放哨,在路口检查过往行人,为红军和游击队通风报信。他们拥军优属,参加扩红运动,为解除红军战士的后顾之忧出工出力。这些实践形式既锻炼了儿童的胆识,也为苏区的军事活动做出了贡献。同时,由于儿童团员年龄小,受封建旧思想的影响较少,有利于革命思想对他们的正面影响,客观上宣传了共产党的先进思想和理念,也为党和政府培养了一批思想觉悟高,责任心强的领导干部。
四、余论
“根据江西、福建、粤赣3省的统计,在2 931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 052所,学生89 710人;有补习夜校6 462所,学员有94 517人。在校适龄学生总数约占3省苏区总人口的6%左右,占适龄儿童总数的50%左右。”[12]而国民党统治时期,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只有10%,可见,中央苏区儿童教育取得的成绩是非常显著的。
中央苏区的办学思路和做法,尤其是其“三位一体”教育治理模式的实践活动,时至今日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它给我们的启示至少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教育要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她让穷苦儿童拥有了上学的权利,真正做到了为穷苦大众争利益,不论是苏区时期还是当前,她代表的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性质没有改变。二是中央政府层面要更加侧重治理而不是管理。中央政府要做好顶层设计,尤其在教育方针、政策、法规的制定,巡视、督查方面的制度的健全和完善等方面,在当前的行政体制下显得尤为重要。三是各级政府层面要更加注重管理而不是治理。各级政府要认真执行中央政府的教育政策,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发挥实效。同时要动员一切可动员的力量为教育服务。要注重各种社会团体的培育,社会团体要在补充和检验学校知识、发展学生技能等方面提供尽可能的便利。四是要发掘传统家庭教育,尤其是客家宗族教育的优点和长处,发掘客家人崇文重教的经验和做法,为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提供不竭动力。
当然,我们在分析中央苏区办学思路的过程中,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并非在政权建立之初就具有“教育治理”的思想,更谈不上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实施了系列有效的办学措施。主观上,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办教育的经验尚有待提高;客观上,当时苏区的主要任务是反“围剿”,同时扩大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力。加之,当时的环境特别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还无法满足苏维埃政府单独办教育。在主客观条件的作用下,为了适应当时当地的环境和当时形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三位一体”教育治理模式的初步实践应运而生。事实上,这种实践不但体现在儿童教育上,同样也体现在其他类型的教育活动中。
[1] 褚宏启,贾继娥.教育治理与教育善治[J].中国教育学刊,2014(12):6-10.
[2] 江西教育学会.苏区教育资料选编[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8.
[3] 厦门大学法律系,福建省档案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8.
[4] 邬开荷.论中央苏区的客家教育[J].南方冶金学院学报,1997(12):111-114.
[5] 皇甫东玉,宋荐戈,龚守静.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1927.8-1949.9[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55.
[6] 陈洁.苏区小学教材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1:58-60.
[7] 王予霞.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21.
[8] 叶少玲,赵兵.论客家长盛不衰的教育基础[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9):148-151.
[9] 刘向明.华侨捐资办学是侨乡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新时期客家侨胞与梅州教育[J].嘉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9(1):121-124.
[10]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276.
[11] 彭富九.回忆苏区儿童团(一)[J].百年潮,2011(2):32-37.
[12] 娄瑞丽,周景春.中央苏区时期儿童教育的特点及启示[J].党史文苑,2014(4):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