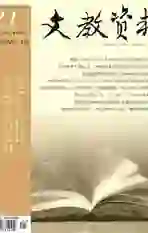感伤而不绝望
2017-11-26邓渊
邓渊
摘 要: 女作家迟子建的小说《逝川》以神秘的意象、温婉平和的语言,力图保持自然生态与人文理想、精神信仰的某种平衡。《逝川》渗透着对自然、生命的感悟,用细腻的笔触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幅清新优美的风景画;用独特的人生体验及审美追求谱写了感伤而不绝望的文明挽歌。
关键词: 自然 《逝川》 泪鱼 女性 关怀
《逝川》是我国著名女作家迟子建早期发表的一篇较有影响力的短篇小说,该作品凭借丰富的内涵受到许多读者的青睐。小说主要围绕一条名叫“逝川”的河流和生长在其中的泪鱼,以及居住在河附近独居老人吉喜的命运进行了文学创作。作家在其后来发表的《我能捉到多少条泪鱼》一文中提到,《逝川》是她十分喜欢的代表作之一,是其在每部作品选集中都难以割舍的作品。
一、对自然的敬畏与向往
“逝川”这一名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的《论语·子罕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具体含义是用奔流而逝的江河之水寓意时间飞逝不可逆回。但在《逝川》这篇文章中,它同样被作家赋予较强的象征意义,“逝川的源头在哪里渔民们是不知道的,只知道它从极北的地方来”,小说将其描写为一条虽不宽阔却平静如水,即使是在雨水充沛的季节也不会呈现波涛汹涌现象的河流,只是以缓缓的姿态在袅袅水雾中往岸两边流去,从而给人一种“逝川的水应该是极深的吧”的幽深感。在作家的笔下,逝川具有与时间相似的特点,它有着同时间相似的神秘感,找不到起源也不可倒流,成为主人公悲喜一生的参照。生长在河岸附近的吉喜,长久以来守望着逝川,把自己从一个“明眸皓齿”的美丽少女守望成了一个“干瘦而驼背”、“头发稀疏”的老妪。作品通过将年轻时吉喜的漂亮、饱满、光艳与年老时的沧桑、干瘪、暗淡形成强烈对比,有限的生命在无限时间面前,显得脆弱而无力,但逝川却没有停驻和任何变化。读者阅读该作品时可以深刻体会到生命及时光逝去带来的无奈感,也会让人深切地体会大自然生生不息的伟大。逝川在这里不但被赋予了对时间的代表意义,而且是对生命的一种表征,虽然它无法与北方波澜壮阔的河流相比,却有着女作家独有的温和,它缓慢不停歇地流动,表面平静无波却深不见底,而人类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等都在它的注视下无声无息地上演,人们命运的多舛与河流的平静无波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这种反差更能让人心生感慨,正如主角吉喜体味到的,“人只能守着逝川的一段”,守住的伴随着它慢慢老去,守不住的埋在它附近。
作品里的自然同样被作家赋予了更多的情感色彩,既是人们生存的基本環境,又是人们情感变化的基本场所,作者着力表现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以及与自然和平共处的关系。例如在作品中,作者对月光下的雪夜进行了细致描写,“红松木栅栏上顶着的雪算是最好看的,那一朵朵碗形的雪相挨迤逦,被身下红烛一般的松木杆映衬着,就像是温柔的火焰一样,瑰丽无比”。通过这段文字,读者可以深切感受到自然对生命的孕育之美,也能真切体味到作者本人对生命的美好祝愿及向往。事实上,如此美好的夜晚仅仅是作者通过想象构建的一个美好缩影,在她的作品中,美好的夜晚,宁静的村庄,美丽的日月星辰,会流泪的鱼等都充盈着生命的活力,散发着灵性的光芒。在作家长期生活的东北地区,人们信奉萨满教,他们认为自然界所生长的草木及虫鸟等所有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有灵魂的,因此他们对所有生灵都心存敬畏感,认为万物皆有灵性,自然是崇高而不可亵渎的。然而就像大自然有天灾意外和弱肉强食,人世间有战争和不平,吉喜身上也有着难以愈合的内伤,但她以一种更智性的方式(为阿甲渔村的新生命接生)自食其力,更通过与自然交流时获得的欣悦满足化解种种悲苦,救赎自己的悲喜人生。对于这种渐行渐远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文化,女作家娓娓道来,让人无限向往。
二、对生命的崇敬与景仰
“泪鱼”是作家在小说中描述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它并不真实存在。与逝川相似,作家将泪鱼赋予了一定的文学意义,在她笔下,泪鱼是一种神秘而忧郁的生物,这可以通过其体态特征体现出来,它有着红色的鳍但鳞片颜色却泛着蓝幽幽的光。这种鱼每年初雪的傍晚都会从逝川上游哭着下来,虽然人们很难明白泪鱼为何要年年哭泣,次次带着哭声而来,然而根据本地的传说,只要谁家没有捉到泪鱼其家中就可能出现灾祸。慢慢的,在每年初雪之际捕捞泪鱼就成了阿甲渔村的习俗。人们常常会在河两岸点起篝火,将渔网撒到河里守候着泪鱼的出现。泪鱼最初被人们捉上岸的时候“双眼总是流着珠玉般的泪珠”,但捕鱼者捉到它们时往往以温和的姿态对待它们,这些鱼这时像突然拥有了一种灵性,将它们放回到逝川时就不再发出类似哭泣的“呜呜”声。这种神奇的鱼类似乎象征着人生难以回避的苦难和悲剧,泪鱼在逝川中不停地往返,在此期间会被阿甲村渔民捕捉后再放生,渔民们与泪鱼惺惺相惜地彼此温暖、相互慰藉,人们安慰泪鱼的仪式实际上像是自我安慰的过程,其中蕴含的是对生命的崇拜,对苦难的消化和对新生的希冀。
泪鱼对于孤苦伶仃的吉喜而言是来年吉祥如意的幸运物,然而在这一年泪鱼来临之际,曾经辜负她的旧情人胡会的孙媳妇却要生产了。一边是自己的福祉,一边是新生命的诞生。尽管吉喜内心波澜起伏,但她还是竭尽全力地帮助产妇,亲手将一对新生的龙凤胎带到了这个世界上。那一刻,吉喜对于原始生命的崇敬与景仰已经远远超过了对于民间咒语的恐惧,即使错过了捕捞泪鱼的时间,她也丝毫不后悔。作家在《逝川》中对阿甲村的渔妇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她们走路时发出咚咚的响声,有极强的生育能力,而且食量惊人”,通过这几句简单的言语就勾勒出了阿甲村的女人是结实的、强悍的、自然的,在她们身上你能感受到自然之美,正是这种天性使得她们拥有极强的灵性。上古时期,由于受自然因素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经常会受到来自死亡与饥饿的威胁,为了维持种族的延续及发展,人们希望妇女们拥有较强的生育机能以保证子孙繁荣并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这是较容易理解的。因此无论是放生泪鱼还是重视接生,最根本意义都可以归结为对生命的崇拜。
三、感伤而不绝望的温情endprint
与“泪鱼”名字里充满的伤感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吉喜”名字透露出的喜庆感。然而在作品描写中,吉喜的命运却与其名字的寓意大相径庭,她的一生并不像其名字那般喜庆而美好,命运的无常令她的一生充满了荒谬色彩。吉喜年轻时才貌双全,她有过心上人——能骑善射的胡会。胡会曾经也喜欢过吉喜,但最终还是与彩珠结为夫妻,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却让人唏嘘——吉喜太过能干。自此,吉喜与他断了关系,即使是后来胡会告别人世之际都没出席其葬礼。虽然吉喜通过如此决绝的方式与自己的心进行对抗,但不能真正排解内心深处的孤寂和凄凉。步入中年后的吉喜开始对唱歌情有独钟,凡是听到过她歌声的男人们心里会极其难过并向她找烟吃,吉喜通过这些行为或多或少内心得到了某种安慰。然而这些男人最终也会离去,人影散尽之时陪伴吉喜的就剩下“月光下的院子里斑斑驳驳的树影”。虽然在阿甲渔村,所有男人们都觉得吉喜是个好女人,却没人真的敢和她结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来自社会对女性的偏见,阿甲村渔民普遍存在的传统与保守的思想,导致能干的吉喜孑然一身。虽然吉喜的人生是爱而不得的一生,但是作家并没有把小说落入俗套的爱情故事,也没有对父权社会进行控诉,她只是以独有的情感方式将吉喜的一生娓娓道来,在这过程中读者能感受到吉喜面对生活不公的坚韧与善良,以及对村民们保守愚昧又不失美好的人性的描写,让整个故事充满深切的悲剧美和宿命感。
小说最后,吉喜由于帮助胡会孙媳妇儿接生而没有赶上捕捉泪鱼的最佳时间。她每次将渔网费力地拉上岸都发现没有捕捞到鱼,但当她筋疲力尽地回去取自己的木盆时,却发现十几条美丽鲜活的蓝色泪鱼在自己的盆中悠闲地游耍。虽然已经上了年纪的吉喜只能使尽全身力气把木盆拉到河岸边,并用瘦弱的手把泪鱼们一一放回到河流中,她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他人给予的关怀与温暖,正是这些关心与慰藉让吉喜把命运带给她的苦难无声地溶入流动不息的河水中。老吉喜的幸福虽然并不圆满,甚至苦难大于幸福,但她的勤劳善良、坚忍执着得到了周围村民的尊重,也使人性的美好得到了证明。
逝川,作为一条有着时间及生命寓意的河流,在其岸边生活着一个善良的吉喜,无论是曾经无比丰富饱满的吉喜,还是年老已然嚼不动生鱼的吉喜,眼神中都迸射出雪亮的鱼鳞般的光芒,在她的木盆中,仍然有鲜活的泪鱼在舞蹈。作家对自己的作品风格进行过解释,她认为虽然她的许多作品在意象创作上给人一种苍凉感,而且整体基调也以忧伤为主,但即便如此仍然可以在其中发现温情的身影,正是這几缕温情让人感到欣喜及温暖。逝川、泪鱼和吉喜,三者之间或对立统一或相互映照。纵然孤独,亦有温情,亦是美好。每一个生命,莫不如此。
参考文献:
[1]方守金,迟子建.自然化育文学精灵——迟子建访谈录[J].文学评论,2001(3).
[2]迟子建.寒冷的高纬度:我的梦开始的地方[J].小说评论,2002(2).
[3]迟子建.我能捉到多少条“泪鱼”[J].当代作家评论,2005(4).
基金项目: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院级课题“论迟子建作品中的女性生态意识”(编号:y17002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