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古塔的笳愁
2017-11-24卜键
卜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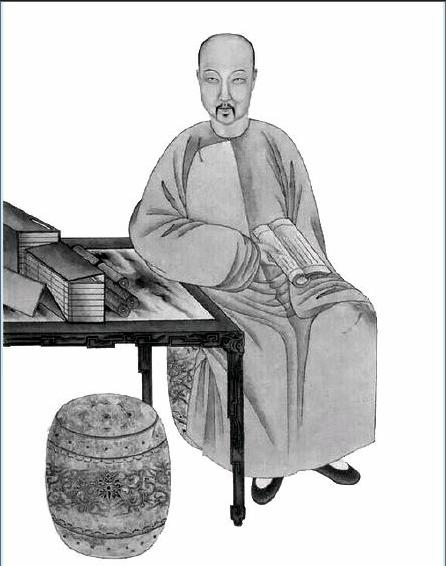
几乎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遭逢大小变故,猝然临之,无故加之,小者数日或数月即告平复,大者历数年数十年险厄困乏,甚焉者万劫不复。此际的生命个体常显得纤弱渺小,当事人的自尊自信多被雨打风吹去,尤显出亲情友情之可贵。老舍先生在太平湖畔长夜徘徊,终于投水自尽,最是灵魂孤凄、精神毁碎的近例;而清代顺康间的江南才子吴兆骞,由于一批亲友不离不弃,也幸得几任满洲将军对知识心存尊重,竟在宁古塔度过二十三年流放生涯,最后回归内地,是情义坚贞人性美好的例子。
自去年起,笔者因撰写有关库页岛的系列文章,拣读涉及东北极边地域的史料,渐而关注几个重要边镇的兴替变迁,如宁古塔、三姓、瑷珲、卜魁等,也注意到流遣其地的汉族文士之命运。本文即以吴兆骞《秋笳集》为线索,述写他的个人遭际,兼及其他流遣文士的边地生活。那也是中国读书人曾经的厄运与宿命,而在冷寂匮乏的“绝域”,文学仍能绽放出小小的花。
一、当才子跌落云端
吴兆骞出于吴江县一个世代簪缨之家,早岁以诗文著称,列名“江左三凤凰”。此类少年成名的才子,自我感觉大多好得出奇。苏州有文社名“慎交”,兆骞活跃其中,常与他社争胜,因此也播下仇恨的种子,而浑然不觉。一次名士汪涵来访,兆骞对他说:“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满是少年未经事之轻狂,哪里得见一个“慎”字?
顺治十四年秋,吴兆骞参加江南乡试,顺利得中举人,岂知庆贺未息,大祸随之:南闱主考官被劾舞弊,皇帝降旨逮治,很快就将主考副主考与十六位房考一律处死;吴兆骞等八名新科举人牵连其中,皆被革去功名,打四十大板,流放宁古塔。清朝多沿承明制,廷杖也由前明传下来,嘉靖三年的“左顺门事件”中,翰林院修撰王相等十余人当场惨死杖下。这次镇抚司见圣上钦命杖责,下手狠辣,幸得一刑部侍郎挺身斥责,受杖众书生才免于一死。
清初“科场案”的内涵颇为复杂。考官弄权舞弊、暗通关节的情形的确存在;但也不乏劣衿煽惑滋事,读书人之间嫉妒倾陷等情;亦有清廷藉堂皇正大之名打击江南士子的因素。以兆骞之才学与傲骨,当是不会作弊。他与父兄都说是遭人陷害,方式为匿名揭帖,并指出造谣者为同声社的章在兹、王发,也有记载指其一位本家参与构陷,皆难以系定。匿名信之恶正在于是,含沙射影,滋生疑忌,大坏人心和亲朋关系。明清易代之际,江南文祸相连,就中的揭发出卖、同类相残、借刀杀人,尤令人感慨愤懑。
清廷也給了吴兆骞机会。在中南海复试之前,兆骞已被视为犯罪嫌疑人,仍准许他参试,以答卷情况再作印证。可那是怎样的考试呢?“每举人一名,命护军二员持刀夹两旁,与试者皆惴惴其栗,几不能下笔。”(王应奎《柳南随笔》)这还是对待普通试子,还给了温书备考的时间。如吴兆骞已知有人诬告,已是数经讯问,心理压力当更大。且原来持续九日的三场考试,复试要求一卷定夺,也觉时间匆迫。考试的题目由顺治帝钦定,赋题为“瀛台赋”,作赋乃兆骞长项,唯此时心绪缭乱,文思枯竭,竟没能答完试卷。
三月九日,兆骞在礼部点名时被当场拘捕,惊惧委屈化为绝望,绝望转为痛愤,再激撞而成诗句,喷发而出:
仓皇荷索出春官,扑面风沙掩泪看。
自许文章堪报主,那知罗网已摧肝。
冤如精卫悲难尽,哀比啼鹃血未干。
若道叩心天变色,应教六月见霜寒。
(《戊戌三月九日自礼部被逮赴刑部口占二首》)
第二首大体相类,说不上精彩,却能见一腔冤情,满腹哀怨。这是兆骞在礼部被捕时嘶喊出来的诗句,在场众人颇受感染,满汉堂官等皆为之叹息,啧啧“称为才子”。此话出于兆骞自记,尽管已身处刑部大牢,仍以才子自矜。他在给父母的信中描述了当日情景:“索纸笔不得,即厉声哀诵,以当庶女之告天。”庶女,特指元杂剧中的窦娥,末句“应教六月见霜寒”,正用关汉卿《窦娥冤》“血溅白练,六月飘雪”之典。
出于舆论的压力,或也出于良知与惜才,刑部对吴兆骞等人的审讯是慎重的,今知至少还有一次“命题限韵”,再试同案各犯的才学。刑部狱对文士的监管并非太严,狱友互相分析案情,兆骞也知只能以诗文证明诬罔,早有腹稿,故尔援笔立就:
自叹无辜系鷞鸠,丹心欲诉泪先流。
才名夙昔高江左,谣诼于今泣楚囚。
阙下鸣鸡应痛哭,市中成虎自堪愁。
圣朝雨露知无限,愿使冤人遂首丘。
(《四月四日就讯刑部江南司命题限韵立成》)
满纸的负屈含冤,满纸见悲情洒落,哀而不怨,捷才与实学亦尽显。刑部司员多为两榜出身,读后自会有基本判断。
当日的审讯细节已不得而知,但显然在定性上存在歧异,存在对受审者的怜惜,审了将近一年,许多事仍难以定案。最后惹得龙颜大怒,将刑部满汉尚书、侍郎与司员等分别革职降级。再也没有什么盼头了,兆骞诸人经历了焦灼等待后,踏上漫漫流遣之路。
朝野对吴兆骞等人命运的关切不平,当时即形诸诗文。吴伟业深知其间冤抑,知江南文社之陋习、文人之间的倾轧,连写三首长诗,以《悲歌赠吴季子》最为著称:
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君独何为至于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十三学经并学史,生在江南长纨绮。词赋翩翩众莫比,白璧青蝇见排诋。一朝束缚去,上书难自理。绝塞千山断行李,送吏泪不止,流人复何倚?……生男聪明慎勿喜,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
长歌当哭,既哭素来爱赏的后起之秀吴兆骞,哭那些大难当头仍内讧不止的小人儒,也自哭身世遭逢。时吴伟业力辞国子监祭酒未久,痛悔三年进京居官之举,亦可称“受患只从读书始”。
二、漫漫遣戍路
顺治丁酉乡试,先是北闱(顺天考场)出事,获罪者与家人流放奉天的尚阳堡,送行之际号泣震天。及得知南闱(江宁考场)遣发更远更冷的宁古塔,又有些庆幸。比,或是化解郁结之妙方,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也。《研堂见闻杂记》特意比较了两闱获罪流遣之地,曰:“宁古塔在辽东极北,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中国人亦无至其地者。诸流人虽各拟遣,而说者谓至半道为虎狼所食,猿狖所攫,或饥人所啖,无得生也。向来流人俱徙尚阳堡,地去京师三千里,犹有屋宇可居,至者尚得活,至此则望尚阳如天上矣。”著者王家祯为娄东人,所写宁古塔情形殊属夸张,应是受了吴梅村的影响。宁古塔距京师实为三千里多一些,虽说冰冻期较长,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远没有所写这般可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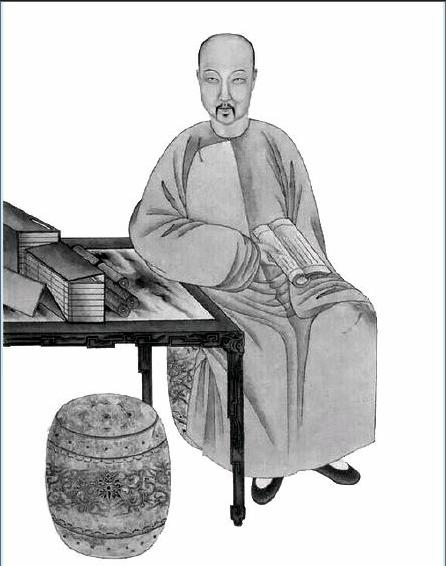
梅村诗中的宁古塔,更是如同鬼域:“七月龙沙雪花起,橐驼腰垂马没耳。白骨皑皑经战垒,黑河无船渡者几?前忧虎狼后苍兕,土穴偷生若蝼蚁。大鱼如山不见尾,张鳍为风沫为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昼相逢半人鬼。噫嘻乎,悲哉!”诗人没有到过此地,所写文字或得自传闻,更多的当是为了染写悲情,有意将流放地描绘得惨淡险恶。
对于两闱获罪之人,清廷处分极严,家产抄没,父兄妻子皆随同流递,而具体执行时则情形各异。以吴兆骞为例,家人先是被逮系苏州狱,知府以其父母年老、妻子多病取保放归,仅收押其六弟;次年刑部命将其父兄解送京师,一年多之后亦赦归。十六年闰三月初三,家人还没有抵京,兆骞仅靠朋友接济些银两,与一众长流人犯被押解着迤逦而去。吴家本富裕,抄检之后资产净尽,父亲捎来拼凑的二两多散碎银子,还有一封长长的信,压根就没到他手上。即使如此,兆骞仍携带了不少书籍,载于牛车之上,成为他在戍地活下去的一种精神支撑。
按照清朝律法,免死遣犯必须镣铐加身,两名解差押送一人,犯人多时以五名为一拨,次第前行。由吴兆骞纪程诗,可知他们在途中过得还不差,可以登临台阁,凭吊故迹,偶尔也会亲访友,吟诗作赋。流人之苦,又细分为许多等级,犯官与文士的待遇,显然与一般刑事罪犯不同。吴兆骞一行在路上走了四个多月,由暮春到初秋,是东北最好的时节。这个看惯江南景色的才子,离京出关,渐行渐远,北地的浩茫壮阔扑面而来,万千感受发诸诗作:
望乡台回边云断,姜女祠空海气寒。
(《关上留别潘守戎》)
敢望余生还故国,独怜多难累双亲。
(《出关》)
万里川原迷大漠,百年亭堠识前朝。
(《同诸公登中后所戍楼》)
海风吹天星动摇,边色横烟月澄廓。
倚笛频惊出塞声,衔杯尚拟华年乐。
(《同陈子长夜饮即席作歌》)
河流秋淼淼,边色夜荒荒。
画角千峰月,羊裘七夕霜。
(《七夕次喇伐朵洪》)
这些诗有的即席而成,有的题于邸舍壁上,另有一些因担心“违碍”在刊刻前被刪掉。遣戍路即伤心路,行愈远而感伤愈甚。读这些纪程诗,自怨自艾似无处不在,可我们也能发现,诗人那胸中郁积渐次消散,开始把关注更多投向北方景物,有时竟是满目新奇。
三、宁古塔的文士
清初东北的第一个流放地是沈阳,接下来是尚阳堡,然后便是宁古塔等,总之越流越远。为多尔衮鸣不平的彭长安、许尔安三年前被遣发宁古塔,传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亦流放于此,与江南科场案约略同时,而诗文记载一无可征。遣戍宁古塔者可谓三教九流,有汉族也有满族,有文人也有武人,更多的是刑事犯,而留传姓名事迹的多是文士,赖有一支笔在焉。后来清朝增设瑷珲、卜魁、三姓等边镇,除卜魁(齐齐哈尔)有几篇简记,其他地方均付诸冻雨飘风,究其原因很多,但缺少文人和不尚文字应为主因。
此时的宁古塔不同,江南科场案流犯不同,这是一批被集中发遣的书生,一批才华横溢、年纪较轻的诗人。
文士流遣宁古塔,吴兆骞等应属较早的一批。抵达之初备极苦况,深山修路,泥途挽车,还要随军做各种杂役,远至混同江(黑龙江与松花江、乌苏里江合流的下游河段,又作“下江”),甚至抵达临近库页岛的入海口一带。他有一首《海边独眺》,推测应写于此处。更为煎熬的又不在随军效力(毕竟还有些吃的),而在于冬月独处的日子。据李兴盛《中国流人史》记述,初到时兆骞孑然一身,常不名一文,冬日呆坐在栅栏门内,或以斧子破冰烧水,煮一点稗子充饥。请看这首五言小诗:
磵户寂无侣,凄凄露尚垂。
楼空秋气早,林密晓光迟。
芜没人三径,萧条海一涯。
此乡弓马地,抱简日垂眉。
(《晓坐》)
所记大约是他抵戍后的第一个住处,邻近山谷,极见清寂困窘。仗着年轻,还有乡亲难友们的接济,总算活了下来。
兆骞是与同年方章钺一同起解、一同抵达的。章钺之父方拱乾时为少詹事,曾力辩与南闱主考官方犹并非同宗,未被采纳,致使他与四个儿子(长子玄成为顺治六年进士、侍读学士;次子亨咸为顺治四年进士、监察御史)皆株连流放,全家数十口押往宁古塔。兆骞与方家一路同行,患难之交,复气味相投,在戍地得其关照甚多,“商榷图史,酬唱诗歌”,生活与精神上皆为依靠。两年后方家认工赎还,临别时方拱乾将兆骞托付好友许尔安照顾,情义之重令人感动。
刚到戍地,对每一个江南文士都是严峻考验,是日复一日的折磨,也是逐渐的适应过程。宁古塔将军巴海给予遣戍文士很多优待,平日减少差徭,年节间还请他们到府中宴集。北地民风本来淳朴,敬重知识,见将军如此,更能引领一时风气。顺治十七年冬,兆骞之妻葛氏在安顿好两个女儿后,起程赶往戍地陪伴丈夫,他的小妹一路相陪至京师,在刑部办理手续,也得到一些京中友人的馈赠。此年二月,葛氏由京师抵达戍地,带来男女两个家仆,兆骞的孤苦情形顿时改观。流戍文士在此设馆授徒、书法绘画、讲学、行医,也包括他们带来的各类种子,种粮种菜,皆令当地人耳目一新。吴兆骞很快有了儿子桭臣,小名“苏还”,祈愿早日返回故乡苏州。桭臣后来作《宁古塔纪略》,记母亲采野玫瑰制作玫瑰糖,又以榛子、松子、山楂等做糕,“土人奇而珍之”。
聚集了这么多文人,宁古塔迎来一个诗文繁兴的短暂时光,主其事者为张缙彦。缙彦曾任明崇祯末兵部尚书、弘光朝河南等三省总督、清工部侍郎等职,动辄改换门庭,自也谈不上气节风骨,却有着一份文雅风流,家资亦丰厚。他是因牵连文字狱被流遣的,毕竟经历过政治上的大风大浪,处之泰然,随行携带歌姬数人与大量图书,一副“扎根边疆”的架势。康熙四年,缙彦创设诗会,邀集姚其章、吴兆骞、钱威等六人,号称“七子之会”或“七谪之会”,每月聚集两三次,分题角韵,所作诗词虽较少流传,仍不失一段佳话。绝域之孤单索寞,使得流放者多不问来路与志节,就像道光间林则徐流遣伊犁,与素不喜欢的原东河总督文冲相遇,竟然成了过从甚密的好友。
“七谪之会”中的钱氏三兄弟,为浙江通海案流犯,而姚其章、吴兆骞、钱威为南闱案犯,诗文中称同年,也同时流递宁古塔。钱威是吴江人,该县丁酉科共有四位试子中举,全部被流遣。其中吴兰友病死于抚顺,吴兆骞为其料理丧事;后来路经松花江,兆骞因天热入江游泳,得了寒疾,濒死而复生,终于到了宁古塔。又后来命运播迁,南闱流犯有的入水师营做了水手,有的被遣往更远的三姓城(今依兰),有的搬到乌喇(今吉林市),大多数终身未归,老死边荒。
四、“海东三万里,笳吹日相闻”
这是兆骞在宁古塔所写诗句,当作于抵戍未久,题名《奉送巴大将军按部海东》。每年夏月,宁古塔将军都要率部巡边。海东三万里,极写将军衙门统辖区域之广,荒凉旷远;笳吹日相闻,则指沙俄殖民者侵扰抢掠,边地部族不断告警,官军出兵清剿,笳鼓竞吹。
对内地流人来说,不仅要忍受宁古塔严酷的自然环境,还要面对外敌入侵的威胁。自晚明始,沙俄将开疆拓土的重点转向东方,负有特殊使命的探险队、政府资助的哥萨克殖民队接踵而来,打破了这块古老土地的静谧安详。清朝定都北京的当年,波雅尔科夫率领近百名武装哥萨克翻越外兴安岭,在黑龙江流域四处抢掠,历时约三年。接下来是哈巴罗夫,在雅库茨克督军支持下,組建了一支更大的哥萨克队伍,甚至侵入我松花江、乌苏里江一带。那也是一帮一伙的“流人”,准确地说是流寇(当地人呼为罗刹、老掐、老枪、老羌,皆见憎恨),得到沙俄官方支持,占据村寨,设立城堡,强行向当地部民征收实物税。达斡尔、赫哲、费雅喀等部族难以抵敌,不少部民被杀害,村屯焚为废墟。那时黑龙江将军衙门与三姓副都统衙门尚未设置,宁古塔作为唯一的东北边镇,三江流域大都归其管辖,有守土安民之责。
顺治九年二月,驻防宁古塔梅勒章京海塞(又作海色)率兵六百进击盘踞乌扎拉村的入侵者,当地部民闻讯赶来相助,敌人在炮击中死伤甚多,哈巴罗夫本人也被击伤。海塞下令停火,要求抓活的,官军攻势顿减,哥萨克得以喘息调整,抢过大炮反攻。到手的胜利化为乌有,清军损失惨重,海塞也因贻误战机被处死。这是清朝官兵第一次对俄自卫反击战,遭遇惨败,给边境部族与满汉军民留下巨大阴影。哈巴罗夫所部也受到重创,率队退回雅克萨城堡。
接下来是更为凶残的斯捷潘诺夫,所部已变成名副其实的“哥萨克匪帮”,不时乘船而下,滋扰下江地域,甚至窜入松花江、乌苏里江口,一路杀人越货。宁古塔总管沙尔虎达出身于当地苏完部,隶镶蓝旗,随军征杀数十年,接任后多次闻警出征,挫败入侵之敌。十五年二月,为加强边防力量,清廷向朝鲜征调二百名鸟枪手。朝鲜国王李淏表示纵使遇到再大困难,也一定要遵照发兵,“差北道虞侯申浏为将领,率哨官二名、鸟枪手二百名,旗鼓手、火丁共六十名,带三月粮,六月渡江,至宁古塔”,编入征剿部队,随沙尔虎达乘船由松花江北行。在接近黑河口江段,清军与溯江抢粮的哥萨克船队遭遇,沙尔虎达即命炮击,经过连续三天的激战,斯捷潘诺夫被打死,约二百七十名哥萨克被击毙或生俘,焚毁俄舰十艘。这是清军的一次重大胜利,而沙俄残匪败而不溃,仍盘踞在下江一带。
吴兆骞诗中所称的巴大将军,为沙尔虎达之子巴海,是较早的满族读书人,顺治九年得中满洲榜探花,历任秘书院侍读学士、经筵讲官。沙尔虎达积劳病逝,谕旨命他回乡接替父职,曰:“宁古塔系边疆要地,昂邦章京沙尔虎达在彼驻防年久,甚得人心。今已病故,其子巴海素著谨敏,堪胜此任,著即代其父为昂邦章京前往驻防。”(《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三)康熙元年,为强化对东北边疆的掌控,朝廷将宁古塔由总管衙门改称将军府,巴海即为第一任宁古塔将军。
巴海离京赴任之前,江南科场案已经历了漫长审讯,推想这位出身翰林的满洲将军,必也怀有同情心。巴海进京述职,兆骞还托他给羁押中的父亲带去书信。遇到这样一位儒将,吴兆骞等流放者也算烧了高香。他在家书中提到一件事,感戴殊深:康熙五年正月初五,副都统因巴海患病代行管事,发令箭要兆骞与钱德维两家立即前往乌喇(今吉林市),“初六平明起身登车,雪深四尺,苦不堪言……行至三日,将军命飞骑追回,倘再行二日到乌稽林,雪深八九尺,人马必皆冻死,将军真再生之恩也”。(《秋笳集·上母亲书二》)其时宁古塔有两位副都统,不知哪位所为,也不知其为何要这样做。
在抵任的次年夏天,巴海统兵沿松花江出黑河口,往下江清剿哥萨克残匪。兆骞有诗《奉送巴大将军东征逻察》,“军声欲扫昆吾兵,战气遥开野人部”,笔意极雄壮。野人部,指赫哲、费雅喀等下江地域部族,深受哥萨克流寇欺凌。清军在伯力一带江面设伏,炮击敌舰,见其逃窜即紧追不舍。敌人纷纷弃舟逃命,清兵大举掩杀,“斩首六十余级,淹死者甚众,获妇女四十七口,并火炮、盔甲、器械等物”。这是巴海奏捷时所写,也是报喜不报忧,隐瞒了己方损失五艘战船之情,事发后受到处分。可证哥萨克武装的战斗力甚强,清方以多击少,以官军击“民兵”,以伏兵击无备,仍是多有损伤。宁古塔流人并未从征,兆骞有一首《秋夜师次松花江大将军以牙兵先济窃于道旁寓目即成口号示同观诸子》,大约是作为民夫,挽运粮草辎重,送至江边。
吴兆骞写了一批类似诗篇,谴责罗刹的残暴行径,为官军出征鼓与呼,被誉为清代的“边塞诗人”。应说是,但所作与唐代的边塞诗风格迥异,缺乏那种慷慨激越、雄浑豪壮的家国情怀。兆骞的诗不乏宏阔瑰奇,不乏真情投注,但大多属于应景奉承之作。康熙五年早春,为抵御俄人入侵,兵部发文要求所有六十岁以下流人一概当役,并选二百名做水师营水手,到乌喇演练备战。巴海差管家请兆骞等至府中,恳切相告:“我家养你们几年,念你们俱是有前程的,并无差徭累及。不意上面因有边警,俱着你们当差,水营、庄头、壮丁,这三件任凭你们拣择一件,三日后到公衙门回复,此即是我的情了。”(《归来草堂尺牍》家书第十二)将军大人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大家流泪眼观流泪眼,也都无可推却。同时流遣的祁奕喜、杨友声等入营做水兵,吴兆骞与钱、姚二同年表示愿意“认工”。所谓认工,即出钱修造官府建筑。常年以举债度日的他哪里有钱认工,得过且过罢了。
由于担心交不了钱受罚,兆骞再次向母亲要钱,信中细述哥萨克之凶残以及面临的危险,极是哀凄真切:
逻车国(即俄罗斯)人皆深眼高鼻,绿睛红发,其猛如虎,善放鸟枪,满人甚畏之。若国人作水兵,何异汤浇雪,刀切菜,必死无疑。虽今年新当水兵者不跟出征,然将来必不免,此水师营必不可入也。况一选在簿上,即时打发往乌喇去……路上雪深五六尺,车行甚难。他们充当水手者以二月十一日起身,儿送至西郊外十里,哭声震天,真不忍闻。至若官庄之苦,则更有难言者,每一庄共十人,一个做庄头,九个做壮丁,一年四季无一闲日。一到种田之日即要亲身下田,五更而起,黄昏而歇,每一个人名下要粮十二石、草三百束、猪一百斤、炭一百斤、官炭三百斤、芦一百束…… (《秋笳集·上母亲书四》)
兆骞细述这些的目的,是要母亲在家乡筹钱,帮助认工。他有一些家信留存下来,先是写给父亲,父亡写给母亲,历历述说在戍苦况,同时便是要钱,哀苦求告。岂不知科场案后家产已被抄没?大约觉得家中可以告贷,每一封信都求寄钱来,似乎非此便活不下去。其信大多半路遗失,包括这一封,家中并无银两捎来,兆骞也挺过来了。康熙六年,曾参与审办江南科场案的刑部司员安珠瑚来任宁古塔副都统,对兆骞等颇多同情关照,《秋笳集》中有多首写给安珠瑚的诗,可证交往之亲切。十七年夏月,安珠瑚升任奉天将军,兆骞与钱德维合作《奉寄安大将军三十韵》,感念哀伤,亦见交情深厚。
吴兆骞写了不少边地诗篇,也留下一批边地信函,唇吻口角相当悬殊,呈显出一个流人的日常应酬与心中所思所想,真实可信。他憎恨哥萨克的入侵,却也不把那冰雪大地当作自己的家国,大敌当前,诗情激越,想的却是如何不上前线,如何苟且偷生。“塞外苦寒,四时冰雪,鸣镝呼风,哀笳带血,一身飘寄,双鬓渐星。妇复多病,一男两女,藜藿不充,回念老母,茕然在堂”,是他写给好友顾贞观的信,也是谋求相助,意图逃离此地。能要求一个蒙冤长戍的汉族文士怎样呢?
“雨暗江花老,笳愁陇月曛”,是唐代崔涂送友人赴边地的诗句。军中笳鼓多是激昂雄豪的。兆骞写了不少为官军壮行的诗,色泽韵致略同,但他笔下更多见的是“寒笳”“哀笳”“客泪沾笳吹”,透出那无边的笳愁—盘袅在笳声里的乡愁。
五、何处是归宿?
山海关外的官道旁有一岭而二名:流人出关,称之为“凄惶岭”;及至得赦归乡,则呼为“欢喜岭”。二十年十一月,吴兆骞一家终得回归,路经欢喜岭时留宿一晚。据其子所记,兆骞与妻子久久难以入眠,各自讲述当年出关时的景况。这些话在宁古塔必也无数次讲过,此番说起,欢喜是有的,更多的应是感慨庆幸。
流人梦寐以求的是回归故乡,百计营求,虽有极少数人能成功,也是历尽周折。吴兆骞的归乡之路很漫长,在宁古塔二十余年间,他心心念念要回到江南,长昼永夜,不知道冥想出多少办法:让父兄去京师告发仇人,以洗却诬罔;精心结撰《长白山赋》,期望直达圣听;频频央告朝中旧友,求他们想方设法……“人情势利古犹今”,“人情似纸张张薄”,是对世情浇薄的永恒叹息,却也总有一些古道热肠之士。兆骞事涉前朝钦办大案,违反科场作弊之禁条,最后能够赦回内地,有几个人的倾力相助不能不说。
一是在苏州文社的知交徐乾学,与兆骞同岁,为康熙九年探花,才学卓著,性格亦豪放,可入仕的前些年不太顺利,加上先后丁父母忧,尚未攀上高位。乾学一直与兆骞书信往返,鼓励接济,为之奔走联络,为他出版《秋笳集》(又被称为“前集”,凡四卷),并倡议筹措赎免银两。多至数万少至数千两银子,对于一帮京城文职尤其是穷翰林来说,募集大非易易。
第二个是顾贞观,小兆骞六岁,亦苏州文社中好友。贞观在大学士明珠府上坐馆,与纳兰性德交谊深厚,得兆骞求救信心急如焚,作《金缕曲》二首,凄婉哀慕,兹引其一: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据说正是此两支曲辞,感动了一代词人纳兰性德,也正式将营救的想法付诸行动。性德之父明珠为内阁大学士,权势方盛,喜欢延揽人才,而即便是他出手相助,也只能纳锾以赎,要大家来凑钱。有了明珠的关注(可以设法降低赎金的数额),有了徐乾学、顾贞观、纳兰性德等人的倡议,一时京华名士纷纷解囊,“辇下名流,以不与此事为歉”,兆骞的赎归终于办成。
康熙二十年七月,吳兆骞接到准其还乡的公文,喜极而泣。然离别亦难,要一一告别多年共患难的知交,要给已订亲的儿子操办婚事,亲友也要轮番饯行,拖至九月二十日才起身。其子桭臣记辞归时景况:“亲友及门人举送至沙岭,聚谈彻夜,至晓分手。我父哭不止,策马复追二十余里,再聚片时而回。”(《宁古塔纪略》)同年张明荐已病殁,兆骞携带其骸骨与女儿还姐(也有一个“还”字)归乡,而多数同戍文友已鬓发斑白,仍不得不留在宁古塔。
当初遣发时兆骞一行走了四个多月,而归程甚速,其间得奉天将军安珠瑚挽留小住,仍在十一月下旬抵达京师。徐乾学为他举办了一次雅集,赋诗《喜汉槎入关》,京中名流纷纷唱和。国子监祭酒王士禛所作尾联,为“太息梅村今宿草,不留老眼待君还”,唏嘘感叹,令人忆起吴梅村当年为兆骞鸣冤的长诗。自古多言“文人相轻”,其实文人相亲相重、同声同气、情谊不渝的例子也是史不绝书,援救兆骞之事即其一。
欢宴之后,兆骞被太师明珠聘为西席,教其次子揆叙读书,纳兰性德对他很敬重,时相请益切磋。有意思的是,二十一年二月到五月,性德扈从康熙帝东巡至乌喇,将军巴海接驾;八月至十二月性德随副都统郎坦再赴东北极边,过宁古塔后一路相度地形。时康熙帝决意解决罗刹之患,正认真筹划进军与剿除之策,这是雅克萨之战的前夜,与宁古塔流人自也息息相关,却不知性德与兆骞是否讨论过此类话题。
当年末,兆骞始回乡看望生母,拖了近一年未回,大约还是迫于经济的压力。朋友们已然醵金将其赎回,当也不好意思张口再讨资助了。履行了塾师职责,领到了明珠府的束修,兆骞回乡探母,还营建了三间房舍,似乎打算住下来。但他在故乡缺乏稳定的收入,挣扎了一年,其间卧病数月,只得再回京师。归乡的流人多数生存艰难。方拱乾回归后漂泊扬州,卖字为生,仅五年就病逝。“岁岁还乡梦,今朝梦始真。到家仍作客,无地可容身。”这是怎样的悲凉!
自古才子固多恃才傲物、盛气凌人,而可贵可羡就在那股子书生意气。命运弄人,吴兆骞虽勉力保持着自尊,然豪情不再,处处求人,宁古塔赋予的一圈极地光晕迅速消散,苦难岁月留下的刻痕则洗涤难去。据他人描述,居京期间的兆骞,一副拘谨瑟缩、穷困潦倒之相,时时感恩流涕,“朋旧全非,容颜乍老”。复因在宁古塔时间太久,已不太适应关内的饮食与气候,经常患病卧床,手足肿胀,脾胃失调。今存兆骞与纳兰性德的多封书信,几乎全与诊病、寻药包括想吃什么东西有关。他回京后仍在明珠府处馆,仅过半年多时光,即病逝于旅舍。对于他的死,纳兰性德、徐元文、潘耒等写了祭文与挽诗,但悲悼者无多,远不及三年前的欢迎雅集之数。
归乡是流人萦绕难去的梦,而一旦梦想成真,或也成为一条绝路—绝望与绝命之路。不管承认不承认,宁古塔已是流人的第二故乡。假设仍留在那里,吴兆骞会多活些年头么?应说是的。临行前,巴海将军已然礼聘兆骞为幕友,掌书记,管理台站兼府中塾师,这是一份好差使,报酬亦可观。因为要回乡,他谢绝了。在病榻上,兆骞向儿子桭臣及故人之子杨宾表达了对宁古塔的眷恋:
吾欲与汝射雉白山之麓,钓尺鲤松花江,挈归供膳,手采庭下篱边新蘑菇,付汝母作羹,以佐晚餐,岂可得耶?
这番话与金圣叹临刑遗言有些相像,见诸杨宾《柳边纪略》,真切传递出兆骞离世之际的心声。吴兆骞会追悔自己的回乡选择么?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他会怀念宁古塔,怀念那个人性质朴、物产丰富的边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