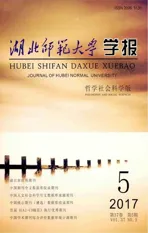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与自尊:人际关系的中介作用
2017-11-21谭雪晴贾晓督李智勇
谭雪晴,贾晓督,李智勇
(湖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与自尊:人际关系的中介作用
谭雪晴,贾晓督,李智勇
(湖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目的:考察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现状及人际关系、自尊的影响机制。方法:抽取湖北、天津、广西5所高校955名大学生,采用自尊量表(SES)、大学生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生命意义感量表(MLQ)中文修订版进行调查。结果:(1)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水平居中,自尊水平较高。虽然人际关系困扰水平整体较低,但仍有42.1%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困扰(主要体现在人际交往方面);(2)自尊与生命意义感显著正相关,与人际关系困扰显著负相关;除人际交往与寻求意义感相关不显著外,人际关系困扰与生命意义感的两个维度均呈显著负相关;(3)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人际关系在自尊与生命意义感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结论:当代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并不乐观。在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不但要引导学生认识自我,更应该提升其人际交往的能力。
生命意义感;人际关系;自尊;大学生
一、引言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对生命意义感的研究逐渐增多,大众也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生命质量。Frankl认为寻找意义是人类一个重要、普遍的动机,缺少这个动机,人们就会感到厌烦、无望、压抑和失去求生意志[1]。Steger认为生命意义感是指人们领会、理解自己生命的含义,并意识到自己活着的目标、任务或使命,可分为生命意义寻求和生命意义体验两个维度[2]。当今社会自杀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而中国大学生自杀率为一般人群的2-4倍,且呈上升趋势[3]。有研究指出,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状况密切相关[4],且生命意义感的提高有助于减少自杀意念的出现[5],因此关注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具有重要意义。
自尊是个体对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情感体验[6],是心境能否得到良好调节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自尊与生命意义呈显著正相关,对生命意义有一定的预测能力[7],并且自尊在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对死亡态度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8]。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交往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心理关系,它反映了个体或团体寻求满足需要的心理状态,也是人的心理行为的综合表现[9]。郭海燕的研究发现,自尊与人际困扰呈显著负相关,并且对人际关系有直接影响[10]。同时,周娟的调查结果表明,人际关系同生命意义感呈显著的相关关系[11]。由此看来,生命意义感、自尊与人际关系间的联系十分紧密,本研究拟通过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自尊、人际关系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分析,探讨自尊、人际关系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机制,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依据。
二、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选取湖北、天津、广西的5所大学进行抽样,共发放问卷955份,回收有效问卷869份,回收率为91.0%。其中湖北486人,天津278人,广西105人;男生297人,女生572人;大一211人,大二272人,大三288人,大四98人;理科生521人,文科生348人;独生子女348人,非独生子女521人;城市家庭来源275人,乡镇家庭来源168人,农村家庭来源426人。
(二)调查工具
1、生命意义感量表(MLQ)中文修订版
采用刘思斯、甘怡群等人翻译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量表(MLQ),共9个项目,分为拥有意义感(MLQ-P)和寻求意义感(MLQ-S)两个分问卷。拥有意义感分问卷有5个题项,寻求意义感分问卷有4个题项,用Likert7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7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生命意义感越强[12]。本研究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5。
2、大学生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
采用郑日昌等人编制的大学生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该量表是一份人际关系行为困扰的诊断量表,共28道题。量表从四个维度考察了与人相处时存在的困扰程度,分别是人际交谈困扰、人际交往困扰、待人接物困扰、异性交往困扰。每道题回答“符合”得1分,“不符合”得0分,分数越高,说明受人际关系困扰越严重[13]。本研究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
3、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SES),由10个项目组成。采用Likert4点计分,从1很不符合到4非常符合,总分越高,自尊水平就越强。在原量表中第8项(我希望我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尊重)为反向计分,本研究依据已有研究的建议采用正向计分[14,15]。本研究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
(三)施测和统计分析
在各大学内选取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匿名作答,有统一的指导语,并且所有问卷当场回收。将所有数据录入后,运用SPSS21.0和Amos17.0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
(一)总体得分情况
1、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总体水平

表1 生命意义感得分情况
表1结果显示,大学生拥有意义感得分显著高于理论均值20(t=22.199,p<0.001);寻求意义感得分显著高于理论均值16(t=27.645,p<0.001);生命意义感得分显著高于理论均值36(t=32.106,p<0.001)。进一步计算问卷各维度及总分的均分得出,大学生寻求意义感为5.05、拥有意义感为4.80、生命意义感为4.91。该问卷采用7级评分,结合评分等级的含义,可看出虽然大学生拥有意义感、寻求意义感和生命意义感均高于理论中值,但仍处于中间组的水平,表现出生命意义感的不确定状态。
2、大学生自尊总体水平
本研究显示,大学生自尊得分为29.62±4.08,显著高于理论均值25(t=33.349,p<0.001),进一步计算出问卷总分的均分为2.96。该问卷采用4级评分,结合评分等级的含义,可看出大学生自尊水平较高。
3、大学生人际关系总体水平

表2 人际关系得分情况
表2显示,大学生在人际交谈、人际交往、待人接物、异性交往四个维度上的得分有所不同。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四个维度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F=159.810,p<0.001),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人际交往>人际交谈>异性交往>待人接物。同时,根据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的计分方法[13]发现,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整体水平较低,但仍有42.1%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人际困扰,其中有一定困扰的(9-14分)占30.2%,困扰较为严重的(15-28分)占11.9%,人际关系障碍者(20分以上)占1%。
(二)生命意义感、人际关系与自尊的相关分析

表3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3显示自尊与人际关系困扰呈显著负相关,与寻求意义、拥有意义呈显著正相关;除人际交往与寻求意义相关不显著外,人际关系困扰与生命意义感的两个维度均呈显著负相关;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中人际交谈、人际交往、待人接物与异性交往四维度两两间均呈显著正相关;生命意义感量表中寻求意义与拥有意义两维度间呈显著正相关。
(三)人际关系在自尊与生命意义感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为进一步分析自尊、人际关系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建构了如图1的模型。

图1 人际关系在自尊与生命意义感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模型

表4 人际关系的中介效应的各项拟合指标
从表4可看出标准拟合指数(NFI)、相对拟合指数(CFI)和拟合优度指数(GFI)均大于0.9,近似均方根(RMSEA)小于0.05,Χ2/df的值小于5,说明模型的拟合度理想,表明模型可以被接受。自尊到人际关系的路径系数为-0.50(p<0.001),人际关系到生命意义感的路径系数为-0.43(p<0.001),自尊到生命意义感的路径系数为0.41(p<0.001),说明人际关系在自尊对生命意义感的预测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即自尊对生命意义感有直接影响作用,同时还通过人际关系对生命意义感产生间接影响。
四、讨论
(一)总体得分情况
1、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状况
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处于中等水平,与王亚杰[16]、李旭[4]结果相同。不论运用何种测量工具,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得分均处于问卷计分的中间组,反映出大学生整体上存在缺乏明确生活目标且找不到生命意义的状态[17]。可能由于个体高中时期以高考为整体目标,习惯接受“填充式”、“封闭式”的教学模式,进入大学后,无法适应自主的学习与生活模式,缺乏明确的学业、就业规划,导致自我约束力降低、大学生活娱乐化,最终失去主动寻找生活目标的意愿,生活空虚、乏味。这也反映出高校对大学生生命意义及生活目标设定等方面的教育有待完善。
2、大学生自尊状况
虽然沙晶莹、张向葵对1993-2013年间的中国大学生自尊研究进行横断历史元分析,发现我国大学生自尊水平在20年间呈显著下降趋势[18]。但本研究显示,大学生自尊整体情况较好,自尊得分与其研究中2013年的26.91分之间存在显著差异(t=19.556,p<0.001),说明近几年来,大学生自尊水平有所提升。可能随着社会的逐渐变革,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社会对大学生的支持与肯定,国家为大学生制定更好的就业与创业政策,使大学生在个人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机会也逐渐增多,进而提升了自我能力感与价值感。
3、大学生人际关系状况
本研究发现,有42.1%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人际关系困扰,与王艳,安芹[19]的调查结果相近,并且大学生在人际关系四个维度的困扰程度有所不同,最突出的困扰表现在人际交往方面。这可能一方面由于大学生入学前以学习为主,生活圈子较小,较少涉及社交场合,导致社会经验不足;另一方面,部分大学生入学后缺乏目标与动力,生活以娱乐休闲为主,尤其网络的沉迷,导致现实中人际交往的能力有所弱化。因此,高校应当更加重视校园文化建设,丰富校园活动,调动更多大学生参与,为大学生拓展人际圈、加强交谈交往能力提供途径,同时也能够满足其希望被别人接受、理解的需要。
(二)生命意义感、人际关系与自尊的相关分析
研究显示自尊与人际关系困扰呈显著负相关,说明自尊越低人际困扰越多,与张燕平[20]、李艾莲、刘宗发[21]的研究结果相同。可能由于低自尊的个体具有较低的自我认同感,他们常否定自我的价值,不能很好地认识和接受他人的关心与评价,因此,在人际交往中缺乏自信、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常处于被动状态;在待人接物方面不知如何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在异性交往中也难以处理好交谈气氛,过于羞涩与沉闷。这些均导致其有心改善人际关系却又不知如何行动而产生困扰。
研究结果也发现自尊与寻求意义感、拥有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与赖雪芬[22]、谭亚菲[7]的结果相同。表明个体自尊越高越认同和肯定自己,对自己越有信心,能够接纳现有的状态与环境,理解包容他人与自身的不足,愿意改变自己做出尝试。这使其不但易于发现自身的生命意义,而且能够主动寻求积极的生命意义,提升存在的价值。
研究结果还显示,人际关系困扰与拥有意义感呈显著负相关,寻求意义感与人际交谈、待人接物和异性交往呈显著负相关。高原发现,大学生人际关系与生命意义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且对生命意义感起到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3],说明人际关系能够影响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人际关系困扰较少的个体,性格乐观、主动关心朋友,更善于交谈交际,不但拥有更多的人际支持,而且充分满足了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因此,和谐的人际氛围使其在学习和生活中能更加积极地发现乐趣,反之则处于消极状态。
同时,本探究验证了拥有意义感与寻求意义感的关系,即两者间呈显著正相关,这一点与王孟成[24]、王鑫强[25]的研究相同,与刘思斯、甘怡群[12]的研究结果不同。表明寻求意义与拥有意义的关系受民族文化影响。中国和日本同属于集体主义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个体虽然体验到人生意义但还要继续去追寻意义;而在美国的个体文化中则相反,已经有人生意义的个体则不会去追寻意义[24]。
(三)人际关系在自尊与生命意义感间的中介作用
高原[23]、李海春[26]的研究均证实人际关系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有直接、间接的影响作用,自我价值感、自我认同亦对生命意义感有直接的预测作用。本研究的结论与之有一致之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显示,人际关系在自尊与生命意义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自尊一方面可以直接影响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影响人际关系间接地影响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本研究认为,个体的自尊越低,越对自己和他人抱有消极的评价,无法很好地与他人相处,在人际关系中的困扰也就越多,从而影响其对生命意义的寻找意愿,并对自己拥有的生命意义产生怀疑甚至否定,导致生命意义感降低。当个体能够很好的定位自己,积极发现、认可自己的价值,客观地对待他人的评价,主动对他人敞开心扉并大胆地表达,才能参与到人际交谈中,使自己不再孤立。如此,良好的人际交谈氛围使个体获得更多的人际支持,进而增强对自身及未来的积极正向的感知[27],能够以新的角度探索生活、发现自己所拥有的意义,最终获得更高的生命体验。
因此,作为中介变量,人际关系很好地体现了由内在的人格特征影响外在的生活体验的过程。可见,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不但可以通过引导学生认识接受自我、以客观的态度对待他人的评价来提高生命体验,同时,更应该多为学生提供培养良好人际关系的平台,教授并锻炼其人际交往能力。在和谐的人际交往氛围中,个体满足爱与归属感的需要,能够主动表达自己、告别孤立状态,逐渐体验到自己拥有的生命意义并更加积极地寻找生命意义,从而提升生命意义感,达到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
五、结论
1、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处于中等水平;自尊水平较高;人际关系困扰水平整体较低,但仍有42.1%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困扰(主要体现在人际交往方面);
2、自尊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与人际关系困扰呈显著负相关;除人际交往与寻求意义感相关不显著外,人际关系困扰与生命意义感的两个维度均呈显著负相关;
3、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人际关系在自尊与生命意义感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1]Frankl V.E.Man’s Search for Meaning[M].New York:Pocket Books,1984:23-40.
[2]Steger M.F.Meaning in life.In:Lopez S.J.Encyclopedia of Positive Psychology[M].Oxford,UK:Blackwell Publishing,2009:605-610.
[3]翟书涛.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194.
[4]李 旭,卢 勤.大学新生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18(10):1232-1235.
[5]向思雅,魏绮雯,郑少丹,等.大学生社会性无聊感、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6,24(4):522-526.
[6]李志勇,吴明证.大学生自尊与社交焦虑的关系: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中介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13,(5):72-76.
[7]谭亚菲.大学生生命意义与自尊、内外控制倾向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3,21(5):823-825.
[8]王佳一.大学生死亡态度及其与自尊、生命意义感的关系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33-37.
[9]王佳欣,陈建芷.大学生自我意识与人际关系的关系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8,16(8):862-864.
[10]郭海燕.自尊、自我评价与人际关系的相关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0:22-31.
[11]周 娟.高职院校学生生命意义感状况研究初探[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8:19-20.
[12]刘思斯,甘怡群.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版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0,24(6):478-482.
[13]郑日昌.大学生心理诊断[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339-345.
[14]韩向前,江 波,汤家彦,等.自尊量表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及建议[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5,14(8):763.
[15]田录梅.Rosenberg(1965)自尊量表中文版的美中不足[J].心理学探新,2006,26(2):88-91.
[16]王亚杰.大学生自我和谐与生命意义的相关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10:31-36.
[17]周 静.重庆市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现状调查与干预研究[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6:22-28.
[18]沙晶莹,张向葵.中国大学生自尊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1993~2013[J].心理科学进展,2016,24(11):1712-1722.
[19]王 艳,安 芹.大学生安全感、自我分化和人际关系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2(5):877-880.
[20]张燕平.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社会支持与自尊的关系[J].开封大学学报,2014,28(1):94-96.
[21]李艾莲,刘宗发.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自尊水平的关系研究[J].亚太教育,2015,(10):263-264,256.
[22]赖雪芬,鲍振宙,王艳辉.生命意义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J].心理研究,2016,9(2):28-34.
[23]高 原.大学生人际关系、自我价值感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研究[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12:30-34.
[24]王孟成,戴晓阳.中文人生意义问卷(C-MLQ)在大学生中的适用性[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8,16(5):459-461.
[25]王鑫强.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在中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3,21(5):763-767.
[26]李海春.大学生微系统人际关系、自我认同与生命意义的关系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4:51-59.
[27]李 旭.大学生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的关系:乐观的中介和调节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15,(1):81-86.
(责任编辑:王国红)
G444
A
2096-3130(2017)05-0103-05
10.3969/j.issn.2096-3130.2017.05.024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510513034)阶段性成果
2017—04—19
谭雪晴,女,湖北枝江人,湖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贾晓督,男,山西朔州人,湖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学生;李智勇,男,河北徐水人,湖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