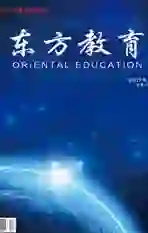《女勇士》的镜像理论解读
2017-10-21赵富入
赵富入
摘要:汤婷婷的小说《女勇士》是当代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该作品一经发表便备受关注。学者们分别从女权主义、中西文化以及创伤理论等不同角度分析过这部作品。本文拟采用拉康的镜像理论探析无名姑姑、姨妈月兰和“我”在《女勇士》不同阶段的镜像形象以及对自我身份的重新构建。
关键词:《女勇士》;镜像理论;无名姑姑;月兰;“我”
一、前言
美国华裔作家汤婷婷1940年生于美国,她先后创作了颇具影响力的小说《女勇士》《中国佬》等,这些文学作品确立了汤亭亭在美国华裔文学史上的地位。保尔·斯金纳兹曾如此评论该书:“据估计,(汤氏的)著作是在各种文选中在世作者收录最高,也是大学生(特别是亚裔女大学生)中阅读得最多的作品之一。”其处女作《女勇士》是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该部作品由五个故事组成,分别为《无名姑姑》、《白虎山学道》、《乡村女医》、《西宫门外》和《羌笛野曲》,逐一讲述了无名姑姑投井自杀,化身花木兰去白虎山学道,母亲勇兰在乡村学医捉鬼,月兰姨妈赴美寻夫和蔡文姬羌笛野曲的故事。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学者们分别从女权主义、中西文化以及创伤理论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本文拟采用拉康的“镜像理论”探析无名姑姑、姨妈月兰和“我”在《女勇士》不同阶段的镜像形象以及对自我身份的构建。
二、镜像下“无名姑姑”的誓死抵抗
中国男性移民为寻找财富而纷纷赴美时,他们的妻子不仅注定要留在家里独守空房,而且还要料理家务、服侍公婆、照顾孩子。然而“无名姑姑”却有些与众不同。虽然她未能逃避男权社会下父母对她婚姻的安排,但凭借着家人对她的喜爱,似乎有些被宠坏了。虽然她丈夫多年不归,她依然很注重打扮,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拉康认为,镜像的第一阶段属于无意识阶段,就像刚出生的婴儿,婴儿在照镜子的同时会看到自己的影像,并将这一影像误认为是自己。一开始的“无名姑姑”对生活充满激情与期待,她追求美丽,时常对着镜子进行梳妆打扮,在镜子中看到美丽的自己就会高兴,使读者认为这就是当初的“无名姑姑”。“为了使她保持恋爱时的美貌,她经常对着镜子梳妆打扮,设想什么颜色和样式会使他感到高兴。她不时地改变颜色和款式。目的就是为了求得最合适的搭配。她希望他能回过头来看她一眼”(汤婷婷,1998:7)。
“无名姑姑”所梳的发髻与当时的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形象一致,在父权与男权统治的社会中,只有展现出自己的服帖与顺从,表现的热情与美丽,才能够得到男性的青睐,才符合社会的审美标准。无名姑姑按照男性社会的标准来构建自己,缺乏对自我主体性的认识。“拉康镜像阶段理论认为,婴儿第一次认出镜子中的自己之后,就开始和镜子中的自己玩游戏,并爱上了这个影像”(王晓琪 51)。与镜像的想象认同使主体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想象的控制能力。因此,在镜像的第一阶段,她就像毫无区别与辨识能力的婴儿一样,并没有认清自己,只是沉浸在镜子中那个虚幻的美好中。
爱美的姑姑渐渐地不满足于傳统女性认同的那种美丽,她渴求得更多,于是逐渐打破男权与父权制社会的束缚,对自己的主体性有了新的认识,开始追求自己心中的幸福。“无名姑姑”与另一个男人通奸并怀有身孕。这样的自己不仅遭受了家人的驱逐,更使得家里遭到了整个村里人的围攻。“真正的惩罚不是村民们的突然袭击,而是全家人故意要把她忘掉。她的不贞使他们恼怒万分,他们要让她永远受罚,甚至叫她死后也不得安宁。”(14)对她而言,被家里人遗忘而没有名字是自己最痛苦的经历。这一阶段,“无名姑姑”对自己的主体性有了认识,不再是镜子中想象的自己。出生在特定年代的她,受到宗族社会制度、家庭等级制度、男女有别制度的压迫,没有人听她倾诉,她也不敢向别人提起心中的苦。可怜的她完全成了封建传统社会的牺牲品,或许她也有过幻想,想象着那个男人会和她一起承担这一切,幻想着家人最终会原谅她,甚至幻想社会可以接受他。然而幻想终究只是幻想,永远都不会变成现实。
在对自身主体性有了新的认知后的“无名姑姑”走投无路,她感到自身的渺小,无法构建出想象中的“理想我”。她遭受了被人围攻、痛骂的经历,忍受了被家人遗忘的痛苦,此时此刻她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无法为自己辩解。于是,在生下孩子之后,母爱的力量使得“无名姑姑”变成了一名女勇士,为了不让孩子留在世上受苦,她带着刚刚出生的孩子双双跳入井中。因为在人们看来“中国人总是非常害怕淹死鬼。“那是水鬼,眼泪汪汪,拖着水淋淋的长头发,皮肤水肿,在水边静静地等候,伺机把人拉下水做它的替身。(汤婷婷)”“无名姑姑”用投井自杀的方式向男权社会宣战,用她们的血液浸染了全村人赖以生存的井水,整个父权制社会以这样的形式被动摇了。
无名姑姑凭借着自己的勇敢坚强和宁死不屈的精神向封建父权制、男权社会作出了最后的抵抗,用无声的反抗完成了自我身份的构建。
三、镜像下“姨妈月兰”自我构建的失败
与“无名姑姑”相比,姨妈月兰虽然有着美丽的名字, 可是她在作者甚至读者眼中却是一个真正可悲的人物。她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压抑着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她低眉顺眼、逆来顺受。被丈夫遗弃了30年的月兰一直保持着沉默。姨妈月兰满足于自己的生活,在她的脑海中,丈夫有权在外生活并给自己提供相应的生活费,虽然自己带大了他们的女儿,却对那缺席的父亲心怀感激,因为他不断寄钱过来,满足了自己的物质生活。“他没抛弃我,他给我寄了那么多钱。吃的、穿的、丫环,我应有尽有。他也供养了女儿,尽管她只是个女仔。他送她上大学,我不能给他添乱,一定不。”(113)因此月兰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去美国寻找自己的丈夫。此时的月兰姨妈处于镜像的第一阶段,满足于镜子中那个衣食无忧的自己。
月兰姨妈正如她的名字,是依靠着别人才能存活。她是一个懦弱,趋于现实,不敢也不愿意抗争的传统中国妇女形象。而母亲却在为姨妈争取幸福这件事上,表现得果断而又坚决。她认为,是她的东西就一定夺回来。所以想为月兰讨回公道。勇兰认为妻子有权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并分享其财产,但是月兰却不想奔赴美国。月兰在姐姐勇兰的帮助与鼓励下卖了她在香港的公寓,只身来到了美国,姐姐的劝说让她看到了与丈夫团聚的希望。然而岁月蹉跎,月兰容颜已老,羞于见自己的丈夫。在勇兰的帮助下,月兰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和他美国的妻子。但是被丈夫婉拒使得姨妈月兰在镜像中构造出的“理想我”由于自己缺乏完全的认知已经支离破碎了,越来越感受到自身力量的渺小,从而不再自恋般地关注“理想自我”,而更多的是与外部的融合,从而走向象征界。endprint
然而象征界的社会对月兰而言又是那么的陌生。从旧金山机场接触到陌生的“白鬼”,接触到陌生的语言和世界再到陌生的姐妹和陌生的丈夫使得自己完全陷入不可掌控之中。月兰来到美国,尽管住在姐姐勇兰家,但勇兰一家无论是在行为还是思想上很大程度上已经美国化了。她始终无法适应美国的生活,在中国,她养尊处优惯了,但在美国,她看到勇兰一家为了生活,勤奋努力,日复一日地在洗衣房忙碌自己却不能跟上生活的节奏,也许真的是文化冲突的缘由,亦或内心压抑所致。月兰也曾试图融入勇兰一家的日常生活中,但语言的不通,令她无法与外甥们沟通。去洗衣房幫忙,又被认为笨手笨脚,干的活儿无法得到认同“她干活的速度从未比第一天快过。”(126)此时姨妈月兰虽然认清了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现实,可她却无法无法像姐姐勇兰一样生活在中西文化冲突下学会适应美国的生活。丈夫的抛弃加上语言和环境的差异使得月兰再也无法承受,变得精神失常,最后在疯人院中孤独终老,没有完成自我身份的构建。
四、镜像下“我”的自我成长
拉康认为,“我们只要将镜像阶段理解为一种认可即可”。 同时,他认为人类自我意识的确立,是与他者联系在一起的。“而镜像不只是在婴儿时期发挥作用,作为他者,他对人类的塑造贯彻始终。由于本质的缺失,他需要外在他者不断的充实和确认自己。”也就是说,“人的‘自我是在‘他者的干预下完成,是一个将‘他者内化的过程”。拉康对“他者”做了区分,即“小他者”和“大他者”,而大他者常常涉及到时代背景、社会需求、制度等大的社会环境。因此镜像下的我需要“小他者”和“大他者”的影响才能够认清现实中的“自我”,才能够获得成长(熊艳玲5)。在《女勇士》中,这些小他者包括无名姑姑、花木兰、“我”的母亲勇兰、姨妈月兰、被欺负的中国女孩等等,甚至还包括各个故事当中的鬼怪们。正是因为这些小他者的存在,才能让我不断成长。
“无名姑姑”在丈夫婚后不久去了美国淘金之后却怀上了别人的孩子。姑姑因此被认为不守妇道,有辱家门,而在死后不许被家人提起,因此也就成了无名氏。家人用刻意遗忘来惩罚姑姑。母亲给我将这个故事是要警惕我,避免重蹈覆辙。这个小他者的存在,在别人看来是一种耻辱,然而我看到的却是“无名姑姑”投井自杀,对父权制和男权社会的无声反抗。“无名姑姑的形象也象征着早期刚上英语学校的“我”———在巨大的压迫面前,拒绝学习英语,以沉默进行抗争。(熊艳玲5)”然而在文化压力下的我,无声反抗根本不能拯救自己,就像姨妈月兰,到美国夺回丈夫失败后,由于不能融入美国社会而最终精神失常。这使我认识到“我”的成长只有“小他者”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生活在文化边缘冲突下的我们势必会受到社会环境或者文化因素这一“大他者”的影响。即使是如“花木兰”一样英勇的母亲,在国内可以做医生,不怕各种“鬼怪”,到了美国的母亲,却对各种“的士鬼、公交鬼、警察鬼等”束手无策。“我”逐渐意识到个人在大他者面前的渺小,于是“我”开始怀疑、否定,并最终在蔡琰的故事中找到了出路。
蔡琰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就被南匈奴所虏去并被纳为王妃,在匈奴一待就是十二年。在异邦期间,她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乡,经常被胡笛尖细凌厉的声音困扰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最终,蔡琰将思乡之情及伤感悲愤的心绪写成词,并谱上曾困扰她许久的胡曲,作出了旷世绝响《胡笳十八拍》。(熊艳玲82)”在这个故事中,异国他乡、胡曲就是文化冲突背景下的“大他者”,是蔡琰无法躲避的。而面对这样的环境她并没有屈从或是自暴自弃,而是要学会找到与之和谐共处的方式。事实上,这也正是“我”的成长历程。从无声的反抗失败后,在“大他者”的环境下寻求自己的求生之路,在文化冲突下学会适应环境进而构建出真正的自我。
五、结语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无名姑姑用死抵抗父权制、夫权制社会这样一面镜子,照出女性的影像,映射出华裔女性的形象,华裔群体以此为鉴,增强对“华裔性”的认识,加速华裔身份的构建的完成。“无名姑姑”用姑妈用投井自杀的方式向男权社会宣战,完成身份构架,正可谓死得其所。“姨妈月兰”在文化冲突下因为自己的沉默,在疯人院中孤独终老,并没有完成自我身份的构建,从而告诉我们“大他者”的影响不容小觑。而“我”正是在小他者和大他者的影响下完成了在文化冲突下的自我构建。因此在面对压迫和歧视的情况下,只有服从和遵守规则才有机会完成自身构建。
参考文献:
[1]董晓烨. 从叙事结构看《女勇士》的修辞效果[J].山东外语教学,2010(6):57-62.
[2]胡亚敏.谈《女勇士》中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融[J].外国文学评论,2000(1):69-73.
[3]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 刘北成 杨远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4]张子清.与亚裔美国文学共生共荣的华裔美国文学[J].外国文学评论,2000(1):93-103.
[5]张一兵.拉康镜像理论的哲学本相田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4(10).
[6]钟洁.《女勇士》身份认同追寻[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16(4):84-87.
[7]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50.
[8]熊艳玲. 论《女勇士》中“拉康式自我”的形成[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1):5,82.
[9]王晓琪. 《女勇士》中无名姑姑的镜像作用[J],大连大学学报,2008(4):51-52.
[10]汤婷婷. 《女勇士》[M]. 李建波 陆承毅译 张子清校译,广西:漓江出版社,199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