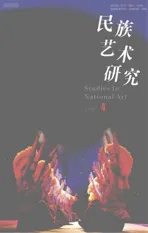一部惨烈的中国式家族奋斗史
——《琵琶记》思想内涵新论
2017-09-08乔丽
乔 丽
一部惨烈的中国式家族奋斗史
——《琵琶记》思想内涵新论
乔 丽
《琵琶记》是中国古典戏曲中的名作,描写了封建社会时期蔡氏家族在努力摆脱平民阶层、晋升精英阶层的艰难历程中,每位成员为了这一宏大目标都付出的沉重代价。蔡公蔡婆是最高指挥者,同时也是最大牺牲者;蔡伯喈是核心实施者,也是陷入两难境地的最大纠结者;赵五娘是最大受难者,更是最大得益者;牛小姐是既得利益维护者,也是新获利益的最大助力者。他们齐心协力,终得门楣光耀,为追求“风化体”,共同演绎了一部惨烈的中国式家族奋斗史,也正是在这样的家族组团奋斗模式中,构成并造就了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
《琵琶记》;家族利益;平民阶层 ;精英阶层 ;“风化体”;代价;生存方式
《琵琶记》是中国古典戏曲中的名作,自14世纪诞生以来,数百年间产生了无数争论,特别是对该剧的思想内涵的解说和探讨,更是众说纷纭。本文认为,《琵琶记》是一部极为真实、极为惨烈又极为平常的封建社会中国式家族奋斗史,正是在这样的家族组团奋斗模式中,构成并造就了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
其作者高明开篇便直述“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琵琶记》第一出《副末开场》,(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第1页。的主旨,前人对此研究颇多,各有建树。笔者认为,所谓“风化”,指的是符合封建社会主流意志的伦理道德秩序,这是封建社会制度建立、成熟、维持并向前发展的核心要素。所谓“体”,指的是社会制度,这种制度是以道德为精神指向的。一个平民家族要想改变自己命如蝼蚁的卑贱地位,必须向现存制度、高度看齐,并以融入制度、甚至领导制度为最高目标。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只有一件核心事情要做,那就是怎样符合“风化体”,甚至成为“风化体”的最高标杆和典型模范,为全社会所钦慕景仰。事实上,从对最高目标追求的最终结果上看,蔡氏家族是获得了全面胜利的。所谓的“好”,首先是要达到主流社会意志主导下的评判标准,再次是符合民间大众道德诉求和心理意愿。如何获得这个“好”,是蔡氏家族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而为了获得这个“好”,整个家族必然要付出特定的甚至是巨大的牺牲和代价。
蔡氏家族总共五位成员,在整体利益上是高度一致的,但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和付出的代价却各不相同。《琵琶记》的故事线索大体上可概括为夫妻和顺、父母康宁——劳燕分飞、父母灾亡——夫妻团圆、衣锦庐墓三个部分,在这样一种宏大的家族叙事中,蔡公、蔡婆、蔡伯喈、赵五娘、牛小姐这五位家族成员,加上义邻张广才和姻亲牛丞相,共同作用、齐心协力,推动蔡伯喈平步青云,蔡氏家族由平民阶层一跃成为精英统治阶层。在这个无比艰难的过程中,每一位成员都发挥了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 蔡公蔡婆是最高指挥者,也是最大牺牲者
《琵琶记》甫一开场,高明就给蔡家安排了一场欢乐的庆寿图。此时的蔡伯喈年满二旬,已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身负济世之才,也新娶了妻房,父母已满八旬。高明在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中巧妙地交代了蔡家实为“小门深巷”的平民阶层。一家人接唱的[锦堂月]意味深长:
[前腔]〔外〕还愁。白发蒙头,红英满眼,心惊去年时候。只恐时光,催人去也难留。孩儿,惟愿取黄卷青灯,及早换金章紫绶。(合前)
[前腔]〔净〕还忧。松竹门幽,桑榆暮景,明年知他健否安否?叹兰玉萧条,一朵桂花难茂。媳妇,惟愿取连理芳年,得早遂孙枝荣秀。*《琵琶记》第二出《高堂称寿》,(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第4页。
蔡公作为一家之长,深感已身风雨飘摇、时日无多,他把振兴家族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把光宗耀祖的重任交给蔡伯喈。重要的是,他认为,经过二十年的不懈努力,时机已经成熟,蔡伯喈必须立刻出门求取功名、改换门楣,这是唯一重要且紧迫的事情。面对蔡婆母子的担忧,他道:
[前腔]〔外〕萱室椿庭衰老矣,指望你改换门闾。孩儿,你道是无人供养,我若是你做得官来时节呵,三牲五鼎供朝夕,须胜似啜菽并饮水。你若锦衣归故里,我便死呵,一灵儿终是喜!*《琵琶记》第四出《蔡公逼试》,(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第8页。
蔡家是封建社会中最平凡和最普通的平民之家。蔡伯喈有条件接受较好的教育,靠着天资聪颖和勤奋努力,学得济世之才,所选的妻子赵五娘也有一定的文化。但是蔡家又并非富裕之家,在后面剧情中,遇到饥荒年月,跟多数百姓一样,陷入濒死边缘,如果不是热心的邻居帮忙,很可能除蔡伯喈外一家人死绝。要想彻底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就必须进入精英阶层,而进入精英阶层唯一的通道就是科举。这样一个宏大高远的目标,唯一能够完成它的人就是蔡伯喈,所以蔡公才孤注一掷,逼着蔡伯喈应试。
蔡婆刚开始并不完全同意蔡公的主张,不放蔡伯喈远行,原因有二:一来考虑养老,“我百年事只有此儿”“难道是庭前森森丹桂?”*《琵琶记》第四出《蔡公逼试》,(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第15页。她一生唯有此子,人丁单薄,深感风烛残年的孤单寂寞和生活的艰辛不易,唯求一家人平安团聚,这属人之常情;二则繁衍后代也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对媳妇的要求是要生育子孙,因为后继有人同样是家族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要看到,虽然在具体意愿上蔡公、蔡婆有分歧,但在总体意愿上都是期望家族繁盛发达,只不过在现实环境中具体实施的路径有先有后。一旦蔡伯喈远赴春闱,就算前程似锦,也终不能尽孝膝下。眼花耳聋、年老体弱的蔡婆已经敏锐地遇见了将来的结果:
[前腔]〔净〕一旦分离掌上珠,我这老景凭谁?苦!忍将父母饥寒死,博得孩儿名利归。你纵然锦衣归故里,补不得你名行亏!*《琵琶记》第四出《蔡公逼试》,(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第18页。
蔡婆关注的是眼前现实,蔡公关注的则是长远现实。蔡公认为,供奉甘旨、披麻戴孝是小节,扬名后世、以显父母才是真正的大孝。他以耄耋之年,毅然扛起一切可能到来的后果,断然要儿子求取功名。这种光耀门楣的迫切需求变成了支撑蔡伯喈科考的强大精神后盾。蔡公是在逼试,张大公是在劝试。张大公作为旁观者,是完全支持蔡公的,原因简单而清晰:只有身登凤凰池,才是福荫家族的唯一正确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逼试这一环节中,赵五娘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蔡公、蔡婆自动且自然地把这个新媳妇的意愿给忽略了,因为二老才是这个家族的执掌者,连蔡伯喈都得俯首帖耳,何况赵五娘呢?细节中体现出来的封建家庭伦理是极为严密且分明的,但在困苦的生活境遇中,严明的家庭伦理却出现了变通,充满了人间温情。
蔡伯喈离家三年,蔡公、蔡婆遭受饥荒灾病,蔡婆先赴黄泉,蔡公临终前痛悔不已,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拜五娘,谢三年侍奉之恩。“我三年谢得你相奉事,只恨我当初把你相耽误。天那!我待欲报你的深恩,待来生我做你的媳妇。怨只怨蔡伯喈不孝子,苦只苦赵五娘辛勤妇!”*《琵琶记》第二十三出《代尝汤药》,(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第93页。第二件:写立遗嘱,不忍五娘身无所依,冻饿而死,要五娘速速改嫁。第三件:赠张大公拄杖,若有朝一日蔡伯喈回转,用此杖重重责罚。沉痛的现实暂时瓦解了严明的家庭等级观念,此时的蔡公,不再是那位高高在上的家族之长,不再是一位严父,只是一位痛悔不已的将死之人。临终三事,对子之失望,对媳之感恩,对人世沧桑之无奈,件件都是经历了深重的生离死别的人生至痛后深刻的领悟。这一刻,时过境迁,改换门闾的希望早已破灭,何况穷途?生无可恋,又怎能瞑目?
可以说,蔡公蔡婆固然是死于灾荒疾病,更是死于儿子数年杳无音信导致的沉沦与绝望,这种精神上的坍塌更甚于身体的饥饿病痛。当初,强逼着儿子承担起改换门闾的重任,临终时却想见一面而不得。说到底,蔡公、蔡婆为了家族的荣光,双双惨死,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
二、 蔡伯喈是核心实施者,也是陷入两难境地的最大纠结者
古今的《琵琶记》研究对蔡伯喈三从三不从的情节已经论述较多,此不赘言。笔者认为蔡伯喈是整个家族利益的实际承担者和核心实施者,从最终结果来看,他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家族使命,但也付出了相当沉重的情感代价。
蔡伯喈甫一出场,是行孝思想的最佳代言人,在行孝和仕途的矛盾与抉择中,他主观上优先选择行孝,但客观上却被迫选择了仕途,而这种被迫选择在蔡公看来才是最大的行孝。从离家赶考到返乡庐墓,蔡伯喈承受最多的是深沉的精神痛苦和闭锁的心灵寂寞。蔡伯喈追求家族阶层的改变,有两个关键环节:一是在意料之中顺利考中状元,二是在意料之外再次婚配。剧本将主要笔墨放到了后者,而正是这次婚姻成为蔡家命运的关键转折点。
开弓没有回头箭,蔡伯喈费尽千辛万苦进入了体制,获得了体制带来的一切福利和保障,也意味着必须接受体制带来的一切规矩和束缚。年轻有为的蔡伯喈一举考中状元,立刻成为当朝炙手可热的新晋势力,精英阶层必然做出快速反应,千方百计拉拢蔡伯喈。事实上,以牛丞相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获得者早已做好周全准备,不管状元是谁,都势在必得。牛丞相身居高位,但从牛家家族发展来说,是有很大缺陷的,那就是缺乏新生力量去维持并最大化地扩充家族利益。唯一能弥补这一关键性缺陷的可靠筹码就是牛小姐的婚配,只要将当朝状元纳入彀中,何愁前程?牛丞相早就布下一张炽热的利益大网,只等着科举放榜,这张网,新晋状元跳也得跳,不跳也得跳。为了让蔡伯喈就范,他甚至不惜争取皇帝支持:“他元来要奏丹墀,敢和我厮挺相持。细思之,可奈他将人轻觑。我就写表奏与吾皇知,与他官拜清要地,务要来我处为门楣。”*《琵琶记》第十四出《激怒当朝》,(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第56页。就婚事来说,恰好新晋状元年轻英俊,不辜负牛小姐的娇媚仪容,最重要的是相对于势力错综复杂的豪门贵族求婚者,蔡伯喈出身平民阶层,背景简单,易于掌控,无力抗衡,只能俯首帖耳,自然难逃牛丞相的如意算盘。“一来奉当今圣旨,二来托相公威名,三来小姐才貌兼全”,*《琵琶记》第十二出《奉旨招婿》,(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第51页。从客观角度看,蔡伯喈纵有千般理由,也无法拒婚。
再从蔡伯喈主观角度来看,虽然他口口声声说自己并不贪恋富贵权势,但终究不得不承认“宦海沉身,京尘迷目,名缰利锁难脱。目断家山,空劳魂梦飞越”。*《琵琶记》第十三出《官媒议婚》,(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第53页。冷峻的现实是,即使考中状元,根基薄弱的他要想在形势复杂的官场站稳脚跟并谋求长期发展,必须与当朝权势把持者结交,而在众多结交关系中,最可靠的就是姻亲关系,这是不容忽视的社会规则。蔡伯喈无论主动被动,都必须遵守既定规则,否则就不能真正完成家族使命。笔者认为,蔡伯喈并不像高明所说的那样是完全被动的,他应该是在半推半就的状态下完成了这桩婚事。毕姻当日,他一面窃喜“喜书中今朝有女如玉,堪观处丝幙牵红”,一面自叹“此事岂吾意欲?有人在高堂孤独,可惜新人笑语喧,不知我旧人哭,兀的东床难教我坦腹”。*《琵琶记》第十九出《强就鸾凤》,(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第78页。旧人代表着他的生身之所,新人代表着他的锦绣前程,他既挂念家中父母、妻子,又难舍眼前繁华,如此复杂的心境,古今罕有,却十分真实。
高明先后用《琴诉荷池》《宦邸忧思》《中秋望月》《瞷询衷情》等大量篇幅来描写蔡伯喈内心两难的痛苦:宦海浮沉,如履薄冰,他挂念安宁田园,平安喜乐;卖货帝王,报效国家,他心怀父母双亲,无人照拂;美人在侧,莺声燕语,他思念糟糠之妻,孤苦无依。他孑然一身,飘零京畿,却绑系着帝王的恩宠、父母的厚望、个人的抱负、妻子的期盼。被重重名利牵绊的他毫无自由可言,更奢谈欢乐:
[三换头]〔生〕名缰利锁,先是将人摧挫。况鸾拘凤束,甚日得到家。我也休怨他,这其间只是我不合来长安看花。闪杀我爹娘也,泪珠空暗堕。*《琵琶记》第十八出《再报佳期》,(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第75页。
此前,他尚且期冀幻想着父母平安,书馆悲逢时,他骤然闻知双亲噩耗,五内俱焚,痛心疾首:
[解三酲]叹双亲把儿指望,教儿读古圣文章。似我会读书的,倒把亲撇漾。少甚么不识字的,到得终奉养。书呵,我只为其中自有黄金屋,反教我撇却椿庭萱草堂!还思想,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爹娘!
[前腔]比似我做个负义亏心台馆客,到不如守义终身田舍郎。白头吟记得不曾忘,绿鬓妇何故在他方?书呵,我只为其中有女颜如玉,反教我撇却糟糠妻下堂!还思想,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妻房!*《琵琶记》第三十七出《书馆悲逢》,(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第145页。
父母牺牲了生命,逝者已矣,对于身为人子的蔡伯喈来说,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这种伤痛又怎能自已?痛定思痛,其何痛哉!为了追逐家族的荣耀,这就是蔡伯喈必须付出的代价。
三、 赵五娘是最大受难者,更是最大得益者
阅遍全剧,几乎找不到关于赵五娘娘家的信息,但能窥测一二。五娘尚未出场,丈夫对她的评价是“仪容俊雅”“德性幽闲”,*《琵琶记》第二出《高堂称寿》,(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第2页。说明她自小应在遵守闺阁仪范的环境下长大;她登场时独唱的[锦堂月][前腔]既写了一个新媳妇的幸福与娇羞,也写了一个未来主家之人的责任和隐忧。此时她的理想是“惟愿取偕老夫妻,长侍奉暮年姑舅”,*《琵琶记》第二出《高堂称寿》,(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第4页。属于平凡人的期望和理想;从后文替公婆画像并能题诗的内容看,她应接受过一定的诗书礼乐的教育。总的来说,她应该是和蔡家同属平民阶层,二人的婚配门当户对。李渔曾经批评过《琵琶记》的诸多情节漏洞,笔者认为,赵五娘出嫁后未与娘家有任何来往,濒死挣扎之际也未获得娘家的任何资助,恐怕也是高明为了突出五娘至孝的艰辛而有意忽略,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把这一点看成是一个漏洞;但如果从本文要论述的家族奋斗史角度来说,赵五娘的平民娘家对提升蔡氏家族无任何助力可言,干脆不提,倒也干净利落。
从出嫁、嘱别至悲逢的数年间,五娘只过了60天的好日子,剩下的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南浦嘱别》时,五娘不舍丈夫,不是因为儿女情长,而是担忧不能承欢双亲膝下、彩衣娱亲,不论是从为人媳的孝道还是为人妻的妇道,即使没有丈夫临行前的托付,五娘都自觉将自己与公婆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并以高度的自律性、强大的执行力、坚韧的意志力去应对饥荒年岁里的重重难关:第一重难关是官吏克扣赈灾粮,第二重难关是灾粮被抢夺,第三重难关是糟糠自厌却被公婆误解,第四重难关是音信阻隔、拐儿欺骗,第五重难关是剪发卖葬和麻裙包土,第六重难关是千山万水、前途渺茫,第七重难关是人情冷漠、不知是否会被丈夫嫌弃,第八重难关是处理和牛小姐的关系。她吃尽千辛万苦方熬到了夫妻团圆,重重难关反成就了赵五娘孝妇的美名,成为她独一无二的晋身之阶,只不过这条条苦楚非常人能够忍受,但毕竟,从死亡线里挣扎着活过来的赵五娘终于拥有了在讲求封建伦理道德的社会里的最重要的资本——道德模范、伦理标杆。
书馆悲逢时,蔡伯喈对赵五娘感恩戴德,一个弱女子,独木难支,在纷纷乱世中竟完成了身为人子所未能完成的奉亲大事,这是其一。其二,有了五娘这一彪炳千古的孝妇招牌,蔡家获得了他人难以企及的道德标杆,从此如虎添翼。从五娘个人来说,她全部的希望都在丈夫的身上,她慨然承担起供养公婆的重担,至善孝名天下传扬,自己也如愿以偿地跨入了社会精英阶层,不但赢得了蔡家和牛家的集体敬重,更赢得了帝王的恩宠和社会的高度道德评价,从这点上说,劳苦功高的她也是家族利益的最大受益者。
四、 牛小姐是既得利益维护者,也是新获利益的最大助力者
幼年丧母的牛小姐高度自觉遵守闺阁仪范,“任他春色年年,我的芳心依旧”,*《琵琶记》第三出《牛氏规奴》,(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第12页。对于未来的婚配,她自诩卓文君,充满了信心,相信必有一个如司马相如之才貌的人。至于此人是谁,以父亲严命为大,她信任父亲的选择。
在与蔡伯喈成婚后,作为蔡氏家族的最后一个成员,牛小姐看似姻缘得意,但实际上却身负重任。她必须处理好三层关系。
第一层是与蔡伯喈的关系(新弦与旧弦的关系)。牛小姐并不是一个俗人,她对自己的婚姻很有主张,对方的身份有父亲担保,无须忧虑,她唯一的要求就是夫妻一定要真正和美:“百年姻眷,须教情愿。他那里抵死推辞,俺这里不索留恋。……满皇都少甚么公侯子,何须去嫁状元。”*《琵琶记》第十五出《金闺愁配》,(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第58页。面对“况兼他才貌真堪羨,又是五百名中第一仙”*《琵琶记》第十五出《金闺愁配》,(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第58页。的蔡伯喈,牛小姐心中满是欢喜。但丈夫总是陷入凄惶之色,牛小姐冰雪聪明,不断试探。第一个阶段,《琴诉河池》中,二人借琴曲各言胸怀,牛小姐闻知丈夫有旧弦,直问是否变心,并且认定自己并非丈夫的知音,一定是另有他人。第二阶段《中秋望月》中,二人各有各的月,人齐心不齐。第三个阶段《瞷詢衷情》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相公,试说与何妨。”“相公,你有甚事?明说与奴家知道。”“你有话如何不对我说?”*《琵琶记》第三十出《瞷詢衷情》,(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第116-118页。她始终要求的是夫妻能够敞开心怀,知心知音。蔡伯喈顾虑重重,无可奈何的牛小姐只得采用偷听的方法探寻丈夫的难言苦衷,一切明白了之后,她唱道:
从这三个阶段可以看出,牛小姐是真心想与丈夫和睦相处、为丈夫分忧的,探明丈夫终日忧戚的真实原因后,她立刻非常关心丈夫的公婆和妻子,并当机立断决定找父亲谈话,且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成功。
第二层是与赵五娘的关系(与已逝公婆、蔡氏宗族的关系)。当赵五娘埋葬公公,身背琵琶,乞讨寻夫来到京城佛寺之际,她已经不再是一个平凡的民妇,而是周身环绕着至纯至善的孝妇的无上光环,衣衫褴褛遮不住其熠熠光辉,坎坎风尘掩不过其赫赫英名。她并非孤身来到京城,而是代表着蔡氏宗族,特别是已逝的蔡公蔡婆。《两贤相遘》时,当牛小姐得知眼前心忧貌苦的道姑便是赵五娘时,她立刻行礼,称颂五娘的孝行:
[金衣公子]〔贴〕一样做浑家,我安然,你受祸。你名为孝妇,我被傍人骂。〔旦〕呀,傍人骂夫人怎的?〔贴〕公死为我,婆死为我。姐姐,我情愿把你孝衣穿着,把浓妆罢!*《琵琶记》第三十五出《两贤相遘》,(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第141页。
牛小姐已经嫁入蔡家,是蔡家的媳妇,面对公婆的代言人赵五娘,她立刻抓住了这个难得机会,斩获先机,以赢得自身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经过精心安排,蔡伯喈和赵五娘在书馆相会了,蔡伯喈对五娘感恩戴德、顶礼膜拜:“娘子,你为我受烦恼,你为我受劬劳。谢你葬我爹,葬我娘,你的恩难报也!做不得养子能代老。”*《琵琶记》第三十七出《书馆悲逢》,(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第150页。这几句话早已经超越了夫妻情感,五娘成为了蔡家的大恩人,自然也成为了牛小姐的大恩人。无论从道德上还是情感上,赵五娘都有着牛小姐不能取代的功勋,牛小姐必须维护好与五娘的关系。
第三层是与父亲牛丞相的关系。牛丞相按照封建礼仪和伦理要求严格培养和管教女儿,一切都是为了待“嫁”而沽,他说的话在女儿面前就是圣旨。他地位崇高,志得意满,对于招婿,必须是有文章有官职有福分的当朝状元。当朝状元是皇帝钦点,仕途无量,前程似锦,是人人艳羡的新贵,若是能通过姻亲将状元拉拢到自家羽翼之侧,将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利益,巩固自己的权势。至于当朝状元所属何人,倒在其次,他看中的首先是状元的身份。在得知蔡伯喈已经娶妻后,他毫不介意,强势将聪慧美丽的女儿嫁给蔡伯喈。在这桩婚事的前前后后,牛丞相言道:“何必顾此糟糠妻,焉能事此田舍翁”,*《琵琶记》第三十一出《几言谏父》,(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第120页。糟糠妻当然指赵五娘,田舍翁则指的是蔡氏父母,可见,他从未将蔡伯喈的家人考虑在内,这是一种身居高位的权势自信,也透露出他对平民阶层的不屑。女儿的谈话使得他重审形势,一改前态,盛赞赵五娘,并拜托五娘在返乡庐墓时多多看顾牛小姐。
牛小姐无限信任自己的父亲,但在婚后,父女二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牛小姐探得蔡伯喈的真情之后,一向被动接受管教的她却主动与父亲进行了一次影响深远的谈话。牛小姐这次谈话底气十足,有“已嫁从夫,怎违公议”*《琵琶记》第三十一出《几言谏父》,(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第122页。这八个字就足够了。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她不再是牛家人,而是蔡家人,她必须首先考虑夫家的利益,当然,也不忍丈夫继续承受心灵的煎熬。从人情上说,不能因为自己一个人,耽误了丈夫全家,何况她所谈的内容句句都是“风化所关”,更重要的是,与家族的实际利益休戚相关。这次谈话后,她成功地将牛氏家族的利益与蔡氏家族的利益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利好对接和优势组合,两家一个占领道德制高点,一个占领权势制高点,以姻亲为媒介,强强联手,“耀门闾,进官职,孝义名传天下知”,*《琵琶记》第四十二出《一门旌奖》,(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第166页。共同达到了除最高统治者皇帝外当朝统治阶层的两个新高度。
《琵琶记》的结尾历来倍受研究者关注,著名的观点之一是清代毛声山提出的无结为结说:“人谓《琵琶》之结于旌门,是以有结为结,吾谓《琵琶》之结于旌门,犹之以无结为结也。”[1](P431)一方面是朝廷旌表与一夫二妇大团圆,另一方面是父母双亡的风木余恨。可以说,高明突破了一般南戏的悲则极悲、欢亦极欢、离则皆离、合亦皆合的常套,以不全之事和不平之事为终篇。有学者认为:“他(指高明)用‘可惜二亲饥寒死,博得孩儿名利归’作为点睛之笔,并借此直接提出了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名利的代价如此昂贵,还值不值得一‘博’?‘何如免丧亲,又何须名显贵?’主体痛苦的生活体验,在科举时代显然具有社会的普遍性,足能引起人们的深沉的思考,它使场上喜庆的氛围里,仍然飘荡着一缕缕驱不散的悲情,给蔡邕的全忠全孝打下了负价值的印记,一门旌旗的荣耀遂因此而黯然失色。”[2](P355-356)本文论述的主要观点恰巧也回答了这个问题,蔡伯喈一家为了从平民阶层进入精英阶层,付出了极其惨重的牺牲和巨大的代价,但也获得了极其丰厚的回报,成功地实现了家族利益的最大化,逝去的人与活着的人均如愿以偿,从最终结果上看是值得的。
再回到“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这一主旨上看,整个《琵琶记》故事看似是高明以“名公”身份写曲宣扬封建社会的主流意志,但其内容极其丰富,蕴含着强大的思想性和思辨性,引起后世多少研究和争议,恐怕早超出高明的预知范畴。明代王世贞认为《琵琶记》“体贴人情,委曲毕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3](P33)读之使人唏嘘欲涕。高明对剧中的每一个人都充满关怀、关心备至,归根到底,《琵琶记》恰如一部平民阶层如何付出惨烈代价晋身精英阶层的《陈情表》,这样的历程步步艰辛、处处陷阱、重重难关,反映出封建社会里人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生存方式,而这种中国式的生存方式直到今天依然有效并将继续存在。
(责任编辑 薛 雁)
[1](清)毛声山.毛声山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一门旌奖[M]//侯百朋.《琵琶记》资料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Mao Shengshan, Mao Shengshan’ Review on the Seventh Gifted Youth’s Writing ofPipaJi: Yi Men Jing Jiang, in HouBaipeng,CollectedMaterialsofPipaJi, Beijing: Bibliography and Document Publishing House, 1989.
[2]黄竹三,冯俊杰.六十种曲评注(卷一)琵琶记评注[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Huang Zhusan and Feng Junjie,AnnotationofSixtyMusics(Volumeone):AnnotationofPipaJi,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1.
[3](明)王世贞.曲藻[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Wang Shizhen, Qu Zao, inIntegrationoftheWorksonChineseClassicalOperas(Volumefour), Beijing: China Drama Press, 1959.
About the author:Qiao Li,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of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The paper is funded by the following:Phased results of the arts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und (No. 13BB015)StudyoftheTransmissionandDevelopmentofYuOperaandModernandContemporaryLocalOperasinHenanand the Young science research seeding fund of Henan University.
A Miserable History of Struggles in Chinese Families: New Views on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The Story ofPipaJi
Qiao Li
As a masterpiece of Chinese classical opera, The Story ofPipaJidescribes the Cai family’s difficult struggle to up-grade their family from the civilian class to the elite class in the feudal society period during which every family member paid heavily for the grand goal. Cai Gong and Cai Po are the highest directors, who are also the worst victims. Cai Bojie is the core executive, as well as the one situated in a huge dilemma. Zhao Wuniang is not only the worst victim but also the most benefited. Miss Niu is both the vindicator of the vested interest and the biggest facilitator of the new gained interest. They all work together to make fame and to pursue “Fenghua Ti”, thus performing a miserable history of struggles in a Chinese family. It is in this family-teamwork struggle mode that the Chinese ancient social system and ideology and culture are constructed.
TheStoryofPipaJi, family interests, civilian class, elite class, Fenghua Ti, cost, survival mode
2017-06-08
[本刊网址]http://www.ynysyj.org.cn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豫剧与近现代河南地方戏传承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3BB015)、河南大学青年科研种子基金阶段性成果之一。
J805
A
1003-840X(2017)04-0034-07
乔丽,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河南 开封 475001
http://dx.doi.org/10.21004/issn.1003-840x.2017.04.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