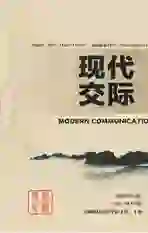对亚当?斯密仁慈德性价值的再评价
2017-08-09罗惠霞王明真
罗惠霞 王明真
摘要:亚当·斯密认为仁慈是经济体系社会中四种基本德性之一。但亚当·斯密在对仁慈德性进行价值评价时呈现出了内在矛盾与外在冲突,主要是其价值评价与社会作用不相称,仁慈的自愿性与责任性的矛盾,过多的仁慈与正义、谨慎的冲突。本文尝试回溯到仁慈德性本身,对其进行价值的再评价,以期给予恰当的定位,使其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发挥更多的潜能。
关键词:仁慈 德性 价值评价
中图分类号:F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5-0030-02
亚当·斯密(Adam Smith),18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先后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评论亚当·斯密:“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但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对“利他”的两种德性——仁慈和正义的价值评价呈现出内在矛盾与外在冲突。
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赞同霍布斯,认为美德是社会的主要支柱,而恶行是主要乱源。所谓美德就是公正的旁观者根据合宜的社会的普遍规则所推崇和赞美的那些品性。谨慎、正义、仁慈、自制就是四种主要的德性。其中谨慎是理智加上自我克制,是关乎自己幸福的德性;而仁慈和正义是关乎他人幸福的德性,但这些美德的践行都离不开自制这种德性。一个没有自制能力的人是没有能力拥有美德的,因此自制是自足的最基本的德性。[1]
关于仁慈和正义的德性,亚当·斯密认为仁慈是从同情出发,由情感迁移和换位思考,对他人行为与情感的合宜性与正当性的认同而引起的情感共鸣以及帮助行为。“仁慈只不过在于,旁观者对主要当事人的感觉怀有敏锐的同情,以致为当事人的痛苦感到悲伤,为当事人的受伤感到愤怒,为当事人的幸运感到高兴。”同时“仅仅是缺乏仁慈并不会受到惩罚;因为这并不会导致真正确实的罪恶。它可能使人们对本来可以合理期待的善行表示失望,由此可能正当地激起人们的厌恶和反对;然而,它不可能激起人们会赞同的任何愤恨之情”。在亚当·斯密看来仁慈是自愿的,并且按仁慈原则去做会带来善的结果,但“还有一种美德,对它的尊奉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愿,它可以用压力强迫人们遵守,谁违背它就会招致愤恨,从而受到惩罚。这种美德就是正义,违背它就是伤害;这种行为出于一些必然无人赞同的动机,它确确实实地伤害到一些特定的人。因此,它是愤恨的合宜对象,也是惩罚的合宜对象,这种惩罚是愤恨的自然结果”。斯密认为正义是具有外在强制性的,违背正义会招致愤恨之情,从而会受到惩罚。
一、仁慈德性的内在矛盾与外在冲突
亚当·斯密在对这些德性尤其是仁慈德性进行价值评价时,呈现出了内在矛盾与外在冲突。
1.仁慈的价值评价与社会作用的内在矛盾
一方面,亚当·斯密承认仁慈被认为是高于一般美德的,“正是这种多同情别人和少同情自己的感情,正是这种抑制自私和仁慈的刚强,构成了尽善尽美的人性;唯有这样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激情协调一致,在这中间存在着人类的全部情理和礼貌。”即仁慈德性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的力量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生活中如同经济规律左右着经济形势,在政治生活中则以社会法规的形式发挥作用。在市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最大化地利己而无须他人的仁慈,因此从利己心来看,仁慈德性正在逐渐被边缘化,发挥作用的余地越来越少甚至成为多余的道德行为。
2.仁慈与正义的冲突
正义德性“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 ,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而“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因此作出劝诫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强加于人”。因此,就由强制性而发挥的实际社会作用而言,仁慈德性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正义的德性,而这显然与亚当·斯密对于仁慈的崇高的价值评价相冲突。
3.仁慈与谨慎的矛盾
亚当·斯密一方面强调仁慈德性的崇高性,一方面又认为仁慈不应当过多,因为不利于谨慎德性下的自利。在人们为利益驱使而散居各地的经济体系社会中,由于“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人为己比人人为他能更有效地利他,因此仁慈应服从于经济生活的需要,其的存在状态依存于经济生活的必然性。即仁慈的崇高性已然被社会利益的现实性架空,成为一种满足利益需求的手段。
二、仁慈德性的价值再评价(重新定位)
介于以上的问题,刘飞和聂军[2]認为一种德性的价值评价应当与其社会作用保持一致,相对称,并且对亚当·斯密仁慈德性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活动建议来践行仁慈德性:一是捐款捐物的慈善活动,二是志愿者(义工)的利他慈善活动,三是见义勇为的利他行为以及奖励机制、关怀机制。
本文主要是从其关于德性的价值评价的不同观点出发抛砖引玉。刘飞和聂军在文中对仁慈进行价值评价时并未区分仁慈德性与仁慈行为,而从具体的分析来看,刘飞和聂军强调对仁慈的社会作用(即仁慈行为引起的事实结果)的评价,却未重视仁慈作为德性本身具有的超越性与理想性维度的价值评价。对于行为的价值评价,是价值观基于对行为引起的价值事实的评价;而对于德性的价值评价,则有别于行为的一点是,德性作为我们不断追求和涵养的目标,本身包含了已实现的和潜在未实现的价值。不能仅以实现了的价值来代替所有的价值。因此如果只对仁慈德性做事实的评价,势必会忽略其潜在的价值,从而也会导致忽视其对现代社会提升道德修养的潜在作用的发挥。
如果以A来代表仁慈德性的价值,B来代表正义德性的价值,1代表已实现的价值,2代表可能实现但还未实现的价值,则A=A1+A2,B=B1+B2。正如亚当·斯密所分析的一样,仁慈德性在为利益所驱使的经济体系社会中已逐渐被边缘化,在现实中发挥的作用比之正义德性已微乎其微。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得出A1
对此,可以说在评价和处理仁慈与正义、谨慎的价值重要性时发生冲突,关键问题在于亚当·斯密不当以垂直式的单向度价值来进行评价,不考虑在不同层面不同问题上价值多向多维的处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多种德性进行垂直式单向度的评价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它不能作为有效理论指导实践,甚至有可能误导实践的价值选择,埋没德性在不同维度不同潜能的发挥。
如果我们把仁慈这种崇高性理解为A>B,那么由于:
A=A1+A2,B=B1+B2,且已知A1
也就是正义未实现的价值小于仁慈未实现的价值,这与正义对于维系社会秩序犹如建筑物地基一般的功能密切相关,正义由其外在强制性能使一个社会长久稳固地维持安定的秩序,但对于一个社会群体的道德水平的提升却是无力的。亚当·斯密认为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将仁慈德性比作锦上添花起装饰的作用,但很明显我们都不可否认雪中送炭正是仁慈德性的表现。故在正义德性与仁慈德性社会作用的对比中,亚当·斯密考虑了正义德性的刚性影响力,但对仁慈德性的柔性影响力和影响深度的评估并不充分。
仁慈从同情感出发,设身处地换位思考而引发道德情感及帮助行为,它是内在于个人,并且如其他人性中的原始感情一样,并不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虽然他们在这方面的感受可能经过理智的反思做得更好。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的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如何才能将这种内在于个人的道德情感不断地扩充和提升呢?也就是如何使仁慈德性对现代社会公民普遍的道德水平发挥更大的潜能,扩大其柔性影响力,这便是我接下来重点关心的问题。
三、仁慈德性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潜能作用
正如陈根法[3]在他的《德性论》中所言:“一个社会如果没有道德的底蕴,就没有公正的法律。只有发达的伦理素质人能造就公正的法官;只有尊重德性的社会,才能制定和执行惠普万民的公正的法律。”相较于法律,德性是法律的素质奠基,德性也通过对法律的影响而发挥其社会作用。刘飞和聂军将亚当·斯密对仁慈责任的强调看作仁慈的强制性,但我更认同这种强制性并不属于仁慈德性本身,而是其通过对习俗、观念、社会风尚、法律等的影响而出现的衍生特性,同时也是其发挥潜能的隐逸方式。正是这种作用方式的不外显的隐逸性,容易让人误以为其不再具有社会作用的影响力。但德性作为文明的内在积淀,它是民族精神的灵魂,因为崇高的价值信念与人格追求才是民族精神的核心。
仁慈和正义、谨慎、自制四种德性各有不同向度的特性,在对它们进行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时,应在不同向度依据其特性和影响力给予不同程度的重视和发挥。在现代经济体系社会,如同斯密已看到的,正义、谨慎、自制已经发挥了其较好的作用。又限于篇幅、时间,本文仅从个人教育、人情风俗和法律层面探讨如何使仁慈德性对现代社会发挥更大的潜能作用。
1.个体的德性教育
在教育之前,须先有对仁慈德性本身理念的具体而深入的阐释和理论构建,再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入手,培育充满仁爱精神的家风、校风以及从个人理念出发,提升公民德性修养的意识。
2.人情风俗的引导
曾国藩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原才》)一二人的人格感召与精神建动,无形中在其周围养成一种“空气”,由一地的空气播荡弥漫于社会,从而影响一地方群体的共同意識与心态理念。因此,在人情风俗的维度上,学界对仁慈德性的具体深入的反思和讨论,地方政府对慈爱、仁让、廉洁等风俗理念的宣传,对慈善活动的倡导,对高尚人格的敬爱与推崇等可以起到对社会清源活流的作用。
3.法律仁慈精神的倡导
一方面可以在刑法、民法等判决后的酷刑(如死刑)来考虑对生命的仁慈原则,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由仁慈而引出感恩等其他的品行,从而形成提升公民道德素养的良性循环。
以正义来维护社会的安定秩序,以仁慈的内在性来提升社会普遍道德素养水平,以谨慎自制来提升个体对自我的关爱,以价值的多元配合来实现价值的增值不失为一种可取模式。[4]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刘飞,聂军.论亚当·斯密仁慈德性的内在矛盾及其现当代启示[J].湖南大学学报,2015,29(3).
[3]陈根法.德性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56-157.
[4](德)埃德蒙德·胡塞尔.伦理学与价值论的基本问题[M].艾四林,安仕侗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孙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