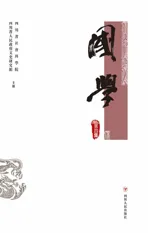《碧雞漫志》四劄
2017-03-14彭東焕,王映珏
近年來,筆者致力於《碧雞漫志》的箋證工作,其間針對相關的學術問題作詳細考察,幾年來得劄記三篇近三十條,分别刊於《蜀學》第六、七輯,《國學》第一集。今又得“樂、音、聲、律”“聲依永”“中正之聲”等若干條,謹爲“四劄”。
樂、音、聲、律
卷一“歌曲所起”条引録了《舜典》《毛詩序》《樂記》關於詩歌聲律的記載:
《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記》曰:“詩言其志,歌咏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注]王灼撰、岳珍校正:《碧雞漫志校正》,巴蜀書社2000年版。《碧雞漫志》原文皆依此書。
按對上述文獻的理解,首先是對“樂”“音”“聲”“律”等概念的基本含義的認識。
先秦時期的“樂”,是指“禮樂”之“樂”,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音樂。禮樂又分兩個層面,一是作爲治國安民的政治手段,一是作爲德教的手段。在禮樂制度層面,狹義的“樂”專指樂舞,如《樂記》所謂“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注]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版。即是這一含義。廣義的“樂”包括禮樂中的歌、樂、舞。如《周禮》中的“樂”,大多爲這一含義。作爲德教的“樂”,則是指合乎“德”的要求的“君子之樂”,包括“先王之樂”“古樂”“雅樂”等名目在內。《樂記》所論“樂”包含了以上兩個方面。但《樂記》所反映的是處於“禮崩樂壞”之後德教盛行的時代,故而强調雅俗的對立,“樂”“音”“聲”也因之具有倫理高下之别。然而“樂”“音”“聲”作爲宫廷禮樂建設中的一組音樂術語,不過是“作樂”的不同階段或步驟。“作樂”首先是制律,其次是定宫商、制樂器,樂歌舞的創作與整理,最後纔是音樂的教習和運用。從《尚書》《周禮》等文獻記載及其諸家注疏可知其大概。如:
《尚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聲依永,律和聲。”孔安國傳:“聲謂五聲:宫、商、角、徵、羽。”[注]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版。
《尚書·益稷》:“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孔安國傳:“言欲以六律和聲、音。”
《周禮·春官》:“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玄注:“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隂聲者也。此十二者以銅爲管,轉而相生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大合樂者,謂遍作六代之樂。”“(六樂)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注]鄭玄注,陸德明音義、賈公彦疏:《周禮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版。
《周禮·春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黄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吕、應鍾、南吕、函鍾、小吕、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宫、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陸徳明音義:“五聲以律吕調之,其八音亦使與律吕相應,八音亦合五聲。”賈公彦疏:“大師以吹律爲聲,又使其人作聲而合之,聽人聲與律吕之聲合,謂之爲音。”
《周禮·春官》:“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律”有廣義和狹義兩層含義。狹義的“律”是指樂音的音高標準,依律度製成的定音器亦稱爲“律”。“範天下之不一而歸於一”,這是“律”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從樂律學角度而言則是合和衆器,即是使衆器音高、宫調統一。制律首先是以“人聲”爲本,以人聲適度的音域確定律的範圍,再考訂音高製成律管,用以校正樂器音高(詳下文“聲依永”“中正之聲”相關考述)。廣義的“律”則包括音高標準、十二律體系的構成、音階形式、調式等內容,與“樂律”“音律”“聲律”“律吕”等名稱相互通用。
“音”,見於《尚書》和《周禮》內,多聯繫於樂器,“八音”即八類樂器的分類。孔穎達疏《樂記》云:“音則今之歌曲也以樂器次比音之歌曲而樂器播之,並及干戚羽旄,鼓而舞之,乃謂之樂也。”[注]孔穎達疏《樂記》:“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間,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結合賈公彦所釋“以六律爲之音”,可知“音”側重於指器樂。
“聲”指宫、商、角、徵、羽。每“聲”以黄鍾大吕爲音高標準,故而黄鍾大吕又稱之爲“聲”,十二律稱爲十二聲。鄭玄注《樂記》:“宫、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聲”與“音”相對時當作此解,但“聲”與“律”相對時,“聲”的意義則在於聲與聲之間的音程關係,五聲爲一個整體,各聲之間的音程是固定不變的,配合以十二律,每一律皆可爲宫爲商,一組五聲(或七聲)即爲一均。這樣的“聲”雜比纔爲“音”。鄭玄所謂“六者言其均”云云,即是從這一角度而言。戰國以後文獻,“音”“聲”則多混用。
宫廷音樂皆是以六律、五聲、八音爲基礎製作而成,故宫廷音樂均被稱爲“樂”。《周禮》中“燕樂”“縵樂”“夷樂”“散樂”等,均是這一含義。春秋戰國時期,雖然儒家强調“德音爲樂”,但宫廷音樂仍然有“女樂”“世俗之樂”“新樂”之稱。宫廷音樂首先是以音樂的標準衡量“樂”,如《尚書》中所載,察“治忽”,首先是審訂六律、五聲、八音。《儀禮》中的“正歌”“無算樂”亦均屬“樂”的範疇。[注]“正歌”是配合儀式的音樂,“無算樂”則是以娱賓客爲目的。鄭玄注,陸德明音義,賈公彦疏:《儀禮正義》,《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版。儒家衡量“樂”的標準則是“德”,“德音”的標準爲“雅樂”,而“雅樂”是以“宗周”爲前提,與“鄭聲”相對而提出的,“先王之樂”“古樂”,自然成爲“雅樂”的重要內容。[注]拙文《碧雞漫志續劄·二部伎》對雅樂概念的産生及演變已有考述,可參閲。《蜀學》第七輯,巴蜀書社2012年版,第131~133頁。後世崇雅往往與復古相聯繫,即是源於此。“樂”除了以上的含義之外,還用以代指樂器或用樂器演奏,如《儀禮》“笙入樂《南陔》”,《樂記》“比音而樂之”,《毛詩》“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謡”。[注]毛公傳《詩·魏風·園有桃》“我歌且謡”。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版。前二例“樂”指用樂器演奏,後一例指樂器。大概是因爲六律五聲皆由樂器來體現,大合樂亦“待五聲八音乃成”。
聲依永
卷一“歌曲所起”條全篇圍繞“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討論歷代詩歌聲律,其中有云:“永言即詩也,非於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乃制詞從之,倒置甚矣。”
王灼所謂宋代倚聲填詞“倒置甚矣”,很顯然是將“歌永言,聲依永”理解爲一種聲辭關係:“聲”“聲律”爲曲調,“聲依永”即是先辭後樂。下文所言漢文帝“倚瑟而歌”、魏世三調歌辭“因筦弦金石造歌以被之”皆非古法,即是從先辭後樂的“聲依永”之法的角度而論的。王灼的這種觀點在宋代具有普遍性,如趙德麟《侯鯖録》卷七載王安石言:“古之歌者,皆先有詞,後有聲,故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如今先撰腔子,後填詞,卻是永依聲也。”[注]趙德麟:《侯鯖録》卷七,中華書局點校本2002年版,第184頁。《宋史·樂志》載南宋高宗時國子丞王普上言:“蓋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協和而成曲。自歷代至於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詞,於是詞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乞復用古制。”[注]《宋史》卷一三〇“樂志”,中華書局點校本1977年版,第3030頁。吴曾《能改齋漫録》:“明皇尤溺於夷音,天下薫然成俗,於時才士始依樂工拍彈之聲,被之以辭。句之長短各隨曲度,而愈失古之聲依永之理也。”[注]吴曾:《能改齋漫録》,臺灣商務印書館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朱子語類》卷七八載朱熹釋“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謂:“古人作詩,只是説他心下所存事。説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詩之語言,卻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卻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語言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卻是永依聲也。”[注]黎靖德:《諸子語類》卷七八,中華書局點校本1986年版,第2005頁。此外還有另外一種觀點認爲“永言之法”是一字配一音,如《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二八載太常禮院主簿楊傑上言:“惟人禀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足以權量八音,使無重輕高下洪細長短之失。故古者昇歌,貴人聲。八音律吕皆以人聲歌爲度。以一聲歌一言,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夫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闋而樂聲未終,兹所謂歌不永言也。伏請節裁煩聲,以一聲歌一言,遵用永言之法。且詩言人志,詠以爲歌,五聲隨歌,故曰依詠,律吕協奏,故曰和聲。先儒云:依人音而制樂,托樂器以寫音,樂本效人,非人效樂。此之謂也。”[注]《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二八《禮樂》,臺灣商務印書館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如何正確理解“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一説。首先要對“詩”“歌”的早期含義有一個認識。據聞一多先生《歌與詩》考察,“詩”的本質是記事,“歌”的本質是抒情,“古代歌所據有的是後世所謂詩的範圍,而古代詩所管領的乃是後世史的疆域。”詩於文字産生以前,憑記憶以口耳相傳,詩之有韻及整齊的句法,都是爲着便於記誦,所以詩有時又稱“誦”。[注]聞一多:《聞一多講國學》,華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6頁。《詩經》有謂“家父作誦”“吉甫作誦”,[注]見《詩·小雅·節南山》《詩·大雅·崧高》。“作誦”即“作詩”,表明西周時期,“誦”亦是“詩”的重要傳述方式。《周禮·春官》所載,瞽蒙掌“諷誦詩世、奠系”,便是源於“詩”的記事功能和儀式誦唱史詩的古老傳統。“詩言志,歌永言”在原文的記載中是作爲樂師典樂的內容,“詩”“歌”皆是儀式樂的項目。[注]《尚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周禮》中,“詩”有風、賦、比、興、雅、頌六詩,而六詩皆稱爲“歌”。[注]《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這種變化,當與禮樂功能的變化有關。早期的禮樂用於“和神人”,周代的禮樂則用於“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説遠人,以作動物”。[注]《周禮·春官·大司樂》。禮樂功能的擴展,勢必引起“詩”的功用的擴展,“詩”的內涵自然也隨之而擴展。從“詩”與“歌”的並列,到在“歌”名義下六詩的並列,《周禮》中幾種“詩”的用例,反映的是禮樂制度發展的不同階段“詩”的不同內涵。概而言之,“詩”與“歌”的分合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詩”包括聲、言、誦三個要素,“歌”則包括聲、樂器兩個要素;第二階段,六詩皆爲“歌”,包括聲和辭兩方面內容;第三階段,詩之辭與詩之樂分離,“詩”專指詩之辭,詩、聲、歌爲依次遞進的關係。王灼所謂“永言即詩”,“詩歌聲律,率有次第”,即是“詩”“歌”發展到第三階段以後的含義了。
其次是要對“聲依永,律和聲”含義有正確的理解。“聲依永”的本來含義,宋人蘇軾已有詮釋。蘇軾《書傳》在解釋“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一語時稱:“聲者,樂聲也;永者,人聲也。樂聲昇降之節視人聲之所能至,則爲中聲,是謂聲依永。永則無節,無節則不中律,故以律爲之節,是謂律和聲。”[注]蘇軾:《書傳》,臺灣商務印書館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代樂律學家朱載堉在《樂律全書》中亦是從“人聲”與“樂聲”的角度來解釋“聲依永”的,且更爲通俗易明:“詩既成矣,其吟詠之間,必悠揚宛轉有清濁高下之節,然後可聽,是之謂歌永言。今俗樂之唱詞曲,乃其遺法也。當歌之時,欲和之以樂器之聲,其樂聲之清濁高下必與歌聲之清濁高下相應,是之謂聲依永。俗樂唱詞曲之時,或吹竹彈絲與之相應,乃其遺法也。至此則樂已小成矣。若並奏衆音,清濁高下難得齊一,故須用律以齊之,如作黄鍾宫調,則衆音之聲皆用黄鍾爲節,作太簇商調,則衆音之聲皆用太簇爲節,然後清濁高下自齊一而不亂,是之謂律和聲。”[注]朱載堉:《樂律全書》卷五,臺灣商務印書館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詩言志”云云,於《舜典》內聯繫前後文,所講的正是關於儀式中詩、歌、聲、律諧和的問題,“聲依永”體現的是重“人聲”的傳統,而不是“因聲度詞”或“詩而聲之”的問題。“重人聲”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注]《禮記·郊特牲》,《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版。二是制律以“人聲”爲本。如《文心雕龍·聲律》謂:“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也”。[注]劉勰撰,周振甫注譯:《文心雕龍今譯》,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299頁。《左傳·昭公元年》:“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注]杜氏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版。蘇軾所説的“中聲”爲“視人聲之所能至”,聯繫於曾侯乙編鐘剛好五個八度,由此可以推斷,律的範圍是以人聲適度的音域來確定的,再考訂音高度量成數值,據相應的數值製成律管作爲定音器,[注]《國語·周語》有云:“古之神瞽考中聲量之以制”,這裏“中聲”是指音高標準。詳下文“中正之聲”。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32頁。用以校正樂器音高,大合樂時使衆器宫調統一。[注]《周禮·春官》:“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説文》段注云:“律者,所以範天下之不一而歸於一”,[注]許慎著,段玉裁注:《説文解字》第二篇,成都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頁。這是“律”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見於先秦兩漢時期的文獻所解釋的“律”,其含義是很明確的,一是指樂音的音高標準,依律度製成的定音器亦稱爲“律”。如《國語·周語》:“律,所以立均出度。”[注]《國語·周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高誘注《淮南子》:“律,律度也。”[注]《淮南子》,《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蔡邕《月令章句》:“律,帥也,聲之管也。上古聖人始鑄金以爲鐘,以應正月至十二月之聲,乃截竹爲管,謂之律。聲之清濁,以律管長短爲制也。”[注]《後漢書·律曆志》注引《月令章句》。司馬彪撰,劉昭注補:《後漢書》,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001頁。“樂律”“音律”“律吕”等名詞相互通用,包括音高標準、十二律體系的構成、音階形式、調式等內容。宋人則往往將“律”“聲律”“音律”等名詞作“曲調”的同義語來使用。如蘇軾《哨遍·爲米折腰》詞序云:“乃取《歸去來》詞,稍加檃括,使就聲律,以遺毅夫,使家僮歌之。”[注]《東坡樂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頁。劉克莊跋《劉瀾樂府》:“詞當葉律,使雪兒、春鶯輩可歌,不可以氣爲色。”[注]劉克莊:《劉瀾樂府》,《四部叢刊》本《後村大全集》卷一〇九。王灼於下文亦云:“唐中葉雖有古樂府,而播在聲律則尠矣,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體自名耳。”姜夔《長亭怨慢》序云:“予頗喜自製曲,初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以律。”[注]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四川人民出版社影印鮑廷博手校張奕樞本。王灼以宋人的習慣用法來理解早期文獻,自然相去甚遠。先秦文獻中“律”“音律”等名稱絶無“曲調”這一含義。《吕氏春秋》專有“音律”一章,講的是十二律相生之法等內容。[注]吕不韋著,高誘注,畢沅校:《吕氏春秋》,《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宋代詞樂重宫調,如詞調有以“轉調”爲名的,周邦彦的“三犯”“四犯”之曲等,《樂章集》以宫調爲序。[注]柳永撰,薛瑞生校注:《樂章集》,中華書局1994年版。宫調一定,“聲”“律”即定,加之宋代採用的是固定調記譜法——半字譜字與律吕一一對應,有曲調,自然合律。這大概就是宋人將“律”“音律”指代曲調的原因。
“樂府”與“詩”,“歌”與“謡”
卷一“歌曲所起”條有云:“而士大夫又分詩與樂府作兩科。古詩或名曰樂府,謂詩之可歌也。故樂府中有歌,有謡,有吟,有引,有行,有曲。”
樂府,原爲秦漢宫廷音樂機構。見於《漢書》所載,“樂府”之名均是作爲音樂機構的名稱,如《禮樂志》:“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寛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至武帝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吕,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注]《漢書》卷二二“禮樂志第二”,中華書局點校本1962年版,第1043頁、1045頁。《藝文志》:“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謡,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注]《漢書》卷三〇“藝文志第十”,第1756頁。《宣帝紀》:“(本始)四年春正月,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樂府减樂人,使歸就農業。’”[注]《漢書》卷八“宣帝紀”,第245頁。《張放傳》:“使樂府音監景武强求不得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群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注]《漢書》卷五九“張湯傳”附傳,第2655頁。《霍光傳》:“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注]《漢書》卷六八“霍光傳”,第2940頁。另1976年在秦始皇陵區出土的鈕鐘上有銘文“樂府”,2000年在西安秦遺址出土“樂府承印”封泥一枚,説明秦代已有樂府機構。《漢書》所謂武帝“立樂府”,當指樂府恢復古之“采詩”制度,制作禮樂始於武帝時。
漢代合樂之“詩”稱爲“歌詩”,與不合樂的賦相對。[注]《漢書》卷三〇“藝文志第十”:“不歌而誦謂之賦。”六朝時期纔將“歌詩”稱爲“樂府”,詩、賦、樂府成爲並列的文體。如《文選》分“賦”“詩”“樂府”等幾類,[注]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玉臺新詠》分别有“古詩”和“古樂府”。[注]徐陵編,吴兆宜注,程琰删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中華書局1985年版。説明這一時期“詩”和“樂府”均爲獨立的兩種文學體裁了。唐代“樂府”一名或指一種詩體,或指代音樂機構,宋代則多將詞體稱爲“樂府”,即王灼所説的“以詞就音,始名樂府”。
“歌”“謡”對稱時有兩層含義:一是《韓詩章句》所云“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謡”[注]《初學記》卷一五引。徐堅:《初學記》,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76頁。,即有曲調的爲歌,無曲調的爲謡。按“章曲”即指“曲調”。如《宋書·律志》:“今鼓吹鐃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注]沈約:《宋書》,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年版,第204頁。陳暘《樂書》:“韓詩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謡。故釋樂以徒歌謂之謡,則徒擊鼓謂之咢,其無章曲可知矣。”[注]陳暘:《樂書》,臺灣商務印書館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二是《毛詩》所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謡”,“歌者,比於琴瑟者也,徒歌曰謡”。如此,則合於琴瑟等樂器的爲歌,不合樂器而歌爲謡。這層含義的“歌”和“謡”都有“章曲”,亦皆可稱之爲歌,正如孔穎達疏《左傳》所云:“襄二十九年季札請觀周樂而云爲之歌齊,爲之歌鄭之等,亦是不依琴瑟而云歌,此皆是徒歌,曰謡,亦得謂之歌,若依琴瑟謂之歌,即毛云曲合樂曰歌是也。”孔穎達疏《周禮》云:“徒歌謂之謡,言無樂而空歌,其聲逍遥然也。”“謡”“其聲逍遥”,大概因無樂器所節,因而具有節奏散漫自由的特點。“我歌且謡”[注]《詩·魏風·園有桃》。,這裏的“歌”與“謡”對稱,即是合樂與不合樂的區别,反映在音樂風格上則是節奏緊凑與節奏散漫的區别。
其餘“吟”“行”“曲”等名詞,鄭樵《通志·樂一》“正聲序論”中略有概括:“主於人之聲者則有行、有曲,散歌謂之行,入樂謂之曲。主於絲竹之音者,則有引、有操、有吟、有弄,各有調以主之。攝其音,謂之調,總其調亦謂之曲。凡歌行雖主人聲,其中調者皆可以被之絲竹,凡引、操、吟、弄雖主絲竹,其有辭者皆可以形之歌詠。蓋主於人者有聲必有辭,主於絲竹者取音而已,不必有辭,其有辭者通可歌也。”[注]鄭樵:《通志》,中華書局1987年版。
采進之詩與樂章
卷一“歌曲所起”條云:“古者采詩,命太師爲樂章”。
《漢書·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注]《漢書》卷三〇“藝文志第十”,第1708頁。《漢書·食貨志上》:“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注]《漢書》卷二四上“食貨志第四上”,第1123頁。按,關於周代的採詩制度,已多有學者研究。大概而言,“詩”的來源一是“列士獻詩”,這類多是徒詩;二是行人採集的民間歌謡,則有聲有辭。《周禮·秋官·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賈誼新書》:“號呼謌謡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訟逆序凡此其属詔工之任也。”[注]賈誼撰、盧文弨校:《賈誼新書》,《二十二子》本。“詔工”,孫冶讓正義《周禮》謂“詔工,蓋即大師。”表明行人所採之“詩”並非無曲調,而是需要大師審訂整理,合宫商律吕。“比其音律”之“比”,子夏《易》彖傳:“比,輔也,下順從也。”[注]《子夏易傳》卷一,臺灣商務印書館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顏師古注《漢書》:“比亦和也。”[注]《漢書》卷五八,第2616頁。則“比其音律”是民間歌謡“遵從”於宫廷的“音”“律”。“比”與“律平聲”之“平”作用相同,皆是使樂“和”;不同之處在於,“比”是客觀上對照兩個音是否相同,“平”是主觀上調整一個音與另一個音的音高相同。除合律之外,還在於對曲調的整理,禁“淫聲”,去“邪音”,《周禮·春官·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慢聲。”《荀子·王制》:“修憲命,審詩商,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注]荀况撰、楊倞注、盧文弨等校:《荀子》,《二十二子》本。宫廷音樂的“樂”“音”“聲”“律”皆有其相應的規則,這也是區别民間音樂的重要標志。“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謡”,“歌”與“謡”的區别亦可視爲宫廷歌曲與民間歌曲的區别。
中正之聲
卷一《論雅鄭所分》條云:
或謂雅鄭所分。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至論也。何謂中正?凡陰陽之氣,有中有正,故音樂有正聲,有中聲。二十四氣,歲一周天,而統以十二律。中正之聲,正聲得正氣,中聲得中氣,則可用。中正用,則平氣應,故曰:中正以平之。若乃得正氣而用中律,得中氣而用正律,律有短長,氣有盛衰,太過不及之弊起矣。自揚子雲之後,惟魏漢津曉此。
“中正則雅,多哇則鄭”,出自揚雄《法言·吾子》:“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鄭或雅,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請問本,曰:黄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注]揚雄撰,李軌、柳宗元注:《揚子法言》,臺灣商務印書館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中正之聲與中正之氣的關係見《宋史·乐志》載劉昺《樂書》“八論”:“魏漢津以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九寸之律,三數退藏,故八寸七分爲中聲。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宫架環列,以應十二辰;中正之聲,以應二十四氣;加四清聲,以應二十八宿。氣不頓進,八音乃諧。若立春在歲元之後,則迎其氣而用之,餘悉隨氣用律,使無過不及之差,則所以感召陰陽之和,其法不亦密乎?”同卷載劉昺《樂書》“十二律應二十四氣圖”之旨意:“二十四氣差之毫釐,則或先天而太過,或後天而不及。在律爲聲,在曆爲氣。若氣方得節,乃用中聲;氣已及中,猶用正律。”[注]《宋史》卷一二九“乐四”,第3004~3005、3007頁。
魏漢津,北宋皇祐崇寧間人,因知音獲薦,其樂律理論載於《宋史·樂志》,大體而言有三點:一是以帝指爲律度;二是黄鍾九寸得正聲之律十二,黄鍾八寸七分得中聲之律十二,以應二十四氣,加四清聲,共二十八聲,以合二十八宿;三是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注]《宋史》卷四六二,第13525~13526頁。大晟樂即是據其理論製作的。[注]《宋史》卷一二六“樂一”謂:“於是蔡京主魏漢律之説,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以帝指爲律度,鑄帝鼎、景鐘。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頒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宋史》第2938頁。
按,“正聲”指正律之聲,正律是相對於低八度的倍律、高八度的半律而言,或相對於變律而言(詳後);在樂論中正聲指雅正之聲,是與奸聲、鄭聲等概念相對而言。
“中聲”,宋以前有兩種含義,一是以人聲適度的音域爲“中聲”,已詳前文。二是高低大小適中,合於律度之聲爲“中聲”。從《國語》《吕氏春秋》中對“適”“和”“平”“律”的詮釋可知其一二。
《國語·周語下》:“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逾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注]《國語》,第128、132頁。
《吕氏春秋》卷五:“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夫音亦有適,太巨則志蕩,以蕩聽巨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故太巨、太小、太清、太濁皆非適。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黄鍾之宫,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太,和者是也。”
單從聲、律角度而言,“衷音”爲“適”,“適音”爲“和”。“適”爲高低大小適中,而高低大小首先遵從人的聽覺感知,符合聽覺的審美要求,然後以“律”爲準度。“律以平聲”“細大不逾曰平”,所謂“平”,《國語·鄭語》有謂“以它平它謂之和”,[注]《國語》,第515頁。從聲律的角度而言,即是以“律”爲標準調節“聲”,使“聲”高低合於律度。“中正以平之”,意即以“中正”爲准度來調節“聲”。“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就很容易理解了,其意是指通過音樂聽力異常靈敏的神瞽辨别和諧之聲,將音高量化、物化(如律准律管之類),用以製造樂器、校準音高。正如《周禮·春官》所謂:“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那麽對於揚雄所言,陳暘《樂書》卷九六的解釋則較爲恰當:“有正聲焉,有間聲焉,故其聲正直和雅合於律吕,謂之正聲,此雅頌之音,古樂之發也。其聲間雜繁促不協律吕,謂之間聲,此鄭衛之音,俗樂之發也。雅頌之音理而民正,鄭衛之曲動而心淫,然則如之何而可不過乎,黄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注]陳暘撰:《樂書》卷九六“和聲”條。揚雄是從聲律關係來評判雅俗的,合於律度則雅,反之則鄭。
“中正”,實是以“中”爲正。中正思想在儒家論説中尤爲明確,如《論語·堯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注]楊伯峻譯注:《論語》,中華書局1980年,第207頁。《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説苑》:“奏中聲爲中節,故君子執中以爲本。”[注]劉向撰:《説苑》卷一九,臺灣商務印書館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這些論説所强調的“中”,皆具有以“中”爲正的內涵。中國古代很早便有四方五位、八方九宫的意識,無論是四方、八方還是九宫,“中”皆居於中心,而中心之地,“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注]《周禮·地官·大司徒》。漢賈誼《新書·屬遠》亦謂“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注]《賈誼新書》卷三。居中而治方能致和,後世以中原政權爲正統的思想便源於此。這一思想反映在樂律學中,便産生了以黄鍾爲律本,宫爲音主,宫爲君等觀念,成爲樂律學的理論基礎。[注]如《漢書·律曆志上》:“﹝黄帝﹞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黄鍾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國語·周語下》:“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黄鍾。”“夫宫,音之主也。”《史記》:“(琴)弦大者爲宫,而居中央,君也。”按非指宫弦居於七弦之中,而是宫屬土,土於五行居中。
綜合以上的考察,揚雄所説的“中正”與王灼所理解的“中正”顯然不是相同的概念。在宋前“正聲”和“中聲”從未作爲一對並列的概念來使用,以黄鍾九寸爲正聲,黄鍾八寸七分爲中聲,將“中正之聲”分爲正聲和中聲始於宋代,正如蔡攸上書反對魏漢津中正理論時所説的“考閲前古,初無中、正兩樂”。[注]見《宋史》卷一二九“樂四”,第3023頁。宋代中聲和正聲的律學依據在於三分損益生律法以九寸黄鍾爲始發律,損益十一次所生成的第一組八度內的十二律爲正律。但回生黄鍾時,僅得八寸八分有餘,比始發律九寸黄鍾少約一分,若以此相生下去,每次回生黄鍾時均會少一分有餘,京房六十律便是據此生至六十律。[注]見《後漢書·律曆上》,第3003頁。宋代的八寸七分黄鍾,即相當於京房六十律中的“丙盛”,也就是以九寸黄鍾爲始發律,生兩組十二律後所回到的黄鍾律。[注]京房六十律中,九寸黄鍾與大吕之間有五律:色育約八寸九分,執始約八寸八分、丙盛約八寸七分、分動約八寸六分、質末約八寸五分。見《後漢書·律曆上》。宋代就是以八寸七分黄鍾所生成的這一組十二律爲中聲。
周天,即天之一周。一周天約三百六十度,太陽日行一度,太陽繞周天行一周爲一年。《禮記·月令》唐孔穎達疏:“星既左轉,日則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舊星之處。即以一日之行而爲一度計,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之一周之數也。”
二十四氣,即二十四節氣。立春、驚蟄、清明、立夏、芒種、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爲十二節,雨水、春分、穀雨、小滿、夏至、大暑、處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爲十二中氣。《素問·六節藏象論》謂“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注]《黄帝內經素問》,臺灣商務印書館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淮南子·天文訓》謂“日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黄鍾。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云云,[注]劉安撰,高誘注,莊達吉校:《淮南子》卷三,《二十二子》本。則十五日爲一氣。節與中氣依次相間排列,一年共二十四個節氣。見《逸周書·時則》《禮記·月令》《淮南子·天文》《漢書·律曆志》等。
確定節氣的方法除了立表測影的方法外,還以律管候氣以正時。如《禮記·月令》鄭玄注云:“律,候氣之管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更相治,間不容飄忽。”[注]《史記》卷一三〇,中華書局點校本1982年版,第3305頁。《史記·律書》:“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禀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建律運曆造日度,可據而度也。”[注]《史記》卷二五,第1239、1253頁。《漢書·律曆志上》:“故黄鍾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顏師古注:“律得風氣而成聲,風和乃律調也。”“風氣正則十二月之氣各應其律,不失其序”等等論述,[注]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二一,中華書局點校本,第960、976頁。無不體現了律氣相應的思想。在月令曆法中以十二律紀十二月陰陽之氣的變化,反之在禮樂中則依月用律、依氣用律以應陰陽之氣,如《周禮》所云:“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後世亦多因之,《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建初五年)冬,始行月令迎氣樂。”[注]《後漢書》卷三,第141頁。《後漢書·孝順孝冲孝質帝紀》:“(陽嘉元年)冬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黄鍾,作樂器隨月律。”[注]《後漢書》卷六,第263頁。《魏書·臨淮王傳》:“臣今據《周禮》依十二月爲十二宫,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注]魏收撰:《魏書》卷一八,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年版,第427~428頁。《唐會要》:“大唐雅樂,以十二月律各順其月,旋向爲宫。”[注]王溥撰:《唐會要》,中華書局1955年版。《宋史·樂志》:“設十二鎛鍾、特磬於編架內,各依月律。”[注]《宋史》卷一二九,第3014頁。最早完整記録二十四氣與十二律相應的見載於《淮南子·天文訓》:
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黄鍾。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五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五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黄鍾。加十五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蹄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鍾。
節氣應陽律,中氣應陰吕。而節氣、中氣與正聲、中聲如何配屬則首見於宋人的爭論,如上文所録《宋史》中的兩種觀點:“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若氣方得節,乃用中聲;氣已及中,猶用正律。”從王灼的語意來看,“正聲得正氣,中聲得中氣”,“得正氣而用中律,得中氣而用正律”,所謂“正氣”與“中氣”當是二十四氣中的“節氣”與“中氣”。或許爲與正聲和中聲對應而稱之爲正氣和中氣。
王灼於下文稱蘇軾知有中聲,而不知有正聲。蘇軾之説見《書傳》卷四《虞書·益稷第五》:“樂工所以不能致氣召物如古者,以不得中聲故爾。樂不得中聲者,器不當律也,器不當律,則與擿植鼓盆無異,何名爲樂乎。使律能當律,則致氣召物,雖常人能之,蓋見於古今之傳多矣,而况於夔乎。”按蘇軾所説的“中聲”是指合於律度之聲,正是上文陳暘所説的與“間聲”相對的“正聲”,而非王灼所説的與正聲並列的“中聲”。全篇所論雅俗之分,僅是從律學尤其是宋人爭議的聲氣配屬問題來議論的。然而從先秦産生雅俗觀念以來,樂律、樂器、音樂的來源、歌辭的內容與形式、音樂風格等等均有雅俗之辨。該問題較爲複雜,另文詳探。
柳 詞
卷二“樂章集淺近卑俗”條云:
柳耆卿《樂章集》,世多愛賞,其實該洽,序事閑暇,有首有尾,亦間出佳語,又能擇聲律諧美者用之。惟是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予嘗以比都下富兒,雖脱村野,而聲態可憎。
王灼對柳詞的議論雖是立足於崇雅抑俗而發,但基本上道出了柳詞的幾個重要特點。《樂章集》“變舊聲作新聲”[注]語出李清照《詞論》。黄墨谷編:《重輯李清照集》,齊魯書社1981年版,第56頁。,尤以民間新聲爲多,衆體皆備,有令、慢、引、近,有减字、攤破、犯調等,其中以長調慢詞爲多,占了三分之二;以賦爲詞,層層鋪展,一氣貫穿,渾然一體;善於叙事寫景,即事而發,由景而入,事以景繫,情以景見;平白如話,多用俚語俗語,即王灼所説的“淺近卑俗”,劉熙載《艺概》並以之比於白居易。[注]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柳耆卿詞,昔人比之杜詩,爲其實説無表德也。余謂此論其體則然,若論其旨,少陵恐不許之。耆卿詞,細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於叙事,有過前人。”“詞品喻諸詩,東坡、稼軒,李、杜也;耆卿,香山也”。劉熙載:《藝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07~108、113頁。王灼於前文相對於“詩與樂府同出”而提出的“柳氏家法”[注]《碧雞漫志》卷二“各家詞短長”謂“或曰:(東坡詞)長短名中詩也。爲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得不分異耳。”,則應是僅指後者。
柳永從以詞名世開始,其詞便受到極大的關注,品評褒貶不斷。究其原因,與其所處的時代有關。柳永“大得聲稱於世”時,正處於北宋詩文革新運動時期,晏殊、歐陽修等人以餘事作詞,承花間“詩客曲子辭”遺風,講究風調閑雅、風流藴籍,以助娱賓遣興。葉夢得《避暑録話》卷上載,晏殊每宴“亦必以歌樂相佐”,《樂府雅詞》歐陽修《採桑子》序稱其爲“聊佐清歡”之作,[注]曾慥編:《樂府雅詞》,臺灣商務印書館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小山詞序》称“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諸兒,吾三人持酒聽之,爲一笑樂而已。”[注]晏幾道撰:《小山詞》,臺灣商務印書館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黄庭堅序《小山詞》也自稱“余少時間作樂府,以使酒玩世”,[注]黄庭堅撰:《山谷集》卷一六,臺灣商務印書館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均表明其作詞不過爲遊戲而已。晏殊“未嘗一日不燕飲亦必以歌樂相佐”,宴畢,遣歌樂,“乃具筆劄,相與賦詩,率以爲常。”[注]《避暑録話》卷上:“晏元憲公雖早富貴,而奉養極約。惟喜賔客,未嘗一日不燕飲,而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頃,有蘓丞相子容嘗在公幕府,見毎有嘉客,必留,但人設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案上已燦然矣。稍闌,即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遍,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爲常。前輩風流未之有比。”葉夢得撰:《避暑録話》,臺灣商務印書館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可見當時詩與詞界綫分明。而柳永“忍把浮名,换了淺斟低唱”,[注]柳永《鶴冲天》。柳永撰,薛瑞生校注:《樂章集》,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239頁。“日與獧子縱遊娼館酒樓間”,[注]《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九引《藝苑雌黄》云:“柳三變喜作小詞,然薄於操行,當時有薦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日與獧子縱遊娼館酒樓間,無復檢約。自稱云:‘奉聖旨填詞柳三變’。”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周本淳重訂:《苕溪漁隱叢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335頁。採擇民間俗歌俚調填詞作歌,其聽衆不外市井小民、販夫走卒,即王灼所説的“不知書者尤好之”。與晏歐諸人的遊戲態度完全不同,柳永一生致力於詞的創作。柳詞遭人鄙薄實不在於是雅是俗,晏殊亦作“婦人語”,歐、蘇於尊前花間亦嘗作浮豔之詞,而在於柳永“謬其用心”。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載范鎮與柳永同年,“愛其才美。聞作樂章,歎曰:謬其用心!”待聽唱柳詞復歎曰:“仁廟四十二年太平,吾身爲史官二十年,不能贊述,而耆卿能形容盡之。”[注]薛瑞生《樂章集前言》引。柳詞在當時不僅不知書者好之,知書者亦好之,如陳師道《後山詩話》所載:“柳三變遊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毎對,必使侍從歌之再三。”[注]陳師道撰:《後山詩話》,臺灣商務印書館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黄裳《書樂章集後》:“予觀柳氏文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氣象,如觀杜甫詩,典雅文華,無所不有。”[注]黄裳:《演山集》,臺灣商務印書館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再者王灼對柳詞的深惡痛絶,亦是由當時的時代背景所决定的。南宋初期,詞的創作沿着蘇軾開闢的“以詩爲詞”的詩化道路發展,而强調復古復雅。王灼於本書卷一卷二多以“古法”“古意”“古雅”爲標準品評歷代樂曲歌辭,[注]《碧雞漫志》卷一多次討論的“古法”“古俗”“古意”,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歌曲所起”條討論的先辭後樂的“聲依永”之法;二是因感發而歌,“歌曲所起”之“有心則有歌”,本文之“因所感發爲歌”,“漢初古俗猶在”之吟詠情性;三是以“詩”入歌曲,如“唐絶句定爲歌曲”條所謂“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繡球》《楊柳枝》,乃詩中絶句,而定爲歌曲。”三者皆是王灼所理解的“詩言志”所包含的“古法”要素。卷二評論諸家詞之長短,同樣是以“詩”爲標準。可見出王灼是“古雅”派忠實的奉行者,對於以俗詞而享盛名的柳永,自然首當其衝成爲其批判的對象。
大晟府與依月用律
卷二“大晟樂府得人”云:“崇寧間建大晟樂府新廣八十四調,患譜弗傳,雅言請以盛德大業及祥瑞事迹制詞實譜。有旨依月用律,月進一曲,自此新譜稍傳。”
大晟府爲北宋晚期徽宗時設立的音樂機構,《宋史》記載頗詳:
《宋史·徽宗紀》載,崇寧四年八月,“徽宗設大晟樂府名大晟,置府建官。”[注]《宋史》卷一二,第375頁。
《宋史·樂一》:“徽宗鋭意製作,以文太平,於是蔡京主魏漢津之説,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以帝指爲律度,鑄帝鼎、景鐘。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頒之天下,播之教坊”[注]《宋史》卷一二六,第2938頁。
《宋史·樂四》:“帝御崇政殿,親按宴樂,召侍從以上侍立。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比詔有司,以大晟樂播之教坊,試於殿庭’”[注]《宋史》卷一二九,第2938頁。
《宋史·樂十七》:“政和三年五月,詔:‘比以大晟樂播之教坊,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樂頒之天下。’八月,尚書省言:‘大晟府宴樂巳撥歸教坊,所有諸府從來習學之人,元降指揮令就大晟府教習,今當並就教坊習學。’從之。”[注]《宋史》卷一四二,第3018頁。
《宋史·職官四·大晟府》:“以大司樂爲長,典樂爲貳。次曰大樂令,秩比丞。次曰主簿、協律郎。又有按協聲律、製撰文字、運譜等官,以京朝官、選人或白衣士人通樂律者爲之國朝禮、樂掌於奉常。崇寧初,置局議大樂;樂成,置府建官以司之,禮、樂始分爲二。宣和二年,詔以大晟府近歲添置冗濫徼幸,並罷,不復再置。”[注]《宋史》卷一一七,第3886頁。
可知大晟府置於崇寧四年(1105),宣和二年(1120)即廢止,存續時間僅十五年。期間太常寺、大晟府、教坊分掌禮、雅樂、燕樂。
八十四調是指十二律與五聲二變通過旋宫轉調而構成八十四個調。八十四調最早見載於《隋書》。《隋書·音樂中》卷一四志第九載:“譯遂因其所捻琵琶,弦柱相引爲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注]《隋書》卷一四,中華書局點校本1973年版,第346頁。《隋書·萬寶常傳》:“寶常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並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爲宫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注]《隋書》卷七八,第1784頁。其後兩唐書、《宋史》以及文人筆記小説亦多有相關記述。大體而言,八十四調有兩種推演方法,一種是十二律依次旋宫構成十二宫(均),每宫七調,共八十四調;另一種是一律有七調,十二律則有八十四調。
依月用律,即十二月與十二律相配,各月所行典禮用樂即用該月之律。依月用律源於以律候氣的古老傳統,已详前。較早完整記録月律配屬的典籍有《吕氏春秋》《禮記》《逸周書》等書。據諸書制“十二月律配屬表”如次:

十二月一二三四五六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律太簇夾鍾姑洗中吕蕤賓林鍾黄鍾夷則南吕無射應鍾黄鍾大吕五音角角角徵徵徵宫商商商羽羽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