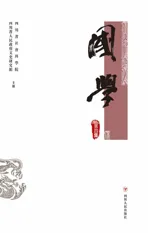中國文學版圖視閾下的《詩經》 創作地域考察①
2017-03-14鄧穩
梁啓超《中國地理大勢論》指出中國地理特點與風俗、文學等的關係:“中國者,天然大一統之國也:人種一統,言語一統,文學一統,教義一統,風俗一統,而其根原莫不由於地勢。中國所以遜於泰西者在此,中國所以優於泰西者亦在此。”[注]梁啓超:《亞洲地理大勢論》,《飲冰室合集》第2册,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77頁。統一有一個逐漸擴大空間的過程,因此梁啓超又説:
“文學地理”常隨“政治地理”爲轉移。自縱流之運河既通,兩流域之形勢,日相接近,天下益日趨於統一,而唐代君臣上下,復努力以聯貫之。貞觀之初,孔穎達、顏師古等奉詔撰五經正義,既已有折衷南北之意文學家之韓、柳,詩家之李、杜,皆生江河兩域之間,蓋調和南北之功,以唐爲最矣。由此言之,天行之力雖偉,而人治恒足以相勝,今日輪船、鐵路之力,且將使東西五洲合一爐而共冶之矣,而更何區區南北之足云也。[注]梁啓超:《中國地理大勢論》,《飲冰室合集》第2册,第87頁。
從文學版圖的角度來看,“文學地理”常隨“政治地理”轉移實則表明在中國歷史上文學版圖是政治、疆域版圖融合、發展的進一步深化。因此,文學版圖的展開恰好可以反映出不同地區乃至多民族文化融合在中國疆域版圖上的作用過程。但要考察中國文學版圖的展開過程,還應該從中國文學的源頭——《詩經》説起。
《詩經》作爲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有一個漫長的形成過程。《墨子》言:“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注]孫詒讓著、孫以楷點校:《墨子間詁·公孟》,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18頁。《史記·孔子世家》亦説:“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注]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936頁。可見,諸家皆以詩爲配樂演唱之歌。宋以後,有人懷疑《詩經》內有部分徒歌,程大昌《詩論》認爲:“《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注]程大昌:《考古編·詩論二》,俞鼎孫、俞經輯刊《儒學警悟》,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496頁。顧頡剛著《論〈詩經〉所録全爲樂歌》一文駁之。[注]顧頡剛:《論〈詩經〉所録全爲樂歌》,《古史辨》第3册,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608~657頁。據聞一多《歌與詩》,“詩”的本義是記事,包含記憶、記録、懷抱三種含義,它們分别“代表詩的發展途徑上三個主要階段”[注]聞一多:《歌與詩》,《神話與詩》,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85頁。。鄭玄《詩譜序》對詩的産生時代提出懷疑和推測:“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注]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頁。下引版本同此,不另注。《虞書》並不能肯定爲虞舜時人所作,自不待辨,因此不能據“詩言志”一語有“詩”肯定其時已有如《詩經》之詩。然探本溯源,歌在詩之前卻可肯定。漢代文獻中有不少證明“詩”爲晚出的材料,《漢書·匈奴傳》:“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注]班固:《漢書·匈奴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744頁。可知班固認爲西周懿王時“王室始衰”,“詩人始作”。高誘注《淮南子·詮言訓》也認爲“詩者,衰世之風也”[注]高誘注:《淮南子》(《諸子集成》本),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247頁。。因此,“詩”在此層意思上並不包含《頌》全部和《雅》的大部分詩歌。所以,《毛詩序》也提出“正”“變”理論予以説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注]《毛詩正義》,第271頁。這種“變風”“變雅”即是古人觀念中比較狹窄的“詩”的觀念,鄭玄《詩譜序》對此有更爲詳實的闡釋:
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録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絶矣。故孔子録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注]《毛詩正義》,第262~263頁。
這段話再次證明,變風、變雅謂之“詩”,“詩”與贊頌之歌不同。根據文字學來考察,“‘詩’字的造字之義應爲規正人行、使之有法度的言辭,也就是説,‘詩’字是在指代諷諫之辭的意義上産生出來的”[注]馬銀琴:《兩周詩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頁。下引版本同此,不另注。,《文心雕龍·明詩》“詩者,持也,持人性情”、《毛詩正義》“爲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墜”可爲之佐證。因此,今本《詩經》風、雅、頌三部分在周代曾有並不統稱爲“詩”的階段,如《周禮·春官·籥章》云: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租,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蠟,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注]鄭玄注、賈公彦疏:《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01~802頁。
歷代學者對“豳詩”“豳雅”“豳頌”的理解差異頗大[注]鄭玄注、孔穎達疏認爲三者皆指《豳風七月》;朱熹《詩集傳》疑《七月》爲《豳詩》,《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爲《豳雅》,《臣工》《豐年》《載芟》《良耜》等爲《豳頌》。,但《周禮》此段文字至少表明:今本《詩經》風、雅、頌三部分,曾經被區分爲詩、雅、頌三部分。
然而,“歌”“詩”合流的現象也出現較早。《大雅·卷阿》“豈弟君子,來游來歌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大雅·崧高》“吉甫作頌,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即以“詩”指代頌美的樂歌之辭;《大雅·桑柔》“雖曰匪予,既作爾歌”,《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即以“歌”指代怨刺之詩。“詩”側重於詩歌的內容、文辭,“歌”則側重於它的形式、音調。至晚從西周厲王時代起,中國人的詩歌觀念已經開始發生轉變,詩歌創作由歌、詩别類階段進入了歌、詩合流的時代。公元前642年,宋司馬公孫固引《商頌》、鄭叔詹引《周頌》仍然以“頌”相稱,但是四年之後,開始出現魯國臧文仲引《頌》稱“《詩》曰”的情况,此後,常以“詩”稱《頌》。可見,最遲至公元前7世紀中葉,“詩”已經成爲歌、詩的通名。
至於《詩》文本的形成,約略經過以下六個階段:康王三年“定樂歌”,今本《詩經》部分詩歌以《雅》《頌》的名稱傳世;穆王時代,《雅》《頌》文本內容擴大,在祭祀樂歌之外,新增了燕享樂歌一類;宣王時代,厲王“變大雅”被納入《雅》,諸侯國風在《詩》的名義下得到編輯,形成服務於諷諫的“詩”;平王時代,《頌》仍單獨流傳,以《詩》爲名,《風》《雅》合集的詩文本産生;齊桓公尊王崇禮,以諸侯國風爲主體,納《周頌》《商頌》入《詩》,《風》《雅》《頌》合集的詩文本出現;至春秋末年,孔子删定詩篇,今本《詩》的面貌基本定型。[注]參《兩周詩史》,第487頁。

綜觀諸家《詩經》地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詩經》所涉諸國的疆域;二是《詩經》各詩所涉地名的考證;三是由《詩》地理以觀風俗、知政教得失,即王應麟“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因《詩》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感發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注]王應麟著,王京州、江合友點校:《詩考·詩地理考》(合刊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79頁。之謂。第三種研究最爲玄奧,第二種最煩瑣難考,第一種由於歷史資料豐富,且諸國疆域又可相互印證,實可得到較圓滿的解决。我們研究《詩經》、賦的創作地域異同,只需要弄清《詩經》發生於各國的疆域即可。朱熹《詩集傳序》稱“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注]朱熹:《詩集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頁。,其創作地域爲西周豐、鎬,東周王城,自可不論。今姑以鄭玄《詩譜》爲主,參校諸家注解,略論《詩經》十五《國風》所涉地域,並籍此探討《詩經》創作地域在中國文學版圖展開過程中的地位。
一、《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在十五《國風》中較爲特别,因爲在歷代學者的注釋中,周、召有確切的地域可指稱,周南、召南所指何處則衆説紛紜。鄭玄《詩譜》:“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注]《毛詩正義》,第264頁。據《詩譜》可知周公所封之地在東漢右扶風美陽縣。據《經典釋文》“召,亦地名也,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注]陸德明撰,黄焯斷句:《經典釋文·毛詩音義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5頁。可知,召公采邑召在右扶風雍縣。考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東漢“司隸校尉部”圖,美陽、雍縣俱在岐山之南,屬陽。美陽在雍縣之東[注]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秦、西漢、東漢時期),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版,第42~43頁。,與《公羊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注]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元年》(《十三經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7頁。相合。周、召之地在陝西,可爲確證。而周南、召南似乎只是表明周公、召公所治疆域以南的模糊地名,並非實指。鄭玄《詩譜》認爲:
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録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注]《毛詩正義》,第264頁。
周公、召公分治岐之東西,德化所及的《周南》《召南》究指何所,尚需明辨。朱熹認爲: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文王)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佈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成王誦立,周公相之,製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子也。[注]朱熹:《詩集傳》,第1頁。
由鄭玄、朱熹等儒學大師釋《周南》《召南》可知,他們認爲《周南》《召南》之詩作於周公、召公所在的西周初年,所采南國之詩也是爲了彰顯周公、召公“化自南而北”的政績。
陳致《説“南”——再論〈詩經〉的分類》在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第一版《釋南》、唐蘭《殷虚文字記·釋南》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證明“南”本爲一種竹製樂器:“‘南’字上半從‘繩懸’之形,下半從‘’象竹節,則其本義當爲一種可懸而擊之之竹筒類樂器。因竹多生於南方,故此竹筒類樂器也於南方流行。方位詞之‘南’,蓋因此而産生。《説文》‘南,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其義雖未確,亦未盡失。”[注]陳致:《説“南”——再論〈詩經〉的分類》,臺灣《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998年。有學者據此認爲:“周人在立國之先已與江漢巴蜀之國來往密切,起源於南方的南樂很可能傳至岐周。因此‘化自北而南’之説或出於後儒附會,‘周南’‘召南’爲流行於周、召二公采地的南樂則屬可能。”[注]《兩周詩史》,第23頁。西周末年,《小雅·鼓鐘》“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最早明確提到南樂。《韓詩薛君章句》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注]范曄:《後漢書·陳禪傳》李賢注引,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686頁。可見南樂的地位已經超越諸國風詩。隨着平王東遷,周朝的政治重心、文化重心東移,“二南”由歧南音樂變爲東周畿內音樂。既然“南”是由陝西岐山之周南、召南轉用到今本《詩經》的《周南》《召南》的音樂,則並不能確指其産地爲江、漢之間的南方諸國。現代以來,不少學者認爲《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詩是西周、東周時代長江流域諸小國所作,即産生於今天河南、陝西南部及湖北北部。[注]參見高亨《詩經今注》、余冠英《詩經選》、金啟華《國風今譯》、袁梅《詩經譯注》。而最近的研究,否定了這一種假設。徐公持《論〈二南〉》認爲“《二南》是一種貴族音樂,它的音樂的社會本質與《雅》《頌》相接近,而與《風》距離很遠”[注]徐公持:《論〈二南〉》,《哈爾濱師範學院學報》1963年第4期。,可見《二南》之詩可能不是周所統轄領域外的南方諸國的作品。黄奇逸《〈詩〉〈周南〉、〈召南〉、〈王風〉地望辨》通過對《周南》《召南》中的名物、方言的考證,指出:“《周南》不産生於江漢,而當産生於成周”、《召南》十四首也“斷不會是江、漢之詩”[注]黄奇逸:《〈詩〉〈周南〉、〈召南〉、〈王風〉地望辨》,《文史》,1986年第二十七輯。。翟相君《二南係東周王室詩》以“從《論語》中管窺二南”“從季札觀樂中管窺二南”“從《詩序》中管窺二南”“二南爲東周王室詩的內證”“二南和王風的地域相同”有力地批駁了“二南爲南方詩之説”,翟相君認爲:“《詩序》説的‘言化自北而南也’,其原意是,‘自北而南’地教化南方。换言之,南方是教化的物件,並不是詩的産地;教化者在北方,即詩的産地在北方,所以纔説‘自北而南’。這恰好證明二南爲東周王室之詩。”[注]翟相君:《二南係東周王室詩》,《鄭州大學學報》1985年第3期。
歷代學者多據《周南·漢廣》反復詠嘆“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召南·江有汜》反復申説“江有汜江有渚江有沱”認爲,周南“南到江漢合流即今武漢地帶”,召南“南到武漢以上長江流域的地帶”[注]高亨:《詩三百篇的地域和時代》,《詩經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頁。,並因此得出二《南》有江漢流域詩作的結論。翟相君《〈周南·漢廣〉的地域》認爲:“詩的開頭便説‘南有’,作者顯然是立足於北方。如果作者身在江漢而説‘南有’,指的則是比江漢更遠的南方。據‘南有’二字可知,詩中所説的‘喬木’‘游女’‘江’‘漢’,都是作者立足於北方而説的據此,《漢廣》中雖有‘江’‘漢’,但並不是南方的詩。”[注]翟相君:《〈周南·漢廣〉的地域》,《南陽師專學報》1985年第1期。《詩經》十五國風中常有一國詩歌涉及它國地名的現象,如《邶風·谷風》地屬衛國,第三章卻云“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可見隨着時人地理視野的擴大,每一國風的詩也開始借用它國地理言志抒情。《王風》是東周王畿的詩,地屬今河南洛陽市,不應有江漢流域的詩,《王風·揚之水》借征人“戍申”“戍甫”“戍許”等戍地的變動不居,反映征人怨戰和思家的情緒。據《説文》“汜,水别復入水也”“沱,江别流也”[注]許慎撰,徐鉉校定:《説文解字》,中華書局1963年版,分見第232、224頁。,《召南·江有汜》既反復詠嘆“江有汜,之子歸”“江有渚,之子歸”“江有沱,之子歸”,實是以江水的分流終究又要回歸長江來暗喻“之子”必將離别後又復返於我。揣其用意,與《衛風》用涇、渭作比相同,並不能證明其創作地域在江、漢之間,“我們從多方面考察,認爲二南是東周王室之詩,産生於東周王室洛邑,即今河南省的洛陽市”[注]翟相君:《二南系東周王室詩》,《鄭州大學學報》1985年第3期。,較合實情。
二、《邶風》《鄘風》《衛風》
鄭玄《詩譜》:“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之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並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於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吴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注]《毛詩正義》,第295~296頁。由此段可知,邶、鄘、衛原爲商代王畿,以漢代河內郡爲中心,北達今河北南部,南抵今山東西北部。《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即鄘國。”[注]杜佑:《通典》卷一七八,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946頁。《漢書·地理志上》注解河內郡的“朝歌”云:“紂所都。周武王帝康叔所封,更名衛。”[注]《漢書·地理志上》,第1554頁。《通典》認爲:“古殷朝歌城在今(衛)縣西。”[注]《通典》卷一七八,第946頁。由此可知,邶、鄘、衛三地在故殷王畿爲歷代學者公認。
三、《王風》
鄭玄《詩譜》:“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注]《毛詩正義》,第329~330頁。《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新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內東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注]《史記·周本紀》,第131頁。因此,《王風》十篇應爲周王室東都王畿之內的土風,大部分詩歌作於東周都邑洛陽及其附近。
四、《鄭風》
鄭玄《詩譜》:“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曆、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注]《毛詩正義》,第335~336頁。《漢書·地理志下》云:“鄭國,今河南之新鄭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注]《漢書·地理志下》,第1651頁。清高儕鶴《詩經十五國地域辨》云:“舊屬畿內,後得檜地爲新鄭。”[注]高儕鶴:《詩經十五國地域辨》,《詩經圖譜慧解》,見《清代稿本百種彙刊》,臺灣文海出版社據康熙四十六年手稿本影印1974年版,第43頁。“舊屬畿內”指原在西周王畿,“得檜地”後纔東遷至河南新鄭。可知,《鄭風》二十一篇約作於今天河南中部。
五、《齊風》
鄭玄《詩譜》:“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吕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注]《毛詩正義》,第348頁。《史記》:“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注]《史記·齊太公世家》,第1513頁。朱熹也認爲:“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注]朱熹:《詩集傳》,第58頁。清人高儕鶴、焦循對此無異議。是知,《齊風》十一篇所産地域在今山東中西部。
六、《魏風》
鄭玄《詩譜》:“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注]《毛詩正義》,第356頁。《漢書·地理志下》云:“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按:括弧中的兩句,見王應麟《詩地理考》)”[注]《漢書·地理志下》,第1649頁。蘇氏認爲:“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爲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注]見《詩地理考》,第235頁。朱熹也疑《魏風》爲晉國之詩,但持論不堅:“今案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注]朱熹:《詩集傳》,第63頁。無論屬魏,還是屬晉,實際上只是時間上的判定,其地域實在今山西境內。
七、《唐風》
鄭玄《詩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嶽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注]《毛詩正義》,第360頁。《漢書·地理志下》也認爲:“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注]《漢書·地理志下》,第1648頁。由此可知,《唐風》《魏風》皆在漢代河東郡,今山西境內。
八、《秦風》
鄭玄《詩譜》:“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注]《毛詩正義》,第368頁。可見,秦國由今甘肅東部、陝西西部逐漸擴大至整個陝西。《漢書·地理志》曾論述《秦風》與其地理風俗間的緊密關係:“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於修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注]《漢書·地理志下》,第1644頁。《詩經·秦風》所涉地域不及戰國時地域廣大,高儕鶴以爲“汧渭之間隴西地”[注]高儕鶴:《詩經十五國地域辨》,《詩經圖譜慧解》,第43頁。,較得其實。
九、《陳風》
鄭玄《詩譜》:“陳者,大皡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音孟)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注]《毛詩正義》,第375~376頁。《陳風》多表現陳國地名,《漢書·地理志下》:“《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注]《漢書·地理志下》,第1653頁。揭示出《陳風》與其表現地域間的緊密關係。
十、《檜風》
檜,《左傳》《國語》作“鄶”,《漢書·地理志》作“會”,其實一也。鄭玄《詩譜》:“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注]《毛詩正義》,第381頁。《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鄶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二十二里。”[注]《史記·楚世家》,第1691頁。王應麟認爲:“《史記》注:‘徐廣曰:鄶在密縣。’漢屬河南郡,唐屬鄭州,後屬河南府,今屬鄭州。”[注]《詩地理考》,第248頁。因爲檜國後爲鄭所併,蘇氏認爲:“《檜詩》皆爲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注]《詩地理考》,第249頁。《通典》也認爲:“(鄭州新鄭)有溱、洧二水本鄶國之地。”[注]《通典》卷一七七,第941頁。高儕鶴《詩經十五國地域辨》認爲:“地屬鄭州,詩多鄭作。”[注]高儕鶴:《詩經十五國地域辨》,《詩經圖譜慧解》,第43頁。可爲的論。
十一、《曹風》
鄭玄《詩譜》:“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游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注]《毛詩正義》,第384頁。《郡縣志》認爲:“古曹州,濟陰縣東北四十七里,自曹叔至伯陽凡十八葉。”[注]《詩地理考》,第250頁。王應麟注云:“今興仁府濟陰縣,本漢定陶縣地,唐爲曹州,省定陶入焉。”[注]《詩地理考》,第250頁。
檜、曹皆爲小國,滅亡時間也較早,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删詩,系《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注]《詩地理考》,第250頁。因此,《檜》《曹》兩國風詩所作地域被戰國韓、齊兩國兼併。
十二、《豳風》
鄭玄《詩譜》:“豳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大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後成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大王之所爲。大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别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注]《毛詩正義》,第387頁。前文曾言及《詩經》之“詩”在指代諷諫之詞的意義上産生,應該在《周頌》以後,其出現大約在西周中晚期以後。因此,《豳風》不是公劉、太王時古豳國所作的詩歌。朱熹認爲:“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莅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邰,在今京兆府武功縣。”[注]朱熹:《詩集傳》,第90頁。據朱熹所言,《豳風》有周公所作詩以及後人緬懷周公的詩,其創作地域皆應在西都宗周。但20世紀30年代,徐中舒《豳風説》提出《豳風》爲魯詩的説法。[注]徐中舒:《豳風説》,《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四分,1936年。稍後,徐中舒、常正光《論〈豳風〉應爲魯詩》進一步闡述了這一觀點。[注]徐中舒、常正光:《論〈豳風〉應爲魯詩》,《歷史教學》,1980年第4期。據馬銀琴的詳密考證,《豳風》《七月》《鴟鴞》原是周人祖先居住過的豳地土風,後經周公傳述而得到保存,“由於《豳風》與周公的特殊關係,隨着周公的封魯,《豳風》傳自東方魯國在岐豐周文化接受殷文化的衝擊發生質的轉變時,代表周先祖古老文明的豳風,在文化取向上比較保守的魯國得到了保存《七月》《東山》《破斧》諸詩與厲、宣時代詩歌相似的語言特點則給我們這樣一個啟示,它們是在宣王時被寫定並編入詩文本的。《國語》《史記》都記載了宣王十二年魯武公來朝、宣王立其少子戲一事。宣王時代制禮作樂的背景以及當時魯與周王室的關係證明其時具備魯人進獻《豳風》的條件。”[注]《兩周詩史》,第291頁。馬銀琴的觀點,能夠得到傳世文獻的證明,季札觀樂評論《豳風》即云:“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注]《史記·吴太伯世家》第1452頁。可見,《豳風》確有經周公整理後流傳至魯,後又回流宗周的可能。
《詩經》《周頌》《大雅》《小雅》大半作於兩周王畿之內,《魯頌》作於魯國。《商頌》較爲特殊,它本是殷商文化的遺存,在西周、東周交替之初,得到商人後裔——宋國大夫正考父的整理,最終形成《商頌》十二篇,在宋國內部流傳,齊桓公尊王攘夷、稱霸中原後,《商頌》五篇才納入以《詩》爲名的詩文本,在諸侯各國間流傳。[注]《兩周詩史》第四章第六節《正考父與〈商頌〉》,第295~299頁。綜合上面對十五國風的地域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從創作地域來看,《詩經》所有詩篇皆作於黄河流域中下游,即西起汧渭,東漸於海,北不過恒山,南不過淮河的中原地帶。《周南·漢廣》《召南·江有汜》雖論及漢水、長江,但不能證明其創作於漢水下游、江漢合流之處,綜而言之,實爲東周王城詩人以江、漢爲喻進行的地理想象。
其次,從創作時間來看,《商頌》《豳風》有商代、周代祖先公劉時的土風痕跡,但今所傳諸詩已經過正考父、周公等人的整理、改編,其語言及詩歌形式打上了周詩的特色。今本《詩經》多西周宣王時的作品,周平王即位不久,《詩》正式結集,至春秋中期尚有極少詩篇收入《詩》集,但數量少,不具有代表性。
梁啓超論近代中國地理可以概分爲兩部分:“一曰本部,十八行省是也。二曰屬部,滿洲、蒙古、回部、西藏是也。”[注]《中國地理大勢論》,《飲冰室合集》,第2册第78頁。案之今天中國版圖,新疆、西藏、內蒙、寧夏、青海屬於梁啓超所稱“屬部”,其餘爲梁氏所謂“本部”。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本部確爲華夏文化的主體部分。文明的發生與河流關係緊密,而中國本部地勢被三條河流分割:“中國者,富於河流之名國也。就本部而三分之,復可爲中南北三部。北部者,黄河流域也;中部者,揚子江流域也;南部者,西江流域也。三者之發達,先後不同,而其民族之性質,亦自差異。此亦有原理焉,凡河流之南北向者,則能連寒温熱三帶之地而一貫之,使種種之氣候,種種之物産,種種之人情,互相調和,而利害不至於衝突。”[注]《中國地理大勢論》,《飲冰室合集》,第2册第78頁。梁啓超所説三條河流,今天分别稱爲黄河、長江、珠江,它們在中國歷史上先後起着不同的作用:“自周以前,以黄河流域爲全國之代表。自漢以後,以黄河、揚子江兩流域爲全國之代表。近百年來,以黄河、揚子江、西江三流域爲全國之代表。”[注]《中國地理大勢論》,《飲冰室合集》,第2册第78頁。《詩經》的創作地域正反映出中國文學版圖的早期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