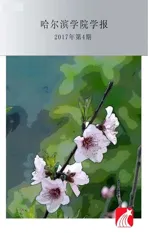驳《单向度的人》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2017-03-10李铖
李 铖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驳《单向度的人》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李 铖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是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尔库塞分别从逻辑、语言两个方面对实证主义进行了批判。大多数学者没有就实证主义理论自身进行探讨,便对马尔库塞的批判采取了肯定态度。文章从实证主义相关理论自身出发,意在表明:马尔库塞所主张的实证主义的形式逻辑与革命性的辩证逻辑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式上其实是殊途同归,而日常语言哲学并不如马尔库塞所言是非批判的。故而,马尔库塞借由逻辑、语言两个方面批判实证主义是无效的。
《单向度的人》;实证主义;逻辑;语言
马尔库塞本人就实证主义提出了自己关于它的相关界定:“自从‘实证主义’一词第一次被使用,它就一直包含着如下意义:(1)人是根据对事实的经验而获得有效性。(2)认知活动以物理科学为确定性和精确性的模型。(3)相信知识要进步必须以此为方向。”[1](P137)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实证主义在《单向度的人》中并不等同于孔德所创立的哲学流派。马尔库塞将自孔德以降的、在哲学倾向上类似于孔德哲学的哲学都视作实证主义哲学,其范围包括早期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哲学、操作主义。马尔库塞分别就逻辑、语言两个方面对实证主义进行了批判。
大多数学者对马尔库塞的批判采取了肯定态度:有的学者就马尔库塞与马克思的关联方面肯定了马尔库塞的批判,其中代表性的文章是吴学琴《挑战单向度的意识形态》;有的学者从理性这一西方哲学核心概念自身发展的角度赞同了马尔库塞的批判,持这个观点的代表俞吾金《理性在现代性现象中的四个向度》;也有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肯定了马尔库塞的批判,这在马举魁、张和平两人合写的《实证主义的现代性迷误》有突出的表现。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学者没有仔细分析实证主义自身的观点,便从其他视角对马尔库塞的批判进行了肯定。本文旨在就马尔库塞所圈定的实证主义具体理论出发,表明马尔库塞在逻辑、语言两方面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是无效的。
一、马尔库塞对实证主义形式逻辑的批判
马尔库塞将实证主义哲学所采用的逻辑视作“肯定的逻辑”,而把与之相反的视为“否定的逻辑”,进而将这两相对立的逻辑思维方式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它们的冲突可以回溯到哲学思想自身的起源,并明显地表现在柏拉图的辩证逻辑同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的形式逻辑的对比中。”[1](P100)
在马尔库塞看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建立在主谓式“S是P”这种判断陈述之上,将逻辑限制在区别真理与谬误方面,力图分析主项(S)与谓项(P)词项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关于判断的形式逻辑。这种“纯形式”的逻辑对内容是不管不顾的,内容在形式逻辑面前,作为“可以替换的记号或符号”“成为同一组织、计算和推论的普遍规则的附属物”。[1](P109)而这种普遍规则将导致“普遍控制”。虽然20世纪的数理逻辑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古典逻辑不同:数理逻辑采用的是逻辑符号形式化的语言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采用的是自然语言,但“同样根本反对辩证逻辑”,视辩证逻辑为“非科学的”。[1](P112)
相比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在他之前的柏拉图所创立的辩证逻辑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柏拉图的辩证逻辑通过对“一与多”“运动与静止”等范畴的考察,揭示了事物之间是存在矛盾的。故而,柏拉图的辩证逻辑不仅强调经验事物肯定的一面,更加强调对于经验事物的否定性。辩证逻辑在马尔库塞看来具有规范作用,倘若发现在眼下状况不真实的东西、与现存的情况相矛盾的东西,就否认它的真实性。[1](P106)当辩证逻辑的否定性起着规范作用时,还引入了应当,便构成了“是”与“应当”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辩证过程就是由“是”与“应当”的紧张关系导致的,不断从肯定走向否定再到肯定的历史过程。
由马尔库塞对“肯定的逻辑”形式逻辑和“否定的逻辑”辩证逻辑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是真理(肯定性),而辩证逻辑的研究对象是否定性(无);形式逻辑的研究目的是为科学寻找基础(科学性质的目的,求真),辩证逻辑的研究目的是批判社会,使社会走向应然状态(伦理学性质的目的,求善);形式逻辑的研究方式是纯粹形式的、静态的,辩证逻辑的研究方式是非形式的、历史的。
二、马尔库塞对日常语言哲学的批判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花了大篇幅批判了日常语言哲学。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哲学认为,哲学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人们对日常语言的错误使用。所以,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治疗日常语言使用的错误,消解由日常语言错误使用带来的矛盾与冲突。但这些在马尔库塞看来,日常语言哲学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种哲学“缩小哲学范围,贬低哲学真理……宣称哲学的节制和无效。它不触及已确立的现实,它憎恶超越”。[1](P138)马尔库塞分别从三个角度对其进行了批判:
1.日常语言哲学是单向度的
马尔库塞认为,日常语言哲学对语言进行分析,力图将矛盾、冲突这些概念都转化为日常语言。通过这种转化,语言中对于社会批判否定的、采取批判的因素被消解掉了,进而可以化解现实社会的矛盾与冲突。这样的哲学是一种肯定性质的哲学,不具有批判的哲学,为资本主义现存社会辩护的哲学。
2.日常语言哲学进行的语言分析是虚假具体性的分析
马尔库塞认为,日常语言哲学对语言进行的研究看似具体,但这种具体实则是一种表面化的具体,造成了大量虚假问题的产生:“操作性或行为性的转译把‘自由’‘政府’‘英格兰’之类术语与‘扫帚’和‘菠萝’同化起来,把前者的现实与后者的现实同化起来”。[1](P145)语言的意义不能离开说话者与说话者所处的环境空谈语言。真正具体化的语言分析要把握具体东西的统一性,从表面现象看到背后的本质,是一个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的过程。而日常语言哲学的分析只停留在现象的表面,对表面的现象进行规范以符合科学设立的标准,丧失了对具体现象的全面了解。
3.日常语言哲学使得形而上学神秘化
日常语言哲学致力于让语言符合日常语言的用法,清除日常语言在用法上的错误,使得语言更加符合科学性。但具有批判特性的形而上学语言在很多时候不采用日常语言用法,而自己独创运用一种新的用法。故而,日常语言哲学把“显露超越性的术语”“模糊观念”“形而上学的全称命题及类似的东西”[1](P152)都当做神秘化的、非科学的东西拒斥掉了,进而一个社会的话语领域只有肯定因素,而失去了批判、超越的因素。
三、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殊途同归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马尔库塞分别就实证主义的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式上进行了区分,并由此得出了实证主义所奉行的形式逻辑造成了单向度的思想。但这样的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两者在这三个方面殊途同归。
1.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和辩证逻辑的研究对象有着共通之处
对命题成真的研究虽然是形式逻辑研究的核心部分,但是形式逻辑并不是按照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忽视对于否定性的研究。古典形式逻辑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在有关命题逻辑的讨论中就涉及到了全称否定命题与特称否定命题的讨论。此外,亚里士多德在他整个逻辑学的核心部分词项逻辑三段论中谈及了三段论的两条思想原则:大小前提都为否定命题,得不出结论;大小前提中只要有一个前提为否定命题,则结论为否定命题。现代数理逻辑(按照马尔库塞的说法,现代数理逻辑与古典形式逻辑的立场是一致的,属于广义的形式逻辑)谈论否定的经典例子是罗素悖论。罗素悖论的缘起就是对“0”这个数采取了一个否定性集合的定义:“0”是一个不属于自身的集合。根据罗素的分析,这种否定自身的定义导致悖论,故需要建立类型论予以克服。总而言之,否定性在形式逻辑中与肯定性具有同等的位置,对于否定性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肯定性的探讨。
与形式逻辑相对应的辩证逻辑在对待研究对象方面同样也不是将否定性作为其最高的对象借以排斥对肯定性的研究。相反,肯定性原则的确立是进行否定的基础。一种没有建构的解构是全然无效的。马尔库塞所赞扬柏拉图的辩证逻辑显然不是为了否定而否定的。柏拉图进行否定的前提是一个肯定性的前提,即理念。离开了理念,柏拉图的否定无从谈起,也没有归所。另一个是马克思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强调否定,强调对事物进行批判。但是他的否定、他的批判建立在物质生产、实践这样肯定性的基础之上,建立在达成共产主义这样肯定性的目标之上。离开了物质生产、实践这样肯定性基础,离开了共产主义这样肯定性目标,马克思的否定、批判无从谈起。总之,辩证逻辑强调否定,但是这种否定必须以肯定为基础,否定只有从肯定原则出发才能成立。
根据以上分析,形式逻辑是从否定性问题出发来确立肯定原则的,辩证逻辑是从肯定原则出发来进行否定的。两者虽然路径不同,但都强调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
2.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研究目的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
马尔库塞认为,形式逻辑只按照经验实在来描绘真理,而不构成对经验实在的批判。故而形式逻辑仅仅是一种围绕经验实在成真条件的研究,一种科学基础的研究。这种围绕科学基础的研究无法构成对经验实在的批判,不考虑应然状态,达不到伦理学求善的目的。很显然,马尔库塞没有考虑到现代逻辑的进展,可能世界理论的建立、反事实条件句的研究都是围绕一种不同于现实经验实在的研究。模态逻辑、道义逻辑等非经典逻辑的出现意旨建立一种元伦理学,研究必然、可能等并非描述现实经验实在的词汇,为伦理学清晰的语言表达奠定了现代逻辑基础。
按照马尔库塞的看法,辩证逻辑探讨否定(无)这样的对象,进而辩证逻辑的主要目的是研究社会的应然状态,而不把重心放在科学基础之类的研究上。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如下两个关于否定性(无)的典型讨论,我们会发现它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科学的基础,而非社会的应然状态。
第一个例子是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对于“无”的描述。在黑格尔看来,“纯有是纯粹的抽象,因此是绝对的否定。这种否定,直接地说来,也就是无。”[2](P192)单独拿出这句话令人费解:有怎么是无,肯定怎么是一种绝对的否定?黑格尔之所以要把有看做无,是因为他有着建立一种哲学体系的需要。把有看做无是为了他建立体系的目的而服务的。只要我们把这样一句费解的话放置到整个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去理解,我们会发现这种费解就会立马消失。黑格尔认为,哲学是科学之科学,是一切具体科学的基础,其核心是研究绝对精神。他把关于自然的科学(自然哲学)以及关于社会历史的科学(精神哲学)都视为绝对精神辩证发展的应用逻辑学阶段,最终促成绝对精神的实现。黑格尔探讨“无”、建立辩证逻辑的目的并不是批判现实社会,而是为科学知识找到自身的基础。
另一个例子是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中对于“无”的讨论。在《形而上学是什么》的开篇,海德格尔提出了他要进行形而上学追问的缘由:“我们的此在,在研究者、教师与学生共同体中的此在,是由科学来规定的。科学已然成了我们的激情,就此来讲,我们的此在的基础发生了什么本质性的事情呢?
诸科学的领域各有千秋。诸科学处理对象的方式亦是大相径庭的。在今天,各种学科的分崩离析的多样性只还通过大学和系科的技术组织结合在一起,并且通过各个专业领域的实用目的而保持着某种意义。相反,诸科学的根基在其本质基础上己经衰亡了。[3](P120)
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们对对象的研究往往采用科学的方式。但科学的根基在本质基础上出现了问题。只有解决科学的根基问题,才能有效地采用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这种科学的基础显然不能在科学内部寻找,因为“从诸科学出发来看,没有一个领域对另一个领域具有优先地位……没有一种对对象的处理方式高于另一种方式。”[3](P120)每一类科学都研究不同的存在者,没有哪一类存在者比其他存在者更高级,每类存在者都具有同等地位。不能将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视作全部科学的基础,这样做显然是不成功的。但从形而上学中为科学找本质基础,却不会找到这样的麻烦,因为形而上学“是一种超出存在者之外的追问,以求回过头来获得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以及存在者整体的理解”。[3](P137)要体现这种超越特征,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就落在了“无”上。
综上,我们可以了解到: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都是以科学基础为自身的研究目的。形式逻辑也不是按照马尔库塞所论述的那样只研究科学基础而对批判社会、社会应然状态的研究不管不顾,批判社会、社会应然状态问题可以归为逻辑问题,可以在科学的基础上加以研究。
3.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共同性
马尔库塞关于实证主义所秉持的形式逻辑是研究纯粹形式、非历史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以孔德的第一代实证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为例:孔德在论述自身实证主义基本观点之前,为实证主义做了一个历史角度的说明。他认为,人类历史可按人类思维方式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神话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具体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很显然,孔德关于人类历史发展三阶段的理论表明了社会是进步的,以一种历史眼光对实证主义进行考察,具有技术向度和历史向度双向度而非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对应了具体的社会形态,不局限于形式的研究,而放眼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研究,而非马尔库塞所表明的纯形式的研究。
第二个例子是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原则虽然是形式化的、非内容的,但可证实性原则的提出是面向具体的科学实验的。如果没有科学实验的可重复性作为可证实性原则基础的话,可证实性原则是无法成立的。可证实性这形式化的原则建立在具体的科学实验可重复性之上,并从科学实验出发确立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线。此外,可证实性原则存在经验的可证实性以及原则的可证实性,其中原则的可证实性就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向度。原则的可证实性是说事件按照现在的条件不能证实,只是具有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能让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将不能证实的东西变为可以证实。石里克在《意义与证实》一文中提到了一个关于月球背面的例子。[4](P53)按照石里克时代的科学水平,人们还不能对月球背面具体什么样子进行经验证实,只能在理论上通过空间、物质等概念进行推断,是一种在理论上的可证实性。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能够利用新的科学探测手段来对月球背面进行经验证实。可证实性这种从原则、理论上的可能性到现实的可能性体现了一种从可能到现实的历史维度,另一方面还体现了从形式到内容的深化。很显然,可证实性这一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不是静态的、纯粹形式的,而是历史的,抽象形式与具体内容相结合的原则。
马尔库塞将辩证逻辑视为一种历史的、考虑具体内容的逻辑有一定道理,但这不足以刻画辩证逻辑的全部。我们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例子。很显然,马克思唯物史观依凭的逻辑着眼于人类历史发展是一种动态的,考虑具体内容(历史事件、历史背景)。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原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一种规范的、非历史的、去除内容的原则。我们不能把这两条原则按历史的角度、按具体的内容去进行认识与理解,因为:如果这两条原则只适用一个时期、一定范围的社会,那么这两条原则就丧失了对整个社会历史的真理作用,最终导致历史相对主义。所以,即便是强调历史、注重内容的辩证逻辑也有规范的(静态的)、形式的一面。
通过对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研究方式的梳理,我们可以了解到: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都有强调历史、注重内容的一面,同时也有着重规范、突出形式的一面。
综上,我们可以了解到,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式三方面共性大于个性,两类逻辑看似千差万别,实则殊途同归。故而马尔库塞在逻辑上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是没有效力的。
四、日常语言哲学具有批判意义
马尔库塞对日常语言哲学的界定是不合理的,因为日常语言哲学也有鲜明的批判性,具有革命性的因素。
1.将日常语言哲学视为单向度是不正确的
日常语言哲学同样也具有批判的一面。日常语言哲学看到传统哲学的弊端:传统哲学在表面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哲学流派,各自流派拥有自身的立场,呈现出一种相互批判、自由、继而具有超越特性的局面。但这些哲学流派在对哲学问题的思考方式上都有着惊人的一致,它们将哲学问题的解决固定在一种模式之上,这种模式就是古典逻辑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总是问如下问题“物质是什么”“时间是什么”。围绕着这些问题,不同的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很少有哲学家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批判。日常语言哲学就从日常语言的角度对这种思考方式进行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对语言意义的阐发并不局限于指称这一种思维方式,[5](P1)而是在于我们对语言的使用。
表面上传统哲学流派众多,发出多种声音,呈现多向度,但是如上述所言,这些自由和批判都是为了解决“是什么”(寻求一个确定的本质,尤其是善的本质)服务的。这个“是什么”的答案本质对社会现象的承认有决定作用,凡是不符合这一本质的都必须消灭掉,这其实是一种寻求本质带来的暴力,非本质的声音就消弭了。“是什么”这样的指称认识方式、寻求本质的方案就不具有统治地位,不会对其他认识方式产生消灭作用,完成了对其他认识方式的承认,这样一来,非本质的看法和本质有着并驾齐驱的、等同性地位。允许了不同的声音,社会便具有多样性,有着多向度选择的可能。
2.日常语言哲学将形而上学神秘化的做法并不消解形而上学的地位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谈到“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要保持沉默”。[6]“不可说的东西”是指形而上学领域。这些领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派,这些流派各自有各自的立场,都希望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具有权威性。维特根斯坦认为形而上学这些领域是最重要的领域。如果进行言说就会选择站在一个立场反对其他立场,力图消解其他立场,这恰恰损害了形而上学的批判维度,造成对这些领域的戕害。维特根斯坦等人将形而上学神秘化以拒斥形而上学不是为了消灭形而上学,而是为了保护形而上学的发展。
五、结论
根据上面的分析,实证主义所秉持的形式逻辑与马尔库塞所声称的、具有批判意义的辩证逻辑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式上是殊途同归的。日常语言哲学并不是按照马尔库塞所言完全没有批判维度,而是具有重要的革命意义,这种革命意义主要表现为对传统哲学单一思考方式的去除。故而,马尔库塞在逻辑、语言两方面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是无效的。
[1]〔美〕马尔库塞.刘继.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2]〔德〕黑格尔.贺麟.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德〕海德格尔.孙周兴.路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洪谦.逻辑经验主义(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奥〕维特根斯坦.韩林合.哲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6]〔奥〕维特根斯坦.韩林合.逻辑哲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责任编辑:谷晓红
The Criticism Against Positivism in “One Dimensional Man”
LI Che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The criticism against positivism makes key part in Marcuse’s “The One dimensional Man”,which is made from the aspects of logics and language. Many scholars approve Marcuse’s criticism without considering positivism. Based on the theories related to positivism,it aims to argue that there is similarity between Marcuse’s formal logic and dialectical logic in terms of research subjects,goals and approaches. Furthermore,philosophy of language (on everyday language) is critical rather not critical as what Marcuse claims. Therefore,Marcuse’s criticism is invalid.
“One Dimensional Man”;positivism;logic;language
2016-09-02
李 铖(1993-),男,湖南耒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研究。
1004—5856(2017)04—0017—05
B5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4.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