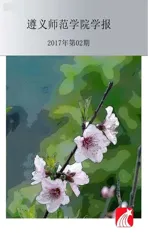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贵州境内民族政策实践研究
2017-01-27党会先汪学平
党会先,汪学平
(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贵州遵义563006)
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贵州境内民族政策实践研究
党会先,汪学平
(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贵州遵义563006)
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12月长征转兵至贵州境内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作家“民族自决权”理论为指导,红军总政治部在湘桂境《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的基础上,颁布了《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在贵州境内模范执行党的各项民族基本政策,为红军顺利通过贵州奠定了坚实的民族政治关系基础。
长征;中央红军;贵州;民族政策
中国工农红军自1934年10月10日从江西苏维埃根据地出发进行战略转移以来,经过一路艰苦的浴血奋战,至12月初翻越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开始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这样,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就成为中央红军一个现实和迫切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作家的民族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工农红军制定了以《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为代表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并在1934年12月转兵至贵州境内后,模范执行了这些民族基本政策。
一、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理论渊源
诚如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中所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1]P443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理论依据,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的民族观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和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实践化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观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
1.民族问题的本质是阶级问题
民族问题,是指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在社会生活、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和阶段产生的各种矛盾。在分析民族问题时,列宁把世界上的民族区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别,即“有权利和特权的民族”和“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2]P46。关于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马克思在标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的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人与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3]P47,要求“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3]P46,同时还“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4]P409。在1917年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早期共产党人就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阶级分析观点,承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民族关系问题的本质和根源,如李大钊哀叹:“凡外竞无力之民族,其内争必烈,卒至亡国而后已。”[5]P245
2.民族自决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途径
17-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从古典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出发,阐述“天赋人权”和国家起源理论,逐渐衍生出“民族自决”思想,如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强调“独立自主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的荣誉”。[6]P339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马克思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视为国际无产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其在1865年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声援波兰时号召“必须在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基础上”运用社会主义道路解放波兰[7]P164,这是马克思首次提出“民族自决权”原则。以此为基础,列宁对民族自决权进行了系统、深入地阐述,指出“无产阶级如果不坚持民族自决权,它无论在完成本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方面或帮助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任务都是不能完成的”[8]P262,民族自决思想自此成为指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武器。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包括“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9]P115-116,党的纲领性文件第一次涉及到民族问题。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明确提出“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发生关系由该地民族自决”[9]P141-142,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自决”的初步表述。1931年11月7日,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蒙、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者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独立的自治区域”[10]P775,民族“自决权”最终以宪法的形式被确定并延伸至民族“自治”层面,至此,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理论原则和框架构建成型。
二、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贵州境内民族政策的实践
1934年11月底,湘江战役鏖战之时,中央红军已经逐步进入湘桂界瑶族、苗族和壮族聚集区域,面对复杂的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日益重视此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民族关系问题。毛泽东对陈昌奉等工作人员进行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教育,反复要求严格遵守少数民族区域群众纪律,不能以“打土豪”名义动用苗族物品。[11]P23-3011月29日,红军政治部颁布《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要求“汉族与瑶民的民族平等,给瑶民的彻底自决权”、“对于他们的统治方式、思想习惯及宗教仪式,应表示尊重”。[12]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决定“西进”贵州,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命运转折的伟大序幕。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部,境内山峦起伏,地貌类型复杂,历史上一直是民族交汇的大走廊和民族集结地,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等17个少数民族世居贵州[13]P1,此基本省情使贵州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理想实践区域。
1.民族政策的切入点是民族救济
马克思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14]P24因为自然地理因素、军阀混战、社会历史等原因,贵州是民国时期特别贫瘠的地区,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贵州千万群众“生计几绝”、“老弱转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15]P93。鉴于此,中央红军把民族救济作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切入点。1935年12月14日,中央红军解放占领黎平后,在荷花塘小学门口召开群众大会,将打朱信昌、张风占等20多位地主土豪所获的粮食、油盐、衣被、布匹和日常用具等按照贫困程度以甲、乙、丙三个标准分配给群众。在黎平的西侗寨,红军把地主家的东西分给贫农,如吴冬庆得40斤谷子80斤大米。12月下旬,从黎平出发至黄平行至剑河附近村寨时,毛泽东看到一老妇因冻饿倒卧路旁,把身上的毛衣以及被单1条、干粮袋2条一并赠送给她[16]P441。在进驻剑河县城期间,中央红军领导民族群众没收以蒋玉鹏、丁培生为代表的三四十户地主财产,并在伪县政府门前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分配胜利果实给现场300多群众,涉及谷子两万一千多斤,被盖五十多床,棉布80多匹以及其它无法统计之物[17]P15,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济民的革命方式和党的民族政策实现有机对接。
2.民族平等和团结的实践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乃至最后的民族联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一个基本政策理念。中央红军1934年12月进入贵州后,根据长征沿途各族群众的实际情况,努力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和团结政策。12月14日,中央红军占领黔东南重镇黎平,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期间,红军总政治部再次通告全军:在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时,要绝对遵守纪律,绝对尊重少数民族群众,搞好民族关系[17]P1。12月15日,中央红军在锦屏县启蒙地区暂驻,在临街房屋两根银杉柱上刷上标语:“实行民族平等!实行民族自决!苗人汉人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平等权利!”[17]P11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和纪律。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正值秋冬季物资补给困难时期,但是红军坚持公平交易不欺行霸市,不劫掠少数民族群众的粮食、猪牛等财物,向导带路不打不骂反而给吃给报酬。剑河十字街张钟国的粉馆每个红军吃粉付钱分文不少,一天共卖30多块大洋,比平时多了20多倍[17]P12-14。黎平高场侗族群众杨光华、杨光勤和吴明胜的父亲做向导给红军带路到八寿,返程时一个女红军发给他们每人大米一斤半、大洋一元和路条一张[17]P8。在黎平少寨,红军一位刘姓排长不慎造成火灾导致侗族群众30多户房屋烧毁,红军立即根据情况进行赔偿,贫农左欧桂桃家得到猪肉五六十斤、猪油二三十斤、衣服数件、青蓝布各一段、大洋若干。[17]P7
3.民族自决和解放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解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问题的基本途径是民族自决。中央红军12月中旬占领黎平后,以召开群众会议和标语的形式宣传党的革命纲领,如黎平城内标语有“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打倒法西斯蒂”、“打富济贫”、“打倒土豪劣绅”、“红军是工农的队伍”[17]P4,在黎平高场,红军战士主动进山寻找恐惧的民族群众,表明工农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打富济贫的,将来还要给穷人分土地”[17]P4,驳斥地主和乡保长的造谣破坏。中央红军在锦屏县启蒙地区暂驻期间,号召民族群众“武装起来,暴动起来,实行土地革命”。[17]P11在剑河县城,红军开展广泛宣传,街头巷尾写满“苗家客家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倒压迫苗民的王家烈!”“组织自己的阶级工会!”“打土豪分田地”这样的标语[17]P13。在台拱平兆苗族寨子,红军在大地主熊世勋家的砖墙上留下两条珍贵标语,其一是:“苗人们不穿破衣服,到财主家穿新衣去。”,其二是:“打倒压迫苗民的国民党军阀王家烈。”
1935年12月24日,针对个别违反群众纪律的特殊现象,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明确传达和执行本部对苗民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加强纪律检查队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犯群众脱离群众行为”[18]P220-221。1935年1月红军进入黔北重镇遵义后,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再次重申“对于苗瑶等少数民族,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与汉族工农同等待遇,反对汉族的地主财富者的压迫。”[19]P1。由此,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从长征出发时处于单纯理论认识阶段,经历黔东南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初步运用阶段,终于在黔北地区再次回到理性认识阶段,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行了初步的结合。
三、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贵州境内民族政策实践的影响
从1935年12月12日自黔东南入境贵州,至1935年4月23日转战至云南,中央红军频繁接触贵州境内各少数民族,其制定和实践的民族政策为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复杂的少数民族区域,为此后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和中国共产党自身政治理念的社会化都产生了深远而显著的影响。
1.确保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区域
鉴于历史上汉族主导的中央政权大汉族主义思想以及各种压迫剥削政策,造成国内各民族之间严重的隔阂和不平等,红军长征过程中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反动势力对红军极尽所能地进行诬蔑,企图挑起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央红军的仇视。如贵州台江县番召乡敌伪乡长恐吓当地民族群众说:“哪家藏了红军,就把他家斩尽杀绝,房子烧光。”[19]P19台拱苗族贫农廖树清听到国民党说“共产党共产共妻”[19]P22,施秉伪县长金某正说:“共产党专门杀人放火。”[19]P27以至于少数民族群众一听说红军来了,就藏匿财物,并一窝蜂地往山里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红军在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理论的指导下,科学制定和模范执行民族政策,取得了贵州少数民族群众的认可和支持,为中央红军提供住宿、当向导、补给后勤物资、伤病员养护等服务,为红军顺利通过这些地区创造有利条件。
2.为以后制定成熟的民族政策提供经验借鉴
作为联共(布)指导下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1943年5月15日决定解散前,其政治组织路线深受苏联主导下的共产国际的控制和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也概莫能外。客观地说,虽然列宁承认民族自决权是为了各民族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实现民族联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民族自决权容易给人造成制造民族分裂的歪曲认知,而这与我们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相违背。毛泽东在1919年7月14日的《湘江评论》痛斥一战结束后西方国家所倡导的“民族自决权”时说:“好个民族自决!我以为直是不要脸。”[34]P316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在摆脱左倾教条主义束缚的情况下,把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实现创造性地结合,党的民族政策初步形成。此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核心理念为“民族自决”,但是随着伪“满洲国”、“华北自治运动”、伪“蒙古军政府”、伪“蒙疆联合会”等“民族自决”异化现象的产生,党的民族政策核心理念由“民族自决”转变为“民族区域自治”就成为现实的选择,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综合我国民族状况和基本国情的产物。
3.党的政治理念社会化得以初步实现
中国共产党要想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核心,获得民众的了解和支持,在革命过程中,首先需要把自己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传递给人民群众并使之成为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这个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的社会化过程。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这个“武装的政治集团”一方面行军打仗以求群体生存、政权建设和战略转移目标的实现,一方面通过群众大会、走访座谈、标语传单等各种手段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党的政治理念、价值取向和政治习惯。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模范执行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的结果是贵州沿途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央红军的高度信任和支持,对中国共产党的北上抗日和政治理念的了解和支持,少数民族群众踊跃参加红军队伍走上革命道路,如中央红军在遵义期间,“十二天中确有四五千人加入赤军”[21]P61,或者少数民族群众在当地建立革命武装和自治政权,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化得以初步实现。
[1]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8]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1]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
[12]蒋文龙.一份我党早期民族政策的重要文献[J].文史博览,2006,(11):57.
[13]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上)[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5]谢本书.西南军阀史(第1卷)[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7]刘绍励,刘传林.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调查(第二集)[Z].贵阳:贵州省民族研究所,1965.
[18]贵州省革命文物调查征集办公室,贵州省历史文物调查征集办公室.黔山红迹——红军在贵州的革命活动[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19]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红军长征过云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316
[2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陈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魏登云)
On National Policy of Central Red Army in Guizhou during the Long March
DANG Hui-Xian,WANG Xue-ping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Zunyi Normal College,Zunyi 563002,China)
In December of 1934,guided by“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in Marxism,Chinese Red Army issued“A Decree on Strengthening Discipline ab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Miao Nationality and Red Army”which was predicated on“The Slogans for Miao and Yao Minority Group”addressed by General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the Red Army.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policies in Guizhou laid a solid national and poli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Red Army to cross Guizhou Province populated by minority groups.
Long March;the Central Red Army;Guizhou;National Policy
K263
A
1009-3583(2017)-0025-04
2016-12-20
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遵义师范学院红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JD201417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遵义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支持项目;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2015年项目(15KRIZY10)
党会先,女,河南洛阳人,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黔北地方史。汪学平,男,河南洛阳人,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共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