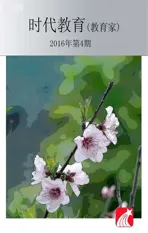文礼学子:在混沌中成长
2016-09-21杨军张艺芳
本刊记者_杨军 张艺芳
文礼学子:在混沌中成长
本刊记者_杨军 张艺芳

1995年,新儒家最后一位大师牟宗三先生去世,余英时先生写文纪念,讲到一段轶事。说牟先生上大学二年级时,选修胡适先生的《中国中古思想史》,最后成绩80分,胡适当时在日记中有一批注:颇能想过一番,但甚迂。
和文礼学子聊天,这句话时常浮现脑海。但是得反过来用。正如余英时写道:“这时牟先生似乎还没遇见熊十力先生,但可看出他对中国思想传统的根本态度已与‘五四’以来的潮流格格不入,这大概是胡先生‘迂’之一字的根据。”和胡适一样,现在社会谈到读经,脑中浮现的还是这个“迂”字。
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这些读经的孩子,或许以后工作面面俱到,每一样都能做到100%,但绝不会有创造力。读经真的是这样吗?
且不妨听听孩子怎么说。
以传新儒家为志业
牟宗三先生80岁时,出版了一本《五十自述》,回顾求学历程,他写道:
生命原是混沌的。只是每一人冲破其混沌,透露其灵光,表露其性情,各有其特殊的途径与形态。这在当时是不自觉的。惟不自觉,乃见真情,事后反省,有足述焉。

很多年后,当18岁的黄雨林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心中一时明朗,隐约中明白了人生方向。那时2008年,黄雨林刚从山东赵升君的读经学堂退学回家。再往前一年半,他从一所重点高中特快班辍学。家庭变故,学业厌倦,都使他对人生感到迷茫。
即使在读经学堂,这些问题依然无法消解。“没读书之前是糊里糊涂过的,读了之后你发现圣人是那样讲的,社会却是这样的,就更加痛苦,生出巨大的厌离之情。”他开始问自己,为什么要学这个。一开始,或许受父亲读经学堂的影响,但现在他困惑了。
碰巧这个时刻,他读到了牟先生文集。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那套书是谁寄给他的。“哲学家思辨的轻灵的美”一直吸引他读下去。他感同身受,仿佛窥见了自我。尤其是牟先生在文章里不断引用经典,让他对山东读书的经历渐渐得到印证,同时和生活印证。
“现在回头反省,2008年能够挽救我的,一个是牟先生思想的高度,一个就是妹妹出生,给我的人情上的温暖,新生的希望。”黄雨林对记者说。在这之后,他决定重回学堂,跟随赵老师去了遂昌。2009年,一次偶然,他听说王财贵教授正在规划文礼书院。书院设想听完,他知道,那就是他将要去的地方。虽然书院还不知道哪里,“但我知道自己这一生的使命就是要传新儒家的志业,完成传统文化复兴的责任。”从此再没变过。
立志难,读书更难。从2013年来书院,黄雨林不觉已25岁,成了书院中最大的“孩子”,平时学弟都管他叫大师兄。如果严格按照文礼书院规划,25岁的年纪,已开始进入游学阶段,各处拜访名师,术业有专攻了。但现在,黄雨林才开始打基础。读经,解经,读经,解经。对这些课业,他有时也不免心生气馁,觉得快要忘记自己的志向了。但正是这种锻炼,逐渐磨练了他的性子。“我原来性格孤僻、偏激,后来慢慢和先生交流,就形成了一种安静的方法。原来先生不动,坐在那里就是我们的榜样。”
对后来的学弟学妹,他成了兄长一样的人物。有时,他甚至还会在他们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看见他们重复自己之前同样的错误。换了之前,他可能会急躁,但现在他开始放心。“就好像你种花,洒点水,施点肥,花不了多长时间,但很长时间你还是等他们自己慢慢成长。”说这句话,更像是对自己说。他引用《孟子》的话: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
实则,类似的话记者在书院至少听到过三个版本。一是带班的生活老师陈桂林,因为大学时机缘巧合接触书院冬令营,参加了师陪班,毕业不久就直接到书院做助教。几乎和黄雨林一般大。她还记得第一年来,经常和孩子发生摩擦。后来发现,其实自己太急躁了。先生的心法,看自己。而在18岁的侯信佑那里,读经道路几度波折,但王财贵教授也总对她妈妈说:等一等,磨一磨。
漫长的读经解经,让黄雨林变得持重笃定。他不再担心时光荏苒,“像我这样,至少要到四五十岁才能成才吧。”他笑笑对记者说。他常常用希腊神话皮克马里翁的故事比喻自己的修学道路,理想就是求自己,不断地打磨自己。年龄越大,学问越长,他越领悟到“终日乾乾,夕惕若”的滋味。而一旦有所进步,则真是“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求经之反复
和黄雨林一样,很多读经的同学来书院之前都曾有过困惑。这次采访的孩子,年龄大如黄雨林的还有班长王泰恒(23岁),年龄一般的16-18岁,最小的13岁。年龄越往上走,读经的历程越波折。
波折,一方面是迫于外界压力(如社会舆论,家庭反对),另一方面也或是到了青春期,一个身体和思想混沌的孩子,自然的反应。
民国时期,张爱玲有句名言,出名要趁早。在这个世纪初被反复引用。如从新概念作文大赛走出的一批少年作家,可谓典型代表。但近年来,随着他们成家成熟,争议也越大。如郭敬明《小时代》系列折射的拜金风潮,或众多新概念作文昭示的“无因的反叛”,人们发现,这世界早已丧失了某种单纯的美好。

尤其让人痛心的,还有近年来抑郁症自杀的数字不断增多。今年春节后不久,两位青年学者接连自杀。尤其后者,还是一位18岁的高中生。除了病理讨论,人们似乎无可奈何。但在教育上,我们应有充足的理由追问,这一切是如何造成的?学问何时与抑郁、自杀挂上了等号?记者也把这个问题带到了文礼书院。
实际上,我们在上文写到的黄雨林,如果没进入文礼书院,记者担心,他可能是最易得抑郁症的一个人。但他走出来了。采访快结束时,记者问他:现在有没有关注过社会上对新儒家的争论?他答,没想过。他觉得,目前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赶紧把做学问的进路建立起来,每个概念搞清楚,打好基础。有段时间,他跟先生抱怨说,读牟先生的书好像逛花园,完全没方向。王教授就让他先放下,继续老实解经。
在书院,除了解经之外的读书都必须经过先生同意。解经是日常最重要的功课。书院规划虽曰“博览群书”,但打好经学基础永远是第一位。
后来,记者也曾就读书的一些困惑请教王教授。先生给出的一个总原则是量力而行(力便是理解力,也是行有余力,也是学习之习)。基础不到,非礼勿动。在这里,黄雨林后来的体会是:做学问首先是单纯的相信。
在解经过程中,他有时也对先贤的注解有所疑惑,但很快放下。“根基不稳,你遇到争论却没有一个分辨是非的能力,便容易误入歧途。这或许就是孔子说的‘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吧。”黄雨林对记者说。单纯的相信,就是先求自己,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有同样感受还包括王泰恒和侯信佑。
王泰恒是书院第二大的学生,来自遂昌王财贵读经学校,和黄雨林同学。2012年从学堂结业后,19岁,也曾迷茫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定向。尝试过找工作,做夏令营,考大学,甚至在饭店当服务生,最后再读经典,来了书院。
来书院的孩子以惯例都会由王教授取字。王泰恒取字泰恒,对这个名字,开始或许是先生一种期许。两年学习下来,他感受到这个名字的重量。安泰,恒久,《论语》有“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有“士无恒产而有恒心”。和先生、同学交流越多,他越感到踏实。问到以后做什么,他不再如以前那样轻浮。“人不能决定自己的际遇,只能决定他的能力和德行。”对新儒家的志业,他信心笃定。
“道,其实既抽象,又可以很具象。书院给了我们一个最大的意义是:壁立千仞,能者从之。先生立定在这里,给我们立定了这个东西。每人根器不同,但只要开始去做了,有一天就会内化为自己。”王泰恒说道。
王泰恒健谈,思维敏捷,对记者提出的问题总是反复思考。说到后来,甚至还反问了记者一个问题:我其实是一个不太会问问题的人。所以很想请教你们问一系列问题,是怎么问出来的?是不是前期要很长的准备,或者有一个连贯的东西?当记者说到“同体之悲”时,他欣然一笑。

要在这里待一辈子
采访三天,侯信佑可能是书院里令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每次吃饭,她总是最快的,吃完就在屋外的小河边看书。手里总拿着一本《四书章句》。饭后散步,先生左右总离不了她问学的身影。实际上,在来文礼采访前,记者对她就有所耳闻,源于微信公众号热传的一篇作文《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她在文中说:这篇文章写给自己,已立志的自己。那时她正好15岁。
后来再提这篇作文,她就笑笑说:“其实我哪里立志了啊!如果已经立志,可能第三年也不会那么痛苦了吧。”我们这才知道她这三年的变化。
原来两年半前,母亲执意将她送入文礼书院,她还很不理解(详见对侯信佑母亲净老师专访)。总觉得“这里同学这么多读书时间比我长,比我优秀”,还想回学堂背书。断断续续郁闷一年。“那段时间做什么都没动力”,一直想着转学。直到后来听先生讲《颜回的生命境界》,她突然警醒,原来自己还一直是向外求。

也是那时,她体悟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的真义。“如果你的心不安定,那到哪里都不会安定。”16岁的侯信佑告诫自己。她记得台湾的张丽华老师过来,有次对她说:你的桌面这么乱(她的习惯总是把桌上的书磊得老高),心怎么会安。一句点醒了她。她说,张老师的生命有很亲的一面。“第一次见面,她甚至没问我名字,更没问读经多久之类,就问我看没看过牟先生的书,唐(君毅)先生的书。”一本《生命与学问》,一本《青年与学问》。
在书院呆得越久,她开始体会母亲的苦心和先生的话。在书院,他们用的词是“体贴”,再恰当不过。体贴有人情的温度。不是古人,不在未来,就在当下。“等一等,磨一磨”,这些简单的话原来如此明白。
在后来进书院的自传里,她还写道:
在北京的四个月使我感触颇大,刚开始因心急背书,嗓子突然说不出话来,母亲举先生的例子教育我,生活学习中一切都是炼心,想要成熟首先要坚强。后段时间母亲生病……那段日子我每天都很害怕。我发现我不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从小到大都和她对着来,总埋怨她对我太过严格,她的期待我总觉得无所谓。想起子歆说过,“如果你一直与你母亲关系僵硬,有天你会后悔的。”此后,我慢慢放下些自己的执拗去亲近她。其实母亲很温柔,只是我不听话,她把世间最好的全都给了我,她似孔孟的母亲般智慧。有时我心态还有起伏,她就用先生的话照醒我,渐渐我对先生所讲道理也有贴心的感受。
自传是去年写的,17岁,现在对照,来温州后,越来越有感应。
“我不能说现在是完全体贴。每天跟先生散步聊天,慢慢就有感应。先生说要悦乐。悦是自己开了,乐是朋友感染了,先生还说悦乐里有忧患意识,还有对时代的一个体贴。”春节刚满18岁的侯信佑对记者说。
从《易经》开始包本,开始看镜头都会紧张,不会讲话,现在学会了“论语”。怕讲错,但不再彷徨。今年开始解经,古文功底薄弱,总是不停问问题,搞得学长们总笑她问的问题低级。“现在真能体会到那种悦乐的感觉。我这些都不懂,怎么问高级问题呢。”
她愈来愈明确自己的方向。再回看15岁那篇文章,成人可能总会觉得有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但如果没这样的初心,或也不会有她现在的成长。
还记得有次照相,底下摄影师问:你们要在这里待多久?大家都说10年,她说一辈子。希望可以像先生一样,再不济给先生当书童。一众忍俊不禁。
约我以礼
采访回来,徐浩峰的电影《箭士柳白猿》上映。电影里解释箭士为何敢做武行仲裁,因为拳法通射箭,箭术即拳术。师父教导徒弟说:你的箭是射出去了,但还没收回来。
射箭怎么收回来?回来细想,明了孔子说:君子無所争,必也射乎!《礼记射义》言: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然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所谓收回来就是反求诸己。箭士敢做仲裁,不止凭的是技艺,更凭的是正己(电影台词叫气势)。春秋贵族习六艺,有射御,不止是打仗,本在修身。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如此。
在文礼书院,“博文约礼”,令人印象最深的,倒不是书院恢复了多少古礼,而正是师生身体力行,约我以礼的清明。在讲书院名称缘起时,王教授就说:约礼便是博文能不能诚心去践行。
也难怪乎从台湾来的林子歆说,现在解经,体会最深的一句话是克己复礼。在现代人眼里,这句话常常成了孔子维护封建制度的罪证。实则再简单平常不过。
问林子歆的体会,她解释说:希望自己做的每一件事,跟别人交谈的每一句话,尽量要求自己不过位的,中正一点。零食啊,想吃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这只是你一部分欲望,其实你不需要吃这些的。
记者对林子歆很熟悉,原来在微信看过她不少新闻。读经七年,曾以50万字背诵量的优异成绩成为文礼书院第一个正式学生,却有一个曾经反对读经八年的爸爸。但是,孩子的成长最终让父亲放弃了偏见。
这位父亲后来到书院参观,紧紧跟着王老师几天,看到书院孩子每天作息四点起床,五点不到,在一楼列队,恭恭敬敬地等候老师,老师一来,众人拱手行礼,一一问候。然后晨练。不禁深有感触。一位书院老师还记得林爸爸当时说,送到书院去是对的,台湾要赶快办读经学校,大一点的孩子,待在家里,真的会被家长毁掉。
“毁掉”这个词,林爸爸不是开玩笑。林爸爸疼爱孩子,在家里对女儿呵护备至。水果切好了送到眼前,喝杯水都不用自己倒。孩子一声令下,爸爸就成了马上办中心。
后来陪着林子歆到北京安顿,忧心忡忡回去,本以为女儿肯定接受不了。结果情况恰好相反,女儿经过一段时间挣扎,很快适应了学校生活。
现在,无论老师同学都对林子歆有个一致的评价,体贴人。助教陈老师说,书院来了新同学,一定是挨着子歆坐。曾经的“后进生”侯信佑就和林子歆这样相识相知。刚开始包本,林子歆就一直在她身边耐心鼓励,给了她无微不至的帮助,至今记忆犹新。在自传里,她还惺惺相惜地写道:她推着我一步步成长,并与我共享成功之喜悦。觉得我俩之友情会像牟先生与遵骝先生的友情一样“如兄如弟,毫无距离之感。彼解衣衣之,吾即衣之,彼推食食之,吾即食之。彼以诚相待,我以诚相受”终到“超越施与报之对待,进入一无人无我绝对法体之相契。”
15年文礼书院搬迁,侯信佑暂时滞留北京,还在网络上告诉林子歆,“以前我俩总是形影不离,都觉生活中有彼此才有意思,后再想,太感性,朋友不一定每日要在一起,各有各的功课,只要共同向往于道,才是最亲近。”朋友相交如此细腻,又如此平淡。
自身的清明,便是待人接物的亲和。在文礼书院,晨夕上课有拜圣礼,上下课有上下课礼,用餐有进餐礼,与人相见有拜揖礼。看似繁复,实则再平淡不过。在《文礼书院日常礼》讲解中,王教授就引《礼记》说:礼,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我是跟各位商量而不是规定,我不是圣人,我不敢规定。我只想,这样的表达,是不是能够尽我们师生的情,而合乎我们的书院的目的,也就是是否能合乎或激发一个人的实感,能辅助他平正性情,养成品德,维持他的向学之志。假如违背了这些目的,那我们的礼要改的。礼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身心的调理才是最重要的。”
礼是人情,是调理身心。六书通里仁字有上身下心的写法,《左传》说:礼,体也。(繁体:禮,體也。)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再回看春节后网上关于“女子不上桌”的争论,这还仅仅是礼仪的问题吗?
只有一个老师
在书院第一天拜望王财贵教授,问起现在书院有多少老师时,王教授笑着说了一句:严格地说,只有一个老师。一个老师就够了。当时诧异,不便多问。随后几天体验,又和学生聊天,不禁疑虑渐消。
只有一个老师,便人人可以为老师,而不只是被称呼的那个人。或许这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文礼书院,自学是最主要的学习方式。目前解经阶段,学生每天除了温经外,就是解经。如解《论语》,参照书目有三,朱熹《四书章句集解》、张居正《论语直解》、钱穆《论语新解》。王教授很少到课堂亲自上课,他认真说:讲四书,朱子讲得比我不知好多少倍了,学我不如学朱子。
学生们说,书院搬到泰顺后,先生一共只上了两次课。平时主要是学生主动问学。不仅是请益先生,更是同学相互请益。
采访学生,大家异口同声说得最多一个词是师友夹持。
壁立千仞,能者从之。“好的朋友是一道很坚韧的墙壁,好的老师是一道更高更坚韧的墙壁把你夹在中间。你便只有这条路可以走。”班长王泰恒谈起问学的感受,如此解释。
他说,“一开始先生和我们讲颜回的生命境界。颜回是学生的标杆。但人还有习气,后来先生跟我们讲无明,这就没办法退而求其次了。只论性不论器,不备;只论器不论性,不明。先生一开始是对我们只论性不论器,告诉我们把现在生命放下,全身心投入学问。很多同学可能会不舍现实,时时观照我们的现实身体。后来讲无明,无明就是对照嘛。你不能消除了无明就算了。那只是空无。现在要做对照的功夫了,你得有一个东西竖立起来。”竖起来的是师友,也是自己。
去年10月才进入书院的孙子龙,1 3岁,是公认解经最快的一个。但比起学长学姐,他非常有自知,“虽然现在学得比较快,但比较死。自觉性,理解力,触类旁通,我比不过他们。”就在采访那天,他刚解到《孟子》: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就对“盈科”一词深有体会:做学问就好比一条水源,始终会流向大海,一路上要经过很多波折。如果你遇到一个困难,水就会坚持不懈把这个坑填满。
前几天生病,遗漏了很多课业,他这两天便努力想赶回来,总觉时间不够用。孙子龙来自广东明德堂。在读经界,明德堂的管理是出了名的严格。现在来到书院,要自己管自己,孙子龙反而有些不适应,懈怠了。但也就十多天,他发现不行,很快反省。
王泰恒对这位小学弟印象深刻,刚来没几天,让他最感动的一点,就是孙子龙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挨个儿叫他们起床。“我们等于是哥哥一样的辈分了,实在惭愧。他要犯错了,有时我们说话很严厉,面子上过不去,他可能会尴尬,但十秒钟就过去了,很快虚心接受。这点比我强太多了。有错就能改,我12岁还是混球呢。”班长笑着对记者说。
比起孙子龙,同样13岁,来自明德堂的陈世浩就要稍微弱一些。比较贪玩。在课堂跟班,记者与他同桌,也发现他有时会开小差。但相处久了,就会感受到他的真诚。每次吃完饭,记者正起身收拾,他就说,我帮你拿。最近学习倦怠,也许他还未调整过来,但愿如他解“学而时习之”的习一样:像鸟学飞,一次能飞多久,后面就越飞越久。
在文礼书院,虽然有惩罚措施,但不常用。在访谈中,王教授一再讲到目的王国。目的王国来自康德哲学,换到汉语,即是反求诸己。现任班长王泰恒,是五年级开始脱离体制学校读经,在小学,连续做了几年班长。在读经学堂也经常担任班长。和体制学校相比,他觉得在书院做班长完全不一样。一般学校,班委总是承担监督管理的重任。但书院的班委只有一件事情,提点大家向学。“先生常讲,如果要管,那就不是书院了。我们不在现实上解决问题,只在发心上解决问题。”
两年班长,即将卸任,王泰恒最迫在眉睫的一件事就是希望这届能完善好班委制度。而且这个制度,一定是以志气为本。王泰恒想的是,各班委更像是一个示范角色。在书院,没有体育老师,体育委员就要负责体育课,体育课怎么上,怎么监督,班委制度都要设立一个底线。
“譬如北辰,众星拱之。因为没有处罚措施,便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其身正,不令而行。”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卸任了。”这两天制定完班委制度草案,他终于轻松地说。他的想法是,学长总在上面压着,下面的同学就永远起不来。做班委,上上下下,站的位置不同,看待事情的角度会不一样。“班委可能会多为书院考虑一些。有些同学从来没做过班委,你让他换位思考,这可能太难了。所以一定要让他们来做。这个角度特别重要。”
在这个目的王国里,王教授还在想更长远的事情。现在书院27个孩子,他还能每个都亲自教导。但随着以后人数增加,自己年龄增大,如何维持这样一个书院,激发孩子自我成长自我学习的能力就更加重要。这不仅是一套制度的问题。
在这届学生中,他正在尝试做的一件事就是组织孩子们编写一本解经疑难注疏。将孩子们解经过程遇到的难点疑点收录起来,以后将派上大用场。

后记:
由于成文限制,这篇报道还有好几位采访的同学没有写到,而每一位都很有个性。
如有志做建筑师的许瑞成,在遂昌时就因爱看建筑杂志,画建筑设计图而闻名。但来到这里,反而收下心来,钻进精进教室专心包本、解经。和同学相处,他最害羞。
同样来自台湾,林子歆的同学李谦,可能是这次采访中说话最有逻辑的一个。令他最感动的是,他从9岁读经,父亲就一直不很支持。但这次来学堂,他反而说服了父亲。他很坚定地对父亲说,他来书院,就是要做新儒家的学问。一句话,父子和解。
范家鸣,16岁,来自明德堂,在后面的文章我们还会写到。他解经很细心。有次解到《孟子·尽心下》,他见程子的理解是:“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王阳明则说:“心也,性也,命也,一也。”心生困惑,请教先生。先生说,只在一个理字,程朱陆王系统判别分明。这一问学成了同学相传的经典佳话。
最后还有李懿贞,18岁,也来自遂昌。她的英语全班最好,很有立志要做一个东西文化交流学者。她背英文不一样,只要听一遍就开背。总是最快的。寒假在家里,在母亲协助下,她在小区组织了一个英语公益读书会,以读经的方式帮助朋友学习,反响很好。
如此,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们还会问,读经会让人“迂腐”吗?论语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这些孩子身上,记者看到的正是这般悦乐。悦,是自己开了,乐,是朋友感染了。来书院两天,记者们也无时无刻不被感染着,甚至警醒着。不妨再借班长王泰恒一句话结尾:
如果你真的读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了,你在此时此地,翻开书,有了一个体会,你的体会和古人接的上,千古之下千古之上的人接的上,这就是一种自我的创新,就是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