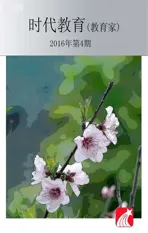这就是一个目的王国
——王财贵季谦先生文礼书院访谈
2016-09-21吴梅杨军张艺芳
特约记者_吴梅 本刊记者_杨军 张艺芳
这就是一个目的王国
——王财贵季谦先生文礼书院访谈
特约记者_吴梅 本刊记者_杨军 张艺芳

文礼书院暂驻泰顺县竹里乡文化礼堂。三楼上楼左侧,是书院27名学生的教室,右侧,相距十数步,是季谦先生办公室。间或有学生请益,先在门外一揖,入门再一揖,先生示意后方开口。来往盘桓人多,请示者,请教者,慕名远来者,季谦先生一一接待,不露倦色。2016年3月9日上午,记者一行三人在季谦先生办公室访问,相谈甚怡,历时三小时。是时先生盘坐榻上,身旁,是这个初春最盛的几支紫玉兰。
“目的王国”
记者:能否给大家描述一下,文礼书院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季谦先生:这不容易说清楚。文礼书院最核心的定位是培养人才,是读经的孩子进修的地方。而读经的目的是传承发扬人类的文化,文化包括内圣外王,所以书院要做的事可以扩充很广。但既然以经典为号召,所以整个文礼书院,不论主题与配套,可以用一个词总括--“典范”。
这里不论是书院师生还是工作团队的相处,希望是一个“目的王国”。什么是“目的王国”?“目的王国”是康德的一个观念。一般的机构都由“领导者”来制定规则,纵使现在是民主时代,也要由民众选出来有才智的人来制定法律。但这并不尽人意。规矩一定,成员就要遵守,一遵守,就有紧张,人常常变成工具,被规范,被安排。我希望在文礼书院,每个人要成为目的,而不是工具。不论师生或职员,要有理想,依理想而为学而做人而做事,他自己立自己的志向,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成就自己。而大家的志向、状态与成就,恰好就是书院原初立意所在。在这里生活的人,要有志道行道之心,不只是来这里求文凭,谋职业。每个人在这里……好像有人管,又好像没有人管,终归是自己管自己。这就是一个目的王国。
如此,文礼书院会是一个典范,任何事情都要能做出典范。除了理想是典范,教学是典范,管理也是典范之外,即使从大环境说,也是典范,我选址,就选了六年,走过大江南北十三个省份,勘察过六十几个山头,最后落脚在这泰顺县竹里乡四面环山的山腰上,有如“世外桃源”,将千年不受繁华所干扰,这也是典范。
说“典范”不一定是为了给别人看,更不是“好为人师”,想要做别人的楷模,而是“从理而行”“从道而行”。理,是客观的;道,是永恒的。我们只向往于客观而永恒的道理而做人做事,便是典范。所以,与其说典范要做给人看,不如说是要为自己负责。我已经67岁,虚岁是68了,自年轻以来就是立志于求道、行道。现在来开这个文礼书院,当然更不会枉费自己有限的力气,做一些没有价值的事。所以,如果做学问,以学问之道为典范;办教育,以教育之道为典范;经营事业,以经营事业之道为典范。内圣外王,是儒家必然的理想,为当代的儒家而做出典范,是我的理想。这是我的意愿,而我相信一定可以达到,为什么?因为既然从道而行,而道本来就在天下,如大路然。我愿以此意自励,愿以此意勉励诸生,并愿以此意与天下志于道者相呼应,相提携。
记者:据说,南怀瑾先生曾说,东南海湾边未来几十年是气最旺的地方。选泰顺作为书院地址是不是有这个考虑?
季谦先生:没有。我做书院不是为将来几十年,是为将来一千年。将来几十年的事我不会在意。

学生:以颜渊为教
记者:您将教育分成了两个阶段,13岁前,尽其可能地背诵经典;13岁后,解经、行经。目前,读经教育在实践中走过了前一个阶段,日益进入第二个阶段,文礼书院正是承此而设。外界对此很关心。
季谦先生:13岁之后,第一,解经;第二,博览;第三,游学;之后,成家。“成家”并非成家立业,是学有所成。解经,有一定内容,博览的内容就不可限量了,越多越好。而行经,照圣贤之教而行,是随时随分的事。书院主要的功课是解经和博览,游学是10年毕业之后的事。至于成就学问,经世济用,内圣外王,更是终身力行不已的事。书院只是打基础。以前,学堂为书院打基础;现在,书院为日后生命的光彩打基础。书院还不是成就。

记者:外界会有两个好奇或疑问:1、经过了第一个阶段打基础而来到这里的这些孩子,是否如您所期望?2、这些孩子在这里再经过10年的书斋学习,出去后又会如何?做事会否有问题?
季谦先生:我的规划是:3岁到13岁读经,13岁到23岁在文礼书院解经和博览,23岁以后,游学,33岁以后,去成就学问和功业。做事是在33岁以后了。要不就是23岁以后他不去游学,直接走入社会。不论23岁或33岁进入社会都不会太晚。
记者:这些孩子是您所预想的吗?
季谦先生:百分之五十的满意度吧。
记者:还有百分之五十不满意吗?
季谦先生:(笑)因为有两方面的要求,德和业,我规定的功课是进德修业。进德,我希望他们有颜渊的品行;修业,我希望他们有颜渊的好学。这两个要求很高,能有百分之五十满意就不错了。我以颜渊之学为教学宗旨,这是古来大家都不敢做的,我也不大敢做,因为这实在是太高了。但我还是要在这里提倡颜渊之教,现在这些学生,德行上还达不到颜渊的“不迁怒,不二过”,“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好学上还达不到渊颜的“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达不到“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还差得远。
不容易,要做个书院的学生不容易。所以他们听到我跟人说我还不承认他们是我的学生,他们很伤心。不过,如果要像颜渊那样我才承认他是我的学生,他们也不必太伤心,因为普天之下有几个颜渊呢?但是,如果不以颜渊为志,就没有成才的希望,我开书院就白费了。所以我一直勉励他们要志于道,我们的校训是:誓此身心,奉诸先圣;志道乐学,以报师恩。这师恩不是说我的恩,而是历来古圣先贤之恩。
记者:我们找了书院的九个学生聊天:黄雨林、王泰恒、侯信佑、李懿贞、林子歆、孙子龙、范家鸣、许瑞成、李谦,您对这几个孩子有何评价?
季谦先生:(笑)我也不大好下定评,只能有大略的观感。这几个大概都是比较自觉的,首先是自觉于道,其次是自觉于学。自觉于道和自觉于学又不大一样。志觉于道是指,对进书院的意义比较有所领悟。知道书院是为了传道,他们是来这里求道,一辈子要为道统之传承而努力。有几个同学是蛮有“气象”的,对自己的责任是有所领悟的,开口就是家国天下。王泰恒、黄雨林,年纪较长,立志比较坚定,道心比较强。其他有的同学,也都略有向道之渴望,也可以静下心来读书。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们虽然不敢称为“乐学”,但已经稍有“好学”之意了,至少说“勤学”是当之无愧的。当今之世,能够有好学的学生,已经不容易了。能知学就不错了。
记者:书院的规章里有劝退一条,但学生们说,目前还没有被劝退的学生。他们说,您对他们非常珍惜,舍不得,总想尽可能给他们机会。我想问,有没有孩子让您很失望?面对这样的情况您会怎么处理?
季谦先生:非常失望的倒没有,不过我是希望他们能赶快步入轨道。所谓的步入轨道,就是进入所谓的“目的王国”。他们有没有跟你们讲到“目的王国”?
记者:没有。
季谦先生:目的王国就是刚才说的,人人在这里,自己就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没有任何人是被支配的,自己为自己立法--王国有一定的法,但王国的法刚好又是每个人自己所立的自己所愿遵行的法。我希望书院是目的王国。我们有一些规矩,但这些规矩不是我定给他们遵守的。我定给他们遵守,他们就要约束自己来遵守,这样他们就不自由,不自由就不能长久,他一定会有所谓的叛逆或松散,会偷偷摸摸——偷偷摸摸是很不好的心境,我希望他们自己觉醒、觉悟,自己自理,自治。如果这样,我就不必管理了。我是以不管为主的。如果有问题,累积一段时间,我就去给他们训话,训一顿话就会好一点。
很难一下子就达到标准。我也知道做人不容易,但是总是希望如此。我一直警告他们,如果真的再不改,我就要把你劝退了。我曾经叫他们写切结书:一,如果私藏手机;二,如果谈男女感情,就毫不客气,请你自己辞退。要他们签名。不签名的马上走。签名了就要遵守。我认为这不是我霸道,这是他要来书院时自己为自己老早就应该定下的规矩,因为来书院就只为一个目的--成才。如果没有遵守这样的规矩,是成不了才的。当然,如果有任何人不同意这规矩,他也可以随时离开,来去是自由的,便不是霸道。

记者:我们跟班长王泰恒聊到了班级管理,初步体会到了您说的“目的王国”。现在班级基本是自治状态,助教小陈老师也说她基本是无事可做。班委们似乎在起草一个简单的章程,王泰恒在考虑扶持新的一批班委出来,这样他们这批老班委可以退到后面帮助学弟学妹成长。
季谦先生:所以你刚才说外界有疑问,担心他们不会做事,不会啊。做事是人类的本能,人怎么不会做事?到一个地方学一套规矩,是很容易的。甚至可以使那个规矩更加完善。只怕心中无道,只怕肚子里没有学问,不怕不会做事。
老师:就像一个泥菩萨
记者:在书院做老师,与您过去在大学做老师有什么不同吗?
季谦先生:嗯……应该有很大的不同吧。在大学当老师要上课,我在这里不必上课。他们自学。大学的学生是不会自学的。书院的学生自己学习,老师只是备问,这就渐渐走入理想的教育模式:《礼记·学记》说“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我是一口钟,他们来敲,敲得小,我的声音就小一点,敲得大,我的声音就大一点。
教师最重要的责任是指点。有些时候是主动的指点,我看到了就告诉他。有些时候是被动的,看到他有问题也不告诉他,让他自己去领会,或者自己来提问,我答。孔子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老师不要讲太多话,最好的老师像泥菩萨一样,坐在那里,教化众生。你讲太多,只能教一个两个。所以我最想做个泥菩萨。(笑)
同学之间也会讨论。只是,我没有给很多时间让他们讨论。他们最喜欢讨论了,一张嘴就讲个不停。他们在书院里,同学之间讲个不停,回到家跟家人也是讲个不停。我没有给他们太多时间讲话,赶快埋头用功比较重要。越用功,将来就越有话讲,而且讲出来的话才有内容。如果尽讲一些没内容的,那有什么意思?
记者:言不及义,好行小慧。
季谦先生:是啊,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所以还是赶快读书最重要。我偶尔会去巡堂,看他们都认真在读书。把这个习惯养成了,他们将来就有成就的希望。
常有人问:这里有多少老师?我说,只有一个。他们嫌一个老师不够。我说,其实也可以有很多老师,但要看这些学生受教的能力到了没有。他们没有受教的能力,你请大师来也没用。他们又说,程度不够,可以请一些比较粗浅的人来啊。我说那何必呢?浪费时间嘛。所以请来的,一定是学问家。学问家来的时候,你如果没有问学的能力,不是浪费吗?所以,至少三年五年之后我才会请人来。那时,一方面学生有受教的能力了,一方面他们也有提问或者进一步讨论的能力了。如果连提问都不会,是没有什么用的。我常常说教育是“画龙点睛”,每人先把自己的龙画好,待高人来点睛,便可破壁而飞。龙都没画好,画成一条虫,点了睛也没用。
与先贤们的书院不同
记者:之前也有先贤尝试恢复书院的理想,马一浮先生在战火中开办了复性书院,结果短命而散。在您看,复性书院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季谦先生:最要的原因:苗子不好。所以我先推广读经再开始做书院是有道理的。我书院的学生一定要有三十万字的基本背诵量,这也是有道理的。
记者:人们通常只看到马先生身处战乱时代这一原因,没看到苗子这一面。
季谦先生:当时那些学生都大人了,他们是五四以后甚至是接受白话文教育长大的,国学经典的基础不够。当然战乱也有影响,大家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学问。还有就是,书院没有学籍,想去的人本来就不多,学生人太少,基本面太少,难有出众者。我希望文礼书院每一个都是人才,但这很难实现,看几千人里能不能出几个。其实,几千人里面出一个人才,也就够了。
目前全国的幼稚园加上小学生,有三亿孩子,大概十万个孩子里有一个读经,全国共有三千儿童在读经。三千人里面才有十分之一是老实、大量读经的。所以最近几年,大概每年可以有几十个升入书院。三年以后,或许每年一百个。大概要五六年之后,每年才有三百个。每年三百个就合符我的预计了。将来书院是满额是三千人。或许有些人十年后也不走,所以以后书院可能是维持三四千人的样子。有些人从入学起就打算二十年才毕业的,也有立志终身要留在书院的,那书院就要养着他。他是不用交学费的,书院还要给他生活费,因为这是为国养才。
记者:学生多以后,您会分身乏术。学生的传带方面怎么解决?
季谦先生:对,这个问题我正在构想。有两个方式,一是学长带学弟,一是,求学的过程中,有些问题,我叫他们记下来有机会问我。举个例子,学生解经是先解四书,用朱注做注本,加上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有空还可看程树德先生的《论语集释》,还有的同学在看张居正的《论语直解》。《论语》的参考书比较多。《孟子》、《大学》、《中庸》参考书就少些,不过还是以朱熹注解为主。但是朱熹的注解里有一些不好懂的,我会分配给他们这些陌生的词语和典故,分别查出来,集成一本札记,发给每个学生。朱熹注四书,我们再来注朱熹的注。我们会把这十几部经,含中英文,都这样整理出来。这样基础的解经就可以自修了。这些学生,把他们所背过的十几本书全部都解过,能力就很强了。现在他们就是这样,越解越顺。以前不懂的,现在一看,啊,懂了。

记者:是,学生们也跟我们说到过这个体会。
季谦先生:这是一定的。我们还没有做事以前就会知道一件事情会往哪里发展。我们要有先见之明,才能仙人指路。他们越读书,越印证我跟他们说的预测。其实不是我预测,我是根据根据人性发展,先看到了学问发展的历程。所以他们的感受,都在我的预测之中。就好像我推广读经,几年要推广到什么地步,我二十年前就预测了。这二十年,大概是依照我二十年前的预计而动。这不是我有超能力能预言,而是人性本来如此。
我对他们学习的规划是,以自学为主,讨论及听讲为辅。在解经时期,只要介绍给他们好的注解本,他们就能自学。解经之后,要求他们博览群书,这所谓“群书”不是一般的开卷有益随便读,而是为他们选择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著作。解过经的学生,对于阅读,是遇强则强的,他们先是吸收,有能力之后是批判。阅读有一个规律,就是读书越多,领悟力越强,所以,也是可以自学的。何况学问是要自己做,才是扎实的。当然,如果期间有问题,可以互相讨论,或和我商量,如我不能解决,我会帮忙找专门书籍来参考,或找专家给予指导。到了相当时机,也会不定期请国际的专家来短期驻校。到了他们读书破万卷,学问有个样子了,即将成家了,会把他们放出去周游世界,去向世界一流学者请教。以他们一向的求学之诚以及那时的功力之深,相信所有大学者,都会不吝教导的,甚至喜欢收他们为徒。所以,我不怕书院的学生不用功,不怕他们没有人指导。
记者:再往前追溯,还有更多的先贤从事过您今天的事业,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我们唐宋时代的书院高峰。您的书院与这些先贤的探索相比,有哪些独特之处?
季谦先生:这个独特,不只是在现代,从古以来,文礼书院也是相当独特的。最大的独特性就是,从古以来的书院,包括西方的,学生都是大人,学有所成的大人,至少是青年以上。我这里是青少年。这是年龄上的不同,以及由此来的培养方式的不同。
记者: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孔子讲学面对的是成年人。
季谦先生:对。前几天还有人说:孔子有叫学生背书吗?有叫学生老实大量读经吗?孔子就是跟学生讨论的。我说,你要知道孔子的学生是几岁。所以啊,有些人不能全面思考,我们丧失了全面思考能力。不仅是中国人,西方人更没有。
记者:貌似还是很有的,而且给世人的印象好像还特别有思考。
季谦先生:对。因为西方文化的起源从希腊开始,就是走的不完整的路。什么叫不完整?就是对人的生命的总体把握,西方从希腊以来,就走了一条现实的路,或者说庸俗的路。佛家分真谛俗谛,西方走的是俗谛的路。俗谛就是现实生命,俗谛就是以认知心为标准。而真谛是以智慧心为标准的学问。中国和印度从一开始,学问的方向就是对人性的体悟和开发,东方的文化心灵一开始就走了高明的路。求智慧的心灵,必定会涵盖求学问的心灵,人类在东西两方相会的时候,如果还要再发展下去,必定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不是中国人自己这样说,而是,这本来人性就是如此。
我这个书院培养学生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个学生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都清清楚楚地知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清清楚楚地知道:人类有两层学问,而不是两面学问——中西不是两面,是两层。所有书院的学生都要养成立体的思考能力,有两层存有的见识。这是一般的学校不说的,一般学校只平面地说中和西,甚至只有西方没有中方,把中方跟西方相提并论就已经了不起了,你还敢说中国在西方之上,如果敢说的,不是被看成过街老鼠吗?但我们就是要做今天时代的过街老鼠。但这是人类必走的路,不可以因为别人的反对而放弃。在这里读书的学生都要养成一种超俗拔尘、勇猛坦荡的心灵,不然是受不了打击、受不了质疑的。他如果不够清明,一遭到质疑就慌张了,那就不算是我的学生。
所以啊,我们所要养成的人才是不同一般的,不是故意要不同一般,而是一般人往往是片面的粗略的。我们一面要真正地承继中华文化,一方面要真正的融会西方和印度的文化。一百年来的中国,中华文化算是被自己打败了,断层了,而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只在表层上模仿,并没有从根上接轨。整全的思考、立体的思考非常重要,全面的见识、全面的才华非常重要。
“我一生追求不容置疑的学问”
记者:当代中国还有古代意义上的真正的书院吗?
季谦先生:古代书院是讲学论道的场所。当代有蒋庆先生开了一个阳明书院,在贵州,阳明被贬官的地方。他欢迎天下的学者到那里去讲学论道。他希望大家像古人那样,是背着米去,住几天。刚开始,寒暑假还有人去,也举办了几次学术活动。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少。有一次我去拜访他,非常的寥落、凄凉,只有他一个人,还有一个煮饭的妇人,几栋房子在那里,寂静无人。我问他,人来得多吗?他说,已经很久没有人来了。可能是现代资讯发达,千里相会的人少了,但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没有讲学论道的人了。我想,如果文礼书院的学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毕业出去几千人,天下就又有讲学论道的人了,唐宋书院的盛况就可以恢复。现在,学绝道丧,要重新培养。

记者:放眼望去,以书院为名头的场所很多,颇眼花缭乱。
季谦先生:现在的书院分成几个类型。第一种类型,古代书院的装修,做旅游景点,有的加上不定期学术讲座。第二种类型,学堂号称书院。但毕竟学堂和书院是不同的,学堂是打基础,背书,书院是论学成才的阶段。第三种类型,是才艺传习所,当然,也兼办一些文化活动。第四种就是完全复古的书院,比如蒋庆先生的书院,目前我所知道的只有他这一个,营运困难,而且现在好像营运中断了。第五种就是文礼书院这种。
我是因为时代的需要才开这样的书院,从青少年培养起,他们刚来的时候,还不必讲学,他们也不没有能力论道,但五年十年之后,或许就有些气象,希望文礼书院将来也可以接上唐宋的风采。因为这些孩子长大也可以留在这里,出去了也可以回来,以后天下的学者多了,就会有人来这里讲论。现在我姑且代理做“山长”,自己没有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名气,所以大家不会来这里讲论学问。以后就看这些学生了。
自从我有这种书院的观念以后,社会上也有一些地方认识到这一点,渐渐有类似的书院出现,以培育青少年为主,它们有的叫书院,有的叫作国学院。现在一些大学的国学班也属于这类。但他们的教学内容和目的跟文礼书院不大一样。他们是培养国学人才,课程比较杂,跟一般大学分科一样。但文礼书院不是培养国学人才,是培养时代的国际人才或圣贤之才。有人说我在复兴中国文化,我说我并不是为复兴中国文化,我是为复兴文化--人类整体文化。因为从古以来中国人的“天下”,范围是不定的,所以,所谓的中国文化,就是天下文化的意思。中国古人对所谓的文化,对所谓的学问,对所谓的智慧,本来是有全人类眼光的。文礼书院创立的宗旨就是继承这种文化心量,培养国际人才,为时代担当责任。这个理想就是新儒家的理想。所谓新儒家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学派,它只是一个心量,一个态度,就是——尊重所有文化,为人类理性、人类前途而永恒奋斗。
所以这种学问是不容置疑的。也可以说我一生就是追求不容置疑的学问。对教育,也是要建构一个不容置疑的教育理论。因为理一分殊,月印万川。从人性出发,而不是从自己的偏见建立,人性是客观的,永恒的,所以依人性而行,所做的事便有客观性、永恒性。我希望书院的学生将来的学问是,让所有的学问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不自我泛滥,而是互相尊重,共同完成。
我知道学问艰难,人生艰难,我们是尽其可能去培养,至于,有没有成就?我认为必定有成就。从这里出去的学生,都是成才的,只是大才小才而已。所以我所做的事是永不失败的,我是永远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