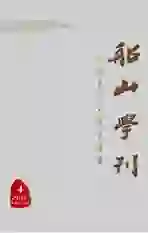从“才性”至“灵性”
2016-09-19杨勇
杨勇
摘 要:
牟宗三的《才性与玄理》是其心性哲学断代研究的重要作品,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该书全面地体现了牟氏对道家和玄学的判释态度、哲学地位和思想意义等方面的内容。过去的研究作品多从其“道德形上学”的角度给出了牟氏的道家和玄学研究的特质,而本文将以“才性”之源到“灵性”之相的逻辑展开为线索,试图从道体论、生命论、境界论和审美论四个角度,对牟氏的玄学研究做出立体的诠释。
关键词:牟宗三;儒家;道家;玄学
牟宗三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其核心的理念是通过融会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建构以儒家道德为基质的圆教思想体系。从而为世人展现出一个建构型、时代型、圆融型的哲学体系。
在牟先生众多的作品中,《才性与玄理》是一部参佐孔门道体论的,关于道家及玄学思想研究的文本。从文本创作时间和思想逻辑发展看,《才性与玄理》的出版时间后于“新外王”三书,以及《中国哲学之特质》,该书是牟氏从历史哲学转向心性哲学的,第一部以断代形式阐发其心性思想的专著。故而具有独特的文本价值。
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先贤大多将视野放到了牟氏关于“道德的形上学”的分析,而忽略了其作为除了道德之外的,作为生命的、境界的、审美的内容,可这恰是牟宗三在《才性与玄理》中意欲向读者开显的重要思想。故而,我们将通过这四个方面对之作出探讨。
一、道体论
《才性与玄理》是以儒家贯通天人的道体论来评价道家(玄学)突出主体的境界论。具体而言,牟宗三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以下几点:
1.魏晋玄学中的“才性”,是由“气性”开出的,是生命消极的一面;
2.王弼到向、郭的发展,是对“气性”的一种反动,由此演绎了一条境界的理路——从似“存有论”的本体论、宇宙论,到纯粹主体性的“境界论”;
3.境界论发展到阮籍、嵇康,便由理论性发展为一种审美的生活方式;
4.魏晋的言意之辨特征是“吊诡”,是对境界论的必然诠释方式。
事实上,前三项表达了牟氏对魏晋玄学的判释,及对其哲学式发展的梳理。最后一点则是从方法论上分析,语言怎样辅助了玄学的开展。
此处所谓的判释,是指牟宗三始终站在儒家的心性论、道体论,对魏晋时代学术做出了分别和评价。他认同宋明儒的看法:“《论》、《孟》、《中庸》、《易传》是通而为一而无隔者得同时即是宗教的,就学问言,道德哲学即函一道德的形上学。”①先秦儒家为道德哲学的确立开辟了两个矢向,分别是孔、孟、《中庸》、《易》的天道之心性,及荀子依气质之性分析道德之心。而先秦道家则直就自然之性的消解,从负面的方式探讨道德的建立。就上面的发展方向看,牟氏基于他关于“道德的形上学”标准,将“孔门”一系判为真正完满的道德体系,而将荀子与道家,划归作为气性一类的,有一定缺憾的道德体系。“‘才性者,自然生命之事也。此一系之来源是由先秦人性论问题而开出,但不属于正宗儒家如《孟子》与《中庸》之系统,而是顺‘生之谓性之‘气性一路而开出。故本书以‘王充之性命论为中心,上接告子、荀子、董仲舒,下开《人物志》之‘才性,而观此一系之原委。此为生命学问之消极一面者。”②
牟宗三的判释是源于其道德理想。他认为“孔门”所提出的“仁”、“四端”是道德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创造性的体悟,这是对生命的一种反省。“孔子的仁和孟子的性是一定和天相通而唯一的,这个仁和性是封不住的,因此儒家的metaphysics of morals一定包含着一个moral metaphysics”, ③就是说,孔子一系看到的天道,并非孤立在经验世界之外的,它的创造性是生命存在的根据,而孔子的“仁”就是对生命存在的感悟和实践,在这层意思上,可以知仁而践履,所以天道与仁心相同。另外仁心或四端之心本身要通过存在主体来实践,并且基于“仁”等道德观念是人类生存状态下最普遍的原则,其实践也必须为道德的。这样主体的道德性,既包括了普遍性和个体性,又涵盖了存有性与实践性。它是天道人性相贯通的,天道是道德的创生的“理”,而知仁、尽心尽性则是主体的“行”。在这样的前提下,儒家道德圆满了自宇宙论至本体论,最终完成于人生论的即理即行的道德理想。
与孔门不同的是,由“气质之性”为切入的另外一支。牟宗三在《才性与玄理》中,将之分成两类,一是以王充的《论衡》和刘劭的《人物志》为标志的“气质说”,一是遵循道家思想的王、向、郭之“境界说”。
对于前者,牟氏借以对王充地检讨和评价,回顾了告子、荀子、陆贾、董仲舒、王充、刘向到刘劭的所谓“用气为性”之理路。按照他的说法,以气为性,虽然可以上拔到形上学的高度,并成为普遍意义的前提,但是问题在于“气性”的本质决定了它的非道德性。“气性”即自然义(自然而然)、质朴义(人的物理机能)和生就义(自然所赋予生命的独特状态,如气质等)。由气性的特点看,将具有抽象意义的“性”委于“气”下,那么主体的人,所表现的就只能是自然意义的,这样会导致牟氏认为的自然主义、材质主义,而由于气的流行,是一种宇宙生命力的扩张和凝聚,它完全没有任何道德意义上的超越,气使之然,性即然之,结果便形成了命定主义,人完全没有超绝的能力,圣人和凡人,圣人与天道也就无法贯通。
在气的理论下,道德善恶成为了一种偶然性的存在。故有告子的性非善恶说,荀子的性恶说,以及董子的三品说。“‘用气为性,则所谓善只是气质之‘善的倾向,并非道德性本身(或当身)之性之定然的善。……善意之为绝对的善即道德性本身(Morality Itself)之定然的善,孟子之‘性善即此道德性本身之性之定然的善。而所谓气质之‘善的倾向,则不过是在经过道德的自觉后,易于表现道德性本身之性之‘定然的善的资具而已。”④牟宗三认为,若就气言性,则关于说“性”非善恶,可善恶的看法,都是成立的,“用气为性”只是提供了“善的倾向”。这样,“性”作为普遍原则的基础,就渗透了善或恶的可能,是杂驳的,而非纯一的。结果是:一方面,道德失去了可靠、必然的前提,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心”的觉悟来逆转“性”的恶,使圣凡之异,只在于圣人的独特的明觉之“心”。虽说具有进步意义,即重视了“心”的道德主动性,但更大的局限,却是完全割裂了圣凡贯通、及圣人处贯通天人的可能。故而,牟氏指出只有建立了先天的、必然的道德理念才能够实现圣之为圣,以及凡亦可为圣的道德理想。
二、生命论
牟宗三的道德理想是建立在对康德“道德的神学”批判的基础上,其改造的理论便是 “智的直觉,即是‘直觉的知性”⑤之上。简单的说,就是人具有直觉的,非概念的纯智形式,主动地判断表象自己,通过逆觉,而创造性地实践普遍、必然的道德原则。⑥事实上,牟氏此观点,是融合康德的道德哲学和儒家天人贯通的人性论之后的结果。对此,先贤已作了大量研究,我们此处需强调的是,这一原则必不能离天道流行的宇宙生命论。
生命论是牟宗三打通天人,使“智的直觉”成为可能的关键,同样也是《才性与玄理》的境界论和审美论的前提。牟氏以为“‘个体的人皆是生命的创造品、结晶品。”⑦孔子之所以能够认识到“仁”的价值,就是因对生命有所感慨。生命的流行具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积极的,另一个是消极的。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正是从正面看到了生命的可贵,看到天道演化万物,使物得其所适,这就是一种“道”,而主体的人,能通过人伦的亲善,而使生化人作为人的存在意义,并由此创立道德作为人本质性存在的价值意义。这样天道与“仁”都体现了一种是其所适的特质,而得到贯通。更重要的是儒家从天道之处获得了创生性、普遍性、存有性,而从“仁”那里得到了具体性、实践性。这样天人真正达到了一致,获得了通达。由此,“仁道”即“天道”。其中含盖了从理性到感性,从抽象到个性,从理想到实现的全方位、全过程。儒家因之而得到了“道德的形上学”,其“内在道德性”,也因此是“从德性实践的态度出发,是一自己的生命本身为对象”⑧。这就与康德“道德的神学”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仁”虽为形而上,但它不是虚设的,也不是封死的。因为仁即天道,而天道流行,故而它是实在的,又因为天道创生,故仁以道德的形式实现其价值的挺立,其实现即是通过逆觉的玄智获得对仁道的理解,并由此以生命存在形式将之贯彻到现实中去。所以“仁”为道德原则的同时,更内在的呈现出一种“活脱脱”的生命之价值。恰在此意义上,儒家是表达了生命的正面意义。
与之相对的是以才性为特征的儒家之外的别支。在《才性与玄理》中就是以气性为主的儒家和道家、魏晋玄学。牟宗三指出,生命同样需要“气”来表达,但是却存在着差别:一是逆气而行,代表为孔门一支,一是顺气而行,即才性一支。如果顺气而行,那么人与人的不同便仅为生命强度的等级性差别而已。即是说,生命即“气”的流行,气的运动是盲目的,自然的。当气性作为实现人现实存在的动因时,它仅能自然成化出人的自然属性,“垂直线的命定论”,即宇宙生命之气在根本上对个体的规定,故而道家是通过“养”这一自然之性,而达到最高层次的道,使此自然生命自由自在。⑨至于主体的不同——才性的不同,则是生命之气的强度表现了不同等级性的差别,是人呈现出“智愚”、“清浊”、“善恶”、“是非”等包含着自然才能和道德意识的不同。由于气质之性是一种自然的、盲动的,它仅存在着生命强度的相异,所以偶然性成为其道德理论的特质。“用气为性”,则“性是才资之性”,“才质之气性并无绝对的纯善,亦无绝对的纯恶,但却可有强度的等级”。 ⑩其结果就会如刘劭《人物志》中纯以品鉴的方式来诠释人的自然材质,甚至高扬英雄的才能,而忽视了道德原则的建立对人性的正面善导和发扬。不过在牟宗三看来,从另一方面说气性一路,却开出了以审美为导向的品鉴说。
三、境界论
在宇宙生命论和人性论的积极、消极向度的框架下,牟宗三赋予了道家和玄学极高的赞誉,并将之评价为“用气为性”一系的时代和哲学的高峰。其标志就是发展和完善出了统一,异于孔门、释家的“境界论”。
境界论,即通过玄智,或对“无”的逆观,呈现出主体对万物的超越、自由的认知和生活状态。牟宗三指出,境界论是建立在体用论、宇宙论和工夫论上的,所以它首先必须对客体普遍性、存有性进行消解,之后,通过诡谲的言辞方式表达出主体的心灵地知觉方式,最后才能达到以主体超越为特征的自由境界。
首先,牟宗三以为,王弼的《老》《易》注释,是对汉以来“元气论”的一大反动。王弼分解了元气的形而上意义,而代之以心的功能,通过心的逆向能力来体悟“道”。但牟氏强调,此处的“道”虽有普遍性,抽象性,但却没有存有性,只是心灵的冲虚之用。而“道”的这些特征,又是源于王弼关于“无”—“有”—“物”的重玄理论。他将世界分成可道、可名与不可道、不可名两层,二者的界限就在“指事造形”之上。“指乎事,则为事所限;循乎形,则为形所定:自非恒常不变之至道。”?即以固定的名称规范事物,这就可道、可名。而不可道、不可名之部分,则没有分限和定名。这就自然凸显了相对于概念的“有”的“无”,即“无”是相对于“有”而言的一种描述,表达的是无可称谓,无可定性的特点。故而从语言上的“无名”,可推出性质上的“无”。由此“无”可生“有”,“无为天地之始”,这是第一玄。“有”亦等同“有名”,但这里的“有名”,是主体对存在物之存在的一种抽象描述,是某种认识力的“徼向性”,即朝向存在的一种能力,但却不存在定性。因为必须存在着“有”,这样才可能以“指事造形”的名言方式给予“物”以特定名称,物也由此得到了现实性和多样性。所以“有为万物之母”,这是第二玄。第一玄建立了“道”以“无”、“无性”、“无名”的特征,第二玄则建立了“道”的存在现实化、具体化的性质。这样“道”得到了一贯的“遍在性”和“先天性”。
其次,境界论上表达的体用一如,就“用”而言是运用语言的遮诠能力,这是心灵的直觉之智。虽然“道”相对于具体的事物(“物”)、甚至具体事物的抽象(“有”)而言,都是无法实体化的,但是语言却可以通过其表意的性质对之进行描述。这样,体用的问题,首先内化为人的认识问题,“无”之体具有“吊诡”之“用”,牟宗三将之命名为“辩证的融化”。 ?“道”的纯粹抽象性,导致其只存在形式的意义。语言表意的功能,一层是指向实体性的,不论实物,还是概念,另一层则是描述、或指向非对象的意向性。故而第一层是得言、得象,但“道”属于得意者,所以应该忘言、忘象所表,而指向思维的意向性。牟宗三认为这就是纯粹的“无”,它只是纯粹的思维的形式。由此,“无”贯穿于“有”,“有”又贯穿“物”,首当为语言表达,为思维的逆反维度。这样,“道”“无”作为体所表现的一贯性,必须是通过认识的方式达到的,这便是思维在语言上表现出的“用”。于是不但体用,甚至是天人都包含着彼此如一、相即不离的关系。当用语言去描述“道”的时候,“道”就很自然的内化在人的认识范围内,所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道”,就决定了“道”呈现的理论特质。道家和玄学在此实行的以语言之诡辨取消“道”的存有性,即导致只能以主体的智识能力来看待“道”,故而“道”完全被消解成为了主体之内的认识,认识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主体”的心灵境界。于是境界论便自然而出了。
但是境界论,不能只局限于认识的范畴,牟宗三以为道家的贡献,便是将此境界扩展到实践方面。“此境界形态之先在性乃消化一切存有形态之先在性,只是一片冲虚无迹之妙用。此固是形上之实体,然是境界形态之形上的实体;此固是形上的先在,然是境界形态之形上的先在。此是中国重主体之形上心灵之最特殊处也。”?被完全消化的“道”,在语言上呈现的是“正言若反”的诡谲之用,完全消化“道”的实体性而为“无”,而在实践中则被逆向直觉的智慧观照为“冲虚”的意境或玄智的境界。在观照的地境界中,“道”对万物“不生而生”,故“道”以道化之功而治万物,既然它不是积极而是消极的生化,故而“无为”、“无待”是冲虚境界下的必然智慧。“无为”即顺道化而无所作为,就是否定一切会引起道实体化的倾向,保证“道”始终是纯粹的思维形式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圣人体无”可因道的遍在性和先天性,而回归道体的本源;“圣人有情”,又可因具体的有而应化万物。于是体道和有情,成为圣人贯通天人的实践方式,只是这一实践是在观照德境界层面达到的。因圣人本身就是一个饱含形式与内容的完满主体,故以主体所获得的冲虚境界为中心,万物的纷繁多样都可被纳入到主体的心灵境界被划归于同等的性质,即“齐物”。这里的“齐物”并非“物”之各性具有客观相类的特点,而是个性在境界中被消融,被主体的玄智所消化。圣人因玄智之功,而无心于外,溟灭一切差别,超越“物”的限制而挺立出主体性卓绝的自由状态,这便是“逍遥”,“灭除一切追逐依待而玄冥于其性分之极也。此即通于逍遥、齐物、自尔、独化之境矣”。?
但牟宗三认为,境界论虽然也阐述生命的意义,虽然也叩问了天人贯通的玄义,同时尽管也思考了道德何以实现的问题,但是按照他判释的标准,道教和玄学并没有完整的、积极的建立“道德之形上学”,而是片面的、消极的描述了“道德的境界论”,可恰恰是境界论却开出了魏晋时期独具的审美理论。
四、审美论
牟宗三认为尽管道家和玄学没有正面地建立起道德体系,积极地应对人生的价值问题,但魏晋时期的人物和理论却以审美的角度表达了独特的生活情趣和理论思考。然而实质上,这一理论透露出的,正是主客体、道德自由无法正面统一,而只能在境界层面下和谐的问题。
所谓“审美”,对人物而言是“美的判断”或“欣趣判断”,而对理论而言则是建立审美的形上思考,它是对人之灵性的哲学思考。
《才性与玄理》一书大量列举了东汉末至魏晋的名士风范,并从生命论的角度对他们的生活行为作了说明。基本观点是强调生命力在气质或才性方面表现出的具有审美意义的情趣。牟氏始终认为,宇宙生命力在人性论的全幅发展必须是即道德即材质的。但是魏晋学人接受老庄之后,便偏于才性一路的发展,从而展现了怪诞、乖违的行为和生活。并形成了品鉴的审美风尚,如《人物志》对品鉴标准的分类。魏晋时人对俊秀、飘逸等气质的追求,正反映出人们对生命的一种态度。总的说来,“名士”风范的格位是“唯显逸气而无所成”,“可谓魏晋时代所开辟之精神境界也。”?“逸气”是生命力在材质上的呈现,它只是依附于主体的材质,当主体表现为具体职业,如道德家、思想家等时,它可增添主体的外在气质,使之具有“逸气”的类特征。但当逸气成为唯一的主导占据主体时,便成为一种审美的境界,即名士。可是牟氏认为这种境界只能作为艺术的欣趣和美学的判断,它的实质是表达了对生命无奈的消极感慨,其境界上的审美情趣,表征为与众不同、怪异、乖违的行为和想法,这是负面上对生命的感悟。因为它的“逸”,“异”,故表现出超越一般而特立,故具有审美的倾向,可是正因其是遮诠得反映生命,故对生命的建设是破坏的,对道德理想的形成是反动,并最后走向虚无主义。所以即使是阮籍的放逸亦被牟氏判为生命之盲动。
虽然魏晋时代呈现了丰富的,具有审美意义的现象,但是牟宗三指出,这些现象恰恰反映了自由与道德(名教)之间的严重冲突,因而其审美形式是存在缺憾的,不圆满的。牟氏参照黑格尔的艺术理论,结合其道德理想的理念,分析了魏晋的审美学,强调魏晋玄学的内在矛盾源于原始道家自由与名教的不合,而其关键又在于“内在主体性”的问题。
牟宗三认为原始道家的时代是一次“内在主体性”凸现的重要时期。在理想的历史状态中,国民对三代礼法仅是自然的、不加反省的、以高贵的美德去接受。但原始道家意识到礼法与内在自由是冲突的,故而走向反动,采取了虚无礼法的倾向,以“无为”对待礼法,意欲突出主体的意志和自由,即以“无为”之用,消极地保存外在礼法而片面地发展主体内在的自由,结果开出了境界下的主客统一。魏晋是其继续和扩大。在此境界中的主体却是“非道德而超道德的自然无为之主体”,?它只能体现某种精神生活的情趣,只能将名教和自然内化到主体之中,从而展现出审美意义的精神现象,但这些现象反应的却是无法解决名教规范现实主体的矛盾。而儒家则意识到须从内在的道德生命建立积极的道德体系,开发内在的道德性,并将之推出而成为客观的道德原则。由此道德(礼法)不再成为外在于主体的形式,而是可主体化的;而自由也不只是消极,却是可外在实践的,因为礼法是经过自由的反省后去行为的。故而在道德的前提下,主客、天人、自由与道德均达到了统一。回到审美的意义上,儒家的审美论是基于道德的——圆善的,而道家、玄学则是境界的——才性的(偏执的),不过牟宗三亦给予道家一系哲学以很高的评价,即一方面道家过渡到儒家是一进步,“使吾人自美感阶段超拔而进至道德的阶段”,?另一方面,“因为对于存在不着,故道家本质上含有一种艺术境界。中国之艺术、文学之精神大半开自道家,正以此故。”?
五、结语
从上文对道家和玄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牟宗三始终是以儒家道德理想作为判断标准,分别从道体论、生命论、境界论和审美论等方面立体的呈现了道家与魏晋玄学的思想特点。前二者是牟氏立论的基础,而后二者则是道家和玄学独特的理论形式。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正是道家与玄学的这些特征,恰恰暗合其道德理想之建立的逻辑,即在论证其缺陷时,亦开发出作为圆教之过渡的必然阶段。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牟宗三对魏晋的研究已经预设了理论前提,故而更多的是呈现出黑格尔式的精神概念之发展,而非严格学术史的方法,所以在看待其《才性与玄理》的学术意义时,应该更多地将之规范到牟宗三的内在哲学体系中,而似不能完全放在历史中去考量。
【 注 释 】
①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一),台北正中书局1986年版,第17页。
②④⑦⑩????????牟宗三:《才性与玄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8、16、110、152、第123、177、59、328、327、319页。
③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⑤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101页。
⑥郑家栋:《本体与方法——从熊十力到牟宗三》,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277页。
⑧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性》,台北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11页。
⑨牟宗三:《四因说演讲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