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佛教介入政治冲突的表现形式及其原因探析
2016-08-18李宇晴
李宇晴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084)
泰国佛教介入政治冲突的表现形式及其原因探析
李宇晴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084)
僧人干政;泰国;佛教;功能主义
从古至今,泰国不断有佛教介入政治冲突的事件,佛教积极介入政治的方式是僧人干政,消极介入的方式是以接纳政客出家的方式为其提供庇护。从政客角度来看,是为了获取宗教庇护、积累功德以及保护自身名誉;从佛门人士来看,是为了在政治斗争中利用宗教身份为自己迅速树立权威;从佛教教义和佛教在泰国的本土化特征来看,佛教论证了国王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连。泰国的佛教在历史舞台中展现出功能性和世俗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为佛教介入政治冲突事件提供了土壤。泰国佛教观念留出的阐释空间为佛教赢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它不断被人们用来建构泰国社会的象征权威,这是催生出政教乱象的根本原因。
引言
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佛教在整合泰国社会过程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佛教不仅仅为大众提供了一套宗教信仰体系,还影响着泰国社会各个方面。佛教的功德观整合了个人前世、今生与来世的关系,也整合了个人与其他生命体的关系,成为连接个人与社会的纽带[1]。人们通过“功德”共享和让渡形成道德共同体,形成了泰国公民社会的基础[2]。20世纪初泰国开启现代化进程之后,泰国政治、经济、文化均在不断发展和变动之中,佛教在泰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仍然是人们关心的主题。人们一般认为,佛教在泰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安定剂的作用,减轻了泰国社会从君主制走向君主立宪制过程中的社会动荡程度[3]。
然而,佛教在泰国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似乎并不全是正面。佛教和政治的互动、僧人乱政的情况从历史到现在一直没有断绝。阿瑜陀耶末期,泰国出现枋长老的僧人武装割据势力;19世纪,出现反抗暹罗统治者的千禧年宗教异端运动,自称是先知的人利用佛教术语表达自己的超自然力量,詹姆士·斯科特把它看做边缘人群对国家中心的抵抗[4]。1902年,泰国五世王颁布了第一部《僧伽法》,将僧伽集团的管理纳入法治轨道和社会管理体系当中来,对僧团组织的治理进行了指导规范。然而不管如何整顿僧团体系,僧人与政治的关系仍然十分紧密,这从2013年至2014年发生的反英拉政府事变中可见一斑。佛教僧人仍然以各种方式介入到了这场政治动乱之中:寺庙成了世俗政客的避难所,僧人似乎也可以毫无障碍地踏出庙门参与政事。信仰“出世”的佛教为何与世俗政治有如此直接而密切的互动?泰国佛教在泰国现代社会转型中到底饰演了怎样的角色?
一 泰国佛教介入政治冲突的表现形式
在泰国政治震荡的过程中,宗教因素总是或明显或隐秘地卷入其中。不管泰国佛教在隐秘的层面如何和政治互动,泰国佛教有两类介入政治冲突的表现形式如此明显以至于我们无法忽略:第一类是泰国僧人干政的现象,即僧人主动介入政治冲突,佛教积极介入政治冲突;第二类是泰国佛教寺庙为政客提供庇护的现象,即政客通过出家进行政治避难,佛教消极介入政治冲突。
(一)政治人物的宗教避难法
2015年新年伊始,素贴·特素班*素贴·特素班,反英拉政府头目,泰国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PDRC)创始人。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主页上附上了一幅自己身披佛袍、削发为僧的照片。然而2014年此时,作为反政府示威头目的素贴·特素班还在曼谷街头激昂地号召所有反对英拉政府的民众走上街头,不将英拉政府赶下台誓不罢休。英拉迫于压力宣布辞职后,按照程序将重启全国大选。深知英拉所在的为泰党牢牢把握东北部人口基数占优的票仓,自己所在民主党选举获胜希望不大的素贴继续领导旷日持久的街头抗议,他的诉求升级为:选举前必须进行改革,消灭选举腐败现象,彻底清除他信家族。双方胶着阶段,掌握军权的泰国陆军首领巴育出来控制反政府和英拉政府两方,自己成立临时政府,不久便宣布卸下军职,华丽变装,并得到国王的支持,于2014年8月25日成为泰国第29任总理。政治游戏暂时结束,素贴身负法院多项指控。在缴清保释金之后,他悄然在老家素叻他尼府的寺庙里出家当了和尚。
泰国历史上许多政治人物都有出家的经历,出家时间或长或短,出家时机各不相同,但巧合的是,很多人都把时机选在了政治斗争情况激烈、处境险恶之时。最早的案例当属素可泰王朝的立泰王*立泰王(1347—1370在位),泰国素可泰王朝政权第6任国王。。1362年,素可泰地区的立泰王向南沿着巴萨河进行扩张时,遇到了新兴的阿瑜陀耶政权的激烈反抗,立泰王非但没占到便宜,还被阿瑜陀耶的乌通王拿下了重镇彭世洛城。经此一役,立泰王遭到巨大打击,返回素可泰,停止了武力征讨并选择出家修行,想以宗教形式的让步作为筹码,争取从乌通王那里取回彭世洛城。乌通王同意交还,但是也提出条件,要求立泰王到彭世洛城去,将王都素可泰城和甘烹碧城交给其他人管理,《暹罗历史》对此有详细描述:
当立泰王不再使用武力,便剃度成为了功德之士(Nak Bun)……立泰王希望利用自己僧人的身份在政治上谈条件,他找乌通王化缘,请求他把宋开城(后来的彭世洛城)还回来。
乌通王也很乐意归还,但并不是那么简单地还回去,条件是立泰王必须住在宋开城,素可泰城和甘烹碧城必须交给他人统治。[5]
立泰王在彭世洛呆了七年,期间写下了著名佛教典籍《三界经》,一直等待时机,谋求东山再起。1369年乌通王去世,阿瑜陀耶陷入争夺王位的内乱,立泰王好不容易盼来了机会,重新回到素可泰。
除了上述情况,还有很多国王以出家的方式退出政治斗争的案例,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曼谷王朝四世王蒙固*曼谷王朝四世王,即拉玛四世(1804—1868) ,名蒙固,拉玛二世之子。。1824年,曼谷王朝二世王病危,他预感由皇室成员、国家高级官员和佛教僧侣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将会支持他的大儿子切特萨达柏丁继任王位。切特萨达柏丁虽然是长子,却是妃子所生;蒙固比长子小16岁,但是为拥有皇家血统的王后所生,按照传统,王后所生的王子比妃嫔所生的王子拥有更高的地位。太子争储事件背后暗流涌动。为了保护宫中势力单薄的蒙固,避免王子之间自相残杀,二世王在死前两周宣布:到了蒙固王子成为一名佛教僧侣的时候了。于是,蒙固被剃度,住进了寺庙里,此后27年间,他在全国四处游历,以僧人身份自处。“即使蒙固想去参与政治,他也别无选择,他必须认真对待佛教,因为离开佛教将把自己带入危险的王朝政治的漩涡中。”[6]直到哥哥三世王去世,蒙固才继承王位,成为曼谷王朝四世王。
(二)僧人干政
泰国2014年刚刚平息的反英拉政府政变事件中,反政府头目之一伊萨拉和尚*伊萨拉和尚,为佛统府甘蓬散县偶农寺的住持,在2013—2014年反政府示威阵营中表现活跃。因其僧人的身份分外引人注目。一般来说,佛教教义崇尚出世之道,须无欲无求,伊萨拉和尚却如此大张旗鼓地入世参与政治事件,表达政治诉求,十分不同寻常。他带领一群反政府人士,长期占领曼谷市郊占瓦塔纳地区的交通要道,多次配合反政府领导人素贴·特素班发声,要求英拉下台。僧人身份也让他“享受”了一些特殊待遇,比如警察在控制示威人群时,对占瓦塔纳地区使用催泪弹后,亲自登门向伊萨拉和尚道歉;陆军总司令巴育尊他为僧,对其行跪拜礼的照片在网上流传。5月份,军方清场后,尽管身披佛袍,伊萨拉和尚还是免不了被指控为叛乱分子等8项罪名。缴清保释金后,伊萨拉和尚仍然保持对国内政治的关注,公开在媒体批评巴育将军自己担任总理的行为不光彩,并另外提名了一位候选人,俨然以公共政治人物自处。
伊萨拉和尚并非开僧人干政先例之人。纵观泰国历史,僧人干政现象古已有之。吞武里王朝*吞武里王朝,1769—1782年,是泰国历史上第三个王朝。初期,便出现过僧人武装割据集团:1767年,阿瑜陀耶王朝灭亡之后,暹罗出现了5个较大的割据势力,其中之一便是难府、帕府的枋长老建立的僧伽武装势力。据称,枋长老的和尚军,“身着红色长袍而不是藏红花黄色长袍并且以凡夫俗子的身份来生活。顶着神圣的光环,他们在1770年变得足够强大”[7]。次年,枋长老将势力向南延伸,吞并了彭世洛后,到南部各府抢劫粮食和财物。达信王随即派大量军队收复彭世洛城,枋长老见大事不妙,逃到清迈投靠缅甸人,“达信借此机会巡视北方各府,招抚流民,整顿佛门”[8]。
另外,僧人就政治事件公开站队的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也发生过。20世纪70年代,冷战氛围浓厚,在时任军政府总理沙立的领导下,佛教僧团受到严密监控。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僧人吉滴乌笃(Kittiwudho Bhikku)自发站出来为泰国军政府残酷血腥镇压共产主义者的行为发声:“杀共产主义者并不造孽。”[9]
二 泰国佛教介入政治冲突的直接原因
从以上列举的社会事实来看,佛教卷入政治冲突并不少见。从功能主义路径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些许个中原因。
(一)宗教避难换取政治安全和谈判筹码
政治人物可以利用宗教获得政治利益,即进行政治避难,甚至将出家为僧作为政治谈判的资本和筹码,就如立泰王试图以出家为条件,换回被乌通王占领的彭世洛城。出家为僧已经成为泰国政治史上的一种惯例。选在政治斗争的节骨眼上出家,清楚地展示出政治避难的实用性功能。选择出家,一方面意味着暂时退出政治斗争的舞台,暂时放弃争夺政治利益的权力,既然退出角斗场,对手就不应该继续追责;另一方面,披上佛袍会使对手产生一定的敬畏心,一般情况下,迫于民情和舆论压力,不会继续与之进行政治斗争。
(二)投奔佛门以谋求功德,增加个人声誉
除了以政治避难换取人身安全和政治谈判的筹码外,政治人物们选择在政治斗争之时投奔佛门,还有道德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原因。
第一,从佛教道德观出发,出家者通过个人的禁欲、持守戒律,来获得佛教里所称的功德。对于泰国信奉佛教的民众来说,剃发出家是一种积累功德的做法,出家者可以为自己的父母亲朋祈求功德,或为自己忏悔赎罪,以求来世有好的生活。
泰国佛教属南传上座部佛教,其理论体系的核心便是业和功德。“行为便是业,一举一动都构成业行。佛教强调业报论,即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承担后果。业又分为向善和向恶的两端。善业又称为功德。”[10]在普通泰国人看来,无论出于什么初衷削发为僧,只要进入寺院持守戒律,就能获得功德。出家时间越长,说明心越虔诚,所能获得的功德就越多。布施和持守戒律是泰国普通农民求功德的主要方式。在这样的功德观中,没有选择可能导致流血冲突的直接的政治对抗,而选择退让、遁入佛门的政客是值得鼓励的,他们选择隐忍、和平的道路是在为自己积德。
第二,出家对于政治人物的声誉有利。僧侣在民众心目中是受尊敬的阶层。在泰国重要的节假日,不管是佛教节日还是非佛教节日,一般都有给僧侣布施的活动。在泰国启动现代化进程之前,寺院在萨迪纳土地制度之下分配有广袤的土地,寺院经济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的泰国,他们也是被供养的阶级,只不过供养形式发生了变化。他们通过放弃世俗享乐,持戒修行,传播社会伦理规范,理论上应获得世俗世界的尊重。泰国重要政客出家并不是逢场作戏,他们或在寺庙里念诵佛经、持戒修行,或游历四方,进一步学习知识、保留实力。历代好几个因政难出家的国王,利用出家时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立泰王在出家期间,写出了奠定泰国佛教宇宙观和世界观的重要作品《三界经》;四世王蒙固在出家期间,潜心学习佛教教义和核心内容,学习巴利文,后来大力推动了佛教日常实践和仪式的改革。
因此,那些选择出家的政治人物披上黄袍之后,无形之中为自己赢得了民众的好感,将为他们还俗和东山再起打下良好的舆论基础。
(三)利用宗教身份迅速为自己建立关注度
相对于常见的政治避难,僧人干政现象则属于历史时空中偶现的浪花。僧人一般只在乱世踏上政治舞台。
僧人政客能够利用其宗教身份为自己迅速树立关注度。在阿瑜陀耶王朝覆灭后,枋长老之所以能够迅速起势,一方面也是因为“顶着神圣的光环”[11]。伊萨拉和尚如果不以泰国佛统府甘蓬散县偶农寺住持的身份参与反政府游行示威,他也许没有机会担任反政府阵营的头目之一。他利用自己特殊的宗教身份,一方面自恃佛门弟子,以宗教合法性增加自身言论合法性;另一方面以此吸引媒体、普通大众的关注度,制造噱头,炒作自己。
僧人站出来发表政见的行为也被怀疑背后有人指使或被人收买。僧人是政治意见的代言人之一,僧伽的政治意见可能对大量佛教徒的政治选择施加影响。例如,伊萨拉和尚“代表”僧伽阶层发表了政治意见,这种意见可能对佛教徒的政治判断有引导性作用。然而,僧人如果过度介入世俗政治领域发表意见,可能危害佛教的声誉和威望。
三 泰国佛教介入政治冲突的深层原因
前面分析了泰国佛教卷入政治斗争的直接原因,下面将追本溯源,探析在泰国本土佛教信仰文化传统中,这种现象得以产生的土壤。
(一)“佛王合一”:为国王政权进行合法性论证的佛教教义
泰国本土佛教教义中埋藏着政教合一的观念。佛教教义从本源上并没有避讳政治和权力,正相反,很多佛教经文对国王的政权合法性进行了论证。例如,《大本经》中比较了佛陀与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就是现实中具有一切菩萨一样美好品质的君主。的特征,显示出:无论佛陀表现为世间圣王或离世修行觉悟者二者中的哪一个,“其最终真实是同一的。佛教的宗教真实与世俗的帝王权威是同一实在的两面。”[12]早在13世纪,泰国古代的国王便吸收了印度教的“神王合一”思想,随着佛教在泰国的传播和壮大,这一思想进一步本土化为“佛王合一”,即国王既是世俗世界的领袖,又拥有佛陀的善行功德,是宗教世界的权威,王权和宗教权威的结合成就了国王的权威。斯坦利·坦比亚(Stanley Tambiah)亦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论述了佛教与政权的关系,他从佛教发源的印度阿育王时期历史背景开始梳理,认为古代国王是佛教的护持者和净化者,虽然现代政权和宗教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佛教一直被用来作为合法化的工具[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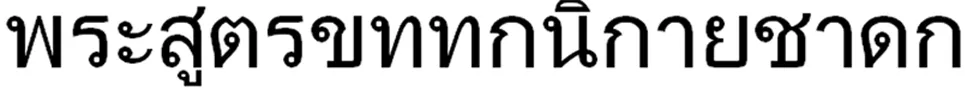
(二)寺庙教育:历经僧伽制度改革而存活
佛教的功能性还体现在教育方面。在泰国五世王朱拉隆功进行教育改革之前,主要由佛教寺庙担当学校教育的功能。“古代泰国的教育,从一开始就跟寺庙结下不解之缘。寺庙就是学校,识字的僧侣就是老师。”[15]五世王进行改革之后,泰国开始建设现代学校,但同时并未完全舍弃传统的寺庙教育,实行的是现代教育与寺庙教育并行的双轨制教育方式。
1932年民主革命以后,泰国由完全君主制过渡为君主立宪制。1944年,僧官考试选拔制度进一步完善。泰国教育部制订了僧俗学位规定,通过巴利语佛学资质考试的学位将拥有相应学位的教师资格,如“获得3级以上僧伽学位的僧人,有资格担任小学老师”[16]。这说明僧侣寺庙教育还是没有从泰国教育体制中消失,仍然拥有一定教育功能,尤其是在乡村。这种教育功能是佛教拥有实质性功能的具体体现,也是佛教在世俗世界延续自身权威的重要方式。
(三)出家:贯通顶层和底层不同地位和观念的平台
几乎所有泰国国王都有短暂出家修行再还俗的经历。一个合格的国王必须同时是佛王合一的,才能获得宗教赋予的神圣权威。在泰国,僧人出家和还俗基本是自愿的,可以在佛门内外自由进出。平民百姓也拥有这一自由选择的权力。一旦出家,在寺庙内,平民和国王便暂时地站在了相对平等的位置,他们共享佛教所传授的宇宙观、处世观等观念,平民能够通过出家感受到与国王的关联。从国王的角度来说,这种贯通感有稳固民心、巩固统治的功能。
除此以外,还有一类人是因为家庭贫困而不得不出家,希望通过出家化缘解决近在眼前的生存问题。目前,佛教基金会能够支持沙弥们出国留学,提高自身素养,对贫民阶层来说,这是获取知识的绝佳途径,也为日后在世俗世界的晋升打下基础。因为僧人可以随时还俗,所以僧人可以走世俗文官的途径,这让出家之路的世俗前景看上去更为诱人。
不管是为治天下、积功德还是为谋生活而出家,佛教的实用性在泰国展露无遗,泰国的宗教实践明显具有政治化和功能化的本土特点。泰国佛教的这些特征为发生佛教介入政治冲突事件提供了土壤。
四 泰国佛教信仰文化中的断裂与延续:不变的功能性定位
查尔斯·凯斯(Charles F. Keyes)认为,在泰国进行君主立宪制改革前后,泰国的佛教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次变革是由曼谷王朝四世王蒙固引领的僧团改革所开启的。蒙固王扶持创立了法宗派,由此推动了泰国佛教主导观念的变迁:从相信前世因果决定一个人现世的位置转变为相信现世因果决定未来的业报,从稳定论转变为发展论。这种观念变迁与泰国现代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亚于韦伯(Max Weber)所述的新教伦理和西方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凯斯指出了泰国佛教随着现代化进程进行的自我变革,强调了传统的断裂[17]。
确实,曼谷王朝五世王改革前后,西方的坚船利炮将让人羡慕的“现代文明”带入暹罗,泰语中开始频繁出现siwilai(civilization,现代文明或西方文明)这个词,这体现了在全球化和西方殖民胁迫背景下暹罗人追求现代文明和进步的梦想。然而,siwilai和泰国传统佛教宇宙观*泰国传统佛教宇宙观集中体现在《帕銮三界经》中。大相径庭,现代文明是沿着指向未来的时间轴,siwilai这个词标明了时间的过去和未来;佛教宇宙观则是循环的、静止的。“siwilai和charoen(繁荣)两个词体现的是逐渐显露的世俗意识……暹罗有跟上时代脚步的任务”[18]。因此,佛教观念从过去指向未来的变革应运而生。
然而,我们更应看到泰国佛教内在的延续性。佛教从进入泰国开始,便主动融入了泰国世俗社会的方方面面,它积极建立了与王权、政治、教育、民间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为统治者提供了一整套意识形态和文化体系。根植于南传佛教教义中的“佛王合一”思想,不仅具有为政权进行合法性论证的功能,还道出了泰国社会的象征权力的分配机制。1932年泰国民主革命之前,神权和王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谋”建构了泰国社会处于支配地位的象征权力。民主革命之后,议会政治开始在政治舞台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所谓现代的议会选举政治极不稳定,从1932年至今,泰国军方已成功发动多达10次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2013年反英拉政府事件后,至今没有开启选举程序,事实上,王权和神权依然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幕后发挥稳定性作用,是相对稳定的权威象征。
在20世纪现代思潮冲击之下,泰国佛教宇宙观并没有瓦解,它只是被提炼和修剪了。“在佛教宇宙观基础上建立的佛教结构仍保持完整,并仍保存着小乘佛教的核心”[19]。除了核心功德业报观念没有变化,佛教教义留给人们的阐释空间一直存在,蒙固王正是利用了这一阐释空间建构了法宗派;近几十年来,商业市场精神又催生出法身派*法身派佛教徒将功德和金钱挂钩,认为功德和商品一样,可以进行买卖,认为捐的金钱越多,积的功德越高,甚至有人称之为“佛教经济”。的壮大。佛教观念一直顺应时世发生着变化,但它对于国家、王权、泰国文化不可或缺的象征意义与功能性没有发生改变。所以相似的历史故事才会不断上演:素可泰王朝的立泰王和曼谷王朝的蒙固王在位时间相距近500年,都选择了同样的宗教避难法;今天的伊萨拉和尚和200多年前的枋长老遥相呼应,均以相似的方式强势介入政治冲突之中。循着这些行为表象深入下去,我们看到了泰国佛教的功能性定位,以及泰国社会精英对宗教象征权力的建构欲望。
因此,展望未来,泰国佛教介入政治冲突的政治化事件必然还会出现。
【注释】
[1] S J.Tambiah,“The Buddhist Saints of the Forest and the Cult of Amulets: A Study in Charisma, Hagiography, Sectarianism, and Millennial Buddhism”,JournalfortheScientificStudyofReligion, Vol.24,No.2,1985,pp.425-432.
[2] 龚浩群:《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66-370页。
[3] 宁平:《佛教在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当代亚太》1997年第2期。
[4] 〈美〉詹姆士·斯科特,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三联书店出版社,2016年,第378页。
[5] 〈泰〉阿努叻·班亚努阔:《暹罗历史》,曼谷:主根书社出版社,2010年,第182页。此段由笔者翻译。
[6][7][11] 〈美〉戴维·K.怀亚特著,郭继光译《泰国史(Thailand: a short history)》,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162页,第123页,第123页。
[8] 段立生:《泰国文化艺术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64页。
[9] Charles F. Keyes,“Political Crisis and Militant 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Thailand”, in Bardwell Smith, ed.,ReligionandLegitimationofPowerinThailand,LaosandBurma, ANIMA Books, 1978, pp.153-154.
[10][12] 宋立道:《神圣与世俗——南传佛教国家的宗教与政治》,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52页,第71页。
[13] S J. Tambiah,WorldConquerorandWorldRenouncer:AStudyofBuddhismandPolityinThailandAgainstaHistoricalBackgrou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5.
[14] 〈美〉贝格尔著, 高师宁译《神圣的帷幕: 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37-41页。
[15][16] 段立生:《论泰国历史上四次僧伽制度的改革》,《东南亚南亚研究》2005年第1期。
[17] Charles F. Keyes,“Buddhist Politics and Their Revolutionary Origins in Thailand”,InternationalPoliticalScienceReview, Vol.10,No.2,1989,pp.121-142.
[18] Thongchai Winichakul,“The quest for “Siwilai”: A geographical discourse of civilizational thinking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Siam”,TheJournalofAsianStudies, Vol.59,No.3,2000, pp.528-549.
[19] Craig J. Reynolds, “Buddhist Cosmography in Thai Histo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Nineteenth-Century Culture Change”,TheJournalofAsianStudies, Vol.35,No.2,1976, pp.203-220.
【责任编辑:石沧金】
The Form of Thai Buddhism Involvement in Political Conflict and Its Reason Analysis
Li Yuqing
(Desect1ment of Soci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Political Intervention by Monks; Thailand; Buddhism; Functionalism
Throughout history of Thailand, there have been incidents in which Buddhism intervened in political conflicts. The active way of intervention is that monks intervene with political affairs directly, while the negative way of intervention is to provide shelter for politicians by accepting them as monks. The reasons are as following: From the politicians’ view, they seek shelter in temples to obtain religious asylum, accumulate merit and protect their reputation; From the Buddhist’s point of view, they can take advantage of religious identity in the political conflicts to establish authority quickly; From the Buddhist teachings in local Thailand, Buddhism proves the legitimacy of the king’s authority, intertwined with politics fundamentally. Thai Buddhism exhibits features of functionality and secularity in the stage of history. These features are the soil in which grows the bud of the phenomenon that Buddhism gets involved in political conflicts. Thai Buddhist ideas actually leave room of interpretation, which has won it a strong vitality. The room of interpretation continues to be used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symbol of authority in Thai society, which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haos.
2016-05-14
李宇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2015级博士研究生
D733.663A
1008-6099(2016)04-0106-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