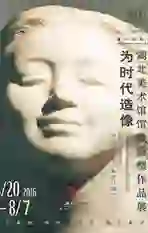情感与正义:多重语境叠合下看电影《老炮儿》
2016-08-11
近年来,没有哪部影片能像《老炮儿》一样激起普罗大众的表达欲,由此催生的关于《老炮儿》的评论,可以说各执一词,众说纷纭,从这个意义上说,《老炮儿》成为近年来不多见的现象级电影。近日,各大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学者就电影《老炮儿》进行讨论,探讨在多重语境的叠合下,如何对电影本身的审美意义进行分析和评价。
王真(浙江大学):
电影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年长一代和年轻一代的冲突。以我自己的经验,确实存在这样的冲突。但我觉得,影片里面化解的方法实际上可以进行商榷。因为六爷最后实际上是牺牲了自己,成就了一个他认为的圆满规则,有点像耶稣,将自己献身于一个崇高的事业,但壮志未酬。在我看来,六爷倒下之后在电影中再出现,当然是另一种结局的设计了。
王杰(浙江大学):
我觉得这部电影里叠合以下几种文化。一是黑帮文化,中国社会很有势力的一种文化。一个外来人到了被人长期把持的地盘,不拜码头一定会吃苦头。第二,一种北京的以游民为基础的文化。再有就是胡同文化。影片中的胡同是死胡同,一般人走不出去,所以很多情景发生跟死胡同有关,我觉得是有一定寓意的。另外就是“文革”文化,和市场经济所导致的消费文化。性别文化也在其中闪现,如六爷和他女朋友话匣子的关系,它牵扯到中国传统中一种很深的男性中心主义视角,等等。
这部电影成功地表达了当代中国文化语境的叠合性,是一个理解当代中国文化很好的个案。同一部《老炮儿》电影,不同的人看出了不同的意义。黑帮文化本来是应该被否定的,但是在这里它却以一个情感正义的形象出现。我感兴趣的是,通过它我们如何解读当代中国社会。
海立波(广西师范大学):
六爷老炮儿所谓的反抗,不是发生在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斗争,而仅仅是过去没落的权贵对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兴起的新一代权贵的反抗而已。这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抗性和斗争性。六爷最后去约架,把对账单寄给了中纪委,这样的行为很明显是不符合江湖规矩的。可以说,为了通过审查,或者其他目的。老炮儿这些人最后都归顺朝廷,归顺正宗的权力制度,或者某种程度上必须向体制妥协。冯小刚想通过《老炮儿》对权力谄媚,说到底,他想塑造一种反抗主流的黑帮文化,其实最终还是对权力加以谄媚,加以投降,希望被收编。
张永禄(上海政法学院):
《老炮儿》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阶层分化对立的情况下的艺术表达,今天我们整个社会表面上非常繁荣、祥和,实际上内里各种矛盾交汇,最大的交汇是底层和上层的交汇。阶层的对立折射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礼乐崩丧、价值的虚无和秩序的混乱。我们需要寻找一个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在没找到它之前,江湖文化或者胡同文化作为一种秩序的抵抗,注定是悲剧。六爷突然心脏病暴发最终没能走到河对岸干架。这是一种过去的文化价值在新的混乱面前不能起作用的隐喻。
我们缺乏一种更加普遍的秩序,但是我们相信有一种传统的仁义道德、小江湖的秩序来支撑这个世界。这个普遍的秩序是管虎们意识到的新兴文化,还没有找到,或者说他压根儿不认为有一种新兴文化可以取代这种秩序,这是主创的失败之处。
强东红(咸阳师范学院):
《老炮儿》的价值观是非不分,颠倒黑白,整个社会底层没有秩序,这是时代的反映。导演的价值观很混乱,这部电影让人感觉非常厌恶。六爷既不正也不善,整个电影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折射是非常真切的。但观赏性比较差,没什么可看性。
赵臻(厦门大学):
复杂、传统的东西已经与现代的文化不兼容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新的文化,我们从传统里找资源,找到的是江湖文化。江湖只是属于一个小秩序,我们想利用小的文化秩序重建一个大的文化秩序。而新的文化秩序应该和现代性相适应,避免走向曾经历史上出现的大一统的文化秩序。
王杰:
中国的类型片还很不成熟,做类型片就好好做类型片,就把这种性格的复杂性塑造出来,六爷这个人就应该是一个悲剧的结局。所以,如果从电影创作的创新角度上看,我觉得谢飞的《本命年》拍得比这个成功。《本命年》里有美好的东西,少年时候的两小无猜,很纯洁的感情表现出来了。《老炮儿》没有历史的纵深感,六爷跟话匣子应该有一段美好的感情,但影片没有任何表现。
肖琼(云南财经大学):
马克思将悲剧两分,一种是新事物的悲剧,它在最初出现的时候势力很弱,但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实现不了必然要出现牺牲。第二种是旧事物的悲剧,就是值得我们去推崇、去传承的一些价值观念。《老炮儿》所反映出来的悲剧,应该是旧事物的悲剧。很多的传统,值得推崇、传承的价值观念,只能停留在旧时人物身上。他们都是当下社会被边缘化的小人物,反而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小,保留着一些旧有价值。这些旧有价值通过他们与新社会、新人物的较量冲突得以“绽放”,在这个瞬间,我们看到他们身上保留着的美好价值。
向丽(云南大学):
影片给我一种很大的压力感,这种压力感来自于戏剧冲突。我看到中国当下阶层之间的对立,代际之间的冲突,它至少引起了我们对于阶层之间的冲突的思考。老炮儿六爷实际上是个缓冲阶层,是一个润滑剂,他没有最后的发言权,但他只是一个调剂品。所以这里面层次的丰富性,随着时代的延伸,不断地在调试,不断地再次细分分化,非常复杂。中国经验影片中肯定是有的,只是怎么在理论上诠释出来的问题。
王杰:
这部电影也许是个拼贴,不管效果怎么样,它提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多语境叠合下的一种价值危机。六爷显然是过时人物。老炮儿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过时的东西。在当代中国社会,他格格不入,电影表达了这一点。在我看来,《老炮儿》的情感逻辑是断裂的。它所讲求的规则和它的影像运行是断裂的。当然你也可以讲是有意为之。但是在我看来,真正好的艺术作品,哪怕形式上拼贴,内在的情感逻辑是贯通的。
许娇娜:(韩山师范学院):
电影和文学不一样,电影在整个生产过程里受到各种力量的影响。我觉得“水浒”文化才是这个影片里的一个核心点,是中国江湖文化的变形。六爷所说的规矩,他自己并没有遵守,他做事是前后矛盾的。他和偷钱包的小偷说钱你可以拿走,身份证寄还给别人就可以了。小飞的女友把钱拿回来了,就是赔偿他儿子晓波划人家车的钱,但是这个钱是她偷来的,他照收不误,他的规矩是什么规矩?我不理解。这部电影为什么让我们有一种价值混乱的感觉,是因为我觉得它根本不适合用悲剧形式来呈现。它如果真的有反抗性的,应该用喜剧形式呈现。所以我看完电影时,第一个跳进我脑海里的是堂·吉诃德。
王大桥(兰州大学):
堂·吉诃德在当下显得可笑,是因为他按照过去的规则做事。老炮儿所代表的过去,我认为是北京胡同文化。在电影当中,胡同多次出现,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儿子晓波骑着自行车,六爷坐在后边,小飞手下人在胡同里围殴他,他对晓波说“出胡同口向南拐,赶紧跑”。这个胡同是不是死胡同,我觉得值得讨论。后来晓波开茶馆,选择在胡同街道丁字路的拐口。北京的胡同文化,是过去在当下显现出的异质性,也恰恰是当代性。
小飞和老炮儿相遇的空间,我以为是一个流动的文化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身份是模糊的。不同阶层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共享某一种生活方式,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酒吧,以及最后茬架的野湖冰面,这两种人或者两个阶层在这样一个空间里相遇。我更愿意六爷一个人拎着刀在湖面上慢慢倒下,对岸空无一人。老炮儿代表的过去文化的异质性反衬出我们当代意义的缺失。
许仁豪(上海戏剧学院):
美学家对于什么是好电影都有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最后是走向哲学性的方向。《老炮儿》是一部商业片。商业片做得最厉害的是美国好莱坞。类型片为什么会出现,因为观众是懒惰的,不喜欢在电影院里思考。而类型片讲故事的方式,永远有一个套路,千篇一律,比方说黑帮片,爱情文艺片,永远会有一些元素套进一个叙事结构里,就像快餐店里的套餐一样。
好莱坞奥斯卡奖和欧洲的影展奖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奥斯卡偏向商业片里的类型叙事,只是这些电影在类型叙事的过程里会溢出惯有的叙事模式。比方说有一部电影《美国丽人》,它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伦理片。这部电影当年为什么会得奖,它一样用了很多惯有的元素,但是最后这个故事讲着讲着,情节发展溢出了观众熟悉的路线,讲出了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崩解,每个人在这个家庭里面都很孤独的问题,从商业片上升到了哲学的层次。
《老炮儿》还在商业片的范畴里。但它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和讨论,我觉得它成功了。我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看到了一些共象。抽离掉社会历史的特殊性之后,这个共象告诉了我们什么,好像是1980年以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在不同的社会里产生了一些同样的社会问题。而这个社会问题,就是价值观的崩解。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运作到了今天,它所崇尚的是一个不断更新,不停地把所有的老旧价值给摒弃,让人在老去的过程里焦虑不安:面对自身的价值和过去所创造的价值,或许在接下来五年、十年里它不再具有价值的时候,人将要如何老去就成了问题。
杨子(上海艺术研究所):
前几天看赖声川的戏《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沙》,讲的是一个摆地摊的妇女20年每天都坚持观测星象,因为她的丈夫失踪20年了,她坚信丈夫被外星人劫持到外星球,会在20年之后的某一天回到她身边。所以她每天在地摊上卖一种手表,手表有两个时间,一个往前走,这个是我们世俗世界里大家都共有的时间,另外一个时间停留在她丈夫离开的那一刻,就是属于她自己的时间。看这部电影不禁想起这部戏,第五代导演冯小刚、陈凯歌、张艺谋等,他们在80、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一直占领中国电影主流话语,但是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渐渐淡出主流之外,反而是郭敬明、韩寒等80后、90后新一代的年轻的“社会主义新人”阶层出现,他们无论拍什么电影,凭借粉丝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票房炒到上亿,这是第五代导演可望而不可即的。
我从电影里看到第五代的怀旧。六爷们的时间始终被置放在他们所设定的辉煌年代,没法和这个社会再缝合,所以这是一群不合时宜的人,就像电影里出现的鸵鸟,是对无法面对现实的象征。我看到小飞这个人物形象时,突然觉得很眼熟,他其实是两个人的结合体——形象很像郭敬明,而韩寒是国内职业赛车手。所以,李小飞结合了郭敬明和韩寒两个新一代导演的特质。为什么这部电影不用专业的演员去演六爷,而是用冯小刚这个第五代导演最典型的代表呢,我觉得这是第五代导演这一类“老炮儿”向韩寒、郭敬明们代表的新的权威世代的一次宣战。这次宣战非常冒险,有可能根本打不过他们。但是事实证明,管虎们成功了。在最近对贺岁档电影的一次调查显示,《老炮儿》的票房在七部贺岁电影里排第一,观众满意度86.5分,也排第一名。如果说这部电影是第五代导演向以韩寒、郭敬明为主的新生代导演争夺话语权的绝地反击,必须承认他们成功了,而且引起众声喧哗。的确,由电影引发的评论已经成为当下一个文化现象。这对电影来说,我觉得是好现象。没有争议的电影不是一部好电影。
王杰:
在当代中国社会,我们所有的人都面临着存在于社会规则之外的潜规则,它有一套所谓的规矩,在我看来带有黑社会性质,《老泡儿》触及到了这一点。但是就电影本身来讲,我觉得是不成功的。它不是一个好的类型片。从电影本身的逻辑来讲,最大的败笔就是中纪委,反贪是法律的逻辑,是现实社会的正常逻辑。但《老炮儿》是用潜规则来处事,这是两套系统,好的电影就应该一以贯之。在当代中国,“潜规则”导致许多社会悲剧。
段吉方(暨南大学):
这部电影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反思和批判的价值大于它的艺术价值,大于它的审美价值。它建立在对个体的一种最基本的关怀基础上。六爷和兄弟闷三如果能杀出重围,两个人把小飞等所有人打趴下,肯定很多人拍手称快。这体现了当代中国民众的心理。找不到反抗的出路,寄希望于想象的江湖,这一点是电影的成功之处——以一种伪装的叙事化和审美化的形式把问题讲出来,这恰恰是这部电影作品社会学、美学的意义,所以它的社会意义要大于它的艺术价值。
尹庆红(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江湖文化有一种英雄形象亦正亦邪。在金庸的小说里,亦正亦邪的令狐冲是受人喜欢的,那些非常儒家的道义感非常强的人物不一定受欢迎。这部电影肯定不是个悲剧,但是让人觉得很窒息,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电影作品如果仅仅表现中国经验是不够的。它没有一个价值指向和立场导向。在美国好莱坞大片里都有价值导向,要么是个人对抗权力,要么是弱者对抗强者,要么是通过个人努力争取正义。在这部电影,我看到的是“你们年轻人不讲规矩,我们有规矩”,很脆弱的价值指向和立场导向。电影没有提供一个反思的立场和价值指向。今天的美学批评或者说电影批评不能回避伦理以及道德的价值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