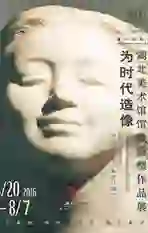荷赛的生命力还能持续多久?
2016-08-11林路
林路

“文化牢笼”与“西洋情结”的纠葛
有人曾说,“文化就是一座牢笼,一个神秘的屋子,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始终决定你的存在”。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也有永远走不进对方屋子的苦恼。这不像藏着十万金银的山洞,靠着阿里巴巴的一句咒语,就可以破门而入,不管喊咒语的是什么人。
早在十多年前,我就曾说过:荷赛是欧洲人创立的,因此也必定是欧洲人的天下。虽然说音乐、绘画、摄影是无国界的,但作为一种人的视觉语言,不能不受到其身后的文化氛围的笼罩。
三十多年前,荷赛对于中国人来说的确神秘莫测。然而有人说,中国人走不进荷赛那间神秘的屋子,外国人却走进中国这间屋子了!比如当年他们拍摄的北京体育学校等照片,或者今年拍摄的中国煤矿业所造成的污染,不就获了奖?其实,他们走入的并非是中国的这间屋子,而是通过窗口的一瞥后,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描述了这间屋子里的情景。是他们的文化背景获得了评委们的青睐,如同我们在某个地方造一座欧洲城,或是唐城、宋城之类,以其为背景拍摄照片,并不说明你真正到过欧洲,回到了唐宋年代。
很早以前,杨绍明的《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获1988年第31届荷赛的新闻人物系列照片三等奖,这是中国摄影家31年来在荷赛中首次获奖——实现了“零”的突破。于是,一时间大小文章都将荷赛高高捧起,反复说明荷赛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如何高,以此来证明中国摄影界的实力,从而反证荷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第二年,中国的137位摄影家满怀信心送去了600幅作品,其数量之多居参赛国家第二。结果呢?无一获奖。落荒归来以后,大小舆论又以几乎相同的口吻贬低荷赛,说荷赛只是代表西方中心主义,它对中国的冷落不能说明问题。但事实却放在那里,使人不得不黯然神伤。这就是所谓的“西洋情结”——无法摆脱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西洋情结”。
这些年,中国摄影人在荷赛上的获奖又重新点燃了人们的希望。从表面上看,大家已经学会了冷静地看待眼前这千奇百怪的世界,尽管有时真的让人有些看不懂。实际上,在冷静的背后是否有点心虚?在闪烁其辞的言语中又有谁敢说真正脉准了荷赛所倡导的新闻摄影真谛(我这里说的是新闻摄影的真谛,而不是西方人的眼光)呢?
“同情的疲惫”与突围
关于荷赛,关于新闻摄影,关于摄影的纪实力量,其实都和摄影的本原相关。尤其是到了上个世纪末,在新闻和纪实领域,摄影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写实本身,而是如何把握写实的限度。有人提出摄影太残酷了,世界上所有的战争和灾难都被摄影家一一收入镜头,令人不忍卒读。但更多的人认为摄影的逼真写实和它的“残酷性”远远不够,理由是人们看到了无数的灾难照片,已经产生了一种麻木,用当年《美国摄影》编辑的话来说,产生了一种“同情的疲惫”,因此需要以更令人触目惊心的图像来刺激人们的神经,以便拯救这个已经堕落的世界。然而这恐怕是勉为其难了!因为摄影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硬要赋予它无法承担的重任,只会令其无可适从。
进一步说,新闻和纪实摄影试图对“同情的疲惫”所努力的突破,有时也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当年一些摄影家对艾滋病患者的拍摄。他们不惜冒着各种潜在的危险与艾滋病患者们生活在一起,在获得他们的允许后拍到了大量的照片。可是他们在成功的同时也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指责和批评,原因很简单:这些报道艾滋病患者的摄影家们一开始就是用揭示与暴露的方式向全世界宣布这一灾难的恐怖与残酷,从而成了一种绝望的叫喊。比如,摄影家尼古拉斯和他的妻子、科幻作家贝比曾经一起进入艾滋病患者的生活圈内,他们用8×10照相机与黑白胶片,通过极详尽的细节和特写影像展示艾滋患者脸部、身体上被摧残的特征以及绝望的神情。当他们的照片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第一次展出时,受到了拯救艾滋病患者积极活动者的抗议,他们认为照片展现了令人绝望的荒芜景象,而且还在艺术圣殿展出,太不像话了。尽管拍摄者的初衷是想唤起人们的同情,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的展览又成了一种无情的“病态广告”——摄影家不得不为此承担巨大的精神负担。
在这以后,一些同样具有同情心的摄影家从中找到另一条出路,他们试图把人们对艾滋病的同情引向生存的希望。纽约女摄影家卡洛琳?琼斯从正面去表现艾滋病患者的积极面,她不仅拍摄艾滋病患者,还拍摄他们所爱的人和所爱的宠物。她的第一个影调明快的黑白影展在曼哈顿世界贸易中心展出。开幕式上,人们往日看到的寒冷、情感漠然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充满笑声和孩子们叫喊声的生气勃勃的空间。展厅中爵士乐五重奏乐团的音乐旋律在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香槟酒的芬芳。纪实摄影的光影使一切都带上了温暖的色彩,这仿佛是一次大海上的航行。每个人的关怀都一起载上了航船,足以将那么多生命的艰难和关怀在漫长的旅程中转换成自信和成功。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在试图突破“同情的疲惫”过程中,新闻和纪实摄影还必须有效地把握其面对现实的尺度,或者说,把握其切人社会的深度。纪实,如果仅仅是流于一种简单的记录,那么就只是对表象的肤浅描绘和叙述,无法获得更为深刻的揭示和升华。正如声名卓著的女摄影家玛丽?爱伦?玛克在早些年出版的摄影集《玛丽?爱伦?玛克:25年》中所做的总结:“这些人生活在边缘上,我通过他们的爱与恨接触他们。我希望照片能说出生活在并不幸运之中的人们的某些东西”。纪实摄影尽管不可能消灭人类的罪恶,但至少可以让人们在充实与完美的过程中走向未来。
新闻摄影死了?
所以,关于荷赛的种种的话题永远不会有一个完美的答案。关键还是前面所说的:文化就是一座牢笼。不是有人坚持说,中国摄影师这些年不都获奖了吗?但是恕我直言,获奖的大多是些无关痛痒的题材和级别,或者说,连“同情的疲惫”或者“同情的颤栗”都还摸不着边。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决定了需要太多歌舞升平的喜剧(是不是也让人疲惫或麻木?),悲剧的表现能力实在是差得很远。
反过来想到的是,这样的“同情的疲惫”是不是会最终葬送荷赛的生命力,或者说,说不准哪一天,荷赛就会“寿终正寝”?因为前些年摄影界就在流行一个很热门的命题,就是:新闻摄影死了!
新闻摄影死了?这绝非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因为在这以前,美国人米切尔早在1992年的《变换的眼睛:过去摄影时代的真实》中就已经说过:“从摄影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后的1989年的这一瞬间起,摄影死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彻底地和永久地脱离了原来的位置——如同150年前的绘画。”他以忧心忡忡的目光对现代摄影的发展投以关注,把摄影的死亡推前到了1989年(也就是摄影术诞生后的150年)。他的理由是: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图像泛滥的时代——在传统的图像规范模式还没有被人们真正消化以前,无数标榜着“新图像”概念的视觉模式铺天盖地而来。在现代化远远没有确立其真正的标志的土地上,又横七竖八地插上了许多“后现代”的标签,让人一梦醒来不得不怀疑是否有真的走错了房间的感觉。如今的摄影师所面临的困惑就是如何不断地加大图像的诱惑力,殚精竭虑地寻找突破的捷径,以加强图像对人们视觉的冲击性。但是摄影师(也许不仅仅是摄影师)所不愿想到的是,图像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尤其是平面的二维图像,在经过了20世纪初以来的数十年突破了“量”的极限,再试图突破“度”的极限时,总会面临着一个无法再向前走一步的边界,甚至面临因“疲惫”而彻底崩溃的可能。
《纽约时报》曾以前些年伽玛图片社的危机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更为伤感:《哀悼一个即将消亡的领域:新闻摄影》。重新将死亡这样的名词,放在当年风光无限的传播巨头新闻摄影之上。尤其是文章提到,伽玛的发言人认为“图片社原有的经营模式在今天已经不合适了,如果不改变,那么未来也不会起作用。而症结在于‘时效新闻摄影已经被终结,伽玛需要将重点放到杂志上,从对日常新闻事件的报道中转移到更为深层次的封面故事的报道上” 。
其实,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突发新闻报道已经没有明显的所谓专业的新闻摄影领域的划分,尤其是“新闻摄影”已经被“融化”了。伽玛、西格玛、西帕法国三大独立新闻报道图片社被转手出售的时间都发生在90年代末。那是业内人士第一次高喊“新闻摄影死亡!”的时刻,当时那只威胁新闻摄影死亡的“狼”是媒体报道的娱乐化,如今仍然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力。其实数字化并不可怕,比如有人就一直鼓励新闻摄影记者拥抱数字化,甚至提到:“所谓新闻摄影的死亡,是全力捕捉一张照片去发表在媒体上那种工作方式的死亡。从石器时代产生的视觉化讲故事的方法只会被新技术所促进,而不会消逝。”
困于传统,或另辟蹊径
核心的问题,或许不得不归于图像的泛滥,以及对图像在新闻等传播领域“度”的把握。这样也就回到了前面所提及的关于视觉冲击力和“同情的疲惫”这样的话题上。因为,荷赛就是一场新闻摄影的年度“狂欢”,新闻摄影“死了”,荷赛还会有生命力?但是也有乐观者——比如前些日子中国的华赛评委就充满信心地宣称新闻摄影没有死亡,因为他并不希望刚刚诞生不久的华赛就此夭折襁褓。而且在那一年华赛的评选结束时,荷赛的总经理也谈到新闻摄影已经死亡或是正在死亡这样的问题。他也认为关于新闻摄影是不是死亡的争论在西方已经进行了一些年了,但是他至今不认为新闻摄影已经死亡了。市民摄影的介入,手机可以拍照片,数码技术让照片的获得很容易——这些非专业的摄影者拍摄的照片是有价值的,不应该被轻视,而且还会看到现在世界上很多媒体也越来越多使用这种非摄影工作者拍摄的照片。因此他觉得这对于新闻摄影工作者来说可能是压力,但不认为是威胁。它只是要求新闻摄影工作者会更加高水平、更加认真地对待他们的工作。所以他再三否认了新闻摄影已经死亡之说。另外一方面,现在很多媒体杂志社越来越不愿意使用过去严肃的新闻摄影的作品,转而使用一些广告摄影作品或是比较八卦的作品作为他们的内容,这确实给新闻摄影工作带来了很大压力。或者说,这也是为了对付“同情的疲惫”不得已之举?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摄影行将入木,取而代之的,将会是多样化的新闻摄影的表现空间。在传统的报纸、杂志将新闻从深度开掘的同时,互联网、手机平台等等数字化媒介则延伸出新闻摄影(或者你可以不把它命名为新闻摄影,但是依旧具有新闻摄影的本质)一片新的空间,更为迅捷、更具亲和力、更有发散性和互动的魅力,也更凸显平民化的特征。这样看来,这些年荷赛有许多新闻照片越来越不像“新闻照片”,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与其“死在”传统的新闻照片的空间,还不如另辟蹊径,找到新的突围的方向。
我的态度也许还是比较乐观的:新闻摄影死了?现在不会!也许还应该再等上半个世纪。所以,荷赛的生命力也会持续这样的一段时间——只是在表现形式上一定会发生不可估量的变化。当然也有这样极端的说法:在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因此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摄影”。以此推理,新闻摄影在中国也就无所谓生和死的问题,我们大可放宽心态参与每一次荷赛的“狂欢”——但愿这只是一个伪命题而已……